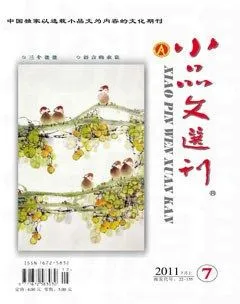小名
小名是私密的名字,只有至親至愛的人知道。
電視劇中的一對戀人,他在她耳邊輕聲喚她的小名,竊竊私語,如大珠小珠落心田。柔情無限,她不答應,只是微微低著頭。心中那朵薔薇花開了,粉色的,如同她臉上的云霞。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那樣的愛,有著蘭花幽幽的暗香。就如同在物質貧乏的童年,過年時得到的一塊奶糖,分外珍惜,舍不得吃掉。一天,拿出來含在嘴里,不敢說話,隱秘的,溫暖的,甜蜜著。清芬暗盈,唇齒留香,它的甘甜,只有懷揣愛情的人知曉。
在書店里,偶見書架上有一套《莎士比亞全集》,譯者竟是朱生豪。莎翁的作品,中文翻譯最飽滿最有神韻的便是朱生豪先生的譯本。
寫到翻譯家朱生豪先生,就不能不提他的妻子-————一代才女宋清如。她端莊秀麗,詩文空靈潔凈。當時,《現代》雜志主編施蟄存先生曾稱贊她的詩文:“一文一詩,真如瓊枝照眼”。
朱生豪先生他在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時說:“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圍內,保持原作之神韻”。這位才華橫溢的翻譯家,一提筆翻譯就是十年,十年里,抗戰爆發,時局動蕩,烽火連天。他貧病交加,為翻譯工作嘔心瀝血,直至病魔纏身,僅依靠一點微薄的稿費維持拮據的生活。此時,妻子宋清如的愛,給了他精神的慰藉和溫暖。他對妻子說,我很貧窮,但我無所不有。是啊,他有愛情在左,理想在右,即使生活困頓不堪,還是有夢可依。宋清如默默守在他的身旁,支撐他病弱的身體,照料他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的翻譯工作,做他忠實的助手和伴侶。
一九四四年蕭瑟的深秋,朱生豪已耗盡生命最后的一息微弱的火苗,握著妻子溫柔的手,他說:小清清,我要去了。他拋下一周歲的幼子和綺年玉貌的妻子,與她永訣。那一年,朱生豪僅三十二歲。
小清清,是妻子的小名,是他在家里滿懷愛意呼喚著的名字。他走了,再沒有人在她耳邊柔情蜜意的這般呼喚。從此后,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可是,她知道,只要她還活著,思念就在,他的夢想就在,愛情永恒。傅雷先生曾說,愛情與天地茫茫而言,實在是小。而我說,光陰走了,即使老去鬢白,唯有愛還在。
有時候,愛一個人和堅守一種信仰,幾乎沒有區別。
而后,宋清如忍住所有的孤寂和憂傷,于亂世中堅韌地活了下來,她一個人撫養大了的孩子。她教書育人,桃李滿芬芳。新中國成立后,她終于完成丈夫的遺愿,出版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
見過宋清如女士暮年的照片,神情從容,端然安詳。她老了,鬢如霜,發如雪。可是,她依然是他的小清清,今生是,來生也是。
歲末,收到朋友自遠方寄來的賀年卡。清秀的字跡,娟,有過多少朋友仿佛還在身邊。我們相識二十年了,人生有多少個二十年呢--------她一直這樣喚我,一如姊妹手足。
猶記年少時的那一晚,月色如水,晚風清涼,穿著白球鞋、藍校服的我們坐在校園的操場上看月亮,橘黃色的月亮,像一丸蛋黃掛在天上。我們說著女孩子的悄悄話,不記得說什么,只記得她說,娟,我只告訴你,這是我們倆人的秘密。人生山長水遠,只那一瞬間鏤刻在心里,一輩子念念不忘。
多年不見,我去北方的城市看望她。敲開門,見她手上牽著四歲的小女兒,細眉細眼的笑,喜悅如蓮花盛開。她喚孩子,快叫姨姨,姨就是媽媽最好朋友。孩子仰著頭,給我一張天使的笑臉。我蹲下來看孩子,星星般的眼眸,可愛的童花頭,粉嘟嘟的小臉,活脫脫是她小時候的模樣。我擁著孩子,仿佛擁抱著幼年時候的她。望著她笑,笑出了眼淚。真是: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森兒五歲時,家里的電話響了,他接起電話,喚我:娟,你媽媽叫你接電話!我生氣得瞪著他,他卻得意的“咯咯”大笑起來。
他十歲了,暑假時候帶著他去桂林旅游,正在機場候機,一會就不見他的人影,我一著急,就喚他的小名,他背著大包飛奔而來,瞪著黑水晶一樣的眼睛警告我:媽媽,在外面不許叫我的小名,叫一聲就罰款一元!旅游結束回家之后,他伸手要錢,媽,繳罰款,共計二十三元。
去時陌上花似錦,今日樓頭柳又青。光陰如流水,只有至親至愛的人還記得你的小名,那一聲輕輕的呼喚,那么令人心喜,心動,心醉,心暖。
在一家賣玉器的門前,立著一副對聯:玉不能言最可人,情不必訴最暖心。真喜歡。中國是有“情”境的民族,這情,乃人間大情、大愛。那一聲輕喚,是寂寞紅塵中的一枚碧玉,是人世給你的一份溫暖。那么,你還向喧囂荒寒的塵世索求什么?
選自《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