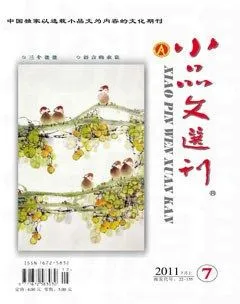空地
那條巷子突然曲折幽深了起來,我走著走著,人恍惚了,明明是記得的,卻沒有了信心。近來我常陷入一種困惑:過去經過的一些地方、事件,總不敢確定它的真實性。細節是很清晰的,我可以把它很完整地敘述出來,但我似乎并不相信自己的敘述。比如多年前我去過一個山洞,我跟朋友們說,我可以帶你們去。但是有人問,是真的有這樣一個山洞嗎?我卻驚愕,說,我當年在洞里撿了些石頭回家。我瞬間就有了一種沖動,要立即回父母的家去找到那些石頭,要真的觸摸到它們,甚至用它們尖銳的棱在手上劃出口子來,感覺到了痛才能讓我欣喜,心里踏實。我總擔心一切經過的人和事,都會變成桃花源,或者說,一場夢。真實與虛幻,相互在我的心上投影,交疊著,又彼此覆蓋,弄得我疲憊不堪。
是夜的幽暗加深了我的幻覺嗎?這條巷子,幾年前,是我每天經過的地方。清晨或傍晚,我出發或歸來,手里拎著菜、奶粉,零碎的生活,也有書、唱片,有時僅僅是一懷的疲倦。巷子的一邊,住著一些零散的人家,另一邊,是一個大院。我住在大院里。如今大院已不在了,建起了很時尚的小區。我很慶幸那道圍墻還在,有它,這巷子就還在。我的腳步是不自覺的,在這樣的一個夜晚,它好像執意要找到什么。走到巷子深處,一種聲音讓我停了下來。那是收音機的聲音。我轉身去看,有些破舊的小院里,一個老人靠在竹椅上,聽著廣播。兩層的舊房子,樓下的門開著,但是沒有開燈。樓上有間窗戶透出白色的光來。老人并沒有注意到我,薄涼的月光下,他像一個靜物。是的,就是這個小院,我認出了它。我當時居住的房子,在圍墻內,正是這個位置,和它相對。臥室在這兒,廚房在前面。這里是一片草地,竹竿上曬著衣服和被子。我發現我的手在空中揮舞了起來,它在比劃著。似乎只要輕輕一拍打,那被子里陽光的芳香,滿院子的花香,都會像從前一樣溢出來。
一直覺得,有個院子是幸福的。院子意味著陽光、雨水和花草,對于每個人來說,這些都是必要的滋潤。路上經過,看見薔薇花從院子里開出來,波浪一樣在院墻上鋪展開來,覺得非常美。看了良久,才明白原來薔薇的美并不在它的艷麗,而是因為融入了這院子的安靜。小小院落,細密花開,風吹過,蜂時有時無。心里便有了一份安定、閑適,感覺和這個熱鬧的世界有了一段距離。走進去,將院門一閉,滿世界的煙塵都關在了門外。人便也和一株花草一樣簡單,只關心生長,只和日月星辰交談。
院子可以更簡陋一些。可以沒有假山池水,可以沒有紫藤花架,甚至沒有花香四溢。只要看得見綠色,只要有生物在長。甚至也沒有圍墻,只是一塊空地。小時候,我家門前有一塊這樣的空地。似乎并沒有誰刻意去種過,卻也開著不少花,梔子、夜來香、鳳仙等等,很是繁茂。夏夜在那里乘涼,陣陣花香不息。后來我出去讀書,有一年帶回來一包花籽,也不知怎么種,就那樣隨手撒下,就不再過問。結果也長出一大片花來,弄得門前倒像個花園了,只是不夠齊整。當時也覺不出珍貴來。直到后來,有了自己的房子,沒有院子。于是想在室內養些花,動了不少心思,卻總是養不活。甚至連給花澆水,也成了一件難以把握的事。必須很認真地去觀察,揣摩每種花所需要的陽光、水分。那些花似乎都成了脾氣刁鉆、喜怒無常的孩子,必須非常小心去侍弄。稍不如意,它們就自殘,萎謝了。對于花草而言,或許只有在無遮擋的陽光里,在風和雨的撫摸下,它們才可能溫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家的老房子幾年前也已經拆掉了,門前的那塊空地也不復存在了,鄰居在那里建了房。每次回去,心里總不舒暢,原來以為是懷舊,是失落。后來知道,并不只是這樣,那是一種非常逼仄的感覺。逼仄到讓人窒息。休息日,我一次次地流連山水,登高望遠,或者是回家來,與田野和山林相依,潛意識里或許我一直都在逃避那種逼仄,人群中過于密不透風的感覺。我需要那樣一塊空地,帶給我一種遠。讓我與世界存有一段距離,好好地喘一口氣,然后調勻呼吸,修復好身體和心靈被擦出的種種痕跡。這很重要。
某一年,我在戀愛。人完全地淹沒了,被內心漲滿的熱情折磨著。醒著夢著,觸目之物,都是他的眉眼。花開月落,都在我的心上,激起巨大的欣喜與失落。我仿佛剛從一場夢中醒來,前世今生,所有的辛苦與感動都記起來。我開始不斷地訴說,他是惟一的聽眾。我變得毫無節制,在他面前哭哭笑笑,任性到極致。明知是沒有道理的,可是拿自己的弱毫無辦法。我要求著他,責怨著他,然后一遍遍地流淚。終于有一天,在一次說話中,我感到了徹底的孤獨。我累了,我埋著頭,抱著自己,沉默了下來。突然想到了空地。我想,我是因為失去了它,才失去了寧靜。再愛一個人,也不能丟了自己的園子。他愛的,或許不只是你,還有你面前的那一段距離。
每個人都需要這樣的一塊空地。它是我們內心隱秘的寶藏,最后一個療傷的處所。
選自《九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