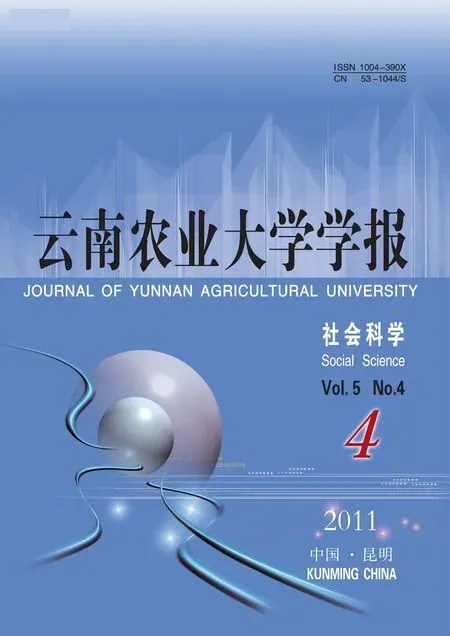葉芝詩歌中的生態性
周海峰
(文山學院 外語系,云南 文山663300)
作為英語文學的分支,愛爾蘭文學在英語文學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而在豐富多彩的愛爾蘭文學世界中,葉芝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他對其后的愛爾蘭文學創作產生了的極大的影響。作為愛爾蘭著名的詩人、劇作家和散文家,他一生著述頗豐。作為愛爾蘭文藝復興的中堅,他用文學積極地投入到愛爾蘭解放運動的大潮中,為愛爾蘭文學的獨立和愛爾蘭的民族獨立作出了貢獻。T.S艾略特稱贊葉芝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
如今,生態思潮的興起對文學研究和批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今天,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以及對人與自然和諧的訴求正在成為人們的共同和必須的追求。文學作品,尤其是數量巨大的文學經典,以其巨大的影響力,持續地對人類的生態意識產生著調適甚至改變。對經典作品的重新解讀,評估其對人類生態意識的積極或消極的作用,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則是生態批評的重要手段之一。葉芝的詩歌,尤其是前期的浪漫主義詩歌,和其他的浪漫主義詩歌一樣,以其對自然的親近和關注,為“詩意地安居”和存在論美學和參與美學的闡釋的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一、 葉芝詩歌綜述
葉芝是英格蘭裔的愛爾蘭人,開始創作于英國浪漫主義時期,并經歷了世界文學由浪漫主義向現代主義的轉變。因此,葉芝詩歌中的象征主義可以說是在愛爾蘭傳統文化、神秘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基礎之上形成的。這也使其象征主義具備了鮮明的特征,也成就了他非凡的文學成就。
葉芝早期詩歌題材取自愛爾蘭凱爾特神話、民間傳說及謠曲。同時,英國浪漫主義的影響也使葉芝非常注重詩歌的格律和音樂性。1899年,阿瑟·西蒙斯的《文學中的象征主義運動》一書把起源于法國的象征主義介紹給了英國。葉芝也在神秘主義知與行的過程中完成了自己詩歌創作向象征主義的轉向。而玫瑰、天鵝則是葉芝詩歌象征體系的核心。
二、 生態批評的思想與審美
生態批評的思想基礎是生態整體主義(ecological holism)。它源自生態學的整體觀、聯系觀、和諧觀,并以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此在與世界作為其哲學和審美基礎。美國生態批評家格倫·A·洛夫(Glen A. Love)在《實用生態批評:文學、生物學及環境》一書中明確指出了文學研究與生態學及進化生物學的緊密關系。而達爾文、奧爾德斯·赫胥黎在他們的著作中所體現出的生命的聯系性,以及進化發展的相互交錯和密不可分性,他提醒人類應該更多地把對人本身的關注轉移到對自然的關注之上。“生態思維——就它要求從更廣泛的視角來考量如何回答諸如有關自然界及人在其中的地位等問題來看……需要采用一種更寬廣的生態學視野以認識文學行為發生的社會背景與生物學背景。”[1]作者還進一步指出了文學與自然及生態整體之間的不可分割性。
王諾教授認為,生態批評的美學原則主要有三:自然性、整體性和交融性。自然性原則即是對自然的審美,它突出自然審美對象,與審美者建立交互主體性的關系,并強調自然本身的美。整體性原則來源于生態整體主義,主要考慮審美對象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和影響。交融性原則源于生態主義聯系觀,主張融入自然的審美。
生態散文家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則在其著作《沙鄉年鑒》(又譯沙郡年記)中提出的“ISB原則”(integrity,stability,beauty),即完整(又譯為和諧)、穩定、美麗,做為生態整體主義的價值判斷標準(即土地倫理)。并認為人們應當“像山一樣思考”。
此外,曾繁仁教授也在其多篇論文中指出由“自然的祛魅”向“自然的復魅”的重要性。即承認自然對象特有的神圣性、部分的神秘性和潛在的審美價值——從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上來探索自然美的價值。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自然或者自然取向的審美在文學批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自然在文學作品中一度被置于附屬性的地位:或者認為自然不過是人類行為的襯托;或者干脆把自然置之不理,如傅雷翻譯《飄》時,就有大段自然描寫的刪節。在生態批評中,則要從整體出發——即人與自然是密不可分的觀念出發——恢復自然在文學中的合理地位,并以此為依據,把人與自然的關系重新理清,使人類不再高高在上——即恢復人類與整個自然生態的完整統一性。最終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為人類的未來創造真正的福祉。
三、 葉芝詩歌中的生態性
葉芝的詩歌,尤其是其前期的浪漫主義詩歌,包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首先以《當你年老時》(When You Are Old,1896)為例:
當你年老,鬢斑,睡意昏沉,
在爐旁打盹時,取下這本書,
慢慢誦讀,夢憶從前你雙眸
神色柔和,眼波中倒影深深;
多少人愛你風韻嫵媚的時光,
愛你的美麗出自假意或真情,
但唯有一人愛你靈魂的至誠,
愛你漸衰的臉上愁苦的風霜;
彎下身子,在熾紅的壁爐邊,
憂傷地低訴,愛神如何逃走,
在頭頂上的群山巔漫步閑游,
把他的面孔隱沒在繁星中間。
(傅浩譯)
此詩葉芝使用了非常簡單的詞匯和句式所寫。詩歌本身是一首膾炙人口的愛情詩,在愛情的主題統領下,詩歌所選取的場所(Place,又譯地方)[注]該術語所使用的譯法不一。筆者對此詞采用“場所”之譯,而所引文獻中,有的采用“地方”之譯。故文中對該術語的敘述有混亂之嫌。特此說明。卻值得關注。筆者認為,正是在愛情主題下這對場所的選擇和表現,才使得本詩的生態性凸顯,并喚醒讀者內心向自然純真回歸的共鳴。
場所,或者地方,是“‘被賦予意義的空間’。地方是‘可感價值的中心’…‘一個地方能夠被見到、被聞到、被想象、被愛、被恨、被懼怕、被敬畏’”[2]。可以說,場所與人的具體的生存環境和由此引起的感受息息相關。我們當前存在的空間,各種物品的位置和狀況,彼此之間的“因緣”都是場所的整體。
在本詩中,作者描述了這樣的一個存在——“老去的愛人”(后文簡稱為愛人)、壁爐和書籍。愛人老去了——頭發灰白、睡眼朦朧——坐在爐邊取暖時,取下書來,而書籍又進一步引起了愛人對下一個“因緣”、感受的描述:對愛的沉思和略帶悲傷的感慨。然而這個場所并未因此而結束。在取暖、誦讀、夢憶、“憂傷地低訴”這一系列相互關系,即“因緣”之后,詩人結尾處卻把空間擴大到“群山巔”和“繁星中間”,也使得全詩的場所,或“因緣”得以升華——自然,才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根本所在,我們就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即所謂“此在的在世”(海德格爾)。老去、爐邊打盹、取書、沉思,在這部分中的場所通過愛神的“逃走”最終完成與群山、繁星的融合——隔離人與自然的墻消失了。這種房屋與自然的簡略描述,讀來則使得人類的居所與自然并無隔閡,“……人與場所是相互滲透和連續的”[3]。從老去到逃走,似乎都指向這樣一種隱喻:最終的歸宿,悲傷也好,閑游也罷,都是向大地、向自然、向我們唯一的存在之所的回歸——既是愛情向純樸的回歸,也是人類情感向生養人類之所的回歸。
如果說《當你年老時》一詩中的自然和人性的融和都是若隱若現地如同火爐中的火光,那么,與該詩在時間上較早一些的《茵尼斯弗利湖心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1892)則明確地描述了作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我要起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湖心島,
用泥土和枝條,建造起一座小屋;
我要有九排云豆架,一個蜜蜂巢,
在林間聽群峰高唱,獨居于幽處。
于是我會有安寧,安寧慢慢來到,
從晨曦的面紗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一片閃光,中午有紫霞燃燒,
暮色里,到處飛舞著紅雀的翅膀。
我要起身走了,因為我總是聽到,
聽到湖水日夜輕輕拍打著湖濱;
我站在公路,或在灰色的人行道,
我心靈深處總聽見那波濤聲聲。
(裘小龍譯)
葉芝在閱讀了《瓦爾登湖》后,受梭羅生態觀念的影響而寫下此詩。“那時我住在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城,城里瓦爾登湖邊有片樹林,我在那兒親手搭了個小屋,方圓一英里內沒有任何鄰居。我用自己的雙手勞作,自食其力。”[4]葉芝詩中的場景與此何其相似。想象中的寧靜來自于自己親手建造的簡單的一切:小屋、蕓豆架、蜜蜂巢;來自于大自然賜予人類的美麗禮物:林間、晨曦、紫霞、湖水,蟋蟀、紅雀,一切均融為一體。這樣一個令人所向往的地方,讓尚身處工業城市的詩人的心也早已飛向了彼處。“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意境呼之欲出。
長久以來,文學作品中的自然并不缺乏。然而,文學研究或者說文學批評中卻一直忽略自然的存在。“縱覽中國文學史的百年書寫,我發現,自然的位置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乃至放棄了。”[5]不僅中國,全世界在對待文學的問題上,在各種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原則的思潮和運動中,自然、田園卻日益飽受批評。但是,“田園牧歌(筆者此處引用田園牧歌一詞取其描寫自然之意,并非專指某種詩歌、文學類型)一直就是一種對生活的嚴肅批評”[1],田園或者說田園傾向的描寫并非一個培植感傷情緒的場所。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認為,盡管意識形態的內容時有變化,但田園牧歌的形式卻始終恒定如一。“田園風情持續不斷的吸引力與威爾遜的生物之愛極為相關,就是敬畏生命,就是對我們自身作為源于自然的生物的本能感受。”[1]
本詩中,自然與文明的對立是非常明顯的。自然豐富多彩,眾多的物種之間和諧相處,到處是歌聲和光明。而城市的、工業的修飾詞只有一個——灰色,灰燼的顏色:從一座座巨大的工廠那矗立的巨型的煙囪里看似緩緩吐出的煙霾,在原本清明的天空下聚集、擴散,偶爾飄來的風把它帶到世界各地,然后慢慢地沉落,覆蓋了這個地球,尤其是工業的城市,只剩下灰色。此外,描寫自然時,作者沿著內心的追尋,隨手即可寫出的美麗如此之多。而自己身處的文明社會,卻只能找到寥寥的公路和人行道,詩人以第一人稱獨立其上,似乎也暗示著工業文明在極大地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其秉承的“技術理性”也瞞下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危險——人類只能孤獨存在于大地之上。
詩中有兩類場所存在:一是湖邊小屋;二則是公路和人行道。同樣是由人所建造,然而區別是巨大的。前者是開放的、包容的。小屋不過是“我”生活的必需,在這方寸之地的周圍,有許多的伙伴,“我”并不寂寞,在一個充滿聲音的場所里,“于是我會有安寧,安寧慢慢來到”。這無疑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場所——“我”只“占有”必需的生存之地,沒有奢侈的享受和消費,小屋在自然中并不是一種突兀的存在,也不是這一“桃源”的中心,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我”與萬物之間不相干擾,卻也享受著彼此給予的安寧,并由此構成一個整體;這是與梭羅一脈相承的簡單生活觀。與此相對,后者則是孤獨地、隔離的。需要指出的是,后者似二實一,公路也好,人行道也好,在承載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也是人類不斷地侵犯、擠壓其他物種的生存空間,并擴大自己脫離了必需甚至是適度享受這個范疇的享受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甚至是割裂的,原本渾然一體的大地,被一條條公路分割開來,公路霸道地躺在大地之上,切斷了大地萬物原本的聯系。這個場所沒有多余的聲音、沒有多余的色彩,時尚和消費贊美它、引領它,如同公路一般不斷地延伸,沒有盡頭,似乎在暗喻著對大地的侵占和分割永不停止。但是,“我”在這里是寂寞的,“我站在公路,或在灰色的人行道,/我心靈深處總聽見那波濤聲聲。”“詩意的安居”還是“技術的安居”,也成為了一個“to be or not to be”式的兩難困境。
與葉芝前期的浪漫主義與自然的天然聯系不同,葉芝之后詩作開始向象征主義轉變,象征主義在工業社會與自然的隔離逐步加大的背景下,其創作基礎和理論顯示出對浪漫主義自然傳統的背離。柯爾莊園在葉芝的象征主義作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柯爾莊園的女主人奧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也一直支持葉芝的創作。盡管象征主義在逐漸的背離自然和田園,但是,葉芝的詩歌在形式上并沒有實驗主義的傾向。相反,葉芝的詩作在形式上一直堅持傳統,對詩歌韻律的追求終身都沒有停止。這種形式上對傳統的堅持,筆者認為,恰恰是作者對浪漫主義的自然原則的潛意識守護,或者說田園牧歌所具有的持久魅力給予人性(具體到本文,則是對葉芝本人)的影響。安德魯·艾廷(Andrew Ettin)指出,“田園這個術語涵蓋了多種體驗和觀念,而這些體驗和觀念永遠是我們思考和寫作的組成部分。”[1]:
柯爾莊園的天鵝(The Wild Swans at Coole,1912)
樹木披上了美麗的秋裝,
林中的小徑一片干燥,
在十月的暮色中,流水
把靜謐的天空映照,
一塊塊石頭中漾著水波,
游著五十九只天鵝。
自從我第一次數了它們,
十九度秋天已經消逝,
我還來不及細數一遍,就看到
它們一下子全部飛起.
大聲拍打著它們的翅膀,
形成大而破碎的圓圈翱翔。
我凝視這些光彩奪目的天鵝,
此刻心中涌起一陣悲痛。
一切都變了,自從第一次在河邊,
也正是暮色朦朧,
我聽到天鵝在我頭上鼓翼,
于是腳步就更為輕捷。
還沒有疲倦,一對對情侶,
在冷冷的友好的河水中
前行或展翅飛入半空,
它們的心依然年輕,
不管它們上哪兒漂泊,它們
總是有著激情,還要贏得愛情。
現在它們在靜謐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測,美麗動人,
可有一天我醒來,它們已飛去。
哦它們會筑居于哪片蘆葦叢、
哪一個池邊、哪一塊湖濱,
使人們悅目賞心?
(裘小龍譯)
自然或者田園與人類社會在本詩中逐漸地產生了疏離。詩人在柯爾莊園這個有著人為色彩的場所第一次見到天鵝時情景是“我聽到天鵝在我頭上鼓翼,于是腳步就更為輕捷。”,我很輕松地就數出了天鵝的數目,田園與人類之間的互相呼應是渾然天成的。此后,田園的風光依舊:林中小徑、秋色下的小河。然而,“我”還來不及數出有多少天鵝,它們就飛走了,“十九度秋天已經消逝”“我凝視這些光彩奪目的天鵝,此刻心中涌起一陣悲痛。”。到了詩歌的結尾,“可有一天我醒來,它們已飛去。哦它們會筑居于哪片蘆葦叢、哪一個池邊、哪一塊湖濱”,天鵝從人類的注視中離開,雖然其他的風光依舊。可是,下一步離開的還會有什么?是樹林、還是河水?在貴族的莊園里,自然與人類社會曾有的和諧,隨著莊園一步步在工業社會的壓迫下被拍賣,這些和諧也在一步步地走向疏離,甚至是隔絕。
天鵝作為詩人詩中美的象征,在本詩中最后一部分則以夢境中的“神秘莫測,美麗動人”變成了醒來后的現實——“哦它們會筑居于哪片蘆葦叢,/哪一個池邊、哪一塊湖濱”。詩人對自然之美的留戀由此可見一斑。
如果說,此詩中的天鵝是詩人自然審美的重要元素和集中體現。它在這里體現了自然與人類關系的親密與疏離。那么在《麗達與天鵝》(Leda and the Swan)一詩中,則表現了自然對人類的粗暴:
突然襲擊:在踉蹌的少女身上,
一雙巨翅還在亂撲,一雙黑蹼
撫弄她的大腿,鵝喙銜著她的頸項,
他的胸脯緊壓她無計脫身的胸脯。
手指啊,被驚呆了,哪還有能力
從松開的腿間推開那白羽的榮耀?
身體呀,翻倒在雪白的燈芯草里,
感到的唯有其中那奇異的心跳!
腰股內一陣顫栗.竟從中生出
斷垣殘壁、城樓上的濃煙烈焰
和阿伽門農之死。
當她被占有之時
當地如此被天空的野蠻熱血制服
直到那冷漠的喙把她放開之前,
她是否獲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識?
(飛白譯)
應該說,粗暴也好,和諧也好,疏離也好,都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持久組成。顯而易見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無論是純粹的服從還是控制都不能真正解決或者緩解已有的生態危機。最終,兩者之間只能走向和諧之路。天鵝在葉芝本人的象征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葉芝認為,正是宙斯化身的天鵝與人間女子麗達的結合創造了希臘文明。在古埃及的神話和建筑中,獅身人面像無疑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隱喻,它本身是人與動物的合體。或許葉芝認為,人類與動物的結合,才導致了人類文明的產生。人與自然不應該是對立的,征服與控制并不能創造文明的人類文明,相互的和諧關系才能創造符合人性或者說自然性的人類文明。
在這兩首與天鵝有關的詩歌里,天鵝的神秘,或者是作為神的化身,并由此與人所產生的種種“因緣”:“誕生和死亡,災禍和福祉,勝利和恥辱,忍耐和墮落——從人類存有那里獲得了人類命運的形態。這些敞開的關聯所作用的范圍,正是這個歷史性民族的世界。出自這個世界并在這個世界中,這個民族才回歸它自身,從而實現它的使命。”[3]在生態存在論美學中,美是關系,是過程,是在自然與人關系的世界結構中逐步得以展開的。“冷漠”和“制服”不過是大自然維持其平衡的手段。 “她是否獲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識?”更像是一種追問:災禍之后,更多的是新生和希望,是酒神的狂歡和重生。
四、 結語
葉芝無愧于一個偉大詩人的稱號,即使在生態批評的背景下,其作品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生命力不僅來自于葉芝本人對詩藝孜孜不倦的追求,也來自于其詩作中持續的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探討。生態思想的注入,必將使葉芝詩作的魅力更為恒久。
[參考文獻]
[1][美]格倫·A·洛夫. 實用生態批評:文學、生物學及環境[M].胡志紅,王敬民,徐常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7,65,76,79,129.
[2][美]勞倫斯·布伊爾. 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危機與文學想象[M].劉蓓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70-80,70-71.
[3]曾繁仁.生態美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325-341,337,287.
[4]亨利·大衛·梭羅.林志豪譯.瓦爾登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1,72.
[5]魯抒元.百年疏漏——中國文學史書寫的生態視閾[J].文藝評論,2007(1):181-186.
[6]王諾.歐美生態批評:生態文學研究概論[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23-67.
[7]王諾.生態與心態:當代歐美文學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8]李美華.英國生態文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200-206.
[9]楊晨音.從摹仿到構建——葉芝詩歌中的象征轉向[J].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9(5):61-64.
[10]甘文婷.從生態批評的角度解讀葉芝的悲哀的牧羊人[J].安徽文學,2009(10):207-208.
[11]傅浩.葉芝的象征主義[J].國外文學,1999(3):41-49.
[12]黃海容.葉芝的象征主義及其發展[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107-115.
[13]曾繁仁.當代生態美學觀的基本范疇[J].文藝研究,2007(4):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