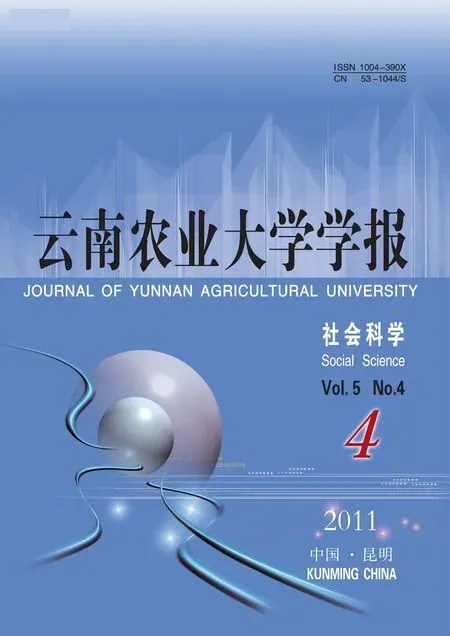論司法過程中當事人的敘事能力
毛高杰
(吉林大學 理論法學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 130012)
從法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司法過程是社會構成的一部分,其運行和其他社會要素密不可分,不能獨立于社會條件,而是諸多社會因素推動下的產物。處于司法過程中的當事人也同樣受其特定的社會條件的制約而不能脫離這些背景。在這些條件的制約下,各司法當事人都運用利己的訴訟戰略,通過對糾紛“故事”的敘事[1][注]在這里敘事采用后現代敘事理論框架下的意義。而重構出對自己有利的一個側面。[注]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如果當事人將糾紛提交司法解決,即意味著當事人相互關系已經嚴重敵對,至少比自力解決的敵對程度要高得多。因此,合作因素在訴訟中幾乎可以不予考慮。而這種訴訟戰略是否能為自己在司法過程中獲得有利結果,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個當事人對法官的說服程度。換句話說,司法就是法官判斷當事人說服強度的過程。同時對于法官來說,就是法官通過當事人對于紛爭本身的論證強弱真偽的判斷過程,“當他們在紛爭事實發生后接觸到案子時,他們所能作的事情只能是:盡力將故事碎片拼湊在一起,同時根據法庭上提出的可資利用的證據,試圖得出一個合理的事實結論”。[2]在這種情況下,處于利益相斥背景下的當事人對糾紛本身的敘事就非常重要,只有自己的敘事強度超過對方,才有可能贏得法官的信任,從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斷。各方的敘事強度直接影響法官對紛爭的司法重構,可以說,各方的敘事強度的強弱直接關聯著司法決斷。
一、資本差異下的敘事能力
從純粹的法律視角來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給予當事人在司法過程中的公正程序,當事人的辯論便可以視為一種完全可以導向正義的機制。只要給予當事人充分的辯論的機會,就能保證辯論結果的正當性。“一個真正的法官應該無視于立于其前的當事人,不將之當作現實之個體而單純的只知道原告及被告。易言之,法官只知道戴著原告、被告面具的抽象當事人,卻不認識面具下的個人。”[3]這種觀點實際上假定一個純粹理想角色,這種角色沒有任何具體的社會角色,沒有自己的獨特心理偏好、沒有任何具體的社會關系、沒有特定的社會身份。他或者她僅僅是訴訟過程中的一個抽象符號,是一個可以滿足程序正義要求的一個符號,只要滿足程序正義的假設要求,結果就具有正當性。
這是一個僅僅在抽象的理想案件中才存在的角色,這樣的角色具有先定的無差異的社會身份和經濟地位以及文化資本,并且在一個社會中的分布是均衡的無差異的,不受任何特定的文化、地理環境的影響,不具有任何獨特的可以區別于他人的社會角色,僅僅是一個純粹的法律角色——即訴訟當事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加奇怪的限制就是,這樣的人在進入訴訟后和訴訟前是截然絕緣的,有關訴訟前的任何個人經驗以及社會關系都是在這一個被稱為司法程序的場域中被截斷了。無疑這是一個反事實的假定,一個人在進入訴訟過程中和過程外的經驗和資本都是連續的,并且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一個人并不會因為訴訟的原因而被切割為兩個截然無關的存在。相反,作為社會個體的當事人,其社會因素不會在司法程序面前戛然而止,而是通過社會理論和形式的司法程序進行交流,使得法律和社會兩個系統都能夠不斷的變遷。從社會現實來看,每一個人都是具體的存在,處于特定的社會位置上,在不同的場域中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源于自然的或是社會的能力差別,并且帶著這種差別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并通過各種社會活動加強不同角色間的互動影響。
從積極的一面來說,可以認為通過一種相對隔離的司法程序的設置,可以有效地避免主體具有的社會關系進入糾紛的解決,進而影響司法的公正性,同時也在成本收益的衡量下最大化司法資源;[4]但從另一方面看,一個人是處在社會之中的,他所具有的各種社會關系,其自身所凝聚的社會資本,毫無疑問都會滲透到司法過程中去,在這種情況下,司法程序的設置將社會影響正當化或者說從司法的視野中剝離掉了,但并非從社會事實上消除掉,理想的程序隔離并不能代替事實上的資本彌散,更不能消除掉主體具有資本對司法的影響。
在布爾迪厄看來,一個社會人都具備三個方面的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一個人擁有的資本數量和類型決定了他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也就決定了他的權力,[5]并進而決定他的社會行為效果。俗語所謂的“人微言輕”實際上就是對個人權力和其言行效果的關系簡要但深刻的描述。一個人所說的話的真假與否,其話語的說服力強弱與否,并不僅僅取決于話語自身的周延,即便話語自身的周延與否也在更加根本的層面上取決于個人所受教育、所具有的社會位置等因素。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剛從農村進城打工的人和一個自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能夠在法庭上同樣流利地進行辯論。布萊克也通過統計數據說明了,“下行的法律嚴于上行的法律。”[6]一個人無論在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任一方面具有優勢,都會使得自己的話語具有優于其他人的說服力。在證據規則中,被普遍采納的利害相關人證詞效力較弱的規則,可以視為對資本影響話語說服力的一種證明;經過公證的書面證據優于其他書面證據也是同樣性質。[7]
因此在司法過程中,當事人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敘事能力,影響到當事人的論辯說服力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案件的判決,最終影響自己利益的保護。
二、敘事能力和司法運作:以“楊乃武與小白菜”為例
考慮到現行司法判決書中并沒有要求完整準確的判決推理,也很難獲得一個案件的完整運作過程,所以很難通過某一現行案件來準確的論證當事人資本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判決的做出,因此本文只有采取一種變通的方法,通過考查清朝同光年間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以從中析出當事人敘事能力的影響。
在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案件的最初形態和最終的形態實有截然的區別,導致這種區別的因素可以從法社會學的視角得到解釋,詳細的論述見徐忠明《楊乃武冤案平反的背后:經濟文化、社會資本的考查》一文的論述。[8]在該文中,徐忠明以布爾迪厄的“資本理論”來分析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背后的社會推動力量。在徐忠明看來,正是楊乃武和小白菜的不同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才導致了整個案件從最初到最終的反轉,小白菜葛畢氏從最初的案件主角到楊乃武作為主角,最終使得案件得到昭雪,其推動力量主要是因為二者的資本力量的不同。
在案件之初,小白菜葛畢氏才是案件的主角,但直到楊乃武作為主角才有了實質的轉機。對于小白菜來說,要想證明自己的冤屈,“京控”起著關鍵的作用,而楊乃武相對于小白菜來說,無論是在經濟資本,文化資本還是社會資本上都有明顯的優勢,也正是楊乃武的這些優勢使自己的京控行為得以實現并使的案件轉向有利的一方,相應的小白菜才能夠得到昭雪。在這個案件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資本能力影響到敘事能力,進而影響到對事實的程序重構,最終影響到糾紛本身的認定。在整個案件過程中,改變的是在不同的敘事強度下所重構的紛爭事實,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看到主體敘事能力和司法判決的直接關系。
在《竇娥冤》中,也可看到一個資本缺乏者面對冤屈的策略,如果剔除掉非人力的超驗因素,即沒有三樁誓言的應驗,沒有竇娥對父親竇天章的托夢這些因素,竇娥的冤屈得到昭雪的機會可以說幾乎為零。所以對于文學作品中的冤屈者來說,就必須借助于非正常的機制,這也導致傳統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兩種洗雪冤屈的類型,一種是借助于具有某種神圣品性的人,相應的形成了清官文學,其中形象以包公為典型;第二種是借助于神啟的因素,相應的形成宣揚善惡觀念和因果報應的勸世文學,以《竇娥冤》為典型。無論哪一種解決方式,都是在自己對于糾紛“故事”的陳述不被認可的情況下,通過一種非正常的力量介入而彌補敘事能力的弱勢,才可能讓自己的敘事具有超越對方敘事的力量。[注]在“三言二拍”中,受冤屈者必須和某一能夠動用官方力量的人具有親屬關系,或者是借助超驗的力量——鬼神來補充弱勢的敘事力量,從而說服司法官員,冤屈才能夠得到最終的平反。
在徐忠明一文中,主要是以資本理論來進行剖析,但如果將這種剖析加以延伸,我們就會發現,在資本能力和最后判決結果之間,還有法官何以接受認同某一方敘事的這一環節。在這一環節中,法官并不能親歷糾紛的過程,而只能通過當事人的敘述來重構,但重構的依據則是來自于當事人說服力度的不同。對于每一個當事人來說,其言語的效果都不是孤立的,其話語權只不過是自己的各種資本的一個集中的顯現,俗語“財大氣粗”顯然是話糙理不糙,如果將“財”作擴展解釋,不僅僅指金錢,而且指身份、知識等內容時,這句話和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顯然具有結構上的內在一致。在這種顯現中,一個人的社會價值才得到實質意義上的實現,才能夠構成社會的上層部分,才能夠獲得對于社會的型構和對自我的塑造的權力,所以權力在實踐中最為牢靠的力量和同盟是語言,《易經·系辭上傳》謂之“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顯然是看到了語言對于事實的影響力量。
因為資本的不同,其所具有的社會效應也有差別,不同的人敘事能力有強弱之別,相應的其說服力的強弱也有區別,但顯然關鍵的是,一個人的敘事能力的強弱和事實的真偽并沒有截然的關系。[注]想一想眾口鑠金,三人成虎等成語,語言和現實的對應關系要比索緒爾所說的能指和所指要復雜得多。一個人如果具有適合一種司法程序的特定敘事能力,那么在司法上,其敘事的效果也會有區別,即一個人的敘事能力強的話,整個司法過程會在很大可能性上朝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發展,而相反,一個人的敘事能力如果很弱的話,那么整個司法過程會在很大程度上向不利于其利益的一方發展。[注]在這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古代的“五聽”技術具有更加合理的因素,因為通過這些技術可以較為有效的排除掉當事人的敘事因素,而更加直接的指向無法通過修辭加以掩蓋的心理、生理特征來判斷敘事的可信與否。盡管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廢除刑訊更加復合現代刑罰理念,但并不等于現在的訊問技術比以前的刑訊可以更加有效地避免判斷的錯誤。在法學教育中強調的職業共同體觀念,正是通過系統性的知識和制度的配合,加強法律人在程序內的敘事能力,這一方面為職業的壟斷造就了知識的門檻,也相對剝奪非法律職業者的司法敘事能力,從而為法律人提供制度性的敘事能力保障。
從敘事能力的視角來看,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很容易得到理解。現代的司法程序對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都有很高的要求。毫無疑問,現代的司法程序淵源于市民社會,而非鄉土社會。鑲嵌于市民社會的司法程序具有對鄉土社會的先天歧視性;嚴格而瑣碎的程序所耗費的時間和金錢則無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能支付這些代價的一部分當事人。司法程序所要求的形式上的平等必然要求無論城鎮還是農村都應適用相同的司法程序,但與此同時,我國卻面臨城鄉差距的現實,這將導致一個不可欲的結果,即農村不能充分享有現代法治的利益,卻要遭受傳統規范的排擠這一尷尬命運。[9]作為高度專業化的解紛機制,司法程序對主體的文化知識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不但農民一般缺乏專業化的法律知識,即便是高學歷的人員,很多也并不具有利用司法解決糾紛的所有知識。大學中法學學科的劃分和相互的隔膜,還有律師對于自己專長的追求,法院中不同審判庭的設置,毫無疑問都隱含在專業化機制中。這也正是律師在訴訟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重要原因。而嚴格的司法程序所要耗費的成本則是巨大的。
對于涉案的農民來說,其所具有的“資本”可以說都是極其貧弱的,就像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小白菜的境遇一樣,其所具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都不可能為其提供足夠的能夠讓法官和公眾相信的敘事能力,也不可能讓前者在涉訟時窮盡一切法律上的保障機制,而對于擁有較高社會地位者則可以動用法律上的所有保障機制,在法律運行的各個環節中利用自己的強大敘事力量。[注]在近年所播出的涉及訴訟的影視作品中,警察嚴格遵循逮捕、傳訊法律規定的,都是適用于高官或者是大公司老總,例如《重案六組》;相應的,而粗暴對待的多半是下層人們。
三、結論
在一切聽從證據的證明力和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的形式正義面前,較弱的敘事能力就意味著司法決斷中的陳述被否定,在民事案件中,也許可以看做是依據可能性來判斷,另外所產生的效果也許可以有所折中,比如在確實無法決斷的時候引入公平責任原則;但在刑事案件中,敘事能力的弱勢實際上意味著當事人所陳述的事實的被否定。所以,在實踐中,敘事能力的強弱帶來的并不僅僅是程度之分,在最終的決斷上,強弱和真假具有同等的效果。因此,在司法過程中,當事人雖然要通過法官的最終決斷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對于法官來說,他們對于紛爭的重構就只能依賴于當事人自己對于紛爭本身的敘事。只有當事人的敘事強度大于對方,才有可能說服法官,從而讓法官做出對于己方有利的決斷。從這種意義上來看,紛爭本身和司法決斷之間必須通過敘事的橋梁才能夠連接起來,而布萊克所說的社會地位結構[6]才能夠通過敘事發揮其作用。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克里.后現代敘事理論[M].寧一中,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TOM BINGHAM. The Judge as Juror: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Factual Issues,38 Current Legal Problem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3] 孫笑俠.程序與法律形式化[J].現代法學,2002,24(1):76-84.
[4]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修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150.
[5] 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192.
[6] [美]唐·布萊克.社會學視野中的司法[M].郭星華,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七條[Z].2001-12-21.
[8] 徐忠明.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法律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83-107.
[9] 董磊明.鄉村社會巨變中的糾紛調解機制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8:149-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