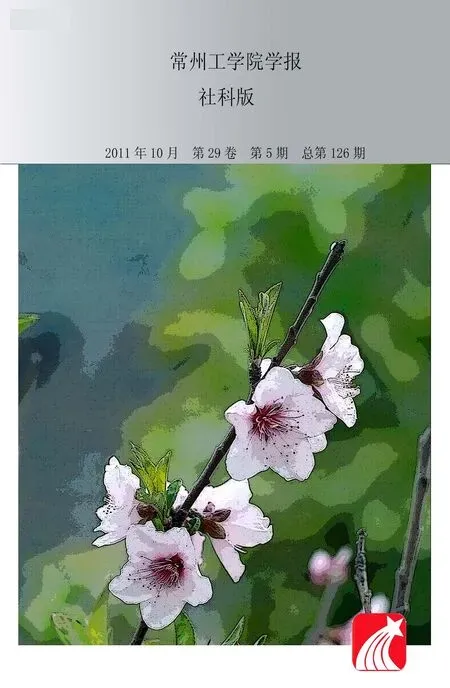論趙元任《阿麗思漫游奇境記》譯本中雙關幽默的翻譯
——基于德拉巴斯替塔的雙關語翻譯理論
張美倫,張清
(常州工學院外國語學院,常州工學院翻譯研究所,江蘇 常州 213002)
《阿麗絲漫游奇境記》(以下簡稱《阿》)是一部斐聲全世界的兒童讀物,是作者智慧與幻想的完美結合,發表于1865年,當時轟動文壇,在英美廣為流傳,作者卡洛爾以橫絕千古的藝術腕力,使用各種藝術手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藝術風格。這部作品以夢幻的形式,將讀者帶入一系列離奇的故事中,情節撲朔迷離、變幻莫測,從表面看荒誕不經,實際卻富有嚴密的邏輯性和深刻的內涵,尤其是那些“不通”之處,在博人一笑后,令人回味無窮。此作品的另一特色,便是它詼諧幽默的語言。趙元任先生曾稱其為一部“笑話書”。英美人善幽默,對幽默有著深刻的認識和嫻熟的運用,常借助多種修辭方法,比如夸張、反語、諷刺、比喻等來表現幽默,然而最能產生幽默感的修辭手法非雙關莫屬。由于原作微言大義,使得《阿》這部作品的翻譯,尤其是雙關的翻譯難上加難。但趙元任先生迎難而上,選擇這部英國童話作為他的翻譯“處女作”。文章擬通過分析趙元任先生譯《阿》中的雙關,探討趙元任先生如何處理原作縱恣變幻、機趣靈活的雙關美,從而再現原作中的幽默。
一、《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中雙關概述
雙關語又稱妙語雙關,是語言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即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利用詞的多義和同音的條件,有意使語句具有雙重意義,言在此而意在彼。雙關可使語言表達既含蓄、幽默,又寓意深刻,給人以深刻印象。在每個民族的語言中它都是一種常用的修辭手法,也是英漢語言中運用最早的修辭格之一。漢語的雙關語與英語的pun基本對應,它是有意利用語音和語義條件,使某些詞語具有雙重意義。《阿》中雙關語是作者所使用的眾多修辭藝術手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或用于人名,或用于對話,或用于故事情節,不僅增添了人物語言的雙關諧趣,對于刻畫人物形象、暗示故事情節、渲染小說歡樂氣氛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顯示出了雙關所特有的藝術效果。據統計,在《阿》這篇不足一百二十頁的故事中,有四十余處運用了雙關語和文字游戲,時而語意豐厚、余味深長,時而含蓄委婉、耐人尋味,時而形象鮮明、印象深刻,時而犀利深沉、鞭辟入里,征服了不計其數的讀者。
二、德拉巴斯替塔的雙關語翻譯理論選擇
雙關語本身便是翻譯的難點,再加之卡洛爾精于此道,創造出許多雙關妙語,因而譯者會感覺心有余而力不足,苦思冥想之后,亦不能得俱全,只能求其近趣。雙關語的成功處理,關系到貫穿全書的幽默效果的生動再現。然而,若按照傳統的觀點來理解“可譯性”,由于中西兩種語言和文化歷史上聯系不密切,雙關的可譯性很低。但如德拉巴斯替塔所指出的,誰也不能否認,對雙關語進行各種各樣的跨語言處理是可能的,只是這些處理方法不一定符合各人心中的翻譯標準。因此,雙關語的翻譯對譯者是很大的考驗,迫使他們做出決定,從而暴露自己的翻譯觀。
德拉巴斯替塔現為比利時那慕爾圣母大學英國文學和文學理論教授。他曾專門針對雙關語的翻譯問題,發表過幾篇文章,并編輯過兩部論文集。在這些著述里,他提出了雙關語翻譯策略的分類方法,我國學者張南峰將其總結為以下10種分類法:雙關語譯為相同的雙關語(同類型)、雙關語譯為相同的雙關語(不同類型)、雙關語譯為不同的雙關語、雙關語譯為類雙關語、雙關語譯為非雙關語、雙關語譯為零、照抄源文、非雙關語譯為雙關語、零譯為雙關語和編輯手段。首先,德拉巴斯替塔的雙關語翻譯分類法是描述性研究,具有傳授翻譯策略和技巧的功效,是針對翻譯研究的實際需要而設計的。其次,他的翻譯分類法比中國現有的分類法全面、細致得多,而且可以提供一些可以采用的策略給翻譯工作者參考。再次,這種分類法相對詳盡,幾乎可以涵蓋一切在譯文中能找到的雙關語翻譯方法。最后,這個分類法所用的名稱和定義都十分準確、明晰。文章擬用此翻譯理論,分析趙元任先生對于《阿》中雙關的處理策略及其翻譯觀。
三、趙譯《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中雙關翻譯處理
德拉巴斯替塔的分類法,不具有語言特殊性,它既適用于歐洲語言間的互譯,也大致適用于英漢翻譯。
(一)雙關語譯為相同的雙關語(同類型)
雙關語譯為相同的雙關語(同類型)是指以同類型的雙關語保留源文雙關語的兩層意思。首先以同音雙關的翻譯為例,探討《阿》中同音雙關的翻譯處理。例如:
(1)源文:“But they were in the well.”Alice said to the Dormouse,not choosing to notice this last remark.
“Of course they were,”said the Dormouse,“well in.”
趙譯:那惰兒鼠道,“自然她們在井里頭——盡盡里頭。”
此處源文為雙關語,上半句話為in the well(在井里頭),下半句話為well in(盡里頭),趙先生以“井”和“盡”二字相應譯出,可謂妙譯。“井”和“盡”使源文的雙關語義自然流出,不加藻飾,并構成了諧音雙關,可謂是完全等值、對應。
(2)源文:“Mine is a long and sad tale!”said the Mouse,turning to Alice and sighing.
“It is a long tail,certainly,”said Alice.
趙譯:那老鼠對著阿麗思嘆了一口氣道,“唉!我的身世說來可真是又長又苦又委屈。”
阿麗思聽了,瞧著那老鼠的尾巴說,“你這尾是曲啊!……”
阿麗思把老鼠講的“故事”(tale)一詞誤聽成“尾巴”(tail),腦海中浮現出尾巴的形象,意在說明她對于奇境中的居民感到困惑。源文利用諧音打趣,趙先生的譯文則以“委屈”和“尾曲”的諧音作相應的文字表達。“尾曲”既保留了“尾巴”的原義,又與前面的“委屈”諧音,這種處理引人入勝,妙不可言,“曲”盡奇妙。同音雙關“委屈”和“尾曲”的運用可謂恰到好處,其淋漓盡致、妙趣橫生地反映了卡洛爾原作的語義精髓和語言魅力,恰當地表達了源文的內容與形式,神味自然躍出,實乃上乘譯法。此類妙譯還有:
(3)源文:“But I know I have to beat time when I learn music.”
“Ah! That accounts for it,”said the Hatter,“He won′t stand beating.”
趙譯:“可是我知道我學音樂的時候要得拍的。”
那帽匠道,“哦,那自然嘞。你拍他打他,他還愿意呢?……”
源文利用“beat”一詞的多義現象,構成表里兩層意思,“打拍子”和“打”。這一類幽默的翻譯相當棘手。如果不采取趙元任先生那種完全“中國化的‘得拍’”的譯法,就得加許多煞風景的注,此處趙先生的翻譯堪稱神來之筆。
(二)雙關語譯為相同的雙關語(不同類型)
雙關語譯為相同的雙關語(不同類型),即以不同類型的雙關語保留源文雙關語的兩層意思。例如:
(4)源文:“And so these three little sisters—they were learning to draw,you know—”
“What did they draw?” said Alice,quite forgetting her promise.
趙譯:“所以這三個小姊妹就——你知道,他們在那兒學吸——”
“她們學習什么?”阿麗思問著又忘了答應不插嘴了。
當惰兒鼠給大家講三姐妹在井底的故事時,原文利用draw一詞多義(既作“畫畫”解,又作“抽吸”解)作雙關語,趙先生的譯文改用“吸”與“習”字作相應處理,譯文將兩詞點出,且言簡意賅,大可涵詠。不僅成功地譯出了原文的意義,畫畫本身屬于學習的范疇,又構成了“吸”與“習”新諧音雙關。
(三)零譯文雙關語
零譯文雙關語指在譯文里加入一些包含雙關語的全新文字。例如:
(5)源文:It was the White Rabbit.
趙譯:來的不是別“人”,而就是那位白兔子。
源文中“White Rabbit”兼有普通名詞和專有名詞的功能,所以是雙關語。而趙元任先生只譯為普通名詞,失去了雙關意味,“不是別‘人’”在源文沒有對應部分,可能是為了補償這個損失而加上的,是趙先生的創造。譯文放棄了雙關語的兩層意思,卻基本上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四)雙關語譯為類雙關語
雙關語譯為類雙關語即用某些帶有文字游戲性質的修辭手段(例如重復、頭韻、腳韻、所指含糊、反語等等),以求再造源文雙關語的效果。例如:
(6)源文:“There′s a large-mustard-mine near here.And the moral of that is—‘The more there is of mine,the less there is of yours’.”
趙譯:“自然是個礦物。這兒近處有一個芥末礦,于此可見——‘所曠愈多,所學愈少’。”
源文“mine”一詞可以表示“我的”和“礦”,是一句由雙關語引發的玩笑話。若直譯,則為“我(得到)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少”。趙先生也是開玩笑的意思,把原文中的“mine”成功地轉化為為漢語中的“曠”,譯為“自然是個礦物。這兒近處有一個芥末礦,于此可見——‘所曠愈多,所學愈少’”。源文雙關語的作用旨在制造氣氛,提供阿麗思和公爵夫人對話的機會,譯文雖放棄了源文的雙關含義,卻起到了相同的效果。
(五)雙關語譯為不同的雙關語
雙關語譯為不同的雙關語,譯文中與源文雙關語相近的位置上有雙關語,因此可視為對源文雙關語的翻譯手段;但是譯文雙關語的一層甚至兩層意思與源文不同。例如:
(7)源文:“I had not!”cried the Mouse,sharply and very angrily.
“A knot,” said Alice,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and looking arou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趙譯:那老鼠很兇很怒地道,“我沒有到!”
阿麗思道,“你沒有刀嗎?讓我給你找一把罷!”(阿麗思說著四面瞧瞧,因為她總喜歡幫人家的忙。)
源文借助“not”與“knot”兩個同音詞成功展現了阿麗思心不在焉、老是聽岔的情景。“not”與“knot”表示“不”和“(繩索等的)結”之義。若直譯,會導致原文幽默情趣喪失殆盡。為了在保留雙關的同時又使得譯文通暢,趙先生翻譯這段對話時,拋開了源文的語言形式,另辟蹊徑,采用“到”和“刀”一組諧音詞進行傳譯,妙趣橫生、別具匠心,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六)雙關語譯為非雙關語
雙關語譯為非雙關語指以非雙關語的方式傳達源文雙關語的一層或兩層意思,有時會使譯文“面目全非”,但趙先生的譯文并非比利時學者德拉巴斯替塔的翻譯策略所言譯文會面目全非,而是清晰地傳遞了原文的內容。例如:
(8)源文:“You see the earth takes twenty-four hours to turn round on its axis—”
“Talking of axes,”said the Duchess,“chop off her head!”
趙譯:“地球要二十四小時圍著地軸轉一回。”
那公爵夫人道,“還說斧子呢,就拿斧子砍掉她的頭!”
源文中axis(地軸)和axes(斧頭)構成語音雙關,語簡意豐,一箭雙雕,公爵夫人的無知與殘暴躍然紙上。而趙先生譯文的不足之處在于趙先生未照顧源文的雙關,使得中文讀者難以領略源文風采。筆者認為張南峰《中西譯學批評》一書中所評價的管紹淳譯文,此處處理得更勝一籌。管紹淳的譯文為:
“要知道地球繞軸轉一圈要用24個鐘頭。”
“說什么頭,”公爵夫人說,“把她的頭砍掉!”
雖然源文的雙關語為“axis(地軸)和axes(斧頭)”,譯文的雙關語為“鐘頭和頭”,與源文有明顯不同,但已達到錢鐘書先生提出的“精神姿致依然故我”和“化境”的標準,盡管管紹淳的譯文并非盡善盡美,但此處的翻譯也達到了極“似”的高度。
趙先生雙關的精彩譯筆不勝枚舉,此處不再贅述。僅從以上例子足以領略趙先生深厚的語言功底及其嫻熟的翻譯技巧。同時,通過分析也能發現中西方幽默感的不同。西方的傳統文化崇尚幽默感,所以西方的幽默在實踐上有比較豐富的積累,而中國“在禮教意識和宗法政治的一體化結構的禁錮之下,‘笑君者罪當死’……”。“不茍言笑”成了規范的行為模式,長此以往,幽默感當然難以蓬勃生長起來。這種傳統非常不利于幽默翻譯的實踐和理論的發展。
四、結語
基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趙先生的雙關翻譯觀,他不是采用雙關語譯為非雙關語、照抄源文、編輯手段三種策略來保證譯文的充分性,而是采用雙關譯為不同的雙關、零譯文雙關語、雙關語譯為類雙關語、雙關語譯為相同的雙關語的策略。因此,筆者認為他處理雙關語的起始策略都傾向于可接受性的策略。就是說,他力求再現或盡可能多地創造雙關,著重藝術等值,以免破壞源文的連貫性。這些做法都是為了使譯文在目標系統中可能被接受為有價值的、行文流暢、結構完好的翻譯文學作品。換言之,他要譯出“以目標文化的文學標準來看結構完好、內容優美”的文本,而不惜“在重建源文特點方面付出各種可能的代價”。這些“代價”最終使譯文詼諧幽默、精彩生動,成功再現原作的風格神韻,從而以韻律優美、生動有趣的藝術語言為中國讀者帶來一部優秀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
[參考文獻]
[1]陳子善.《愛麗絲漫游奇遇記》的第一部中譯本[J].譯林書評,1999(5):123-124.
[2]胡榮.白話的實驗與趣味的變異——論趙元任譯《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的文學史意義[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101-109.
[3]靳秀瑩.兒童文學翻譯之文體風格再現——兼評趙譯《阿麗思漫游奇境記》[J].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09(1):50-53.
[4]呂煦.實用英語修辭[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5]戎林海.論趙元任的翻譯觀[J].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5):5-10.
[6]奚永吉.莎士比亞翻譯比較美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7]楊靜遠.永不消逝的童年的夢——一本老幼共賞的書《阿麗思漫游奇境記》[J].譯林書評,1999(5):115-122.
[8]游潔.論霍譯本《紅樓夢》中雙關語的翻譯[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10(2):123-125.
[9]張南峰.中西譯學批評[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10]趙元任.阿麗思漫游奇境記[M].漢英對照.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