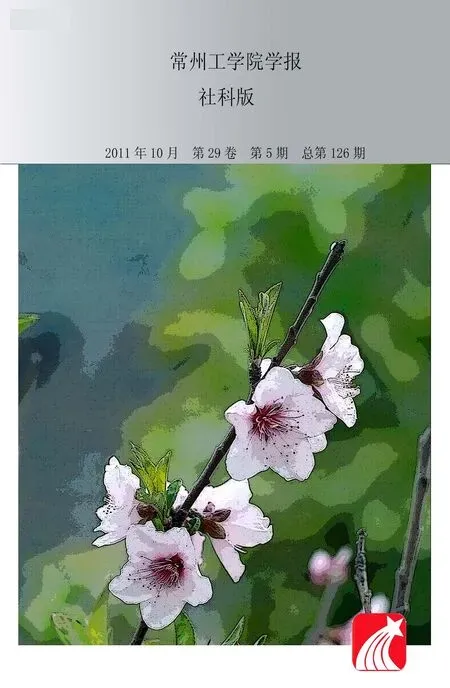奧尼爾戲劇人物性格悲劇論析
王曄一,孫周年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美國劇作家奧尼爾一生都在對悲劇進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奧尼爾曾說過:“悲劇對于我們的生活方式是移植來的嘛?不,我們本身就是悲劇,是一切已經寫出來的和沒有寫出來的當中最令人震驚的悲劇。”[1]246奧尼爾和古希臘人一樣,把人看作是悲劇人物,每個人的存在就是一種悲劇,而這種悲劇不單單是外在因素造成的,“而且也是自己的悲劇性缺陷、荒謬的本身的一種弱點所造成的”[2]407。在奧尼爾看來,造成人類這一悲劇的原因便是隱藏在人之內心的這種神秘的弱點,它包括人的各種情緒、本能、渴望和欲念等內在的因素,也有諸如倫理道德、宗教信仰等外在因素,它們在人的內心中激蕩、斗爭,推動人的行動、追求,甚而造成人們相互對立、廝殺,最終導致人的悲劇乃至毀滅。
作為一位嚴肅而深刻的劇作家,奧尼爾對悲劇有著獨特的理解。在論及悲劇的意義時,他曾說過:“對我來說,只有悲劇才是真實,才有意義,才算是美。悲劇是人生的意義,生活的希望。最高尚的永遠是最悲的……只有追求無法達到的目標,才能得到為之生死的希望,才能得到他自己。人在無望的奮斗中得到希望,這是莫大的精神安慰,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星空彩虹。”[3]220奧尼爾認為悲劇使人變得崇高,悲劇在精神上鼓舞人們更深刻地理解人生的意義,體現生命的價值。生活本身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劇,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沉淪墮落,而是該去奮斗。“當人在追求不可企及的東西時,他注定是要失敗的。但是他的成功在斗爭中,在追求中!當人向自己突出崇高的使命,當個人為了未來和未來的高尚價值而同自己內心的和外在的一切敵對勢力搏斗時,人都是生活所要達到的精神上的重大意義的范例。”[4]157
在了解了奧尼爾的悲劇觀后,就不難理解奧尼爾作品中人物悲劇的內涵。在筆者看來,所謂人物的悲劇性,是指人物的一種獨特的人格傾向,這種力量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能夠引導人們去戰勝人自身的恐懼,從而保持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在追求中體現人之生命的價值。在奧尼爾的每一部悲劇中,幾乎都有這樣具有悲劇性格的人物,如《榆樹下的欲望》中的艾比,《奇異的插曲》中的妮娜,《毛猿》中的揚克,他們都是平凡的,甚至渺小、軟弱、可悲的人物,他們都為環境所擺布,為命運所捉弄,深陷于各種困境中而無法自拔。但與此同時,我們又看到這些人物身上卻有著崇高的品質,他們為追求理想而奮斗著,也許等待他們的是失敗,但是在努力的過程中,他們實現了自己的生命價值。
結合具體作品,論者認為奧尼爾筆下人物的悲劇性蘊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本能與理性的沖突,自我肯定與社會道德的沖突。應該說,正是這些特征構成了奧尼爾特有的心理悲劇,豐富了其戲劇創作的精神內涵。
一、本能與理性的沖突
綜觀奧尼爾的戲劇作品我們發現本能與理性的沖突是奧尼爾作品人物悲劇性格的首要表現,《榆樹下的欲望》就凸顯了這一主題,劇中男女主人公伊本與艾比從抗拒走向融合的過程便體現了本能與理性的尖銳矛盾。關于本能,弗洛伊德認為,性本能是人類本能的核心,而在人類社會中,人的性本能受到了壓制,性欲同道德、倫理等理性觀念是相互沖突的。理性試圖去戰勝欲望,然而,生命卻因欲望而絢爛。在本能與理性的沖突中,人性最終得到了升華。《榆樹下的欲望》即完美地詮釋了這種沖突下的人性的回歸與綻放。
男女主人公伊本與艾比在偷情之初,艾比嘲笑伊本說:“你可以感到它一直燒進了地里——大自然——使萬物生長——長得越來越茁壯——在你的身子里燃燒——是你也想跟著長——長成別的東西——一直長得你和它接合在一起——它是你的——可它也占有了你——使你長得更茁壯——就像一棵樹——就像那兩棵榆樹。”[5]226艾比以榆樹作比,直接指出了伊本的欲望。伊本想用理性戰勝欲望,他始終不能忘記自己的母親,覺得繼母艾比企圖奪取應該屬于母親的農莊,取代母親在家中的地位,自己應該與其戰斗到底。甚至在艾比主動吻他時,伊本也會突然意識到自己對艾比的仇恨,便把她猛地推開,“我不想要幸福——你給的幸福!”[5]239從伊本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用理性來壓制自己的欲望,但是接下來的發展卻是讓其欲望戰勝了理性。伊本的理性驅使他對艾比進行報復,但最終沒有抵抗住艾比那“肉欲和母愛的一種令人可怕的自然融合”[5]243的吸引,他們終于走向了結合。在沖突中,理性似乎輸給了欲望,但讓他們收獲了愛,生命因為欲望而綻放。
作品并沒有以此作結,接下來卻出現了悲劇性的反轉:理性企圖去戰勝欲望,但理性又最終將生命引向悲劇。伊本誤以為艾比對他的愛只是為了得到農場而說的謊話。艾比生下了伊本的孩子,但伊本的爸爸老凱伯特認為這個孩子是他的,決定把農場送給這個孩子,伊本便誤會了,以為是艾比為了騙取農場才與他在一起的,因而非常憤怒。艾比向伊本澄清:“如果這就是他生下來帶給我的結果——毀掉了你對我的愛——奪走了你——我唯一的快樂——我有生以來體驗到的唯一的歡樂——對我說來就像天堂——比天堂還要美——因此,即使我是他的媽媽,我也恨他!”[5]261為了證明她對伊本的愛,艾比決定殺掉自己的兒子,但伊本已無法再信任艾比了。在愛的本能的驅動下,艾比殺死了她和伊本的兒子。伊本非常憤怒,他無法原諒艾比所犯下的罪行,而在理性的驅動下,他告發了艾比。但告發之后,伊本突然感到:“我想起了我多么愛你。這種想法就像有種東西在我的胸口,在我的腦袋里要爆炸似的。——我突然明白過來,我還在愛著你,而且會永遠愛你的!”[5]270可是,悲劇已經造成,命運也不能重來,即使他們的愛情是那么熾烈,但他們的理性卻使他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在這里,奧尼爾既表現了他們的悲劇性格,亦展示了人性在本能與理性的博弈之中走向升華的過程。
在本能與理性的沖突中,人性得到了升華。在愛情本能的驅動下,伊本與艾比放棄了占有農莊的私欲,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的愛情體現了其生命的價值,使人性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劇終時,伊本與艾比被自己美麗的愛情所震驚了,精神得到了升華,靈魂也得到了拯救。
二、自我肯定與社會道德的沖突
奧尼爾戲劇中人物的悲劇性格還體現在人對自身的肯定與社會道德的沖突上。在奧尼爾的劇作中,如何評價自己是人性最直接的體現。個人對自身價值的肯定,便是人性堅韌的表現。在《毛猿》中,揚克的遭遇就體現了自我肯定與社會道德的沖突,這個“比其余的人更健壯、更兇猛、更好斗、更有力、更自信”[6]96的揚克,“代表著一種自我表現、他們身份的最后評價、他們的最高度發展的個性”[6]96的人物,蔑視著傳統的社會道德體系。
揚克是一艘郵輪上的燒火工人,他認為自己是郵輪的一部分,自己就是“世道”,沒有他,一切都要停頓,一切都要死亡。由于他身強力壯,可以比其他人干得更多,所以他毫無畏懼,可以在鍋爐房稱霸。這種優越感使他非常自信。然而托拉斯總經理的女兒米爾德里德的出現動搖了揚克的自信心,他開始質疑自己。米爾德里德下到爐膛口參觀,看見揚克一只手里拿著他的鏟子,兇惡地在頭上揮舞,另一只手捶著胸膛,像個大猩猩一樣大叫。米爾德里德嚇得幾乎要暈過去了,趕緊蒙上眼睛,喊道:“帶我走開!噢,這個骯臟的畜生!”[6]117這時揚克感到盛怒和憤慨,他覺得自己,他的自尊心,莫名其妙地受到侮辱,于是他開始“思考”,思考自己存在的價值。他企圖通過一些舉動去證明自己的價值,甚至去第五馬路報復那些白人。這里我們注意到一個問題,為什么揚克要去報復白人?其實很好理解,一個對自己極度肯定,甚至有些自傲的人,從根本上受到否定后,必定會產生極度的焦慮,而這種焦慮迫切地需要釋放。從這個角度來看,奧尼爾的悲劇從心理和人性的層面上得到了深化。
人的悲劇是由人內在的心理所造成的,因而對人性的肯定,也許是導致悲劇的理由,社會道德起不了扭轉乾坤的作用。奧尼爾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的內心世界有著對人性肯定的渴望,也許這種渴望會導致悲劇性的結局,也許從個體意義上來說,是失敗的,但是這在整體意義上卻獲得了提升,這便是奧尼爾悲劇最深刻的意義。
“自我肯定就是使每一存在物成為其所是的那種努力,假如這種努力消失,存在物便不能保其所有而趨于瓦解。但這種自我肯定并不是輕而易舉的,而是一種克服威脅的奮斗追求。”[4]182揚克便是這種追求最好的體現,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奧尼爾悲劇的目的達到了。正如西西弗斯的傳說一樣,每個人都是推圓石的人,盡管他們無法將圓石推上山頂,盡管他們所推的圓石甚至倒退了,但他們并不是失敗者。人生的價值可能就在此,就是這種堅持不懈的努力,也許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努力的本身就是價值。如果他們都放棄了這種努力,那么圓石就會從山上滾下來,把所有的人都壓扁。
綜上所述,奧尼爾劇作中的悲劇人物體現了其自身的生命價值,而這些人物以其獨具特色的悲劇性格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絢麗的一筆。在本能與理性、自我肯定與社會道德的雙重沖突中,他們仍然保持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在追求中體現人之生命的價值。伊本與艾比在欲望與理智的斗爭中追求真愛,而這真愛最終幫助他們滌蕩了人性中的卑劣和粗鄙,使其人性得到升華與飛躍;揚克在自我肯定與社會道德的沖突中追尋存在的意義,雖然最終他并未找到其自身的價值,但他的努力在整體意義上卻得到了成功與提升。盡管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會面對種種困惑和挫折,但奧尼爾筆下的人物仍然能夠堅持自己的人生目標,努力實現人生理想,創造自己的價值,為追求美與愛不惜付出一切代價。在理解了奧尼爾劇作中人物的悲劇性格之后,我們便能夠更加深刻地透視和領會其悲劇的魅力,人的靈魂在對其悲劇的賞析中得到陶冶,在生存的價值意義之思考中趨向升華。
[參考文獻]
[1]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美國作家論文學[M].劉保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2](美)弗吉尼亞·弗洛伊德.尤金·奧尼爾的劇本——一種新的評價[M].陳良廷,鹿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3]郭繼德.奧尼爾文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衛嶺.奧尼爾的創傷記憶與悲劇創作[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5](美)尤金·奧尼爾.天邊外[M].荒蕪,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6](美)尤金·奧尼爾.奧尼爾劇作選[M].荒蕪,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