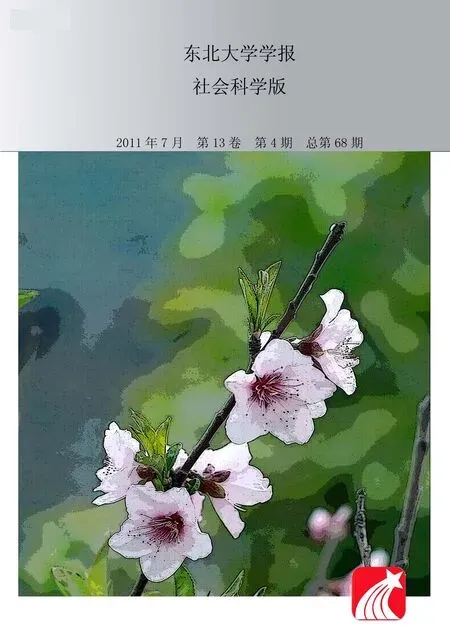阿倫特“根本的惡”的困境及其政治哲學意義
王 義,羅玲玲
(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遼寧沈陽 110819)
肆虐于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屠殺與種族滅絕事件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的浩劫。對于德裔女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來說,對這場歷史事件進行一種全新的認識,關涉到人類的命運。
一、透過極權主義理解人性邪惡的理性困境
對于阿倫特來說,極權主義之種族滅絕政策使其不能再沿用功利主義進行理解。“死尸工廠和遺棄人的洞穴的危險性在于,如今人口到處在增長,無家可歸的現象也到處在增長,如果我們繼續根據功利主義來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眾依然會變成多余者。”[1]573漢娜·阿倫特提到的功利主義是近代西方廣義上的人性觀,以此為基礎,建構了西方近代的社會科學。按照功利主義人性觀看來,且不談及人的本質是否是道德的,至少在現實本性上體現為功利,它以外在的質料為目的,服從于自己的生存或存在需要。由于功利,人可能將其他人當做工具,但是不可將自己當做工具來使用,根據形式邏輯的矛盾律來表達就是“人不可能毀滅自己”,也就是說,功利性是人的自然本性。根據功利性建構起來的人類社會,必然以功利性為其基本自然規律。而死亡集中營等現象表明,極權主義想要通過全面恐怖的方式建立起一種妄圖毀滅人性自然需要的實驗方式。“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目標不是改變外部世界,或者社會的革命性演變,而是改變人性。集中營是實驗室,在集中營里試驗改變人性和羞恥心,所以集中營不光是囚徒們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據嚴格的‘科學標準’來管理他們的人的事情;它關系到所有的人。”[1]572
通過對極權主義歷史進行的意識形態考察,漢娜·阿倫特提出其邪惡動機超越自然功利,它作為一種具有自身目的性的存在,表達出來就是“人是多余的”。該種意識形態,以完美的人類為意向,功利性或者說現實的人類成為被摧毀、被改造的基本對象,摧毀的手段就是以秘密警察為制度保證的全面恐怖,全面恐怖則體現為集中營式的滅絕政策。“徹底的惡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在這種制度中,一切人和其他人一樣是多余的。操縱這個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是多余的,極權主義的殺人者最為危險,因為他們連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關心自己是否生活過、是否出生過。”[1]573由于阿倫特發現該種意識形態的違反矛盾律之處,因此就能推論出一種不包含有任何善意的“根本的”惡意了。“有一些罪行是人們既不能懲罰,又不可寬恕的。當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時,它就變成不能懲罰的、不可饒恕的絕對罪惡,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貪婪、渴望、怨懟、權力欲望、怯懦等罪惡動機來解釋。”[1]572
漢娜·阿倫特提到她遭遇到“根本的惡”時候的理解上的難題,不過就是意味著,如果我們根據功利主義背后的矛盾律來理解極權主義現象的話,我們永遠不能通達極權主義的內在本質,她將這種理解上的困境比喻為加在現代人身上的重擔。“我們實際上不必借助任何事物,就可以理解一種用十分有力的現實來和我們對抗、打破我們所知的一切標準的現象。”[1]573也就是說,阿倫特此時認為必須沖破傳統的理性,進入到一種超出人類理解限度之外的理解方式,極權主義乃至惡才可以被認知。同時,對極權主義進行理性的探究,也就是在動機的探究中,賦予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以超乎人類理解限度的理性根據,它才能超越人類的功利動機。如此一來,阿倫特的“根本的惡”概念就與哲學理性主義的傳統道德觀乃至康德于“根本的惡”中提到的“絕對的惡意”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
二、 理性的二重維度:真理與道德
“我們的哲學傳統從來就不相信一種‘根本的惡’,在基督教神學那里,即使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至少懷疑這種惡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將之解釋成‘反常的惡意’,但是也可用可理解的動機來解釋。”[1]572由于西方的理性主義秉持的矛盾律,一個人不可能在沒有任何功利目標的前提下,將其他人乃至自己當做工具加以利用,也就是說罪惡起源于“自我利益”、“貪婪”、“渴望”、“怨懟”、“權力欲望”、“怯懦”等罪惡動機,本質上是人的 “自愛”。
理性主義的內在邏輯是:其天賦對象即本體的自在自為。自在意味著本體是一個尚未展現自身的、理念上的同一者,可以被理性認知,由于同一而完滿,是一切理性認識最終要符合的朝向者,蘊涵著一切現實的乃至潛在的展現,這是理性的認識維度賦予其對象的理念完滿性即真理;同時,自在者自為,自為就是自在者的展現自身,是對自身的回復,即由理念上的同一上升到現實的自身統一,所有展現出來的現象都是自在的完滿性的表現,是一種完善,是對真理的明證,正是因為此種展現,本體才作為證明了自身的同一者,這是理性的證明維度賦予其對象的道德實踐意義。由于本體的自身統一及其獨立性,與雜多現象的對立就必然成為題中之義,本體至真且至善,雜多的現象相對于理念的完滿性,存有欠缺,從而是相對意義上的惡,同時由于雜多現象又是對真理展開的符合乃至證明,也是相對意義上的善。
所以,對于哲學傳統來說,雜多現象不存在“絕對的惡”、“根本的惡”,同時也不存在“絕對的善”、“根本的善”,而關鍵是,現象總是自在者的自為展現,在這個意義上,一切現象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惡又從何而來?這就引申出康德“根本的惡”概念提出的立意所在,即,任何含有違背理性先天規定的主觀根據,都可以稱做是“根本的惡”,“它雖然也可能是與生具有的,但卻不可以被想象為與生具有的,而是也能夠被設想為贏得的(如果它是善的),或者是由人自己招致的(如果它是惡的),……所以,這種惡必須存在于準則背離道德法則的可能性的主觀根據中,而且如果可以把這種傾向設想為普遍地屬于人的(因而被設想為屬于人的族類的特性),那么,這種惡就將被稱做人的一種趨惡的自然傾向”[2]21。
對于康德來說,既然秉持著理性的真理維度與道德維度之間的內在統一這種哲學的傳統態度,作為根據的根據必然是至善者,從而迫使作為惡的規定性根據的根據不能具有實在性,而只能是一種潛藏于人性之中的主觀根據,既不能是感性的實在,也不可能是理性的實在。換言之,它只能是人類的自愛。“為了說明人身上的道德上的惡的根據,感性所包含的東西太少了;因為它通過取消有可能從自由中產生的動機,而把人變成了一種純粹動物性的東西。與此相反,擺脫了道德法則的,仿佛是惡意的理性(一種絕對惡的意志)所包含的東西又太多了,因為這樣一來,與法則本身的沖突就會被提高為動機(因為倘若沒有任何動機,人性就不能被規定),并且主體也會被變成為一種魔鬼般的存在物。”[2]21
至此,就能發現阿倫特提出“根本的惡”概念并不是康德所說的“根本的惡”,而是康德所否定的“絕對的惡意”。康德所理解的“魔鬼般的存在物”,在阿倫特那里,通過極權主義運動的現實沖擊,成為了擺在現代人面前的現實性與挑戰,導致了人類理性對于“根本的惡”的認知困惑。
三、理性遭遇惡的困境:“絕對的惡意”是否可能?
理解阿倫特放棄“根本的惡”概念的關鍵,在于理性遭遇惡的認知挫敗,或者說,是“根本的惡”概念本身就必然要面臨著如康德所言化解不了的邏輯困境,才導致了對于道德之惡的認知的放棄。對于這種極端的罪惡動機,康德沒有進行深究,那是因為他固守著理性同一律的自我循環,賦予歷史現象以不同程度上的合理性,回避了理解極端事件的現實本質的特殊性問題;而阿倫特執拗地堅持極權主義及其罪惡動機的實在性,強調其惡的“根本”而又自覺無法化解這種沖擊帶來的困惑,隨后提出了“平庸的惡”概念,遭遇到各種不解與敵視,卻無法澄清“平庸的惡”概念的革命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兩人都沒有深入認識到:理性自身設置的道德陷阱,是“根本的惡”無法穿透極權主義的迷霧的障礙。
首先,由于堅持極權主義的超越功利性的惡意及其難以通過矛盾律、同一律來理解的根據,賦予了惡以實在的規定性乃至客觀的根據。繼而這種根據就沖破了建構在至善者的客觀實在性與道德之間的統一關系,沖破了作為最終尺度即作為統一者的統一性,劃出一個人類理性尚沒有涉足的,但是終究是可以被認知的“根本的惡”的實在維度,而同時阿倫特保留了對之繼續進行理性探究、動機探究的可能,這樣就無形中賦予了那個作為“根本的惡”的根據以一種統一性。也就是說,只要理性賦予了事物以根據的時候,就必然同時賦予其統一性,而這個統一性作為“根本的惡”的根據乃至尺度,其本身卻回復了自身,成為一種超越了被相對地評價為善和惡的自在自為者。如此一來,原先作為評價一切的至善者由于受到“根本的惡”的沖擊而與“根本的惡”一道成為相對的善,而又產生了作為自在自為者的終極價值尺度。最終,理性經過一番對于惡的根據的無窮探究,最終的結果不過是對于自己的兩個維度不斷統一的無限循環而已。
正如康德所說,與法則本身的沖突被提高為動機是不可能的,“因為它不會違背自身”,矛盾律、同一律作為形式邏輯不可能失效,阿倫特于極權主義現象中發現的違背自身的邏輯不過是預設了作惡者以理性的能力,進而產生了“根本的惡”概念的循環困境。所以,既賦予了“根本的惡”以迥異于至善的實在性,又保留了對其進行理性探究的可能,最終的困境必然是阿倫特轉向對于作惡者理性動機的理性探究的放棄,是“平庸的惡”概念得以產生并具有重大意義的最關鍵原因。
四、關于阿倫特“根本的惡”的轉折及誤解
美國學者Bernstein認為,在阿倫特提出“根本的惡”概念的時候,她對于康德“根本的惡”概念的批判實際上是對于惡的理性化的放棄,進而進入到一種關于惡的認知的盲區。“請注意,盡管阿倫特提到了康德,但她宣稱,為了理解那一‘以其不可抗拒的實在性面對我們并打碎我們所知的一切標準之現象’,我們實際上無所求助。”[3]有的學者認為,阿倫特對康德“根本的惡”觀點的理性化惡的批評實際上沒有切中康德提出“根本的惡”的所指,他們認為康德提出“根本的惡”本質上是要建立人在邪惡發生的時候不可避免的道德責任。“Arendt的解釋太過強調惡的非理性或者反理性,以至于忽略人即使活在一個邪惡的集權暴力的統治之下,發生邪惡的過程中,個人仍然有不能逃避的責任問題。”[4]
在阿倫特“根本的惡”與康德“根本的惡”概念的比較理解中,諸多學者都注意挖掘康德“根本的惡”概念中的道德自由問題乃至其自身轉化問題,進而證明人在罪惡面前涉及的不可避免的道德責任能力,也就是說,阿倫特沒有涉及到道德與罪惡的責任問題,直接否定了人類的道德承擔問題,也就同時否定了道德存在的可能。然而,先不說康德的“根本的惡”概念中的自由根據僅僅是能夠“被設想為”普遍地屬于人的,而現在關鍵的問題是,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的出現沖擊著、瓦解著這種主觀的根據,極權主義的理性邏輯超越西方哲學傳統理性主義的邏輯規律。也就是說,康德所說的“自愛”即主觀根據,在阿倫特看來奠基于理性主義道德運思的傳統之中,它更為主要的是確證人類的道德能力問題,而極權主義的出現卻沖擊著這種傳統,此時,我們必須“無所求助”,才能理解這突如其來的歷史怪物。
而關于阿倫特為何放棄“根本的惡”,轉而提出“平庸的惡”,尚存在爭論,國內流行的見解大體是,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實質的改變,這兩者不過是兩種惡,或者說,“根本的惡”是潛藏的作惡傾向,另有極端的惡體現為希特勒代表的法西斯納粹體制之惡,而“平庸的惡”不過是體制之下逐漸被剝除了道德能力的“平庸性”表現而已。如涂文娟所言:“根本的惡”的根本特征表現為破壞了人類發展和進步的概念,致力于把人變成多余的人的事業,以及消滅了人的法律人格、道德人格以及作為個體的人,是極權主義專制下道德崩潰的一個根本的理論上的原因,體現為諸如以希特勒為代表的“元首之惡”即一種“大惡”;而阿倫特于之后提到的“平庸的惡”的特征體現為無思想和膚淺性,是一個重要的合謀者。涂文娟進而認為:“根本的惡源于人性的某種東西,只要有人和人類社會,就一定存在這種根本之惡,無論有沒有邪惡的領袖,它都潛在地存在于我們的心中,因為如果人性本身沒有根本的惡,人就不會被魔鬼所誘惑。”[5]
劉英認為:“阿倫特指出的這兩種‘惡’實質上是從社會與個體兩方面揭露了現代社會極權制度下人性的喪失狀況。”[6]如果將“根本的惡”理解為阿倫特所說的極端性,“根本的惡”的確體現為體制上的異化,與“平庸的惡”相互構成,但是,這就等于簡化了阿倫特“根本的惡”與康德“根本的惡”概念之間,乃至與整個哲學傳統之間的轉承關系。忽視了“根本的惡”是理性在遭遇極權主義之惡時候的整合乃至困境,“平庸的惡”是對理性探究、動機探究的根本放棄,轉向哲學詮釋、哲學與政治關系反思,即走向具有阿倫特特色的政治哲學之路。
五、阿倫特對哲學與政治關系的反思
本文只是想在此處指出隱含于“根本的惡”概念中的理性困境,借此梳理阿倫特關于惡的思考的前后轉折的關鍵所在。理性內在的二重維度,真理與道德,盡管經過阿倫特的“根本的惡”概念顯露出缺陷,但也就是僅此而已罷了,相反,就像理性賦予真理以至善屬性一樣,由于阿倫特執著地賦予惡以實在性,就在同時依然秉持著哲學的傳統,尚未超越出去。
所以,只有放棄對艾希曼動機的深究,放棄那個深藏于人性深處的不可告人的惡意,阿倫特才會走出理性自設的困境。“我的看法改變了,已不是主張‘根本的惡’的觀點了。……惡絕不是根本的東西,只是一種單純的極端的東西,并不具有惡魔那種很深的維度,這就是我真正的觀點。‘惡’正猶如覆蓋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樣繁衍,常會使整個世界毀滅。惡是不曾思考過的東西。為什么這么說,思考要達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何況,涉及惡的瞬間,因為那里什么也沒有,帶來思考的挫折感,這就是惡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質的。”[7]166
放棄了價值屬性(在這里為惡)的賦予,而代之以生活背景個人言行的描述,一個真實的犯罪者就呈現出來了,極權主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惡的“平庸性”也展現了出來。“既不陰險奸刁,也不兇橫而且也不是像理查德三世那樣決心‘擺出一種惡人的相道來’。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升非常熱心外,沒有其它任何的動機。這種熱心的程度本身也絕不是犯罪。……他并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絕不等于愚蠢,卻又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這就是平庸,就僅這一點滑稽,如果還去作任何努力嘗試希望能知道艾希曼有惡魔一般的要因,那是不可能成功的。……這種脫離現實與無思想性恐怕能發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表現出巨大能量的事實正是我們在耶路撒冷學到的教訓。”[7]54-55也就是對理性化的邪惡動機探究的放棄,代表公民麻木精神狀態的“無思想”概念才呈現出來,作為阿倫特后期對政治現象與哲學關系、對哲學本身的詮釋的啟動概念。
總之,在“根本的惡”階段,由極權主義的極端到“根本的惡”的價值規定性,被阿倫特默認為一種關于價值屬性的認知行為,無形中賦予了惡以實在性;同時,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由于秉持著對象的統一性,必然在認知中賦予對象以價值屬性。然而歸根結底,道德上的善和惡,都需要一個尺度來評價,也就是說,絕對尺度的道德屬性是被預設的,而善和惡是被相對地評價的,至于那個尺度自身,由于自在自為而被理性識做是至善者。換言之,哲學傳統的理性主義不可沖破,阿倫特轉向了對哲學本身的反思與詮釋,才看得分明,它只不過是一種意義或價值的賦予行為,在其背后,是人類總體如何生存于歷史中,如何在歷史中發現意義的現實問題或者說是人類之間的政治交流問題。
阿倫特在最后一部代表作《精神生活》三大卷本之中,提出哲學與政治的親緣乃至對于政治生活的遺忘。蘇格拉底對于真理的追尋,始終是在與公民的對話之間展開的,而蘇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圖產生了對公共判斷力的極大偏見,對于柏拉圖來說,首先真理成為一種純粹內在的思考,另外,政治生活也成了一種等級關系的統治。作為恢復哲學與政治的親緣關系的努力,阿倫特發揮了康德的“判斷力”概念,“它使我愉悅或者不悅,作為一種感覺這似乎完全是私人的,也是不可傳達的,但實際上這種感覺植根于共通的感覺,因此一旦通過反思的轉換就可以傳達,而反思考慮到其他所有的人及他們的感覺……。換句話說,一個人在判斷時,他是作為共同體的一員在判斷的”[8]。
由于經過“根本的惡”階段的理性困境,阿倫特政治哲學思想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反思到了哲學理性的意義賦予行為,是作為一種對待歷史進程的旁觀——詮釋行為,并通過將哲學思考的這種純粹性引入人類公共生活中,來恢復政治生活的公正性。
參考文獻:
[1] 漢娜·阿倫特. 極權主義的起源[M]. 林驤華,譯. 北京:三聯書店, 2008.
[2] 康德. 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M]. 李秋零,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3] 理查德·J.伯恩斯坦. 對根本惡的反思:阿倫特與康德[EB/OL]. (2005-04-10)[2010-08-30]. 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841.
[4] 陳瑤華. 康德論“根本惡”[J]. 東吳政治學報, 2006(23):62.
[5] 涂文娟. 政治及其公共性:阿倫特政治倫理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163.
[6] 劉英. 漢娜·阿倫特關于“惡”的理論[J].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2009,62(3):319-325.
[7] 漢娜·阿倫特.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M].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8] Arendt H. Lectures i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