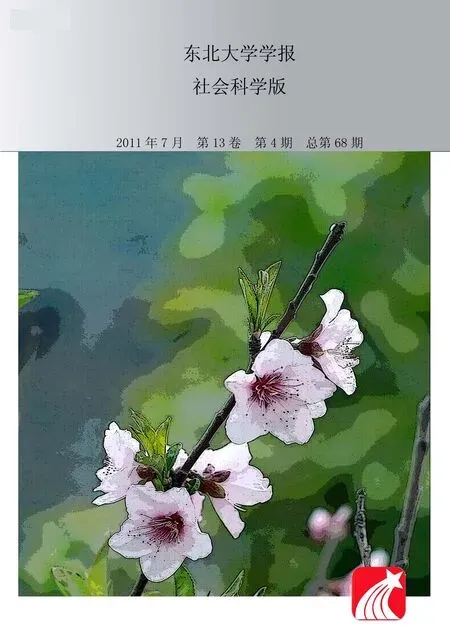沉默與逃避
——論《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的風景
(1.武漢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2.中南民族大學外語學院,湖北武漢 430074)
J.M.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正式進入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無疑是在他獲得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以后。目前國內學界對于庫切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焦點多集中于他的少數代表作,論文選題、觀點也存在重復和扎堆現象,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布克獎得獎作品《恥》(Disgrace, 1999),《福》(Foe, 1986)和《等待野蠻人》(WaitingfortheBarbarians, 1980)。相比之下,庫切的另一部布克獎獲獎之作《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Life&TimesofMichaelK, 1983)(以下簡稱《邁》)則受到了“冷遇”,僅有的論文多限于常規的主題分析,“拯救”也成了出現頻率最高的詞①主要論文分別為:翟亞軍、劉永昶的《無神時代的約伯——論庫切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外國文學》2006年第2期);韓瑞輝的《種植與拯救——小說〈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K的園丁形象分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S2期);高文惠的《規訓、懲罰與邁克爾》(《廣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苗永敏的《自然之善:南非的拯救之路——解讀庫切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作家》2008年第11期);苗穎的《由〈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解讀庫切的自由觀》(《電影文學》2010年第4期)。。那么,庫切真是在他的小說中向讀者傳達南非的“拯救之道”嗎?本文認為,“沉默”與“逃避”才是《邁》這部作品的核心議題。從表面上看,小說中的風景和主人公邁克爾一樣沉默,但它在全書中是一種動態的建構,庫切通過貫穿故事始末的風景,表達出他對于創傷、歷史、權力、規訓等諸多問題的反思,逃避最終成為了邁克爾唯一的選擇。本文也試圖從人文地理學對于風景的論述出發,解讀小說中的風景以及邁克爾對于風景的感知與想象。
一、 風景與創傷
“風景”(landscape)又稱景觀,它是一個具有多種意義的術語,指“一個地區的外貌、產生外貌的物質組合以及這個地區本身”[1]367。本文探討的風景屬于人文地理學上的寬泛定義,既指土地,又包括土地上的樹木、草坪、植物、建筑等,側重于它們的組合排列、外貌特征以及隨之產生的意義。英文中的“landscape”從詞源學上講來自于荷蘭語的“landschap”和德語的“landschft”,準確對應的中文翻譯應該是地景或土地景觀,最初指的就是某一視野中看到的一片土地。隨著文學與生態批評、人文地理學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文學中的風景研究已為更多人所熟知,風景也演變成為一個總括性概念,用以指代“土地”、“地方”、“區域”、“環境”、“空間”、“背景”、“景色”等等,它甚至可以與“空間”、“地方”等詞互換使用[2]。美國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說過,“風景是人的種種努力的聚合之處”[3]126,所以作為一種表征形式,它是一個復雜的意義系統,由地理風貌與文化景觀疊加而成。
《邁》講述了小人物邁克爾在充滿戰爭、軍隊和種族矛盾的南非社會苦苦掙扎的故事。由于天生兔唇,邁克爾注定將不可能得到異性的愛慕和擁有體面的職業,這一無法修補的面部缺陷給他帶來了無盡的傷痛。從殘疾兒監護學校畢業后,邁克爾進入市政園林處成為了一名花匠。后來他也在公共廁所當過值夜人,但他更喜歡美麗的園林,因為“那里有著高聳的松柏和開滿白子蓮的朦朧小徑”[4]3。他對園林的偏愛源于內心的創傷和自卑,也是他沉默的天性使然。旁人總會對他指指點點、竊笑不已,面對鄙夷和嘲笑,邁克爾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緘默。小時候母親帶他去工作,他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母親擦亮別人家的地板。明亮潔凈的空間會將他的兔唇暴露無遺,嘈雜喧鬧則令他緊張局促,唯有安靜幽閉的園林才讓他感覺安全。人文地理學強調人們對自然、對世界的感悟能力,各種感受的綜合就形成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邁克爾對于園林的依賴就是這種地方感的體現。開普敦帶給邁克爾的只有痛苦,于是當生病的母親向他描繪逃離城市返回鄉下的計劃時,鄉村生活瞬間如荷蘭風景畫一般出現在邁克爾的心中:“一座刷得雪白的農舍,坐落在寬闊的草原上,農舍的煙囪冒著裊裊的炊煙”[4]9。風景在這里早已超出了視覺藝術的范疇,它是一種“頭腦和感覺的建構”[3]89,不僅承擔了療傷的功能,還成了邁克爾母子精神的烏托邦。風景給予他們慰藉并讓他們暫時擺脫現實的殘酷,也為母親死后邁克爾的一系列逃避行為埋下了伏筆。
研究者多傾向于在南非這一大的語境下對其作品進行探討[5],解讀《邁》中的風景當然也不能只停留在個人的層面上。南非素有“彩虹之國”的美名,地貌特征復雜多樣,叢林、沙灘、草原、森林、高山一應俱全,號稱“擁有全世界所有的風光”。可邁克爾在回鄉途中看到的卻是滿目瘡痍,當他進入一所被人遺忘的房子的時候,四周一片寂靜,到處野草叢生,蘋果園內“被蟲子咬過的果子遍地都是”[4]47。他隨后被警察毫無緣由地帶走,和五十多個陌生人一道被趕上了火車,經過“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光禿禿沒人照料的葡萄園”;他還被迫參與了鐵路的搶修,親眼目睹“鐵軌被從山坡上傾瀉而下的像小山一樣的巖石和紅色黏土蓋住了,塌方在山腳處形成一道寬寬的裂縫”[4]51。無論是無人打理的空置房屋,還是荒蕪凋零的蘋果園和葡萄園,或者是山崩后布滿傷痕的地表,這些風景描寫絕非閑筆。它們既呼應著邁克爾個人的沉默無語,又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南非社會的真實寫照;既是殖民歷史與動蕩現實的象征,也是種族隔離與文化創傷的空間表述。W.J.T.米切爾認為,風景不應該被僅僅當做“看的對象或閱讀的文本”,而是“社會和主體身份得以形成的過程”[6]。風景除了與地理描述有關,更應該與心理感知與文化建構聯系在一起,它形象地闡釋了居民的生產方式,反映著社會生活與人類的存在,所以邁克爾在觀看風景的同時,也在親歷并審視著南非的創傷。庫切筆下的風景沒有詩意,也沒有所謂的異國情調,但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以冷峻的筆觸勾勒出南非荒涼的地景,關注著南非的歷史與現狀。
二、 風景與權力
風景歸根結底是一種觀看之道,伯格指出:“我們‘看見’風景時,也就身入其境”,“倘若有人妨礙我們觀看它,我們就被剝奪了屬于我們的歷史”[7]。伯格點出了風景與權力之間的關聯,因此看到了什么、怎么看、什么被允許看、什么不被允許看,這些都是討論風景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時應當注意的問題。《邁》深入探討了權力對于人的壓迫與懲罰,書中沉默的風景同樣也受制于權力的規訓,是多重權力關系的表現方式。除了廢棄的農舍、果園,小說里還出現了各種以營地的形式存在的監獄和醫院。逃離了修鐵軌的人群,邁克爾在維薩基農場耕耘種植,又在山洞里穴居了一段時間,人們發現了他并把他送進了警察局,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投入監獄,最后將其關進了安置難民的營地。這個營地看上去是個“黃褐色長方形”,讓人誤以為是建筑工地,周圍全是三米高的圍欄,“上面覆蓋著一層蒺藜鐵絲網”[4]90。營地的房子由木頭和鐵皮搭建而成,室內黑暗壓抑,邁克爾只能走到營地后面的圍欄,從那里凝視空蕩蕩的草原。福柯對規訓問題有過精辟的論述,在他看來“紀律首先要從對人的空間分配入手”[8]。隨處可見的營地體現出庫切作品的南非特色,它們的建造則是權力在空間上的“分配藝術”,象征著政治、軍隊和戰爭在人身上施加的規約。邁克爾在寂靜的營地中失去了觀看風景的權利,因為眼前除了鐵絲網就是荒蕪的草原,而當地理景觀最終淪為規訓場所的時候,權力也就完成了對人類活動的控制和約束。
段義孚認為,人類在面對自然時總是喜歡把強權加在自然之上,扭曲并改造了自然的本來形態[9]。營地從地理形態來說就是權力對于自然景觀的改造,作為人為搭造的建筑,它不僅破壞了大自然的原始風貌,而且強行把人與他們所處的環境隔離開,是強權政治在地理空間上的表征。營地的出現既象征著軍隊、警察對于赤手空拳的邁克爾所實施的規訓,又突顯出了人類對于自然地貌的摧毀,二者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在《邁》中我們看到的不是生態文學中展示的現代工業對于自然環境的污染,卻領略到了權力對于自然景觀的征服和壓迫:“每隔一兩英里就會有一道圍欄”,“一根根木樁釘進地里,豎起一道道圍欄,把大地分割成一塊塊”[4]120。邁克爾不知道,到底還有沒有尚未屬于任何人的土地,即使是被人遺忘的角落和邊緣,也未必能夠逃脫權力的掌握和監控。
福柯曾說:“權力必須被當做是可流通的東西來分析,或者是以鏈條的形式來運作的東西。”[10]簡單講,權力應該被視做動詞而不是名詞。風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米切爾提出風景研究的目的在于將風景由名詞變為動詞,所以除了關心“風景是什么”或“風景意味著什么”,還要詢問“風景做了什么”。小說中的殘疾兒監護學校——休伊斯·諾雷牛斯——是另一個重要的規訓場所,各種殘疾兒童在這里按要求學習文化并參加體力勞動。庫切沒有用過多的篇幅描繪邁克爾在這所學校的經歷,除了在夢境中,它的出現都與風景有關。邁克爾在營地內備受煎熬,于是想起了穴居的山洞,還有那里“奔騰不息的溪流”[4]91,他想象自己第二次回到了休伊斯·諾雷牛斯。腦海中的風景猶如一把鑰匙,開啟了邁克爾內心緊閉的記憶之門,讓他重新回到了當年接受訓斥和懲罰的地方。邁克爾在大山中發現“山腰上漫山冒出了無數粉紅色的小小花朵”,在饑餓的驅使下吃了一捧鮮花[4]84,他也再次回想起了當年在休伊斯·諾雷牛斯的饑餓歲月,還有老師手拿戒尺在學生中巡視的場景。邁克爾后來不無感慨地想道:“我的父親就是休伊斯·諾雷牛斯學校”,就是“宿舍門上貼著的那些規定”[4]129。正是學校里的規章制度奠定并建構了邁克爾的身份,使他成為了權力規訓的產物,也只有在面對風景時他才會浮想聯翩。沉默的風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邁克爾自我的投射,因為它不僅被邁克爾“看”,而且還讓他“看見”了從前身處權力約束下的自己。
三、 風景與逃避
逃避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處事方式,可是“一個人受到壓迫的時候,或者是無法把握不確定的現實的時候,肯定會非常迫切地希望遷往他處”[11]1。逃避的對象既可以是動蕩的社會、政治環境,也可以是忍無可忍的規章制度,還可以是喧囂的城市或破敗的鄉村。《邁》從本質上講是一部關于逃避的小說,邁克爾就曾被新營地的醫務官稱為“了不起的逃跑藝術家”[4]203。城市在小說中意味著暴力和冷漠,無論在學校還是醫院,城市空間都充滿著權力的制約與監視,逃往別處才是邁克爾母子唯一的選擇。是母親首先提出逃離的計劃,至于目的地是記憶中的沃斯盧或維瑟農場,還是邁克爾到達的維薩基農場,都已不再重要。庫切作品的寓言性決定了他對人類處境、現代社會中人生存的悖論的關注。那么,風景對于邁克爾的一系列逃避行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它又在邁克爾的逃避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
趁押送搶修鐵路人群的士兵離開之際,邁克爾鉆過柵欄上的窟窿,走向了沙漠中的綠洲。他找到了母親所說的農場,再把她的骨灰灑進地坑。然后他成為了一個耕耘者,種下了南瓜、玉米和青豆。“他最大的快樂就是在日落的時候,打開水壩壁上的開關,看著那清清的水流,汩汩地沿著水渠流淌,滋潤著那干旱的土地,把它從黃褐色變成深棕色。”[4]73人類自古以來就有逃向自然的情結,久居城市的人們會情不自禁地對鄉村產生向往和親近,但如段義孚所言,“人們逃往的自然必定已經被人文化了,且被賦予了人類的價值觀,因為這種自然是人類愿望的目標所在”[11]21。逃向風景就是邁克爾躲避城市、戰亂的動力,風景以想象的方式成為了他精神世界的庇護所。邁克爾曾有機會接觸母親的雇主被水浸過的書籍,他從不喜歡書籍,卻花時間從插圖書籍上撕下了一些風景照片,它們攝于愛奧尼亞群島、西班牙、芬蘭和巴厘島等旅游勝地。南非動蕩的現實剝奪了邁克爾親歷現場觀看這些風景的權利,但并不妨礙它們以想象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內心。邁克爾羸弱的身體無法與強大的戰爭機器和權力話語抗衡,對美麗風景的渴望驅使他選擇了保持沉默和一次次逃避,回歸最原始本真的自我。看到農場從荒蕪走向欣欣向榮,邁克爾感到抑制不住的狂喜,是變化中的景觀讓他被壓抑的天性得以釋放,他又恢復了園丁的本色,在開墾中享受著遠離塵囂的祥和與安寧。
巴什拉首次使用了“topophilie”一詞,借以指代“場所愛好”[12],段義孚則率先將其英語化為“topophilia”(戀地情結),寬泛地定義為“所有人類與物質環境的情感紐帶”[13],以此闡釋人與地方之間難以割舍的真摯情感。巴什拉意在突出人“與自然界和情感充溢的地方之間的感情聯系所激起的詩意的幻想”,段義孚強調的則是“把個人、團體與對他們而言重要的地理環境聯系在一起的所有想象性體驗”[1]737。“戀地情結”彰顯了地理意識中的美學感知,并將其與懷舊、空想結合起來,是驅動人類環境行為和態度的力量,地方與空間也就成為了人們感受個人或集體身份的場所。在夜色的掩護之下,邁克爾伺機翻過了圍欄,又一次逃回了維薩基農場,“在水壩前他感到像在家一樣自然親切”,他告訴自己:“我要永遠住在這里,這是我母親和姥姥生活過的地方”[4]123。盡管維薩基農場很可能并非母親的出生地,“也許只是一個語言的惡作劇”[4]143,但在邁克爾心中,它早已與家園劃上了等號。他合上雙眼,在腦海中復原母親故事中當年的場景,包括“那些土坯墻和蘆葦蓋的屋頂”、“長滿刺梨的花園”以及爭搶雞食的小雞[4]144。邁克爾的“戀地情結”源于大自然賦予的壯美與風景中感知的短暫愉悅,它們讓他體驗到了一種同樣短暫卻更加強烈的歡樂。除了視覺,這種反應同樣來自觸覺和聽覺,在邁克爾感受空氣,聆聽并觸摸流水、土地時,他也想象性地建構了母親兒時生活的場所,并將其等同為自己夢想中的家園。是大自然的風景讓他一次又一次選擇了逃避,使他一邊離現實越來越遠,一邊完全沉浸在了逃避所帶來的歡愉之中。
四、 結 語
小說結尾,邁克爾在又一次逃跑后回到了熟悉的開普敦,故事在敘事層面上由此形成了一個無望的循環。邁克爾不是圣人,也不是拯救者,如果小說的情節還要繼續下去的話,它必定會重新陷入逃跑與被捕的宿命輪回,有關沉默與逃避的討論似乎也會無休止地持續進行。關于南非拯救之道的說法,其實只是個一廂情愿的臆測,而拯救神話的破滅恰好證明了對抗權力的必然失敗。逃避的最終結果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為本身以及由此產生的意義。《邁》繼承了笛福以來的小說傳統,也蘊涵著卡夫卡、貝克特式的荒誕與晦澀。小說中的風景是無法被簡單視為背景或陪襯的,它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邁克爾的另一個自我,因為“戀地的本質是戀自我”[14]。人文地理學為解讀庫切筆下的自然世界提供了新的視角,它能與生態批評互為參照、相得益彰,而對于庫切小說中風景的研究也將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參考文獻:
[1] 約翰斯頓 R J. 人文地理學詞典[M]. 柴彥威,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
[2] Mitchell W J T.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Landscape and Power: Space, Place and Landscape[M]∥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ⅷ.
[3] Tuan Y F. Thought and Landscape: The Eye and the Mind's Eye[M]∥Meining D W.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4] 庫切 J M. 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M]. 鄒海侖,譯. 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04.
[5] 段楓. 庫切研究的走向及展望[J]. 外國文學評論, 2007(4):139-145.
[6] Mitchell W J T. Introduction[M]∥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1.
[7] 約翰·伯格. 觀看之道[M]. 戴行鉞,譯.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7:5.
[8] 米歇爾·福柯. 規訓與懲罰[M]. 劉北成,楊遠嬰,譯. 北京:三聯書店, 2003:160.
[9] 段義孚. 人文地理學之我見[J]. 地理科學進展, 2006(2):1-7.
[10] Foucault M. Two Lectures[M]∥Gordon C.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Harvester, 1980:98.
[11] 段義孚. 逃避主義[M]. 周尚意,張春梅,譯.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12] 加斯東·巴什拉. 空間的詩學[M]. 張逸婧,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9:23.
[13] Tuan Y 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93.
[14] 唐曉峰. 還地理學一份人情[J]. 讀書, 2002(11):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