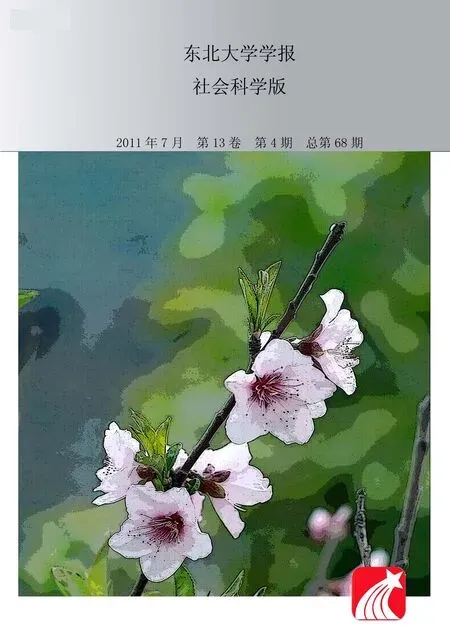“道”與“實踐智慧”:技術發展模式的比較
王 前,朱 勤
(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遼寧大連 116024)
近年來,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重新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現代技術應用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人們事先預料不到的后果,蘊涵很大的技術風險。可是,在對技術應用后果沒有足夠把握的時候,簡單地用已有的道德規范約束技術活動,也會限制技術的正常發展。所以現在一些學者提出要回歸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運用“權益倫理”來評價技術發展,實際上是希望根據不同階段技術發展的情況不斷進行反饋和調整。中國傳統哲學的“道”與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有某些共同之處,同時也有根本差別。中國傳統哲學對“道”和“技”關系的理解,能夠為控制技術應用的社會后果提供新的思路。對“道”與“實踐智慧”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國和西方技術發展的不同模式,對處理當代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也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比較哲學視野下的“道”與“實踐智慧”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道”是一個深奧的很難把握的范疇。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內涵用言語很難說清楚,只能靠直觀體驗加以理解。“道”被視為萬物的本原,但這不是從邏輯的或發生論的意義上理解的,而是從實踐的或過程論的意義上理解的。“道”的最初含義是“道路”,引申為途徑、方法。作為哲學范疇的抽象的“道”,指的是事物演變過程中符合其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優的途徑,它的衡量標準是相關各種要素之間的和諧。自然界的“物競天擇”會使事物的演變趨于合理的、最優的途徑,如物體下落的最速降線、蜂房的最佳形狀、獅子捕食的最優路徑等等,這是自然之“道”。人類社會中的各種實踐活動也會由于競爭和選擇而趨于合理的、最優的途徑,如技術操作的最優程序、協調人際關系的最合理尺度、審美的最佳標準等等,這是社會之“道”。“道”是客觀存在的,但可以通過直觀體驗的過程加以領悟。在體驗的過程中,“道”就轉化為智慧和方法。中國傳統哲學中有一套直觀體驗的認知模式,其中某些范疇難以在西方哲學中找到完全對應的范疇,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方思想界對“道”及其他相關范疇的理解。
“道”與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有某些共同之處。“實踐智慧”強調的是在具體情境中把握德性的能力。德性是“中道”,是適度的理性選擇,既非不足,也不過分,這不能以規則或傳統的節律來表達,只能通過實踐智慧來達到[1]。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道”的追求也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強調適可而止,過猶不及。儒家學說主張“中庸之道”,道家學說強調“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管子學派認為“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都是主張選擇“中道”。對“中道”的選擇是一種美德,須要從具體情形出發靈活加以掌握,體現為一種智慧,這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也是一致的。正因為這樣,有些學者認為儒家的“中庸之道”與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其實是一回事。
然而,“道”與“實踐智慧”還是有一些根本區別的,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其一,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道”是一個知情意相貫通的范疇,而“實踐智慧”是一種理性選擇,與“情”“意”關系不大。
在中國傳統思維方式里,“知”涉及理性的認知活動,“情”涉及認識和實踐活動中的心態,“意”涉及對認識和實踐活動本質特征的體驗。三者相互貫通,相互支持。就儒家的“中庸之道”而言,“中”是靠認知和智慧來把握的,涉及一個人的智商;而“庸”是靠恒心和意志來把握的,涉及一個人的情商。“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僅僅找到“中道”是不夠的,還要堅持下去,持之以恒,守住“中道”不動搖,這才是“中庸之道”。一個人如果智商高而情商低,很可能找到“中道”卻走不到頭,即使有實踐智慧卻未必成功。
知情意相貫通的“意”并非意志或意愿,而是對言語不能充分表達的事物本質特征的體驗,即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無過無不及”是從理性角度的要求,但“無過無不及”的具體分寸要靠“意”的把握,要“心中有數”。實踐中的智慧是“意”的外化,來自“意”又復歸于“意”,知情意相貫通才能保證實踐中的智慧源源不斷產生和發展。
其二,“道”是客觀存在的,是事物演變過程中符合其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優的途徑,而“實踐智慧”主要體現為認識主體的機智,包含權宜之計的成分。
人們在實踐活動中是否領悟了“道”,是可以有客觀標準的,這就是看其采取的途徑、程序、方法是否達到合理的、最優的要求。“合理”的要求注重實踐主體、工具和對象等相關要素之間的和諧。“最優”的要求是從實踐活動的社會價值和效益著眼,注重實踐主體的需求和感受。合理的途徑和方法決定了最優的效果,而對最優目標的追求引導了對合理途徑和方法的不斷揭示。
相比而言,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包含較多的主觀成分,須要根據具體情形隨時加以調整,很難趨向于一個客觀的目標。一個時期的“實踐智慧”與下一個時期的“實踐智慧”之間,并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系,也未必有事實上的承繼關系。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已經看到了理性思維未必能解決實踐中的所有問題,須要用“實踐智慧”加以補充,但在邏輯思維的框架里,對“實踐智慧”很難作更深入的研究。
其三,“道”雖不可言說,但可以領悟,整個領悟過程是有規律可循的。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有損,以至于無為。”要想“悟道”,必須通過親身實踐,了解合理的、最優的途徑和方法如何體現,這樣才能使人為設定的途徑和方法逐漸順應自然,近于“道”,合于“道”。老子多次論及“有為”與“無為”的關系,“有為”說的是人為設定的途徑和方法,“無為”即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途徑和方法。能夠用言語講出來的“道”,實際上是用來指導“有為”向“無為”轉化的。它們本身并不是真正的“道”,而是求“道”的入門向導,其中的章法、程式、規則等等是“有為”階段的訓練要點,一旦達到運用自如時就完全可以忘卻。真正的“道”是體現在實際操作活動之中無形的東西,是“無為”即不刻意而為的狀態,即海德格爾所說的“上手”狀態。人為的技術活動通常很難達到這種狀態,但可以通過悉心體悟逐漸接近這種狀態。從“有為”向“無為”的轉化,意味著使人的知識、能力以及生理心理活動過程逐漸適應對象事物的自然本性,逐步達到“道”的境界。“為學”是知識的積累,所以日益增長。“為道”是向“道”的不斷趨近,所以差別日益縮小,以至于沒有差別,這就是“無為”。
有人將“無為”理解為“無所作為”,這是不確切的。“無為”意味著知識和智慧的存在由顯性形態轉化為隱性形態。現代心理學對隱性認知活動和隱性知識產生過程的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注]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內隱認知和意會知識的產生源于心理資源的分配策略。隨著練習的深入,操作逐漸趨于自動化,動用的心理資源越來越少。自動化過程是建立和運行程序的過程,這里包括模式識別的程序和動作——次序程序。這些程序或能力可以促進知覺——運動技巧、認知技巧、啟動效應等——認知操作的進行,它的啟動和運行一般不能被意識覺察,也不能通過語言表達。[2]。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在一定程度上涉及這種轉化過程,但對領悟過程沒有專門的說明。“實踐智慧”主要還是在理性選擇或者說顯性的層次上起作用的。
總的說來,“道”涉及邏輯思維框架之外的認知活動,而“實踐智慧”是從邏輯思維出發的理性選擇。如果從邏輯思維的必要補充角度考慮,“道”應該比“實踐智慧”更有啟發意義和實際價值。
二、“道”與“實踐智慧”對技術發展模式的影響
“道”與“實踐智慧”的差別,對中國和西方的技術發展模式有深刻的影響。
根據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的研究,中國古代技術在公元1世紀到14世紀保持了一個相當發達的水平,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技術發明,包括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道”對技術發展的影響。
“道”對技術發展的引導并不是提供任何具體的技術手段和方法,而是引導人們如何去了解和把握合理的、最優的途徑和方法。老子講“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這里講的是善于利用自然界的動因和能力,因勢利導,在人們難以覺察的狀態下引發有為的活動。老子認為“相反相成”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當“相反相成”的結果對人們有益的時候,就要力促其“反”。然而當“相反相成”的結果對人們不利的時候,就要避免事物向極端方向發展,這就要“守中”、“知常”、“知足”、“知和”。總之,要利用“相反相成”的趨勢,留出事物的發展空間和“自化”的余地,使自然事物的變化逐漸趨向人們預期的目的。老子還對如何達到優化效果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見解。在他看來,“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3]326,當然是得“道”而行的理想狀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從細微處著手也是一種優化,那就是“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3]301。“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3]298保證優化選擇的根本是遵循事物自然的本性,從細微處入手,以較小的代價控制事物沿著“正道”發展,避免誤入歧途。這些論述有助于人們了解和把握合理的、最優的途徑和方法。
“道”對技術發展的引導,還體現為提供某些結構功能模式,以獲得合理的、最優的途徑和方法,這在技術發明和應用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中國古代醫學、農學、工程技術等許多領域都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思想基礎,這是其突出的文化特征。陰陽五行學說是可用言語表述的知識,它并不等同于“道”,而是用于揭示和把握“道”的思維工具。陰陽五行學說有助于制定技術活動的具體程序,并使之不斷趨向“道”所顯示的理想境界。陰陽互滲互補、相反相成的觀念,有助于防止技術活動程序失控而誤入歧途。而五行相生相克的觀念,有助于建立諸要素的制衡和協調關系,并使各種程序化知識在結構上相互借鑒和啟發。至今流傳下來的一些有價值的技術發明和知識成果,如“魚洗”、透光銅鏡、被中香爐等等,融動靜、曲直、剛柔、明暗、虛實等對立因素為一體,相反相成,變化多端,充滿靈性和智慧,正是“道”對“技”引導的產物。
這里以“魚洗”為例作一點討論。魚洗是一個外緣帶有對稱手柄的青銅水盆,盆底部鑄有四條“魚”。以手來回摩擦銅盆的手柄,達到一定程度時,盆內四條“魚”口中各噴出一道水流,伴有嗡嗡的響聲,水面上形成各種浪花。這種狀況造成的噴涌可在水面上形成水柱,非常壯觀。“魚洗”的原理是利用摩擦手柄產生的振動,使盆中的水形成駐波。這須要掌握相當精密的鑄造技術,才能夠根據“魚洗”的振動方式確定其形狀、尺寸、水的容量以及盆內四條“魚”的位置。中國古代工匠顯然不具備現代振動理論的有關知識,但制作者可能在生產或生活實踐中發現了駐波造成的神奇現象,然后巧加利用,使這種現象通過特殊制成的容器和特定操作方法,得到藝術化的再現。美國學者坦普爾從“魚洗”中體會到,駐波是體現中國古代“中庸”概念或“法道”概念的絕妙模式。駐波造成的神奇現象來自“魚洗”自身的振動,并沒有從外界添加某些特殊物質。這說明“萬物來自道又返還于道,就像魚洗中的駐波那樣”[4]。
“道”對技術發展在思想方法上的引導,帶來了許多積極的成果。由于關注技術操作的途徑和方法,追求合理的、最優的狀態,自然導致對各種設計、組合、變換進行大膽嘗試。中醫藥方劑、籌算規則、煉丹程序等等都是沿著這條思路逐漸摸索出來的。不過,在中國古代技術發展中,“道”對技術發展的引導是在科學理論不發達的情況下,直接在體悟層面上起作用的,因而往往抑制了學理性研究。大量的程序化知識成果在實用目的引導下發展,很少有人關注其原因和一般原理。這使得中國古代技術在直觀體驗的模式里相當發達,但始終不夠精細、嚴謹,缺乏超越感官局限性的能力,這是造成近代科學技術未能在中國產生的重要思想因素。
亞里士多德提出“實踐智慧”的年代與中國先秦思想家提出“道”這個范疇的年代相距不遠。“實踐智慧”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技術發展,很難從歷史文獻中得到確切答案。在古希臘,同哲人和政治家相比,工匠的地位是低下的,技藝的價值遠遠不如純理論的價值。“實踐智慧”主要用于從德行角度解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與工匠的技術活動關系不大。在古希臘文學作品中,并未出現“庖丁解牛”、“輪扁斫輪”之類的寓言故事,社會的上層人物對技藝是不屑一顧的。
在中世紀,亞里士多德的定性研究方式和邏輯學得到推崇,而靈活多變的“實踐智慧”卻很難在基督教統治的社會氛圍中發揮作用。宗教神學的邏輯闡釋,為建立確定的社會結構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發展空間。中世紀早期對技術活動及其社會后果持謹慎甚至是懷疑的態度,理性導致對經驗的囚禁,技術被判定為不能在與自然的競爭中獲勝。文藝復興運動之后,新教倫理主張征服自然為人類造福的信念,技術成為征服自然的主要手段。在市場經濟驅動下,技術的發展遵循“更大、更快、更高效”的準則,不斷開拓新的發展空間,用新的技術解決原有技術帶來的社會問題。當科學技術發展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因素時,科學理論的邏輯發展和技術體系的自身建構都并非必須接受“實踐智慧”的引導。這種狀況直到現代技術發展后果的不確定性和消極影響成為顯著的社會問題時,才得到根本扭轉。近代技術產生以來對生態環境、能源、社會倫理等方面的消極影響,有些是積累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階段才顯現出來的。至少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技術發展狀況的評價與“實踐智慧”關系不大。這使得征服自然的勢頭一發而不可收,直到出現比較嚴重的問題時才想起“剎車”。應該說,技術發展與“實踐智慧”的脫節,很可能是近現代技術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道”:引導技術和諧發展的一種思路
在現代技術發展過程中,“道”和“實踐智慧”可以通過不同方式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實踐智慧”立足于西方文化傳統,對于邏輯思維是非常有效的補充。而“道”的觀念則提供了控制技術發展后果的另一種思路,具有更大的啟發性。
“道”的衡量標準是相關各種要素之間關系的和諧,這里包括技術操作者、工具設備和生產對象的和諧,技術操作者身心的和諧,技術活動中人與人的和諧,技術活動與社會生活的和諧以及技術活動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等等。以“道”來引導現代技術的發展,關鍵在于從技術發明、技術設計、技術決策開始,就充分考慮到技術活動各種相關要素的和諧,及時發現和消除各種相關要素的不和諧關系,使技術活動在人類可控的范圍內合理發展。技術上能做的事情,顯然并不都是該做的事情。僅僅出于急功近利的需求而開展技術活動,全然不顧技術活動可能給人的身心健康、社會生活秩序、自然環境帶來的問題,勢必帶來越來越大的技術風險,這是一種逆“道”而行的趨勢。“實踐智慧”能夠在這種逆“道”而行的技術發展造成問題之后,及時反饋和調整;而“道”的引導作用則應該在可能造成問題之前就發揮作用,防患于未然,這是“道”與“實踐智慧”對現代技術影響方式的一個重要差別。
現代技術活動的某些后果事先難以預知,如DDT通過生物鏈“富集作用”對人類的危害、氟利昂對臭氧層的破壞等等,這些時候“實踐智慧”的運用會有明顯效果。德國技術哲學家胡必希提出“權益倫理”思想,強調保留主體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和判斷的能力,通過避免極端,保持中道,實現行為的可持續性。“權益”的具體含義指預測、預防和可修正性,有能力控制局面,并且逐漸趨向更好的解決方案[5]。英國技術哲學家大衛·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提出實現這種技術評估方式所要求的三個基本特征:可改正性、可控制性和可選擇性。可改正性指在技術發展過程中,整個技術過程由一系列技術決策環節組成,每個技術環節的決策都是容易改變的。當技術發展出現有害結果時,人們可以通過改變這些決策來達到克服技術有害結果的目的。可控制性是指當技術的有害結果在系統中得到反饋后,人們可以通過控制技術系統來消除技術的有害結果。可選擇性是指在具體環節的技術決策中會有多種決策可供選擇,人們應當擁有選擇權。當技術的有害結果出現時,可以通過選擇不同決策來改變技術的有害結果[6]。與此類似,美國技術哲學家卡爾·米切姆倡導工程技術人員應當承擔考慮周全的義務。即當技術活動中暴露出某些弊端時,技術人員應仔細分析這些后果,考慮更多的現實因素,使工程技術設計更加周全[7]。這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都是“實踐智慧”的生動體現。
然而,以上這些解決問題的方案都帶有“試錯”的性質,在具體實行時會遇到一定問題。對于現代技術有害后果的判斷是“后驗”的,而原初的技術選擇和嘗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各行其是。很難設想技術人員在技術活動開始前都進行周全的考慮,在技術設計時都作出可改正、可控制和可選擇的安排。如果有的技術人員異想天開,專門從事別出心裁的發明或嘗試,比如生殖性克隆人、通過基因增強技術制造“超人”、將不同物種的胚胎隨意融合、制造具有進攻性的納米機器人等等,在其他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很可能會造成不可逆的惡果,而“實踐智慧”對此可能起不到約束作用。況且技術活動進行的速度很可能不容許有足夠的時間進行評估和反饋,這樣就很難及時發現和消除技術活動的消極后果。
如果從“道”對現代技術活動的引導角度思考,應該在技術活動開端之處就施加影響,通過技術評估揭示技術活動可能存在的種種不和諧因素。比如,按照“道法自然”的理念,任何技術產品都應來自自然,又和諧地回歸自然。可是現代大多數技術工作者在“造物”時只想著如何使產品有新的功能,如何結實耐用,不易分解,極少考慮這些產品一旦變成廢物時如何處理,如何消解,結果造成“三廢”,導致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又如,按照技術活動中人與人和諧的理念,技術產品應該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應該使操作者運用自如,安全可靠,可是現在技術設計中商業化需求仍然發揮主導作用,商家的功利需求時常造成對生產者和消費者切身利益的漠視。即使在大眾普遍需求的計算機應用領域,大多數便捷的程序也往往服務于商業性較強的具有刺激人們感官和好奇心的內容,由此造成眾多網迷、網戀,而許多專業化較強的程序仍很難為大眾掌握。大多數私人電腦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開發,并未成為人們運用自如的工具。再如,“道”所設定的合理的、最優的技術路徑,是在全面考慮技術活動各種相關要素的和諧關系之后確定的,需要開闊的視野和高度的責任意識,而現在相當多的技術設計只考慮局部的、短期的、可以預測效益和效率的目標。盡管技術工作者的責任倫理問題得到社會上的普遍重視,但對責任的理解和認定仍然是關注局部的。“實踐智慧”能夠在解決局部問題上有效發揮作用,但“實踐智慧”的思維模式很難處理現代技術帶來的全局性甚至是全球化的問題。如果使技術活動從一開始就接受“道”的引導,從技術發明、技術設計、技術決策角度避免偏離“道”的傾向,這類問題的影響就會大大緩解。“道”與“實踐智慧”應該相互補充,相互配合,這樣才有助于更好地協調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關系。
要發揮“道”對現代技術活動的引導作用,須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道”對現代技術活動的引導需要理性的選擇,也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后者是直觀體驗的產物。了解技術活動自身性質和影響社會的途徑,需要理性的思考;而要確定各種技術要素和諧關系的分寸,則須要在不斷體悟過程中進行調整,才能逐漸達到合理的、最優的要求。所謂“中道”、“適度”、“可控制”,都不是靠嚴格的理性分析能完全規定的,豐富的經驗和敏銳的直覺可能在這里發揮重要的作用。
其二,“道”對現代技術活動的引導需要理性選擇與德行修養的有機結合。知情意相貫通的認知模式,有助于培養技術活動中的道德良知,使倫理意識對技術的影響滲透到技術人員的日常行為之中。現在許多技術人員和理工科學生往往只關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活動的經濟效益,不大了解技術活動對社會、環境和公眾切身利益的影響。因此,應當注重開展“道”與現代技術關系的教育,使技術人員了解所從事專業對社會、環境、公眾影響的具體途徑,意識到自身的社會責任。當發現某種技術活動可能損害公眾以及社會利益時,能夠勇于披露真相,使公眾知情。這種教育還應當給技術人員提供實施道德行為的相應策略,尋求必要的社會保護,這本身也是“實踐智慧”的組成部分。中國傳統哲學強調“知行合一”,其核心就是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的統一。只有當技術人員成功消除或規避了偏離“道”的種種傾向,才實現了現代技術活動沿“道”而行的根本目標。
其三,“道”對現代技術活動的引導,還應該使道德層面的“實踐智慧”與技術層面的運作智慧融為一體,這是由“道”的本性所決定的,對德行的追求和對技術完美的追求應該是一致的。技術運作的智慧和產品的完美,正是對事物自然本性充分重視的結果。違背事物自然本性的技術活動最終會以種種方式和途徑傷害到自己或他人。人為縮短技術活動應有的自然的程序,必然會出現“逆道而行”的不正常局面。“道”強調技術活動的合理與最優,“道”所引導的現代技術應該全方位展現這種要求。這樣的技術成果應該是耐琢磨的、有韻味的、滲透靈性的,而不應該是呆板的、單調乏味的。技術應用要注意體現穩妥適中的要求,不顧此失彼,不急功近利,不浮躁盲從。既考慮到當前的需要,又有長久的設計。兼顧生產、經營、消費、環境種種考慮,融合為適度的最佳選擇。這對于人類更合理、更有效地把握和控制技術發展的未來方向,顯然是極為必要的。
參考文獻:
[1] 唐熱風.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的德性與實踐智慧[J]. 哲學研究, 2005(5):70-79.
[2] 劉景釗. 內隱認知與意會知識的深層機制[J]. 自然辯證法研究, 1999,15(6):11-14.
[3] 老子[M]. 陳鼓應,注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6.
[4] 羅伯特·G.坦普爾. 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M]. 南昌:21世紀出版社, 1995:73.
[5] 李文潮,劉則淵. 德國技術哲學研究[M]. 沈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224-231.
[6] 馮軍. 論克服現代技術的內在過程——評克林利德克服技術思想[J]. 自然辯證法研究, 2005,21(4):45-48.
[7] Mitcham C. 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 Hennebach Lectures and Papers(1995—1996)[M]. Golden: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Press, 1997:123-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