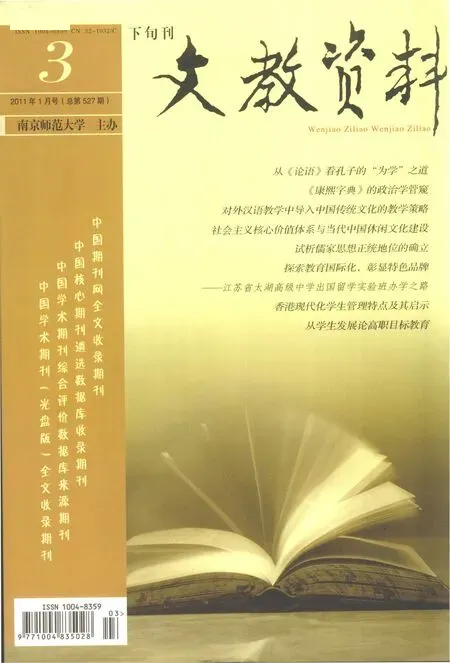蘇軾與文人畫淺論
陳 佳
關(guān)于文人畫的定義,陳師曾在《文人畫之價值》一文中提出:“何謂文人畫?即畫中帶有文人之性質(zhì),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畫中考究藝術(shù)上之功夫,必須于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此所謂文人畫。”又說:“文人畫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xué)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這里面不僅提出了文人畫所應(yīng)具備的條件,即應(yīng)具有濃厚人文價值,而且把畫家的人品和才情提高到了先于技術(shù)之上的地位,著重突出以人和人的文化修養(yǎng)為先的人文精神。被稱為文人畫的畫,已經(jīng)不單純是藝術(shù)品,而是畫家個人修養(yǎng)品德的承載體,而文人畫繪畫的過程,也被認(rèn)作為畫者情感心緒的表露,更多的成了文人雅士的心靈事業(yè)。縱觀文人畫的發(fā)展歷程,蘇軾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以其自身的文化修養(yǎng)和社會地位,給當(dāng)時及后世以深遠(yuǎn)的影響。
一、文人思想對文人畫產(chǎn)生及發(fā)展的影響
文人參與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可以說是源遠(yuǎn)流長的,從東漢時期天文學(xué)家張衡、東漢末蔡邕,到東晉之后南北朝時期的王微、宗炳、謝赫、梁元帝,再到唐代,文人畫畫得就更多了。由此可見,中國繪畫的文人化、文學(xué)化傾向早就暗含在它的基因中了。儒家的畫論講究讀書,其用處為:汰俗、養(yǎng)性、明理。反映到文人畫上比較明顯的應(yīng)該是文人畫對于“品格”的追求。而老子的“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知其白,守其黑”等觀念,對后世注重氣韻和表現(xiàn)文人畫的內(nèi)涵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到了魏晉,玄學(xué)日盛,“魏晉風(fēng)韻”漸漸成為了后世文人畫的一個重要精神源頭。而唐代的大詩人王維則對文人畫的精神導(dǎo)向起到更為直接的作用。所以當(dāng)歷史進(jìn)入藝術(shù)極其繁榮的宋代,文人思想與繪畫藝術(shù)的結(jié)合更為廣泛和親密。
二、蘇軾倡導(dǎo)文人畫的原因
蘇軾早年喜愛的是“大江東去,浪淘盡”的豪放風(fēng)格,所作詩文意氣風(fēng)發(fā),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的歷練,晚年則對含蓄入微的淡雅之氣極為推崇。究其原因,是與其個人經(jīng)歷分不開的。他早年的政治態(tài)度偏于保守,曾上奏神宗,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在新舊黨爭之中,蘇軾屢遭打擊而被貶,先后至杭州、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又因詩文中之言,被捕下獄。哲宗復(fù)朝,他官至翰林學(xué)士,但后來又被貶到惠州,再貶到瓊州 (今海南島)。宋徽宗即位后,蘇軾遇赦北還,但死于途中。由于思想上受儒家和莊子的影響,以及宦途的得失遭遇、生活的顛沛流離,蘇軾產(chǎn)生了許多矛盾的想法,形成了一種憂民傷時、曠達(dá)頹放的復(fù)雜性格。蘇軾詩畫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消沉自適思想、灑脫傲放風(fēng)格,與他一生升降榮辱的境遇,都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正如他自題《偃松圖》所言:“怪怪奇奇,蓋是描寫胸中磊落不平之氣,以玩世者也。”借枯木頑石寄情遣興,寫出胸中逸氣,傲于人間,這便是蘇軾繪畫創(chuàng)作求“象外”之意的真諦。
三、蘇軾對文人畫發(fā)展的貢獻(xiàn)
1.拓展了文人畫的影響力
蘇軾作為文士和詩人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有深厚的藝術(shù)修養(yǎng),而且與當(dāng)時的知名畫家文同、人物畫家李公麟、山水畫大師王詵交往甚密,同時也參與文人畫的創(chuàng)作,這些條件都讓他能以一種更全面、更廣闊的視野認(rèn)識繪畫,而且他不同于普通技藝者的理解力和學(xué)識讓他更有能力表達(dá)自己的創(chuàng)作思想,渠道更為寬泛,受眾也更為眾多。在他的詩文題跋中對于繪畫的各種見解比比皆是,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廣了其繪畫思想。
2.為文人畫找尋理論基礎(chǔ)
蘇軾倡導(dǎo)文人畫,最廣為人知的是其對王維的推崇,在其多處詩詞中均大加贊揚(yáng),例如:“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坐詠皆自見,飄然不作世俗辭……”但是,通過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王維的繪畫技巧與理論對文人畫的發(fā)展究竟產(chǎn)生了多大作用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因?yàn)橥蹙S的畫跡在唐代都不多見,宋代以后流傳的大都是后人的摹本或偽托之作。即使有真跡傳世也不會很多,更無法系統(tǒng)總結(jié)出其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所以蘇軾的極力推崇,更多的應(yīng)該是為自己的這種理論尋找歷史的先例和現(xiàn)實(shí)的證據(jù),就像蘇軾推崇文同,也是把文同看作贊同他的文人畫理論與實(shí)踐的同道者,是在擴(kuò)大他的藝術(shù)主張的影響,以使后人看到繪畫作為一種個人情感流露的藝術(shù)方式,與詩、文具有相同的功能,統(tǒng)一于士大夫知識分子的身上。蘇軾努力使人們相信,這不但有唐代王維作為先例,現(xiàn)在的人也可以如此,文同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jù)嗎?
3.強(qiáng)調(diào)繪畫的思想性
蘇軾把詩歌和繪畫都看作是一種抒發(fā)個人情感的藝術(shù),這樣便將繪畫藝術(shù)提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來看待,從一種完全是技術(shù)性的工作中解脫出來,成為文人們的一種自覺的表達(dá)手段。他認(rèn)為,繪畫作為藝術(shù),應(yīng)當(dāng)是與作為藝術(shù)的詩有著相似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相似的欣賞原則,當(dāng)然也就應(yīng)當(dāng)有相同的地位。“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這樣,便使唐代閻立本這種工匠的技藝一躍而與在士大夫的傳統(tǒng)藝術(shù)中占有最高地位的詩歌創(chuàng)作平起平坐了。正是這種對意氣的推崇,所以他對文同等文人畫家十分欣賞,他說:“故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如兔起鶻落,稍縱即逝矣。”從元代倪云林的“墨池挹涓滴,寓我無邊春”的山水,到明代徐青藤“半生落魄已成翁,獨(dú)立蕭齋嘯晚風(fēng)。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的墨葡萄,再到清代鄭板橋“一枝一葉總關(guān)情”的竹子,無不受到蘇軾的這種影響。
4.引書法入繪畫
將書法帶入繪畫,意味著將有“筆墨”這樣一個詞來評價文人畫技巧。而漸漸發(fā)展到后來,“筆墨”逐漸成為文人畫傳統(tǒng)中最重要的技法標(biāo)志,以至于一個畫家的作品是否有“筆墨”,成為他是否已經(jīng)掌握了文人畫技法的標(biāo)尺。這種作法經(jīng)米蒂、楊補(bǔ)之等人的發(fā)展,到了元代,柯九思認(rèn)為畫竹“凡踢枝當(dāng)用行書法為之”,而趙孟頫則明白提出“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yīng)八法通”。這種傳統(tǒng)發(fā)展到明、清兩代的文人畫家,就變成鑒定一幅畫藝術(shù)水準(zhǔn)的高下,重要的標(biāo)準(zhǔn)便是看其有沒有“筆墨趣味”,因而后來的文人畫家們紛紛稱自己的畫作是“寫”出來而非畫出來的。所以,蘇軾正是把這種理念帶入繪畫中,使得文人畫具有其他畫種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
5.把握了繪畫發(fā)展的時代脈搏
沈顥在《畫麈》中寫道:“古來豪杰不得志之時,則漁耶樵耶,隱而不出。士人不得志,就往往寄情于書畫或琴酒以度時日。”蘇軾所推崇的這種文人畫形式,則十分符合文人這種遁世自娛的心理,以畫寄托思想成為風(fēng)尚,從而給后代的繪畫帶來了以文人畫為主流的重要轉(zhuǎn)折。宋亡元興,蒙古貴族廢除科舉制度,又將百姓分為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南人最賤,從而造成江南文人“學(xué)而優(yōu)則仕”夢想的破滅,曾在宋代十分活躍的職業(yè)畫家活動趨于沉寂,加上元代后期政治腐敗,各種矛盾錯綜尖銳,眾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厭世和逃世心理,轉(zhuǎn)而將繪畫作為個人精神上自我調(diào)節(jié)的手段,這更使得蘇軾的“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理論廣泛被接受。
由于蘇軾的努力提倡,在北宋初年興起的這種新畫風(fēng)很快在士大夫中流行開來。北宋中葉以后,繪畫史上出現(xiàn)了一大批文人畫家,如王詵、李公麟等,而他們幾乎都與蘇軾有一定的關(guān)系,這或許并非是歷史的偶然。
[1]舒士俊.水墨的詩情——從傳統(tǒng)文人畫到現(xiàn)代水墨畫.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8,12,(1).
[2]徐書城.中國繪畫斷代史叢書——宋代繪畫史.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0.
[3]云告.宋人畫評.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12,(1).
[4]邵力華.永遠(yuǎn)的水墨.朝華出版社,2004.
[5]周雨.文人畫的審美品格.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6.
[6]萬新華.元代四大家文人畫的重要里程碑.遼寧美術(shù)出版社,2003.
[7]顏中其.蘇軾論文藝.北京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