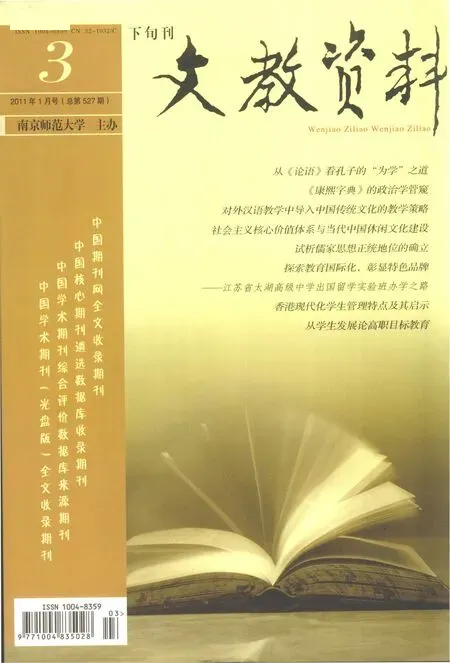從敘事人稱分析小說《河岸》
張曉利
(山西師范大學,山西 臨汾 041000)
蘇童的《河岸》發表于《收獲》2009年第2期,這是繼《碧奴》后,蘇童的又一部長篇小說。在這篇小說中蘇童采用第一人稱敘述,賦予了“我”(庫東亮)全知全能的視角,敘述“我”目睹了那個荒唐年代的所有悲喜劇,洞察了所有人細微的心理活動。
“一切都與我父親有關”,暗示了小說的起點,在將“我”劃進故事的同時,也劃到了旁觀者的席位。讀者透過“我”(庫東亮)的雙眼,看到了家庭、親情發生了極大變化。敘述者“我”帶領讀者一次次穿梭于油坊鎮的大街小巷,從綜合大樓、菜場、土地糧油加工站到學校、棉花倉庫、煤山,再到金雀河上向陽船隊七號船,甚至包括電線桿、郵箱,故事總是在不斷變換地點的同時又一次次展開敘述。
由于受到第一人稱視角的限制,“我”對于歷史的敘述不免有些曖昧和含混不清,在整部作品中歷史始終是個“謎”。第一人稱的敘述決定了敘述成為了限制性敘述,并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不像第三人稱全知性視角敘述那樣客觀和中肯。
第一人稱的限制性的敘述視角決定了“我”對于歷史的追憶憑借的只能是想象,這也決定了“我”視野的局限性,形成了對于歷史理解的多種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導致了人的身份認同危機。
比如對于誰是鄧少香遺孤的問題,就有多種說法,開始認為是“我”的父親喬文軒,后來傻子扁金又來爭奪這一殊榮,再后來又有人說是中學的蔣老師,可是最終那個專門研究革命歷史的青年干部卻指出,鄧少香根本沒有結婚,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遺孤,這就使所有人的競爭都成了一場鬧劇,或者說,這根本不屬于真實的歷史,而只是人們的流言,這樣的流言在沒有歷史見證人的前提下,獲得了理所當然的合法性,它成為了賦予人權力與尊嚴,抑或是殺死權力與尊嚴的語碼,人們在它的轄制下,身份變得含混不清,命運變得沉浮不定。
再比如,鄧少香的身世也同樣鍍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據文具店的老尹說,鄧少香根本不是鳳凰鎮棺材鋪老板的女兒,她只是被人領養的一個孤兒,所以她的故鄉根本不是鳳凰鎮,籍貫也只能待考。老尹的表述,讓“我”感到很迷惘,而且使“我”產生了一個幻覺:
我想象著鄧少香的兒童時代,依稀看見一個滿面灰塵的小女孩,衣衫襤褸,頭發像一蓬亂草,她光著腳在年代久遠的油坊鎮碼頭上奔跑,嘴里叫喊著媽媽。我看不清小女孩塵土遮蓋的面孔……我看見她躺在鳳凰鎮棺材鋪的一口棺材里,淚痕未干,目光已經流轉,她好奇地打量棺材外面的世界,一邊向我招手,進來,進來,你快進來呀!我不知道那棺材里的小女孩究竟是誰……[1]
因為第一人稱限制性敘述角度,使得“我”憑借想象,只能是憑借想象來塑造那段歷史,來塑造鄧少香這一人物形象,并且想通過慧仙這一樣板來看清鄧少香的真實面目,可是無論“我”怎樣努力,“我”的視線終究是模糊的,“我”根本無法辨清哪個是慧仙,哪個是鄧少香。
文本采用這樣的敘述方式傳達出這樣一個信息:這樣的困惑不僅僅是屬于“我”,同樣也屬于父親喬文軒和那一時期的整整一代人。向人們展示了歷史就像一個萬能的主宰者,神秘兮兮,把人類玩弄于股掌之中,同時它又給人類設置了一個個謎局,在這樣的謎局中,人類找不到自我,只能像一葉浮萍,漸漸地淡出歷史的塵煙暮靄,而人類終究無法揭開歷史的神秘面紗,使得文本極富于戲劇性。
另外,文本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使得敘述人“我”與父親的角色聯系更為緊密、自然。而且,第一人稱的敘述角度使得敘述人“我”表現出了對每個個體的成長過程的在乎。主人公對往事的回顧是富有戲劇性的回顧。《河岸》把視線聚焦在一個叫油坊鎮的地方,講述的一個“時刻不忘階級斗爭”的荒唐年代的人的疼痛的記憶。這樣的記憶由“我”的父親(喬文軒)和“我”這一中心敘述人來展現。但主要還是通過敘述者“我”的記憶來展現。在第一人稱“我”的視角下,一個身份因為“魚形胎記”而受到變異的父親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父親原是油坊鎮的黨委書記,因屁股上的神秘“魚形胎記”,被指認為是革命烈士鄧少香的遺孤,備受人們的尊敬。但是神秘工作組的到來,卻否定了父親是“遺孤”的說法,使父親不僅失去了權威性的地位,而且之前那些猥褻的事件,也在母親(喬麗敏)的審問下水落石出。從此,父親變得膽怯、懦弱,他對現實采取了逃避的態度,倉皇地離開了陸地,逃亡到船上。但是他并沒有因此而安全地逃逸,趙春美的出現和辱罵,迫使父親閹割了自己,以向世人贖罪。這樣一種自虐式的殘忍方法,使父親暫時獲得了內心的平靜,但也因此喪失了正常的人性。在世人的眼中,父親是一個不完整的人,這種殘缺也使父親不敢面對世人,所以他在船上開始了蟄居式的生活,直到他背著鄧少香的紀念碑沉入水底。“我”洞悉了父親所有的秘密,對于父親,“我”痛恨他的怯弱,也同情他的不幸。
小說中的敘述者“我”,承傳了父親身上所有的精神因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就是父親的影子,是他生命的延續,這就使“我”和父親的心靈必然是息息相通的,文中多次模糊了“我”和父親的界限,最為明顯的一處是我打水的一次經歷:“那天下午的金雀河躁動不安,我起身拿了吊桶去河里吊水,吊桶投進河里,收集起一片河水的秘語,河水在吊桶里說,下來,下來。我在灶上支鍋燒水,河水煮開了依舊不依不饒,河水的秘語在鐵鍋里沸騰,下來,下來,下來。我坐在船頭守著火灶,心里充滿了莫名的恐懼,我不知道河水的秘語是贈給誰的,是給我還是給我父親。”[2]
父親放浪不羈的性格在“我”的身上更是得到了明顯的傳承。母親審問父親后留下的那本神秘的日記本,成為了我性啟蒙的教科書,所以“我”很小就產生了性的萌動和欲望,而父親的監視讓我感到本能的壓抑,“我”深深地陷入了性苦悶之中。這種壓抑和苦悶,形成了“我”不健全的人性形態。文本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使得敘述人“我”與父親的角色聯系更為緊密、自然了。但文本的敘述會經常從第一人稱敘述角度跳躍到第三人稱敘述角度,進行人稱間的穿插。小說在寫到“我”在糧油加工站的宿舍里居住時,把“癩皮狗”與“母親”放在一起,以及后來的跟慧仙找母親反而碰到“我”的母親時的躲進廁所,體現出骯臟與神圣的結合,是對其母子關系的極大反諷,對我母親的依戀更多體現的是回顧性自我的感受。“回到宿舍她的臉是陰沉的,看見我無動于衷地躺在床上摳腳丫……”[3],“無動于衷”是從人物當時的行為處境出發,但他又看到了他母親的心理反應,由此證明,這里的“我”是雙重角色,即人物和敘述人,雙重自我,并且二者同時在場。在這里,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就得到了限制。小說的敘述方式兼具了敘述和回顧的雙重性質,有了第三人稱敘述的影子。
視點越界在小說中時常會看到。文本的下篇開頭明顯將視點越界推到了首位。人稱由“我”向“她”轉向。有關慧仙成長經歷的敘事效果接近于第三人稱全知性視角,因此,敘述者由“我”被迫向“她”轉向。
在下篇中“理發”這一章節中,當慧仙在理發店看到“我”但又想不起“我”的名字時,“我看見慧仙的目光投過來,余怒未消,懶懶的,很散漫的,突然雙眸一亮,她似乎認出了我,用一把梳子指著我說,是你呀,你是那個——那個什么亮嘛。她對我莞爾一笑,驚喜的表情中夾雜著困惑。我看著她絞盡腦汁回憶我名字的樣子,心里沮喪極了,怎么也沒想到,她竟然記不起我的名字了……”“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失望的表情,內疚地笑著……”。[4]在這里的“我”在敘述中是參與者與旁觀者,是兼具了敘述和回顧的雙重自我,使敘事兼有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
華萊士·馬丁在《當代敘事學》中講道:“敘述者可能會通過某些語句的時間與時態使他們的作品與現實分離,但是也有其他語句,它們缺少這些表明虛構性的標志,它們直截了當地使用話語和交流的語言。每一個不可能被定位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敘述者都創造一個包含人物的世界,對于這些人物來說,這個世界就是他們的現實。為了理解視點的功能上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擴展其意義范圍,使其不僅包括人物與敘述者的關系,而且包括人物之間的關系。每個人物都能夠像敘述者所做的那樣,提供一個透視行動的角度。
在語法人稱和進入意識被視為視點的規定性特征時,關于這一題目的傳統闡釋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區別。“‘進入意識’有兩層含意,一個第三人稱敘述者可以看進人物的內心,也可以通過其內心來看。在第一種情況中,敘述者是觀看者,人物的內心被觀看。在第二種情況中,人物是觀看者,世界被觀看;這一情況中,敘述者似乎已經把看的功能委托給人物,這就好像是一個含有‘我注意到……然后我意識到’這類措辭的第一人稱故事被以第三人稱改寫了(‘她注意到……然后她意識到’)”。[5]
《河岸》的下篇花了大量的筆墨來寫慧仙。這部分對于慧仙的成長經歷是在“我”的視點下完成的,但是“我”只能是從當下的經歷和感知來進行回顧,無法深入人物的內心。于是小說在下篇進行了視點越界,實現了從第一人稱敘述角度跳躍到第三人稱敘述角度,進行人稱間的穿插。就如華萊士·馬丁所言:“一個第三人稱敘述者可以看進人物的內心,也可以通過其內心來看。在第一種情況中,敘述者是觀看者,人物的內心被觀看。在第二種情況中,人物是觀看者,世界被觀看;這一情況中,敘述者似乎已經把看的功能委托給人物,這就好像是一個含有‘我注意到……然后我意識到’這類措辭的第一人稱故事被以第三人稱改寫了。 ”[6]
《河岸》以它極其豐富的內涵和極其混雜的面目,為讀者書寫了一個成長的故事、一個歷史時代的片段。本文從敘事人稱來展開對《河岸》這部文本的分析。敘述人稱主要是運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但是在下篇的敘述中出現了很多的視點越界,敘述人稱從“我”轉向了“她”,進行了人稱的穿插,實現了敘述角度從第一人稱向第三人稱的轉化。
[1]蘇童.河岸[J].收獲,2009,(2):164.
[2]蘇童.河岸[J].收獲,2009,(2):197.
[3]蘇童.河岸[J].收獲,2009,(2):132.
[4]蘇童.河岸[J].收獲,2009,(2):182.
[5][6]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