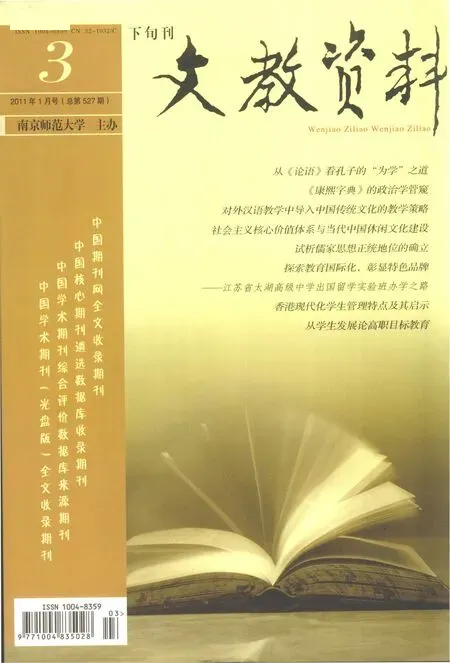建構主義,文學批評中的新思潮?
田 豐
(南京藝術學院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一、引言
建構主義越來越被人們所熟知、所談論,它最早被皮亞杰、維果茨基等人運用于教學研究中,并用來指導教學。在國內也有許多學者談論、研究建構主義,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呂俊教授的建構主義翻譯學。雖然建構主義愈談愈熱,可是至今尚未出現在文學批評中。本文以呂俊教授的建構主義翻譯學為參照,以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為指導,從語言學轉向談起,建議在將意義解構之后應該將其再建構,即將建構主義引入到文學批評中來。
二、語言學轉向(thelinguisticturn)
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理論在語言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打破了當時一統天下的“歷時性研究”(diachronic description),提出了“共時性研究”(synchronic description),還指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間的關系是人為的、隨意的,即語言符號與事物之間不是一一對應的,而是任意的,然而語言學時代的到來,不僅僅是由于語言學本身的突飛猛進的革命進程,更主要的是由于在哲學、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領域里先后發生的“語言學轉向”(馮壽農,2003)。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語言與所要表達的意義是一一對應的,那么用語言描繪出來的世界就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但是漸漸地人們開始對語言的表征能力產生了懷疑和否定,語言開始出現了“表征危機”,尤其是20世紀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的提出,他指出,人一降臨到世界上,就掉落在“先在”的語言懷抱里,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加入到一個語言的系統中,別無選擇。哲學家發現:人無法直接認識實在世界,而首先要轉向認識這個隔在人與世界之間的語言。于是哲學發生了 “語言學轉向”(馮壽農,2003),并且迅速波及其它人文學科。
“語言學轉向”促進了文論、批評眼界的更新,即出現了新的價值取向,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方法知識取向”,二是“思想真理取向”。基于此形成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條路是索緒爾對語言的內部的、結構的、共時的、整體的考察引發的“方法—知識之路”,另一條是海德格爾對語言與存在的思考引發的“思想—真理”之路。在“方法—知識”之路上走來了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等文論流派,在“思想—真理”之路上走來了存在主義等文論流派(孫輝,2002)。
在語言學轉向之前,人們注重文本之外的研究,如研究作者的生平、經歷等可能會給作品帶來的影響;語言學轉向之后,到了結構主義,人們將注意力放在文本之上,強調對文本“形式”的研究,主體被排斥,它強調主體的個性差異,認為每個人對文本的解讀都不一樣,意義的生成是無限制的、任意的。然而意義的生成真的是無限制的、任意的嗎?
三、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呂俊教授提出的建構主義翻譯學在國內頗具影響力,它以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為指導,否定了解構主義的翻譯研究范式。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但他不是簡單地沿襲,而是廣泛綜合當代西方解釋學、語言學、實用主義、精神分析學等各派理論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韓紅,2005:2)。交往行為主義認為:“達到理解的目標是導向某種認同。認同歸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識,彼此信任,兩相符合的主觀際相互依存。認同以對可領悟性、真實性、真誠性、正確性這些相應的有效性要求的認可為基礎。……它最狹窄的意義是表示兩個主體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一個語言表達;最寬泛的意義則是表示在彼此認可的規范背景相關的話語的正確性上,兩個主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協調。此外,還表示兩個交往過程的參與者能對世界上某種東西達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為對方所理解。”另外,交往行為理論還強調“復數主體”,即社會主體的概念,認為在個人的前理解結構中,盡管有差異性,但它不占據主導地位,占主導地位的仍是人類知識的共性。它用卡爾·波普爾“三個世界”的理論闡明了這一問題,即第一世界(外部實存世界)與第三世界(個體主體精神世界)沒有能量和信息的直接交換關系,它要經過第二世界(社會群體世界)才能發生關系,也就是說,正是社會對人類知識的歸納、總結、梳理、整合后才傳授給個人的。這樣就否定了個體差異在理解中所占的主導地位(呂俊,2005)。
那么我們為何要提出建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它究竟比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理論好在哪里?
首先,解構主義雖然打破了結構主義的完全確定性和自給自足性,認為意義是在主體間對話中生成的,強調主義的個性差異,然而解構主義并沒能把握好這個度,使得意義生成缺乏制約,反而成為它的危機。而建構主義強調“復數主體”,它承認個體差異,但由于社會對人類知識的歸納、總結、梳理、整合后才傳授給個人的,因此個體差異在理解中并不占主導地位,從而克服了意義生成的任意性的缺點。
其次,建構主義對之前的理論采取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態度,它不像解構主義對結構主義那樣毫無保留地批判和全盤否定,建構主義既保留了結構主義的語言構成具有規則性這一面,又接受了解構主義的對話理論,但克服了對話中意義生成的任意性的不足,提出了制約性條件。
最后,建構主義以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為指導,通過交往的合理化,重建以主體性和理性化為核心的現代性,對抗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消解,在現代文化批評理論中能獨樹一幟(韓紅,2005:2)。
四、結語
解構主義在否定了結構主義之后,并沒能提出更好的理論來代替它,結果卻陷入意義生成的不確定性的危機中,那么解構之后的重構任務必然要由另一種新的、合理的理論來完成,那就是建構主義。它以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為指導,吸收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優點,擺脫它們的缺點,告訴我們意義的生成并不是無限制的、隨意的,因為社會對人類知識進行了歸納、總結、梳理和整合之后才傳授給個人的,從而克服了意義生成的任意性的缺點。
[1]馮壽農.“語言學轉向”給文學批評帶來的革命[J].外國語言文學,2003,(1).
[2]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韓紅.交往的合理化與現代性的重建——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深層解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呂俊.結構解構建構——我國翻譯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中國翻譯,2001,(6).
[5]呂俊.論學派與建構主義翻譯學[J].中國翻譯,2005,(4).
[6]孫輝.從語言到話語——當代文學理論品評兩度轉向之學理邏輯探析[J].暨南學報,2002,(5).
[7]閻嘉.語言學轉向與文學批評的文化立場[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4).
[8]張杰.批評理論的轉向:從“形式”走向“認知”[J].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