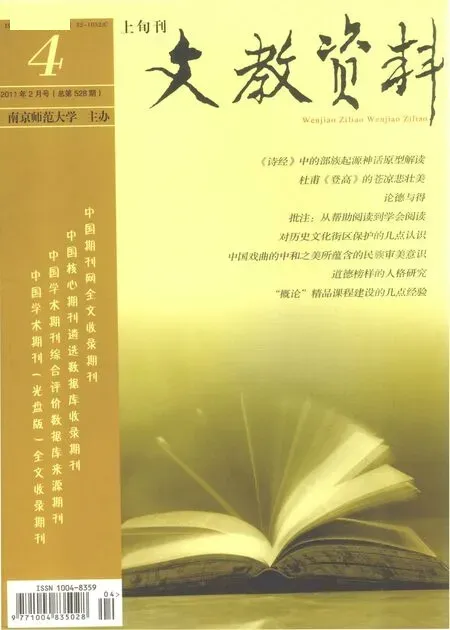中國戲曲的中和之美所蘊含的民族審美意識
常 青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中國戲曲是包含文學、音樂、舞蹈、美術、武術、雜技和人物扮演等多種因素的綜合藝術,是對眾多藝術形式的綜合提升,是中華民族的藝術結晶,凝結著濃厚的民族性格和美學意韻。縱觀中國古典戲曲,我們不難發現,中和之美與大團圓形成了兩個最主要的審美意識。這無疑也折射出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識,以及深層的民族性格。所謂中和之美,是指符合無過無不及的適中原則的和諧美;所謂大團圓,是指戲曲劇目在結尾安排的圓滿結局。無論是對中和之美,還是大團圓,當代學者與戲曲創作者不予茍同的大有人在。然而作為一個美學問題,我們不能回避中華民族特殊的民族性格和傳統的審美觀念在其形成過程中的影響。正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背景、平和的審美追求、中庸的民族性格造就了傳統戲曲的喜劇因素和中和之美。
一、文化滲透進程下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由“中庸之道”融入審美意識轉化而成。中和與中庸在意義上是有聯系,而且有相通之處的,按照朱熹的解釋,中和是就性情而言,中庸是就德行而言。實際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中庸之道的根本含義就是對立雙方都在適當的限度內發展,不偏不倚,不走極端,以保持整體的融洽和諧。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條重要的思想原則。《禮記·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們把是否遵循中庸之道作為衡量天地萬物運行的法則。“中庸”、“中和”的觀點在儒家的典籍、著作中比比皆是。諸如“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樂記·月禮》)。在《荀子·修身》中有:“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另外古代政治家還把“中庸”、“中和”的思想用于政治領域,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制度》篇中這樣論述他的限田主張:“使富人足以使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均調之,是財不匿,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從中我們能夠看出中和之美是儒家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基點,而且滲透到封建社會的諸多領域。
中和、中庸思想既然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必然會影響中國人的審美意識,以中庸、中和的標準要求文學藝術的創作。這種要求早在戲曲藝術產生之前就開始了。《國語·周語下》有這么一段話:“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正視聽。聽和則聰,視正則明……”這段話指出了音樂只有以和音刺激聽眾,才能給人以美感,并把這一點看成關系能否施德于民、政通人和的大問題。中庸、中和在中國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作基礎,有廣泛的社會心理的土壤,有自己的哲學體系。它播散到不同文學藝術作品中,轉化為這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因素,再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在這種社會環境、文化環境中生活的戲曲觀眾,不可能不受中庸思想、中和思想的影響,在戲曲欣賞中,必然表現出對中和之美的強烈要求。既然中和之美強調的是對立成分的和諧、統一,有悲就要有喜,有離必然有聚,所以“大團圓”的戲劇結尾就是中和之美最方便、最充分的表現。故而在中國戲曲中多為始于悲終于歡、始于離終于和。如果在戲曲結尾冤死者沒有伸冤、分離者沒有團聚,觀眾的審美心理就無法消解,他們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就沒有得到滿足,這是中國這片獨特的土壤孕育出的審美觀念,是中國戲曲觀眾所形成的大眾審美需求的強烈表現。
二、情感節制基礎上的內在和諧
基于這一觀點,我們需要對中西方的審美差異作簡單的對比。西方有戲劇,其中尤為推崇其悲劇性;中國有戲曲,其中多以“大團圓”為主調。西方的人是獨立于社會的“公民”,西方的審美主體是個體化的審美主體,而中國的人是“溶解”于社會的“仁人”,中國的審美主體是集體化的審美主體。因此,在西方,“所謂情感,是指忿怒、恐懼、自信、嫉妒、喜悅、友情、憎恨、渴望、好勝心、憐憫心和一般伴隨痛苦或歡樂的各種情感”[1]。也就是說,是一種“天性”,一種自然規定,一種永不滿足的生命動力。它時時要沖破堅實的理性外殼,噴射出去。它不是情感的自然宣泄,而是外在力量對情感的規范和控制。也正是因此,在西方往往是外在的征服自然、征服生命、征服人生,在中國則往往是內在的享受自然、享受生命、享受人生。
另外,“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獨特觀點,它是漢民族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生活經歷在文化心理深層的積淀。這一古代即已形成的哲學觀念,深刻地影響著漢民族的性格和情感,促成漢民族形成了重整合、重中和的人文思想和審美觀。這種哲學觀在人與天之間劃出了界限,將自然世界視為人的對立面。能思想的人,特別指人的理智和靈魂,能認識“思想的對象”。而所謂“思想的對象”即自然界,主要指自然界的本質,而非它的現象。感覺和理智相分離而推崇理智,現象與本質相分離而偏重本質。這種價值觀和思維模式同中國人的“觀象取類”截然不同。在主觀與客觀的物象關系上,西方人更多強調的是再現和摹仿,以認清對象的性質意義為最終審美目的,而中國人講究的是融合和物我兩忘,以人與對象的渾然一體為最高審美境界。亞里士多德就主張美學的最高境界便是“照事物應有的樣子去摹仿”,這一觀點早就滲透到西方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
綜上所述,中國美感意識中深層的情感節制基礎上的內在和諧在中國文學藝術中的集中體現,是固有心態平衡的保持。也就是說,中國文學藝術雖然像西方文學藝術一樣力求引起讀者的心靈震撼,但結果卻又不同,西方的藝術是打破舊的心態平衡并建構新的心態平衡,中國的藝術卻是重建原有的心態平衡。這在古代戲曲中更為明顯,尤其是古典戲曲中的“大團圓”結局,如同一種標志。它是一種“中和”的美學境界,是中國美感意識追求的一種體現,更蘊含著中國人在情感節制基礎上對內在和諧的向往與追求。
三、母性情結泛濫中的柔弱美感
所謂“情結”,是指一組一組的心理內容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簇心理叢。許多心理學家都明確指出:所有的人都是先天是兩性同體,即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既具有雄性的一面又有雌性的一面。榮格認為:“假如要使人格得到完美的調節,達到和諧與平衡,那就必須允許男性人格的女性一面和女性人格的男性一面在意識和行為中顯現自身。倘若一個男子僅只表現其男性特征,那么他的女性特征就會依然停留在無意識里。這樣一來,這種女性特征依然不會得到發展,依舊會處于原始狀態。這將會賦予他無意識一種軟弱的特性和敏感性,這就是為什么外表上最有男子氣概、行為上最強健有力的男子其內心常常是軟弱和柔順的道理。”[2]因此,由于經歷、教養和社會環境的不同,在個體的深層心態層次上,出現女性情結或男性情結并非咄咄怪事。
就中國而言,母系社會發展得很充分,但由于進入文明社會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父系社會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發展。這樣,在中國美感心態中大量沉淀下來的往往是女性化的原始余緒。這方面的例子毋庸細尋。老子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3]字里行間折射出的正是一種女性的心態和特有的視角,所謂“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而且,這種心態更深深潛沉在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而這種心態在古典美學上的詮釋就是中國戲曲觀眾對女性“柔弱美”的追求。它不僅表現在對戲曲人物的要求方面,而且播散到了對戲曲的敘述方式的要求方面。戲曲敘事的線性結構,就是觀眾對“柔弱美”追求的表現。中國人何以對線性運動情有獨鐘?認真觀察就會發現,線給人的感覺是柔和的,團塊給人的感覺是強硬。線,讓人感到它很容易隨著存在環境的變化,可長可短,可直可曲,顯得變化自如。團塊給人的感覺是不大容易改變,難以隨著環境的變化隨方就圓。線性的運動如流水,連綿不斷,一往無前,很有柔弱的品性。老子把水看作最能體現柔弱性能的東西,“天下莫柔弱于水”。水形成的波狀線就更受中國人的歡迎。因此,中國人對線的喜愛,更深層的心理原因是對“柔弱美”的喜愛。
戲曲觀眾對“柔弱美”的偏愛,使中國戲曲中的形象大體以具有“柔弱美”的人物為主導,戲曲的結構、沖突、傳達的情感類型也具有“柔弱美”的特點,戲曲從總體上說來顯示的是“柔弱美”。當然,這不是說戲曲中不存在剛強、猛烈的成分,只是說它總體的風格是偏重于 “柔弱美”。這種美感意識也正是中國特定文化中母性情結泛濫的結果。
綜上所述,我國的戲曲藝術源遠流長,傳統深厚,在其千百年來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中國氣派的喜劇美學體系。尤其是其散發的中和之美更是將華夏美學發揮到了極致,也更能體現中國的文化內涵。我們不難看出這樣的美學意識是在千百年來文化積淀過程中形成的,也是中國人特有的情感節制的結果,更是華夏民族母性情結的依戀所生。它是眾多因素的綜合體,是中國藝術寶庫中彌足珍貴的財富。
[1]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29.
[2]霍爾.榮格心理學綱要.黃河文藝出版社,1987:42.
[3]老子.道德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