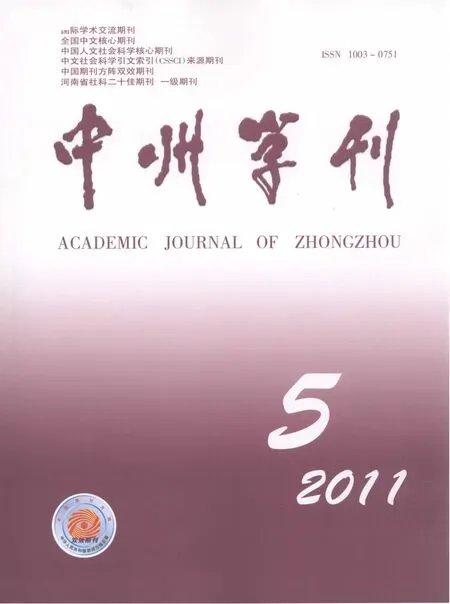農村人情的變異:表現、實質與根源——對當前原子化農村地區人情的一項考察
楊 華 歐陽靜
農村人情的變異:表現、實質與根源
——對當前原子化農村地區人情的一項考察
楊 華 歐陽靜
人情是中國社會普遍的民俗現象。近年來,中國農村人情出現了一種變異現象,但這種人情變異并不是全國農村的普遍現象,它在以人情作為社會最主要連接紐帶的原子化農村地區最容易發生,而在以血緣作為社會基本結合方式的宗族型農村地區較少發生。原子化農村地區的人情變異主要表現為人情的周期、規模、金額、對象、名目、儀式等方面的總體性變化,其實質是規范人情現象的法則由村落公共規則蛻變為個體偏好,個體偏好大行其道從而直接導致人情的變異。而規則之所以蛻變,根源在于原子化農村地區缺乏超出個體家庭之上的結構性力量,公共規則因而缺少生存和支撐的土壤。
農村人情;變異;原子化;自己人;人情周期
一、前言
人情是中國社會普遍的民俗現象,早已引起中外學者的濃厚興趣和廣泛關注。已有的人情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研究領域:一個是從概念、產生、特點和運作規則解析人情現象本身①,這是較為典型的民俗文化意義上的研究;另一個是從文化意義上剖析人情以及與之相關的關系②、面子③、氣④、禮⑤等本土概念,以此深入探究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的行為邏輯和心理特征。這些研究具有相當的廣度與深度,構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論基礎。
然而,只有少量研究關注農村人情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即人情變異現象。黃玉琴發現,人情被農民當做一種手段利用,是農民短期內緩解經濟困難的一種手段。⑥朱曉瑩在蘇北農村也發現了人情變異現象,她稱之為“人情的泛化”,主要表現為人情往來范圍擴大、人情禮金數目增大、人情名目繁多,她還發現人情泛化使人情越來越多地顯露出它的“負功能”。⑦宋麗娜認為人情變異體現在人情的價值性、社會性和功能性等層面的特性上,她將人情變異的程度與熟人社會的性質關聯起來,比較不同區域農村人情變異的差異。⑧陳柏峰研究發現,人情在傳統村落社會中具有經濟互助和維護社會團結的功能,人情變異則表現為人情的互助功能正在喪失,越來越多的農民借人情的互助之名聚斂財富,人情維護社會團結的功能日趨弱化。⑨
上述對人情變異現象的研究偏重于人情變異的表象、層面、原因及社會后果,而缺少對不同農村地區人情變異差異、實質與根源的考察。最近幾年來,筆者所在的農村研究團隊在全國各地農村進行調研,對不同區域農村的人情現象做了詳細調查⑩。調查發現,不同地區的人情及其變異既有相同,又有巨大差異,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湖北江漢平原、貴州遵義和東北丹東等原子化農村地區的人情?;二是中原?、南方?宗族型農村地區的人情。
本文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不同農村地區的經驗,主要對原子化農村地區的人情變異現象的表現、實質與內在根源進行剖析,擬提出以下四個基本假設:第一,只有在人情作為村落社會最基本的連接紐帶的原子化農村地區,人情才容易變異,在血緣紐帶較強的宗族型農村,少有人情變異現象。第二,人情變異不是局部現象,而是涉及到人情的總體方面。第三,人情變異的實質是規范人情現象的法則由公共規則向私人偏好蛻變。第四,人情法則變化的內在根源是原子化農村地區喪失了諸如宗族房頭這樣的結構性力量,而國家建構的規范又沒有成為普遍的行為規范。
二、社會結合方式:原子化農村人情的基本功能
(一)農村社會性質與人情的功能
作為一種民俗現象,人情在農村發揮著巨大的功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根據筆者對全國不同農村地區的調查,人情的功能和角色與農村熟人社會的性質相關,在不同社會性質的農村,人情有不同的功能和角色,其功能和角色的主次也不相同。
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結合形態是“熟人社會”,它是按照差序格局組織起來的“自己人”認同圈。“自己人”建構有兩種基本方式:一為血緣,二為人情。“自己人”的建構方式不同,決定了熟人社會性質的差別。由此,農村熟人社會可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血緣為基礎、以宗族為基本形態的農村社會,其特點是在個體家庭之上有或大或小的血緣認同,包括中原地區多姓雜居村莊的小親族、戶族、聯合家庭,以及南方單姓聚居村落的宗族、房頭和家族,簡稱“宗族型農村”。另一類是以地緣為基礎、以個體家庭為基本形態的農村社會,其特點是農村內部沒有超出個體之上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個體家庭呈原子化狀態,很難達成一致行動,這類農村包括湖北江漢平原農村、貴州農村、東北農村等,概稱“原子化農村”。?人情在這兩類農村有著極不相同的功能和角色。
在宗族型農村,宗族是人們因共同的血緣而結成的一個“自己人”的認同圈,處于其中的人們可以享有某種在宗族之外享受不到的安全、連續和持久的地位,因此他較之其他許多社會的普通個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確信,從而更能生活得悠然自得。?這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之上的熟人社會。在這樣的熟人社會里,血緣構成社會連結的天然紐帶,一個人一出生就被置于宗族的親屬結構和關系網絡中,他與血緣中的人都是“自己人”關系,這個關系不會因個體的喜怒哀樂而有所改變。而這個由先賦的血緣關系形成的“自己人”認同圈,有自己獨特的利益訴求和行為規范,對內整合資源,對外排除干擾,使血緣能夠發展、維系下去。鑒于此,人情在宗族型農村只起著滋潤血緣關系的功能,即人們借助人情而使血緣的硬性關系更具柔韌性和“自己人”的情感性。
在原子化農村,血緣認同與南方的宗族型村落、中原地區的小親族社會相比要淡得多,血緣不再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天然的黏結劑,不構成社會團結、集體行動的基礎,也不是思維、行為及政治正確的源泉。因而,人情扮演著更基礎性的角色,即建構“自己人”關系、結合社會的角色,這也是人情在原子化農村地區最基本的社會功能。
(二)原子化農村的社會結合方式:人情將“外人”內部化為“自己人”
在原子化農村,血緣的不在場并不等于人們在生產、生活和交往中不需要與他人互助、合作,不需要與他人進行感情上的溝通。在一個國家、市場無法完全對人們各方面需求給予供給和滿足的情況下,村落內部的互助合作是必要且必須的。由此,人情在血緣淡薄的原子化農村地區成為聯結各個家庭、社區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橋梁。在江漢平原農村,人情的組織原則以“生產隊”為單位展開,生產隊打破了原有血緣的規則,不僅是生產、生活中的互助單位,也是娛樂休閑、情感交流的共同體,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的人情紐帶滋潤著生產隊里的各種復雜關系。在貴州遵義農村,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也不是建立在血緣之上的,人情同樣成為重要的連接紐帶。事實上,該地區的人情單位已遠遠超出了生產隊互助的范圍,發展到更廣闊的地域。東北農村基本上沒有血緣的認同,村落內部的關系因為沒有血緣的規范而變得十分復雜,人情勾連著各類關系,包括先天的,后天創造的,通過姻親建立的,或者建立在短期、長期基礎上的朋友關系,等等。
可見,在原子化農村地區,人情是將不同血緣之間的“外人”關系內部化為“自己人”關系的一種基本方式和機制。?不同血緣之間的人一旦建立人情,就形成“自己人”關系。人情將兩個本來不具備“自己人”關系的人變成了“自己人”,雙方通過人情將對方納入自己的“自己人”的認同體系。?由此,交往規則發生變化。與“外人”之間的理性算計和依法辦事的交往規則所不同的是,“自己人”交往講究情感、情誼和人情面子。?所以,通過人情建立關系之后,交往雙方的內在行為邏輯也相應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自己人”關系帶有很強烈的情感意念,總是溫情脈脈、柔情似水,田園詩一般,看不到猛烈的對抗和決絕的斷裂。在交往中,由于人情的紐帶作用,人們很難拉下“臉面”,做出出格或者不給對方留一絲“面子”的行為。因此,在原子化的農村地區,人情本身具有本體性特征,撇開人情,農村最基本的“自己人”關系,以及由該關系規定的熟人社會和行動規則都不存在。
由是觀之,在原子化地區,人情勾連著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使互助合作能夠達成,并最終使當地村落熟人社會成為可能,而離開了人情,人們就無法建構關系,村落也就無法結合為熟人社會?。同時,人情還規定著原子化農村地區的基本規則體系和觀念體系,型塑著鄉土風情和人文結構。這一切決定了原子化地區的農民在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中,無法離開人情,即便人情出現變異現象,也會硬著頭皮參與到人情之中。
三、原子化農村的人情變異:與宗族型農村的比較
與宗族型村落相比,貴州遵義、江漢平原、東北丹東等地農村的人情很繁盛,同時又很混亂,似乎沒有什么規則可言。原子化農村人情的變異,主要表現在人情的周期、規模、金額、對象、名目、儀式等多個方面。人情變異已不是局部現象,它具有全面性和總體性?。
(一)人情周期急劇縮短
人情周期是指辦兩次人情之間的間隔時間。一般情況下,人情周期以一些重大的人生禮儀為限,如出生、結婚、做壽、過世等,大約為10年左右,因某些人生禮儀或重大事件會有一定的彈性。人們認可多長時間可以辦一次酒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規矩。超過了這個時間間隔或者在這個時間間隔內多次辦酒席,都被認為是不合規矩的。前者的過失在于沒有給人情對象以還人情的機會,從而致使其承受巨大的人情壓力(心理層面),或者會被認為是看不起人情對象,許久都不請他們喝酒。后者的過失是打破了人情周期的基本規定,使人情對象的人情開支猛增,同樣造成人情壓力(物質層面),或者被認為是主家想通過多次舉辦酒席斂財。
筆者在南方宗族型村落調查到一個近70歲的老太太,她翻開人情本子興奮地告訴筆者,她10年前老伴去世時的人情,前些天剛好還完。言談之間可以感受到老太太因全部償還人情債的舒暢心情。老太太說,她還完了上次的人情,現在可以沒有任何心理壓力地辦另一次人情了,即小女兒結婚。她大兒子在幾年前結婚沒有辦喜酒,就是因為兩次人情之間的間隔太短,不符合當地人情周期的規矩,而且頻繁舉辦酒席,會造成虧欠人情太多而難以償還,心理壓力太大。
而在貴州等三地農村,人情周期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被打破,人們不再受人情周期的限制。人情周期從90年代中期以前的10年,縮短至2000年左右的5—6年,2004年、2005年為3—4年,2008年和2009年為1—2年。時間間隔急劇縮短,辦酒席的次數日益頻繁。除婚喪嫁娶等必辦的酒席之外,許多以前不用辦酒席的其他事情也被納入到辦酒席的范圍之內,而只要能尋找到事由和名目即可舉辦酒席。這種現狀說明人情周期原先的規則被突破。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10年人情周期時,人情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一方面,人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辦酒席;另一方面,人們到一定時候就有壓力辦酒席,因為人情對象希望你辦。從10年周期到后來人情周期的急劇縮短,人們的想法開始變化。有人會根據自己的人情賬虧本與否來決定辦酒席的次數,由此,辦酒席次數越來越頻繁,人情周期越來越短,甚或根本不再有周期。近年來,在原子化農村地區,隔一年辦一次酒席的現象,或者連續兩三年次第辦酒席的現象經常出現。人情越來越成為農民的沉重負擔。
貴州遵義龍口村人給筆者算了一筆賬:若夫妻雙方外出打工收入每月3000元左右,除掉房租、日常生活等開銷外,一年大約剩余1萬元,這其中每年有多達5000多元的錢用于人情開支。為了節省開支,有些外出打工的夫妻決定不再走動一些人情。這種做法帶來的后果是,不走動人情,關系隨之而斷,在家鄉生活會遇到許多難處。如該村曾有一家人因常年在外打工,忽視了許多人情,當其父親去世后竟然無人來幫忙。這種現實的例子使得外出打工人員對放棄人情心存顧慮,于是讓親朋代送人情,記在賬上,回來再結算的現象在該村比較普遍。不少家庭為送人情而欠下不少債務。
(二)人情規模越發隨性
人情規模指的是辦酒席的規模,即一桌酒席需要多少錢。什么樣的規格、什么樣的檔次,在一個地方一般已形成共識,有一些明確的規定,不存在哪家出多出少、有能力無能力的問題。
在南方宗族型村落,一般酒席要多少個菜、哪些菜、什么樣的價位、如何做、每個菜的量、菜的搭配、上菜的先后次序等,都有特定的規矩,不會由著主家的性子或因家庭的貧富而有所改變。當然,根據貧富狀況或者不同性質,酒席會有所調整,但幅度不會太大,一般都會維持在基本水平線上下。這樣的共識,一方面抑制了惡性攀比所造成的奢華浪費,另一方面也照顧到了農戶經濟社會的分化和不同的支付能力。
貴州遵義農村卻呈現出完全相反的經驗。其酒席的規模很小,菜很少且簡陋、粗鄙。與酒席的簡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辦酒席收取的人情特別多,一次酒席主家要賺取三分之二的人情禮金。這種酒席顯然是為了賺錢。而為了賺取更多的錢,酒席則越辦越簡陋,以至于許多人干脆僅送禮金,并不在主家吃飯。在江漢平原農村的酒席屬于另一種情況。酒席上的競爭十分激烈,一家比一家更舍得花錢,有的酒席一桌甚至有二、三十個大菜,要花四、五百塊錢,浪費嚴重。在這種家庭間的競爭下,為了使酒席不賠本甚至賺錢,人們就需要從人情禮金上下工夫,這是最近10年來人情禮金成倍增長的重要原因。可以說,在原子化農村,對人情規模的限制性條件已被打破。
(三)人情金額呈惡性膨脹之勢
人情金額是指送人情的金錢數額。每次送多少人情,與主家同人情對象的關系息息相關。人情對象指的是那些被納入家庭的人情鏈條,成為人情往來一分子的人。傳統上,人情金額針對不同的人情對象而有不同的規定。比如在南方宗族型村落辦“考學酒”,不同的人情對象在人情金額上有所不同:在同姓內部,送人情最重的是五服之內的叔伯,其次是房頭內的家庭,再次是宗族內的家門。在親戚關系中,送人情最重的是舅表親,再是姑表親,最后是姨表親。在一個層次內的關系中,送人情要按照當地的普遍準則,不能隨意送,在此基礎上各個家庭要事先通氣,而下一層次關系送的禮一般不會超過上一層次。總之,在當地,不同的人送不同的禮,相同的人送禮相差無幾。這已經成為人情上的地方性共識,不以個人喜好為轉移,即使某人與其某個親戚私交很好,對方也不能多送交情禮。
而在江漢平原農村,人們已經不再恪守人情對象與人情金額的基本規范,送禮也突破了親疏遠近的原則。許多人依照個人的“交情”來送人情,交情好的,送的人情就多,交情不好的,送的就少,甚至還有中斷人情的情況。還有的人為顯示比別人更慷慨大方、交情更好,在送人情上還出現攀比競爭現象。由此,人情金額不斷向上攀升,一次人情從以前的幾十元上升到幾百元,甚至有的上升到千元水平。這種人情金額不斷地惡性膨脹使許多人不堪重負。在人情對象上,人們也突破了傳統規則的限制,凡是沾點親帶點故的人,不管是否應該邀請,都被邀請進來送人情,這也使人情鏈條無限拉長,造成人情負擔過重。
(四)人情名目越來越龐雜繁多
人情名目即人情的事由。什么樣的事情才能辦酒席、讓人來送人情,也是有規矩的。最基本的人生儀式是必須辦酒席、招待客人的,如小孩出生后做“滿月酒”,結婚做結婚酒、嫁女酒,60歲以上做壽酒,老人過世辦喪事請客,建房子辦酒席,考上大學做“考學酒”,等等。這些都是基本的人情名目,在很多地方都有辦酒席的硬性規定,如果不辦,會遭他人非議。比如在南方農村,建房子是必須辦酒席的,如果不辦,有人會說“這么大的好事,也不做壇酒給我們吃”等帶有期待或者強迫意思的話,如果再不履行,就會被認為是看不起人家。
近年來,隨著人情周期的急劇縮短,人情名目也發展出許多新的形式。2008年筆者在貴州農村看到,當地人情名目五花八門,無所不有。譬如,在建房子上,頭一年建第一層樓房時辦酒席請客,來年建第二層時再請一次;在老人喪事上,老人過世時請客,為老人立碑再辦酒席請客;在為老人過壽上,還沒有到60歲,提前幾年先辦一次壽酒,到了60大壽再辦一次,或是一個老人做壽,幾個兒子分別在不同的日子辦酒席請客,如果實在是找不到好的由頭來辦酒席,還有人把老岳丈請到家里,為他舉辦壽宴。2009年正直高考錄取期間,筆者在東北農村調查發現,人們在學生高考上也打了不少辦酒席的主意。如很多家庭不管孩子是否錄取,先辦“考學酒”收取人情。這些做法都反映出這些地區人情名目的混亂和缺乏規矩的嚴重程度,人們已經不在乎是否符合規矩,完全罔顧人情周期和人情名目的原有規則。
(五)人情儀式漸趨消弭殆盡
人情儀式意指在有人情禮金的酒席中所規定的儀式或活動。它是由一系列的規定動作、話語、行為、人物、象征、物件等組成的過程譜,規定著酒席的基調和氛圍,每個儀式背后都有著深厚的意義內涵。譬如,在酒席的迎來送往、請客就座方面有很多的規矩,首席、次席、三席、四席等主要位置都不是隨便可以就座的,只有特定人物以特定的方式被邀請入座才合規矩,一旦出現差錯,就會產生很大的麻煩;陪客也有講究,沒有相應層次和級別的人來陪客,即使客人被請到主要位置,也會有被輕視的感覺。
在南方宗族型農村,人情儀式非常重要,尤其是傳統婚禮和喪葬的儀式繁復、縝密且充滿禁忌,稍有不慎就會出錯。因此,在傳統禮儀保存較為完整的農村,知客的角色十分重要,凡是有重要的人情儀式時,主家都會請知客來幫忙。知客一般都是由師徒或父子關系傳承下來的,精通禮儀程序及背后的意義內涵,在傳統社會具有崇高威望。?通過知客,許多不愉快的事件可以避免,人情儀式得以順利完成。
在原子化農村地區,酒席上的儀式在逐漸簡化、淡化,有的甚至完全沒有儀式,僅是吃喝而已。在江漢平原和貴州農村,吃的都是流水席,從第一席開始就是隨意就座,不分貴客和普通席位,吃完迅速走人。筆者在貴州農村的一次“壽宴”上觀察到,老壽星在整個宴席上始終沒有被看到,他不是主角,甚至不是配角,僅僅是被利用的“名分”而已。在湖北京山農村,一位老太太喝藥自殺,在她的葬禮上,不見娘家人來“打人命”?,也沒有安排重要席位,只見娘舅家的人混坐于眾人中間嬉笑怒罵。整個喪事簡短而搞笑,完全沒有喪葬儀式的嚴肅性與莊重的氛圍。江漢平原農村的情況是,主持儀式的“知客”顯得并不重要,一個隨機應變、搞怪的主持人更受歡迎。誰能說會道、熱心于搞怪、逗人發笑,就會被邀請做主持。在婚宴上,傳統禮儀被搞怪的“灰公醋婆”所取代,京山農村甚至搭戲臺耍弄翁媳和婆媳。這些花樣繁多的行為所依照的都不是以前的儀式規矩,而是私人性的逗樂和搞怪。由此,沒有了儀式的酒席,就成為純粹收取人情、吃完走人、隨性搞怪的活動。
四、人情變異的實質:公共規則向個體偏好蛻變
由上所述,在原子化農村地區,人情現象的諸方面都表現出去規則化、去公共性的趨勢,以前所具有的公共性規矩和限制性條件逐漸被更為隨意性和私人性的主張所取代,個體偏好在人情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人情變異已不僅是人情周期、規模、金額、對象、名目、儀式等方面的表面增減和有無,而是涉及規范整個人情活動的法則的蛻變,即公共規則被個體偏好所取代。因此,人情變異的實質是人情規則的去公共化、私人化。
所謂公共規則,是在村落地方性共識中對人們行為給予規制、規范和限制的總和,是一套應該如何行為、不應該如何行為的規則體系。在公共規則很強大的地方,個體及群體只有在這套規則體系中尋找行為的合理軌跡,并從中尋求行為合法性的資源。這往往會壓制個體個性的過度彰顯和個體的私性大發,從而將當地社會維持在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公共規則在南方宗族型村落的人情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人情周期的規定難以逾越;人情規模、金額都有硬性規定,與經濟條件沒有太大的關系;人情對象不是依據“交情”來設定;人情鏈條的伸縮有規有矩,不依個人喜好和意志為轉移;人情名目被限制在主要的人生儀式和一些重大的事項,人情儀式保存較為完整,張弛有度。這意味著公共規則在人情中具有至高無上性,私人、個體的奇思妙想還沒有大規模進入人情之中。即使那些最強勢、最富有、最有名望的個體、家庭,也沒有對公共規則發起挑戰。
個體偏好,指的是以個體私人的喜好、意愿、能量、勢力作為行動的準則,而不以外在強加的限制為依歸。它與公共規則相對應,在乎私人的個性、喜好、面子、感受等。在個體偏好之下,個體依照自己的意志行為,不以他人的喜好為轉移。在原子化農村地區的一個個案顯示,當地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去世后,圍繞如何辦喪事問題,她近60歲的兒子與30幾歲的孫子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吵。兒子要按當地傳統規矩辦喪事,而孫子卻要請“脫衣舞”來熱鬧。最后在孫子不出錢、將來也不給父親養老送終的威脅之下,兒子向孫子妥協,結果是“脫衣舞”順利進入村莊,從此成為競爭的標底(對象)。在這一個案中,老太太的兒子原來的主張代表的是公共規則,她的孫子彰顯的是私性感受,孫子的勝利宣告個體偏好沖擊公共規則并最終成為當地主導的行動規則。
可見,個體偏好是以挑戰公共規則的姿態出現的,它帶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后果:一是公共規則隱退。人們行動的一整套限制性條件不復存在,行動趨于無序。二是攀比之風盛行。人們為獲面子而在人情規模、人情對象等方面展開激烈競爭,花費越來越多。三是把辦酒席作為聚斂財富的工具。貴州、江漢平原、東北等地農村都將辦酒席當做收取禮金、賺錢的便捷手段。可以說,個體偏好促使原子化農村地區的人們無視他人感受,大膽而不厭其煩地為了私人的目的而行動,這種私性行動的匯聚形成無限的人情負擔。因此,人情變異的實質體現的是規范人情現象的法則由公共規則向私人偏好蛻變,私人偏好在原子化農村地區的肆虐直接導致人情的變異。
五、人情變異的根源:原子化農村缺少結構性力量
如前所述,宗族型農村的公共規則還在發揮較強大的作用,而原子化農村的公共規則逐漸被個體偏好所取代。究其原因,就在于原子化農村缺少承載公共規則的宗族房頭的社會結構。
任何規則都不是憑空存在的,它是通過一定的載體而起作用的,不同的載體支撐不同性質的規則。在南方宗族型村落,承載公共規則的是宗族、房頭、五服宗親、家族等。在宗族房頭內部,講究的是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尊卑有差的差序規則。當個體在村落里舉辦酒席時,儀式內容就體現出來,假若個體打破了宗族房頭的差序規則,房頭內部的人就會反對,至少表現出不合作的態度。只有老實地按照那套差序規則來做,酒席才能辦得順利。在原子化農村地區,承載和運用規則的是私人個體、家庭。不同的個體、家庭有不同的個性、稟賦以及不同的利益取向,最終加載到個體層面的行動也就不同,因此呈現出來的規范個體行動的規則也大相徑庭。在這里,講究的不是權威與差序,而是個體、家庭的自主體驗,這種自主體驗較少受制于周邊人群的影響和地方“小傳統”的約束。在不違背國家法律的前提下,個體、家庭主要以個體的感受和體驗為準則,由此,個體偏好大行其道。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原子化農村地區在人情來往上都是以私人好惡為基準的。如婚喪嫁娶上的搞怪、跳脫衣舞等,都是完全脫離地方小傳統、只講究個體感官體驗的表現。在人情的其他儀式上,因為擺脫了宗族房頭的“差序格局”?,個體無論老幼都平等地看待彼此,酒席上的亂坐如外甥與娘舅平起平坐、不考慮尊卑等級等現象也就不足為奇。
六、結語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我國的原子化農村地區,人情是其社會結合的最重要方式,是該地區“社會是如何可能的”的根本,因此原子化農村地區的人們不可能輕易退出人情鏈條。第二,該類地區因缺乏超出家庭之上的結構性力量的支撐,人情最容易喪失公共性,導致名實分離、失去本質,也就是人情出現變異。因此,在原子化農村地區,人們會不斷感受到人情變異帶來的壓力,同時又不斷將人力、物力投放到變異的人情當中,使得人情加劇變異,形成惡性循環。
注釋
①參見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15頁;楊中芳:《中國人的人際關系、情感與信任:一個人際交往的觀點》,遠流出版社,2001年,第18—30頁。②楊美惠:《禮物、關系學與國家》,趙旭東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58頁。③黃光國:《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④陳柏峰:《“氣”與村莊生活的互動——皖北李圩村調查》,《開放時代》2007年第6期。⑤[美]閻云翔:《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生活網絡》,李放春、劉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3—130頁。⑥黃玉琴:《禮物、生命禮儀和人情圈》,《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4期。⑦朱曉瑩:《“人情”的泛化及其負功能——對蘇北一農戶人情消費的個案分析》,《社會》2003年第9期。⑧???宋麗娜:《人情的社會基礎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第160—199、44、135—159、160—199頁。⑨陳柏峰:《農村儀式性人情的功能異化》,《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⑩耿羽、王德福:《類型比較視野下的中國“人情”研究》,《青年研究》2010年第4期。?宋麗娜、田先紅:《論圈層結構——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再認識》,《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宋麗娜:《河南農村的儀式性人情及其村莊社會基礎》,《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楊華:《農村人情的性質及其變化》,《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8年第1期。?賀雪峰:《村治的邏輯——農民行動單位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80—183頁。?[美]許烺光:《宗族·種姓·俱樂部》,薛剛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2頁。?賀雪峰:《熟人社會的治理——貴州湄潭農村調查隨筆之六》,《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陳柏峰:《村落糾紛中的“外人”》,《社會》2006年第4期。?楊華:《綿延之維: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義世界》,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頁。?劉燕舞:《國家法、民間法與農民自殺——基于一個地域個案農民自殺現象的分析》,《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0年第5期。?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頁。
C912.82
A
1003—0751(2011)05—0117—05
2011—04—13
楊華,男,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武漢 430074)。
歐陽靜,女,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南昌 330013)。
責任編輯:海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