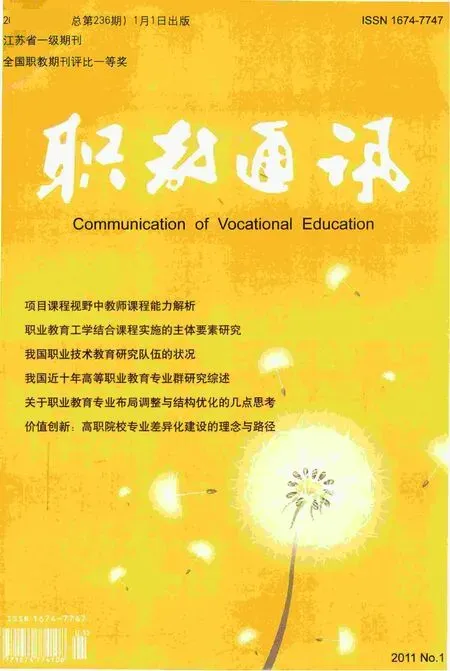談論文的零度寫作
臧志軍
談論文的零度寫作
臧志軍
新年伊始,《職教通訊》改版了,這一期已成為職業(yè)教育理論研究專版。在此之前,全國已經有了幾份專門的職教“理論”雜志。不過,可惜的是,好像職教研究界的理論水平也沒有提高多少,看來,《職教通訊》的理論版也有很長的路要走。
既然是理論版,首先要解決的當然是論文的理論性問題,而這,又首先表現在文風上。網上有個順口溜,諷刺在主流媒體的話語中“開幕沒有不隆重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這些形容詞的濫用豈只在官樣文章中?在許多論文里,說到調查,基本上都是深入的,說到準備,基本上都是精心的,說到開展,基本上都是大力地、廣泛地、積極地……這類給中性概念附加價值判斷的做法在世界各國都是通行的政治宣傳手段,本不足為奇,但此類手段輕易地進入學術討論的地盤,且生命力還很旺盛,大概可以算是中國學術界——至少是職業(yè)教育研究界——的一大特色了。
羅蘭·巴爾特在《寫作的零度》中說有一種寫作,“其作用不再只是去傳達或表達,而是將一種語言外之物強加與讀者”。所以當我們說“重要講話”時并非用“重要”來限定講話,而是想向“被重要”的那位領導傳達一種信息:我承認你的尊貴地位。相類似的,當我們說“深入”調查的時候,并不是在判斷調查本身是否深入,而是想向讀者傳遞這樣一種信息:調查的價值早已得到肯定,你不用再作什么判斷了。這種做法的實際效果往往與作者的希望背道而馳,因為我們的讀者浸淫于這種話語結構中太久了,他們要么早已麻木,要么已經獲得了足夠的免疫能力。結果,這種做法的實際效果常常只是撼動了研究者身份的合法性基礎,使讀者不得不懷疑論文的理論價值。
所以,我們提倡寫作者對自己論文中的語言進行一次歸零,把那些強加、未經學術討論的預設從行文中擠出去,使論文真正成為討論問題而不是宣傳的工具。
但這種倡議施行起來何其之難,因為隨意增添預設并不只是文風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很容易發(fā)現,許多寫作者一屁股坐在了別人為他們提供的椅子上,舒服異常,再也不想挪窩了。最常見的現象是,當一個機構或團隊的領袖提出一個自認為創(chuàng)新的概念后,總會出現一批與這個機構或團隊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寫作者為之搖旗吶喊,極力鼓吹這個新概念。我們當然無法指望這類論文會歸零,因為結論早在文章動筆前就已擺在了寫作者的書桌上。這讓我想起巴爾特的另一段評論,他說文學創(chuàng)作被政治和社會現象控制后,就產生了一種“介于戰(zhàn)斗者和作家之間的新型作者”。如果我們這些自稱為職教研究者的人不能放棄那些未經學術討論的預設,我們大概也會異化為某一機構的寫手和嚴肅的學術寫作者之間的第三者。
除了這個顯性的不能獨立寫作的例子,還有一種有時連寫作者本人都意識不到的依附性寫作。在許多論文里,有些概念是先驗正確的,如職業(yè)教育必然是就業(yè)教育、職教師資必然是雙師型、農村職教必然會促進農村發(fā)展……大量的論文讀來讓人總覺得是這些天然正確的觀點的注腳,從而只能成為這些觀點的附庸,而不具備平等對話的地位。這些寫作者出于思維上的惰性或慣性,主動放棄了對別人觀點的甄別。因為寫作者往往自己都沒有認識到對別人的依附,這類文章就更難歸零了,就像哈斯金斯對經院哲學家的評論一樣,“籬笆對于那些不會想出來的人而言并不是障礙”,因為他們自認為是“自由”的。
我們可以找到千百條說辭來解釋我們必須隨波逐流,領導意志、同事關系、職稱評定……但事實總歸是我們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使我們的寫作無法遵守零度的原則。也許正因為此,長久以來,職業(yè)教育研究的格調總是不高,職業(yè)教育研究論文的最大功用總是自娛自樂:職業(yè)教育研究就像獨立王國,與其他學科基本沒有交流——如果有的話,大多也是從其它學科吸取營養(yǎng),很少有職教研究成果被其它學科采納。
有人可能會誤會,以為我在鼓吹一種中立不偏的研究,其實我也贊同尼爾遜、庫寧漢等人所說的任何研究都“可能帶有強烈的個性”。我們可以接受不中立,但不能接受不獨立,也就是我們可以接納別人的觀點,但只能在檢驗的基礎上接納,而不能因為他是領導或權威而接納。
阿爾都塞說所有閱讀都是有罪的,他的意思是沒有人會不帶成見地閱讀,依此類推,沒有寫作不是有罪的。如果每次寫作都有原罪,那么努力地救贖自己就是寫作者的宿命。職教論文的寫作者們應該有勇氣對自己來一次歸零,把附著在文章上的虛幻的觀念掃地出門。希望在《職教通訊(理論版)》上看到“零度寫作”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