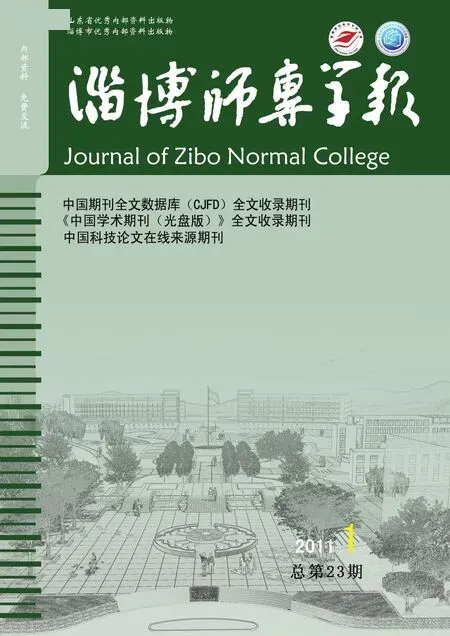諸葛亮“觀其大略”之讀書方法散論
吳 慶
(淄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人文科學系,山東 淄博 255130)
三國史研究中,諸葛亮為永恒話題。陳壽著《三國志》并編纂《諸葛亮集》可視為諸葛亮研究之肇始。由此至近代,前賢對諸葛亮的論述近乎全為宏觀簡略之評論,皆非學術探討。盡管陳壽對諸葛亮的論斷曾引起爭議①,但諸葛亮身后一段時間,對其生平功過的評價還是客觀公允的。自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首創帝蜀寇魏論,“忠義”漸成評價諸葛亮之主題。唐人以詩歌論孔明事跡,雖立意不同,尚曰平直。至兩宋,受理學及正統史觀影響,德行成為評價諸葛亮的基本標準,諸葛亮“忠義”無比的政治形象確立。再至明清,諸葛亮竟變為盡善盡美之圣人而走上神壇。
近代以來,關于諸葛亮的學術研究開始興起,然未成體系,亦不乏偏激武斷者,章炳麟《訄書》之《正葛篇》為典型②。建國以來,漸成規模,近三十年來之成果尤為豐碩,《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第2期馬強、馮述芳《近年來全國諸葛亮研究綜述》一文,全面介紹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研究狀況。《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2期馬強《近二十年來國內諸葛亮研究概述》,全面介紹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成果。相關學者及其論著盡在其中,茲不贅述。
近些年來的研究,一個特點是大問題的研究多而細節研究少,單方面的研究多而聯系性的研究少。鑒于此,在前輩成果基礎上,選擇諸葛亮讀書方法這一細節切入,力求詳盡之分析。該細節問題,方北辰先生《〈三國志·諸葛亮傳〉札記》及王曉毅先生《荊州官學與三國思想文化》二文中皆曾點到③,茲試論之。
一、問題的提起
《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韜)、徐元直(庶)、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諸葛亮、徐庶、石韜、孟公威為同學,于漢末游學荊州,讀圣賢書,皆欲立功名,但其讀書方法截然不同,“務于精熟”與“觀其大略”差別明顯。諸葛亮之于三人,頗具新意。何以至此?述論如下。
二、“務于精熟”
對章句“務于精熟”源于兩漢官方學術——今文經學,為士人主流治學方法④。眾所周知,今學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為代表,積極服務于現實政治,講求圣人“微言大義”,其注文即為“章句”;所謂圣人大義實為時人主張,因無可稽考,故易陷于主觀隨意而空洞無物,大義無窮則章句無窮,今學遂生章句繁亂、派別紛紜之弊。《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曰:
后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后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圣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今學本身弊端叢生,尤以繁詞碎義、偏狹封閉、派系林立等特點備受詬病,加之義理虛無,越來越不適應統治所需。但因其所持所論者終究為倫理道德、禮法綱常,為君主重視,仍得立博士而居各級官學講席正地。
兩漢取士即以今學為本,考察諸生五經章句熟練程度,由此察舉孝廉、茂才等,漢武發其端,東漢成定制。《后漢書》卷六《孝順帝紀》載:
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
諸生需通章句,且年四十以上才有可能被舉為孝廉。此議出自尚書令左雄,左雄章奏中謂之“諸生試家法”[1],即以諸生所師承流派之章句為考試內容,嚴加遴選。孝廉是兩漢最為重要的常舉科目,乃絕大部分士人之入仕途徑,名額極少而又程序苛刻,故而欲得之,務于章句精熟是不二法門,所謂“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猶俯拾地芥耳。”[2]然“一經說至百余萬言”[3],通之何其難也,皓首窮經不為怪,年屆不惑方可應選的制度設計大概也是為了給士人背誦章句預留充足的時間。建安初年,諸葛亮十五歲,其同窗石韜等三人年齒應與之相仿,正當求學之時。三人讀書“務于精熟”,應該是欲通章句而被察舉,入仕漢朝,而后積功累資,步步升遷,以至顯達,走前輩士人的老路。
然而,這條路在建安初年走不通了。首先,黃巾縱橫,董卓變生,獻帝西遷,四海分崩,“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4]漢室已名存實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作為官方學術的今文經學因失去政治支持而黯然凋落;治亂用權謀,繁瑣空洞的今文經學因不合時務而壽終正寢。“務于精熟”不再是讀書正道。再者,荊州牧劉表出身黨人“八及”[5],“無他遠志,愛人樂士”[6],儒者風度,恪守臣道,“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7],“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8],至死不參加軍閥混戰;劉表無意問鼎,甘為漢臣,仍在轄內推行漢制,而依漢制,州郡長官僅察舉本籍士人⑤,石韜、徐庶、孟公威皆為外來流寓之士,無從參選,三人“務于精熟”以求出仕幾乎無法如愿;且劉表所用之人,多為桓靈以來名望已具者,石韜等三人皆為無名后生,恐難入劉表法眼,基本沒有破格選用之可能。最后,僅就經學本身而言,古學經不懈努力,至東漢后期,終于在五經領域全面壓倒今學,雖尚未立學官,但在政治上開始受到空前的重視⑥。古學為主流而不尚章句,“務于精熟”已然落伍了。故而,于建安初年,不思改弦更張,仍遵從歷史慣性而行“務于精熟”之道,不合時宜,難展抱負。“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杰。”[9]三人可謂俗儒,非俊杰也。史實證明,諸葛亮對三人前途的判斷是準確的,《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
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徐庶、石韜之功業卒如孔明所料,仕至郡守一級官職,默默而終,未見大用,此乃漢末三國時勢使然,是三人才學使然,也是三人讀書治學的方法使然,“務于精熟”終究難成大器。
三、“觀其大略”
相對于石韜等三人,諸葛亮讀書“觀其大略”,獨特而新穎。然縱觀兩漢學術史,此種方法似已有先例。
《漢書》卷八十七上《揚雄傳》曰:“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后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曰:“(班)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后漢書》卷六十二 《荀淑列傳》曰:“荀淑……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后漢書》卷六十四《盧植列傳》曰:“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
上述諸賢生活年代各異,然其治學方法略同,即舉大義、尚博通而不守章句。“觀其大略”即“舉大義”而不守章句⑦,諸葛亮與之一脈相承,即讀書只看其主要的大致內容,把握精髓與實質,對細節尤其是章句文字不做要求。上述諸賢皆為古學大儒,則諸葛亮亦應研習古學。
馬融死于延熹九年(166年),鄭玄于建安五年(200年)死于官渡,大師去矣;關東兵起,董卓西遷,諸侯混戰,士人四散,典籍蕩盡,以洛陽為中心的學術體系徹底崩坍,斯文喪矣。《后漢書》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傳》曰: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余輛,自此以后,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后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東漢近二百年的學術積累毀于一旦,古學初具繁盛局面而遭此大變,武夫肆毒,士子奔命,誰人還可傳道授業而延續經學道統?希望在當時仍屬偏僻荒蠻之荊州,那里有亂世中留存的一點學術火種。諸葛亮避難于荊州,人生由此改變。
《后漢書》卷七十四《劉表列傳》載:
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尉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后定》。
荊州平定后,劉表并未北向逐鹿中原,而是恢復儒學以收教化之效,荊州成為戰亂中的王道樂土,引來大批落難士人。劉表善待這些讀書人,使其衣食無憂、地位尊崇,進而發揮他們的文化優勢,重建荊州官學,倡導學術,穩定人心。《全三國文》卷五十六《劉鎮南碑》載:
深憨末學遠本離質,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劃浮辭,芟除煩重……吏子弟、受祿之徒蓋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闿闿如也。
《全后漢文》卷九十一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載:
乃命五業從事宋衷作文學,延朋徒焉。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闿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麟,委介免胃,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亶亶如也,兢兢如也。
以荊州官學為依托,劉表組織儒士們進行了一系列有意義的學術活動。“改定章句、刪劃浮辭”是在前人基礎上將對今學的改造推向深入,成果表現為《五經后定》;聚眾講學、辯論義理,使洛陽禮樂之聲重溫耳畔,可謂興滅繼絕、繼往開來。荊州官學所講授者,為何經義?《三國志》卷四十二《尹默傳》曰: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尹)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
宋衷為五業從事,具體執掌州學,尹默因不滿益州今學而遠游荊州向宋衷、司馬徽二人學習古文經,說明兩漢時期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文經,首先在漢末之荊州得立于官學而取得正宗地位⑧。宋衷等人所傳授的五經,應當為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三國志》卷四十一《向朗傳》注引《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
向朗、徐庶、龐統皆師事司馬徽,而諸葛亮與徐庶“俱游學”,則司馬徽亦為孔明之老師無疑,宋衷與司馬徽同執教于州學,可知宋衷亦為孔明之師。依前文所述,建安初年,諸葛亮與徐庶等共同求學與生活的地方,應為荊州官學。也就是說,諸葛亮早年曾入荊州官學隨宋衷、司馬徽等名儒研習古學,且因深得古學精髓而備受司馬徽賞識,故而在回答劉備的咨詢時隆重推薦了諸葛亮,遂為三顧茅廬之前奏⑨。
諸葛亮師承宋衷、司馬徽,其“觀其大略”的讀書方法實乃兩漢古學治學方式之傳承與發揚。“觀其大略”是古學簡約實用、注重義理原則的具體運用。唯有如此,方可在讀書治學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吸取治國為政的重大經驗等實質內容上而不必為琢磨章句浪費時間,方可具備真才實學而實現其管仲、樂毅般兼濟天下之志。諸葛亮讀書“觀其大略”,是當時荊州古學學風使然,是漢魏之際學術思潮發展趨勢使然,繼承了東漢以來進步思想的精華,并在三國魏晉時期因時勢變遷而大展其用。
同在荊州官學游學,諸葛亮選擇古學新法以讀書治學,而石韜等三人卻頑固堅持今學舊法,前者順應潮流而得馳騁,后者逆流而動不得要領,此中微妙,耐人尋味。
四、“觀其大略”與儒道法兼融
荊州官學以古學為正宗學術,其博大的學術胸襟使先秦諸子理論的重新崛起成為可能,而戰亂年代生命脆弱的刺激與渴求心靈寧靜的向往為道家的興起提供了條件,治亂尚法術權謀的現實需要為刑名之學的興起提供了條件,故而道、法兩家在荊州亦有所發展。
兩漢黃老派代表人物及著作是嚴遵的《老子指歸》。揚雄乃嚴遵弟子,其代表作《太玄經》問世后,即遭儒生非難,未能產生太大影響。而此書在漢魏之際風行士林,被看做“與圣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過也”[10],其地位已經達到經典高度。宋衷不但為古學名儒,亦為研究道家的重要人物。從現有資料看,魏晉時期,《太玄經》賴宋忠方得以廣泛流傳。《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太玄》注本,以宋衷注為最早,這一時期的其他注者陸績、虞翻、陸凱、王肅諸家都與宋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對其中的具體聯系,王曉毅先生有過詳盡論述,茲不贅述。⑩另外,劉表的別駕劉先“尤好黃老言”[11],可見,荊州彌漫著濃厚的道家思想氛圍。
前文已及,諸葛亮在荊州官學中求學,師從宋衷,讀書“觀其大略”而得以博覽典籍的諸葛亮自然受其道家氛圍影響而研習黃老之學,具備道家風骨。《諸葛亮集》載其《誡子書》曰: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
這種崇尚寧靜的思想,具有道家淵源。《文子》一書以闡發老子言論為宗旨,其卷10《上仁篇》云:“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則《誡子書》的話語,直接出自道家始祖老子。由此可見孔明之道家旨趣。在諸葛亮身上,古文經學與黃老哲學并存,儒以經世致用,道以靜心養身。
漢末以來的人物品評風尚在荊州士人中十分流行,宋衷、司馬徽、龐德公、龐統等人皆善此道。而人物品評與刑名之學關系緊密,所以荊州的法家氛圍同樣濃厚。讀書“觀其大略”而得以博覽典籍的諸葛亮自然受其影響而涉獵法家著作。《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后主曰:
可讀漢書、禮記,間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從中可見諸葛亮對法家著作的熟悉。他更是身體力行,在蜀推行名法之治,“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12]以至于“科教嚴明”[13],“風化肅然”[14],“刑政雖峻而無怨者”[15]。諸葛亮治國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從此意義上講,諸葛亮又是個法家人物。
在諸葛亮身上,儒道法三家思想得以并存兼融,以儒家治國,以道家養身,以法家理亂。
荊州官學的古文經學培養了諸葛亮“觀其大略”的讀書方法,從主觀上成就了諸葛亮的大德大才,進而影響了三國歷史進程,其邏輯關系明晰可見。
五、“觀其大略”與《三國演義》
在前面論述的基礎上,再去看《三國演義》中的一些敘述,更能體味其深意,僅舉二例:
其一,《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有文曰:
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于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
諸葛亮反駁嚴峻,說他專治一經、尋章摘句、舞文弄墨,是站在自己所服膺的古學立場上對今學諸多弊端的批判,可謂切中要害。若不了解今古文之爭,若不知諸葛亮在荊州官學中因研習古學而讀書“觀其大略”,就很難真正理解上面一段文字的意境與出處。
其二,《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有文曰:
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發,來到壇前。
諸葛亮登壇著道衣,以道家形象出現。若不了解當時荊州濃厚的道家氛圍,若不知諸葛亮因讀書治學“觀其大略”而得閱道家典籍以備道家風度,很難理解這段描寫。
類似事例甚多,不勝枚舉。人言《三國演義》七分史實、三分虛構,確乎其然,只有在研究相關歷史的前提下方能對其進行深入的文本解讀。
六、結論
至東漢末葉,章句簡明、義理質樸深邃、舉大義、尚博通的古文經學取代章句繁瑣浮虛、內容空洞妖妄、治學偏狹的今文經學而成為經學主流,此乃經學自身發展之結果,亦為兩漢政治實踐、政局變動與學術思想互動中之自然選擇。然古學未及立于學官而遭董卓之變,武夫稱雄,士人離散,學術淪喪,經業道統大有斷絕之危。正當此時,出身黨人的儒士劉表獲任荊州刺史,在平定境內局勢后,恪守臣道,不事征伐,起立學校、博求儒士,于亂世之中創造出一片王道樂土并支撐長達十年之久。外來避難士人大量涌入,擔負起延續道統、薪盡火傳的歷史責任。古文經學被立于荊州官學,成為正統學術,完成東漢未盡之事業,并在馬融、鄭玄等人的基礎上將古學研究繼續推向深入。簡約明了、注重義理的學風在這里傳承,出現了宋衷、司馬徽等一批古學名儒,諸葛亮從其習古學,讀書“觀其大略”,輕章句而重義理,培養真才實學,終成大才。
石韜等三人,雖與諸葛亮為同窗,然其讀書治學仍沿襲沒落的今學舊法,追求專治一經、章句精熟,仍欲走試章句以舉孝廉的仕進老路,可謂抱殘守缺、不識時務,其所學為舊學,其才能不應時需,故事倍功半。
荊州官學寬廣的學術胸懷使黃老刑名之學在其中悄然興起,加之諸葛亮自身讀書治學“觀其大略”而得以博覽眾家,遂兼融儒道法于一身。
“務于精熟”與“觀其大略”,前者徒勞少功,后者成就真才實學,后者遠勝前者,給人啟示良多。當前之中國,政治穩定,四海粗安,可謂治世。然適逢近代二百年以來經濟與社會劇烈轉型時期,社會結構需重新打造,欲和平實現,惟有改革。小平同志講,改革是無硝煙的戰爭,亦需平亂治奸,可比開國創業垂統之時。新形勢需要新人才,新人才來自于新的學術體系與新的讀書治學方法。然新學術之實現,以今日論,只有高等院校與科研機構中飽學之士可為之,此若可為,則以新思想催生新方法,以新方法培育新人才,以新人才鑄造新社會。改革需要真才實學,需要務實精神,需要寬廣博通之胸懷。今日稍顯浮躁、空洞、怠惰之學風絕非當下所需,不學無術之徒,讀書偏狹、死板而又不求甚解者,治學只重外在形式而缺乏實質內容者,筆下雖有萬言而胸中實無一策者,平日玩弄詞句而臨機處變百無一能者,亦絕非當下所需。凡此種種,值得警惕。以此而論,諸葛亮“觀其大略”的讀書方法對當今人才培養機構,尤其高校及青年大學生具有重大借鑒意義。
注釋:
① 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本傳中有評語曰:“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對這一評價,有人認為貶低了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是陳壽公報私仇;有人則認為客觀公允,符合史實。此中區直,難下定論,至今仍為歷史公案。
② 章先生在《正葛篇》中,在幾乎沒有依據的情況下提出了諸葛亮借刀殺關羽的大膽假設。此實為影射,是當時復雜政治斗爭所需。后來,章先生從學術角度對此論斷進行了自我修正。
③ 方北辰先生《〈三國志·諸葛亮傳〉札記》一文見《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王曉毅先生《荊州官學與三國思想文化》一文見《孔子研究》1994年第2期。
④ “今文經學”可簡稱“今學”,“古文經學”可簡稱“古學”,行文以此為例。
⑤ 據《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后,兩漢之察舉皆以郡國為單位,按人口比例限定名額。綜合《漢書》、《后漢書》眾人本傳,郡國所察舉者,基本上全為轄內本籍人士,此應為制度規定。石韜等三人也可走征辟之路,然而,漢廷名存實亡,諸侯割據,獻帝與三公無從征辟,即使可征辟,亦為德高望重者,石韜等三人皆青年后生,明顯難預此流,沒有被征辟的可能。
⑥ 雖然東漢末年仍未專門為古文經設立博士,但當時的博士亦非只為今文經而設。當時選擇博士的標準,已打破今文與古文的界限,強調兼通古今和兼通數經。據《后漢書》靈帝紀,“詔公卿舉能通《古文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四經當中,古文居三,可見東漢朝廷在選舉上也開始向古文經傾斜。同時,大量修習古文經者仕進為高官顯宦,所有這些都表明古文經在政治上受到空前重視。
⑦ 據《三國志》尹默本傳,尹默與諸葛亮皆從宋衷、司馬徽研習古學,尹默讀書“咸略誦述”,不求精熟,也就是“觀其大略”。
⑧ 古文經在兩漢一直處于民間私學地位,即使漢末壓倒今文經后也沒有立于學官。關于今古文之爭,前輩學者論述已詳,若欲了解大致脈絡,可參閱寇養厚先生發表在《煙臺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上的《西漢末期與東漢初期的今古文經學》和發表于《蘇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上的《東漢中后期的今古文經學之爭及其盛衰變化》兩篇論文。
⑨ 據《三國志》先主傳,劉備與公孫瓚皆為盧植弟子。而據《三國志》盧植本傳,盧植與鄭玄同為古學大儒馬融的弟子。則劉備之思想頗具古學淵源。諸葛亮亦研習古學,劉備與諸葛亮在這方面有共通之處。諸葛亮最終選擇輔佐劉備,或許與此有關。另,據《三國志》關羽本傳,關羽喜讀《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而《左傳》為古學主要經典,則關羽在思想上也是崇尚古學的,劉備、諸葛亮、關羽三人的這一共同點,值得重視。
⑩ 詳情參見王曉毅先生發表于《孔子研究》1994年第2期《荊州官學與三國思想文化》一文。
[1] [3][4][5]范曄.后漢書[Z].北京:中華書局,1962.
[2] 班固.漢書[Z].北京:中華書局,1962.
[6] [7][8][9][11][12][13][14][15]陳壽.三國志[Z].北京:中華書局,1962.
[10] 嚴可均(輯著).全三國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