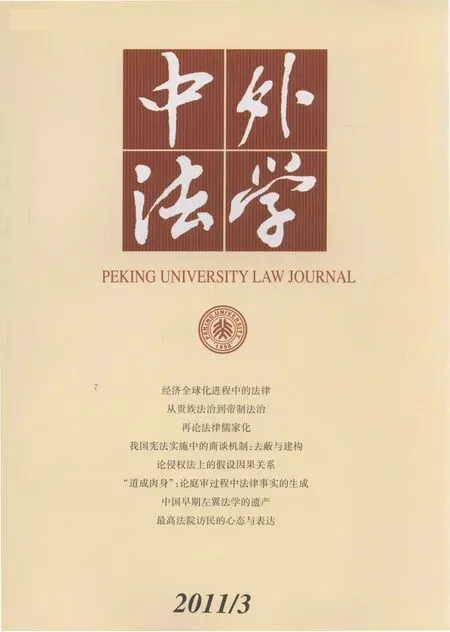論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構成中的善意要件
魯春雅
為保護從無權利人處取得不動產的善意第三人,大陸法系中具有代表性的德國和瑞士民法均規定了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并對該制度構成中的善意要件進行了規定。不同于上述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第 106條規定了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該條款雖將善意規定為構成要件,但未規定善意的范圍。善意要件是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而善意的范圍則是該要件的重點,因此,如何理解善意的范圍,在《物權法》頒布后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綜合當前有關此問題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學者們在如何理解善意的范圍方面,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標準:一種是將善意的范圍與取得人的過錯結合在一起,此標準與瑞士法上的善意標準有相似之處;另一種是不考慮取得人的過錯,以德國法的善意標準來解釋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
不過,上述研究既未全面認識德國、瑞士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善意要件的重大差異,也未充分考慮善意要件與物權法及不動產登記制度在體系上的緊密關聯。這難免使得這些研究成果在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上陷入孤立和片面,未能很好地與我國物權法和不動產登記程序法相契合,從而無法對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在體系上做出合乎邏輯的闡釋。本文擬采用體系化的研究方法,以法律行為對善意保護效果的影響為理論架構,對德國、瑞士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善意要件的立法特點、善意的范圍、善意的決定因素等進行系統、深入的分析,以期為理解我國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研究思路。
一、德國、瑞士法關于善意要件的規定
德國和瑞士雖然均將善意規定為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的法定要件之一,但是并沒有在立法中對善意的含義進行界定。不過,這兩個國家的立法都明確規定了善意要件的判斷標準,并解決了關于善意的證明責任歸屬。
(一)德國法
法律不是將善意規定為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的積極性構成要件,而是將惡意作為排除善意保護的要件。《德國民法典》第 892條將善意要件表述為,取得人明知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除外。這一規定體現了《德國民法典》獨特的立法技術,即通過“除非”(es sein denn)一語,不僅從實體法上實現了對善意要件范圍的限定,而且在程序法上起到了善意推定的作用,從而將證明取得人為惡意的負擔轉移給了持有異議的人。這種立法技術體現了立法者將善意作為默認的前提條件的初衷。〔1〕Vgl.Reinhold Johow,Sachenrecht,Teil 1,Allgemeine Bestimmungen,Besitz und Eigentum,Walter de Gruyter&Co.,Berlin,New York,1982,S.361.這一立法模式簡潔、明確,用一個條文同時解決了實體法上的構成要件和程序法上的證明責任。
取得人明知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究竟應表現為結論性的價值判斷,還是陳述性的事實判斷,在《德國民法典》的立法過程中曾有過爭論。最終頒布的民法典刪除了關于取得人明知導致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事實的表述,〔2〕Vgl.Staudinger/Karl Kober,Band III,Sachenrecht,3./4. neubearb.Aufl.,J.Schweitzer Verlag, Muenchen,1907,S.160.只保留了對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價值判斷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證明取得人明知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對于原權利人來說非常困難。有鑒于此,原權利人只要能夠證明取得人明知導致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事實,常常就能推導出取得人已明知登記簿本身不正確,法院一般也認可此種替代性的證明途徑。類似的證明手段在《德國民法典》中也不乏其例,例如,第 142條第 2款規定:“明知或者可知法律行為的可撤銷性的人,在撤銷時,應按照其已知或者可知該法律行為無效來處理。”可見,這種間接的證明方法雖然最終沒有在不動產登記簿制度中得到明確規定,但其仍在實際上得到了很好的應用。只不過,這種應用不再體現為對取得人注意義務的要求,而僅表現為排除善意時的證明手段。這樣一來,法律進一步降低了對取得人注意義務的要求,并將其轉化為了一種證明風險。
除了上述實體法的規定體現了善意要件的規范特點之外,不動產登記程序法強烈的獨立性也為善意要件的簡明規定提供了保障。〔3〕參見 (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冊),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頁 275。不動產登記程序法的一些特別規定使得善意要件的判斷不僅與債權行為的效力無關,而且通常也不涉及物權行為的效力。這表現為,法律嚴格地區分了不動產登記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從實體法方面來看,盡管不動產物權交易需要以債權合同和物權合意為基礎,由于物權行為具有抽象性,物權變動的結果并不依賴于債權行為。就程序法方面而言,登記申請也僅具有程序法上的意義;除了土地所有權讓與和地上權設立的情形之外,登記同意替代物權合意成為登記審查的對象;登記同意的效力同樣不依賴于債權行為的效力。這就使得善意取得人無須關注不動產登記簿以外的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的效力問題,取得人信賴的客體僅表現為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而不牽涉導致物權變動的基礎行為、登記同意以及登記申請。
綜上可知,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的特征和不動產登記程序規定對善意要件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這個取得過程以法律行為的要素為基礎,而不具有實質性的轉讓性行為的內涵,其法律效果的產生不依賴于當事人的意思,而只取決于法律的規定。因此,善意要件不能用一般的法律行為中的過失標準來判斷。另一方面,物權行為的抽象性和登記同意的特征促進了善意要件判斷上的獨立性,使其不依賴于債權行為的效力和物權行為的效力。從以上方面來看,不論是將善意取得的效力定性為原始取得還是繼受取得,皆不會對善意保護的結果產生實質影響,強調其原始取得特性無非是更重視法律效果的法定性,著重繼受取得則更彰顯法律行為中的意思表示特征。
(二)瑞士法
與德國法上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善意要件的簡明規定相比,瑞士法上對善意要件的規定較為復雜,涉及《瑞士民法典》中的三個條文:第 973條、第 974條和第 3條。第 973條將善意(guten Glauben)作為構成要件,規定出于善意而信賴不動產登記簿之登記的人受到善意保護。不過,此處并沒有明確善意的范圍。這種關于善意要件的規定方式與我國《物權法》第 106條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關于善意要件的規定非常相似。由此,為了理解第 973條規定的善意要件的含義,需要借助另外兩個條文的規定。
第 974條第 1款是關于“惡意第三人”的規定,即物權之登記不正當的,該登記對于知悉或應知悉該瑕疵的第三人無效。從這個條款來看,惡意就是知道或應當知道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當的瑕疵。將這個條款和第 973條的規定相結合,并采用反對解釋的方法,可推知善意的范圍為,不知道或不應當知道不動產登記簿登記不正當。依第 974條第 2款,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當是指,“無法律原因或依無約束力的法律行為而完成的登記”。可見,第 974條的兩個條款不僅確定了善意的判斷標準,而且解決了善意保護與債權行為的關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瑞士法和德國法都承認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的法律效果是法定的。不過,在債權行為與善意保護的關系上,瑞士法與德國法存在顯著不同:不僅作為登記原因的前手債權行為的效力會影響善意保護的效力,而且取得人所為的債權行為效力的瑕疵也將影響善意保護的效力。〔4〕Vgl.Astrid Stadler,Gestaltungsfreiheit und Verkehrsschutz durch Abstraktion,Mohr,Tübingen,1996,S. 513.這兩個國家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差異,原因在于,瑞士法關于物權行為的規定及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的關系與德國法有所區別。瑞士法雖然承認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的區分,但并不承認獨立的物權合意。這就造成在不動產登記過程中,具有程序法意義的不動產登記申請同時也具備了實體法上的意義。登記申請包含了對物的處分,被視為獨立的單方物權行為,然而,它同時也是債權行為的履行行為 (Erfuellungshandlung),其效力要受到債權行為效力的影響。〔5〕Vgl.Heinz Rey,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3.,ergaenzte u.ueberarbeitete. Aufl.,StaempfliVerlagAGBern,2007,S.98,439,441.由此,根據法律行為而為的不動產物權變動可分為兩個過程:債權行為和登記申請。由于瑞士法上物權行為的單方性和有因性,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善意要件的判斷不像德國法那樣不受法律行為效力的影響。從第 974條第 1款的規定可以看出,善意要件是以物權行為的有因性原則和有效的處分為基礎的。〔6〕Vgl.Basler Kommentar ZGB/Juerg Schmid,II,3.Aufl.,Helbing&Lichtenhahn Verlag,Basel,2007, S.2371.
第 3條規定了善意的一般條款,它解決了兩個方面的問題:善意推定和注意義務的標準。該條第 1款規定:“當本法認為法律效果系屬于當事人的善意的,應推定該善意存在。”結合第973條來看,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取得人的善意應被推定為存在。該條第 2款規定:“憑具體情勢所要求的注意判斷不構成善意的,當事人無權援引善意。”〔7〕《瑞士民法典》,殷生根、王燕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頁 3。如將這一款與第974條聯系起來,那么取得人不應當知道的善意顯然應與一定的注意義務相結合。根據善意要件與債權行為有效性之間的依存關系,注意義務的行為基礎應限于債權行為。
瑞士法對善意要件的規定體現了兩個特色:一是對善意推定和注意義務的統一規定,二是善意要件對債權行為效力的依賴。如果說德國法對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善意要件的規定體現了以物權行為為核心的物權變動模式的特點,那么瑞士法關于善意要件的規定則顯現了以債權行為為核心的物權變動模式的特征。
二、善意要件的范圍
(一)研究現狀
我國學者關于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理解可概括為不知情,即不知道。這種理解上的統一并不意味著學者們在善意要件范圍的界定上達成了一致。相反,他們關于善意范圍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概言之,關于“不知道”的外延可分為兩大類型:廣義說和狹義說。廣義說是指不知道或不應當知道說;狹義說包括了三種觀點:不知道且無重大過失說、不知道說和非明知說。
就廣義說來看,它包括了非明知和無重大過失的不知道兩種情形,認為善意即不知情,或將善意等同于不知情且無重大過失,并將知道或應當知道作為排除善意的標準。〔8〕參見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頁 451-452;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頁 102。就狹義說而言,三種觀點關于善意范圍的理解各有側重。第一種觀點只包括無重大過失的不知道一種情形,認為明知屬于受讓人內心狀態,難以舉證,因此善意應以無重大過失的不知道為限。〔9〕參見崔建遠:《物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年版,頁 86。第二種觀點主張有無過失在所不問,并認為與動產善意取得的善意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不同,不動產善意取得之善意不考慮取得人的過失,其目的在于強化土地登記的公信力。就取得人注意義務方面而言,取得人不負查閱義務。〔10〕參見王澤鑒:《民法物權》(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頁 124。此種觀點與德國法的學說最為接近。第三種觀點借鑒德國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善意要件的標準,將善意界定為非明知,與德國法不同的是,它認為取得人只負查閱義務,不負調查義務。〔11〕參見程嘯:“論不動產善意取得之構成要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 106條釋義 ”,《法商研究》2010年第 5期,頁 79-80;程嘯:“論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與動產善意取得的區分”,《中外法學》2010年第 4期,頁 537-538。
由上可知,我國學者關于善意范圍爭議的焦點在于,善意的判斷是否應考慮取得人的過失。以下將結合德國和瑞士關于善意要件范圍的立法、判例和學說,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二)善意的范圍及對善意的理解
1.非明知
《德國民法典》第 892條明確將善意表述為不知道 (nicht bekannt)。按照文義解釋方法,很難得出德國法將善意規定為非明知(positive Kenntnis)的結論。對比我國學者在解釋善意范圍上的幾種觀點,僅從條文的字面意思來看,將德國法上的不知道做廣義或狹義理解皆不為過。那么,德國法是通過什么方法來確定善意的范圍的呢?筆者認為,德國法運用了兩項立法技術在法律條文的字面意義上排除了廣義解釋善意的可能性。一是分別規定的立法技術,即將從無權利人處取得動產與不動產的善意標準分別加以規定。從無權利人處取得動產所有權時,非善意是指知道 (bekannt)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 (infolge grober Fahrlaessigkeit unbekannt) (《德國民法典》第 932條第 2款)。該條文使用了或者 (oder)這種并列式的立法用語,據此,動產善意要件范圍應理解為:非明知或非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12〕Vgl.Soergel/Henssler,Band 14,13.Aufl.,VerlagW.Kohlhammer,Stuttgart,2002,S.511.對比可知,不動產善意要件的不知道并不包含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二是關于善意表達的獨特立法技術。與我國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不同,德國法未將善意規定為構成要件,而只是將知道作為排除善意保護的要件。根據判例和學說的一致見解,這表明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對善意的判斷,不需要取得人證明自己主觀為善意并無過失,并且因為信賴不動產登記簿而為法律行為。取得人即使出于重大過失、間接故意而不知道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也不影響他受到善意保護。這種消極性規定的立法技術將對善意的主觀要求降至了最低限度,取得人所有的注意義務也由此得以免除。〔13〕Vgl.MuenchKomm/Wacke,Band 6,4.Auf.,C.H.Beck Verlag,Muenchen,2004,S.308;Staudinger/Gursky,§§883-902,Seiller de-Gruyter,Berlin,2008,S.437,512.當然,這種立法技術并不是決定善意要件范圍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對原因的一種表現形式,德國法決定善意要件的主要原因將在下文作詳細分析。
雖然德國法將善意規定為非明知,并且法院和學界對善意要件的理解也嚴格遵循了這一規定,但由于實際交易的復雜性,關于如何理解非明知也經歷了一個長期的變化過程。這一變化主要體現在,取得人是否只有對不動產登記簿有積極的信賴時才能獲得善意保護上。也就是說,取得人的信賴與其行為之間是否應存在因果關系。早期的判例認為,取得人對不動產登記簿正確性的信賴是被推定的,而且對取得人善意的推定是可以反駁的,即如果證明取得人并非基于信賴不動產登記簿而進行取得,那么就可以推翻其善意。〔14〕RGZ86,356.例如,取得人的取得僅是因為信賴讓與人的表述,或者不動產登記簿的不正確在取得人為取得行為時尚未發生,此時,取得人皆未基于對不動產登記簿的信賴而取得權利,因此他不受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的保護。〔15〕RGZ61,195;RGZ74,420.后來,判例的立場發生了變化,認為《德國民法典》第 892條對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假定和完整性假定是不可反駁的,除非登記簿的不正確可由不動產登記簿自身推導出來或者原權利人能證明取得人對其不正確是明知的。〔16〕RGZ86,356.這種變化在立法技術上主要表現為,第 892條中使用的“視為正確”(gilt…als richtig)一語不再被理解為一種可以推翻的擬制,而是被看作一種不可推翻的擬制。在這個觀點確立了之后,取得人的信賴與其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被法院否認,并最終確立了對非明知涵義的理解標準:取得人既不需要知道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并信賴該內容,也不需要基于對不動產登記簿的信賴而為取得行為。〔17〕BGHZNJW 1980 2414.
2.不知或不應知
前已述及,瑞士法有三個條款涉及對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善意要件的規定,在理解善意范圍時如何運用這三個條款,學者之間存在分歧。比較有代表性的見解可分為兩種:一種將善意的范圍界定為不知或不應知(nicht kennensollen)。所謂不知是指不以過失因素為要件的不知 (Nichtwissen),而不應知是指包含了過失因素的不知,即未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而不知。此種見解的法律依據是第 973條、第 974條和第 3條第 2款。另一種僅將善意的范圍界定為不應知,其法律依據為第 973條和第 3條第 2款。這兩種見解在如何認識不應知方面是一致的,即都認為輕過失也應排除在外;他們的根本不同在于善意是否應包括不知,即德國法上所稱的非明知。
雖然法律并沒有對善意的涵義進行界定,但是學者們在解讀法律規定時總是從對善意涵義的界定出發。因此,要深入了解學者們在善意范圍認識上的分歧,必須先從他們關于善意的定義談起。與德國學者一樣,多數瑞士學者也將善意理解為消極性概念,而非積極性概念。有的學者認為,善意是不知道重要的法律情勢,即不知道權利取得或權利狀況的瑕疵。從過失的角度來看,這種善意理解方式可表述為對于不知道法律瑕疵沒有過失;與此對應,惡意不僅指事實上知道而且包括因為過失而不知道法律瑕疵。根據《瑞士民法典》第 974條第 1款的規定,在這兩種情況下,取得人皆不得主張善意保護。〔18〕Vgl.August Egger,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gesetzbuch,Band 1,Einleitung Art.1-10. Das Personenrecht,Art.11-89,2.,umgearb.Aufl.,Schulthess,Zuerich,1930,S.82f;Franz Jenny,Der ?ffentliche Glaube des Grundbuches nach dem schweizerischen ZGB,St?mpfli,Bern,1926,S.50f.瑞士著名學者彼得·雅吉 (Peter Jaeggi)則認為,善意是指,在存在法律瑕疵 (Rechtsmangel)的情況下,取得人并未意識到法律瑕疵的不法性 (Unrechtsbewusstsein)。〔19〕Vgl.Peter Jaeggi,Berne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recht,Einleitung,Art.1-10ZGB,Verlag Staempfli&CIE.,Bern,1962,S.388.這個觀點為取得人在法律瑕疵存在的情況下,設定了注意義務。依據這個定義,如果取得人盡到了注意義務,那么他就能夠認識到法律瑕疵。由此推知,取得人沒有認識到法律瑕疵應被看作違反了注意義務,據此,不知道的涵義為應知 (kennensollen),而善意應限定為不應知。〔20〕Vgl.Peter Jaeggi,Berne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recht,Einleitung,Art.1-10ZGB,Verlag Staempfli&CIE.,Bern,1962,S.406.雅吉關于善意的定義為當今多數瑞士學者所接受。這些學者雖然都將此定義作為理解善意的出發點,然而他們卻在關于善意范圍的理解上出現了重大分歧。〔21〕Vgl.HenriDeschenaux,Das Grundbuch,SPR,V/3,II,Helbing&Lichtenhahn Verlag,Basel u.Frankfurt am Main,1989,S.788,792;Dieter Zobl,Grundbuchrecht,2.,ergaenzte u.nachgefuehrte Aufl.,Schulthess,Zuerich,Basel,Genf,2004,S.81.
判斷瑞士法上善意范圍的關鍵為,是否應將善意的范圍與惡意的排除聯系在一起。多數學者及法院對此持肯定態度,理由如下:第一,瑞士法也像德國法那樣,在善意要件的規定上采用了并列式的立法用語。第 974條第 1款將善意規定為不知道 (nicht kennen)或不應當知道(nicht kennen sollte)。類似的規定在《瑞士民法典》中也不乏其例,如第 202條第 2款、第 217條第 2款、第 913條第 2款等。第二,雅吉對第 3條第 2款的解讀與第 974條第 1款的特別規定并不矛盾。雖然第 3條第 2款的解釋只適用于對應知的說明,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將不知道排除在善意的范圍之外。例如,《瑞士債法典》第 26條第 1款和第 29條第 2款同時規定了知道或應當知道的情形,雅吉認為這些規定也體現了第 3條第 2款關于應知的涵義。〔22〕Vgl.PeterJaeggi,Berne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recht,Einleitung,Art.1-10ZGB,Verlag Staempfli&CIE.,Bern,1962,S.388,414.由此看來,在解釋具體法條時,即使是堅持雅吉關于善意的界定,也并不必然意味著應將善意的范圍局限于不應知。因此,將善意界定為不應知與非明知并不矛盾,只不過這種界定方法未能從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前提出發,考察取得人可能為善意的所有情形。第三,法院的判例包括了對善意理解的兩種可能性。法院在實踐中對第 973條中善意含義的理解并不統一,只是要求應根據具體的情況來進行判斷。法院有時將善意理解為既非明知又非因過失而不知,〔23〕Vgl.Basler Kommentar ZGB/Juerg Schmid,II,3.Aufl.,Helbing&LichtenhahnVerlag,Basel,2007,S. 2367,2372.有時又從有無過失的角度,即是否應知的角度來考慮不知道是否是可原諒的 (entschuldbar)。〔24〕Der gute Glaube im Immobiliarsachenrecht,in Das ZGB Lehren,Hrsg.von Alexandra Rumo-Jungo,Joerg Schmid,Peter Gauch,Universitaetsverlag Freiburg Schweiz,2001.
通過上述德國法和瑞士法上善意范圍的分析,可以看出,這兩個國家都將善意作為取得人獲得善意保護的主觀要件。所不同的是,在德國,因重大過失、間接故意等原因不知道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不影響取得人獲得善意保護;而在瑞士,因過失而不知道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將不能獲得善意保護。瑞士法這樣規定的目的不是為了減輕原權利人的舉證負擔,而是從取得人角度對其提出了注意義務的要求,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取得人獲得保護的可能性。瑞士法要求取得人在一定情況下應履行注意義務,這并不代表就將非明知排除在善意要件之外。如果取得人實際上因有意識地疏忽而未去獲悉信息,那么這種不愿了解瑕疵存在的間接故意和對瑕疵存在的明知之間沒有實質差別。〔25〕Vgl.August Egger,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gesetzbuch,Band 1,Einleitung Art.1-10.Das Personenrecht,Art.11-89,2.,umgearb.Aufl.,Schulthess,Zuerich,1930,S.83.從過錯角度來看,因過失而不知的過錯顯然要低于故意不去了解信息。因此,在前者尚不能獲得善意保護的情況下,后者當然更無法獲得善意保護。
三、善意要件的決定因素
如果說在德國法和瑞士法區分動產善意取得和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的善意要件的過程中,權利外觀的可信賴度的強弱起到了決定性影響的話,〔26〕鮑爾/施蒂爾納,見前注〔3〕,頁 500。那么又是什么因素決定了這兩個國家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善意要件的不同范圍呢?在前面從實證法的角度分析了善意要件的范圍之后,下面將主要從理論層面對善意要件的決定要素進行深入剖析。
(一)道德因素與善意的關系
從學者們關于善意涵義的理解來看,是否將道德因素納入善意之中是決定德國和瑞士善意范圍的關鍵要素之一。道德因素與善意之間之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具有緊密聯系,是因為權利外觀的形成與善意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在德國法上體現為對動產善意要求的可歸責性,而在瑞士法上則體現為產生注意義務的情勢與善意之間的因果關系。
善意一詞起源于羅馬法中取得時效制度的善意 (bona fides),德國和瑞士從無權利人處取得制度中善意的涵義均來源于此。究竟應如何理解源自羅馬法中的善意,德國和瑞士的法學家從倫理學和心理學層面對善意的涵義曾展開過針鋒相對的爭辯。認為善意是倫理學概念的學者直接從法律意識的層面來理解善意,將善意看作缺乏不法意識 (Fehlen desUnrechtbewusstsein),或者認為善意是確信自己的行為是可信賴的 (redlich);而主張善意是心理學概念的學者則從認知能力或理解力的角度來看待善意,認為善意是一種認識上的錯誤,或者是不知道的狀態,這種理解堅持善意與自己的過錯無關。〔27〕Vgl.Peter Jaeggi,Berne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recht,Einleitung,Art.1-10ZGB, Verlag Staempfli&CIE.,Bern,1962,S.387;August Egger,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gesetzbuch, Band 1,EinleitungArt.1-10.Das Personenrecht,Art.11-89,2.,umgearb.Aufl.,Schulthess,Zuerich, 1930,S.82.如果說這些爭辯對于瑞士法上善意的判斷以及德國法上的動產交易還具有較大意義的話,那么對于德國法上的不動產登記而言,則意義甚微。就不動產登記法來看,德國立法者并未將道德因素納入善意范圍之中。
關于道德因素與法政策的選擇之間的關系,在下面還要著重談到。不過,從法技術層面而言,道德義務的存在與它所依存的環境之間的因果關系密切相連。前已述及,《瑞士民法典》第 3條規定了善意的一般條款,該條第 2款不僅規定了一定情勢下的注意義務,還規定了這一情勢和善意之間的因果關系。〔28〕Vgl.Peter Jaeggi,Berne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recht,Einleitung,Art.1-10ZGB,Verlag Staempfli&CIE.,Bern,1962,S.406.而德國法上動產的善意取得和很多情況下的善意要件一樣,都需要考慮善意要件的可歸責性,因為對前者而言,一定的道德義務以及決定這一道德義務的情勢與善意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就和上面談到的善意起源中,羅馬法關于時效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要因性有關。〔29〕參見徐國棟:“論取得時效制度在人身關系法和公法上的適用”,《中國法學》2005年第 4期。要因性強調,主張自己善意的人之主觀的善意與客觀的行為之間存在關聯性,以使他沒有理由懷疑自己的善意。這要求他謹言慎行,必須盡到一定的注意義務,以避免使自己的善意受到懷疑和出現對自己不利的結果。就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而言,瑞士法要求取得人不僅要信賴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和完整性,而且沒有理由懷疑不動產登記簿登記的合法性。這就要求取得人必須注意那些可能會動搖他對不動產登記簿產生信賴的事實。如果他懷疑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或者懷疑不動產登記簿之外的事實,那么他將對此負有進一步調查的義務。〔30〕Vgl.Heinz Rey,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3.,ergaenzte u.ueberarbeitete. Aufl.,StaempfliVerlagAG,Bern,2007,S.389-390.因此,毋寧說取得人信賴的是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不如說取得人信賴的對象是在不動產登記簿上被登記錯誤的處分人或讓與人在物權上的正當性。因為,并不是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引發了取得人的善意,而是取得人缺少對違法性的意識產生了善意。〔31〕Vgl.Dieter Zobl,Grundbuchrecht,2.,ergaenzte u.nachgefuehrte Aufl.,Schulthess,Zuerich,Basel, Genf,2004,S.81;Peter Jaeggi,Berne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recht,Einleitung,Art.1-10ZGB,Verlag Staempfli&CIE.,Bern,1962,S.388.
與之相比,德國法上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的善意要件并不要求取得人負有任何注意義務,因為取得人的善意與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權利外觀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哪怕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發生在取得人查閱過不動產登記簿之后,或者是在登記申請被提交之后,皆不影響他根據這個權利外觀受到善意保護。權利外觀并不是促使他為法律行為的動因。因此,即使他懷疑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或者是對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發生持間接放任的態度,或者他根本不信任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也不能動搖客觀的權利外觀。〔32〕Vgl.MuenchKomm/Wacke,Band 6,4.Auf.,C.H.Beck Verlag,Muenchen,2004,S.308;Staudinger/Gursky,III,§§883-902,Neubearbeitung 2008,Sellier-de Gruyter,Berlin,2008,S.439.德國法之所以如此規定,原因在于立法者在制定該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時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根據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的宗旨,不動產法領域只有善意取得人才能受到保護,對此無需以道德義務作支撐。知道實際權利和登記簿記載不一致的人沒有理由要求獲得公信力的保護。二是將善意規定為消極排除條件的立法方法,使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不依賴于善意要件。基于上述考慮,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對于與不動產交易有關的法律關系具有決定性意義,而取得人明知內容的不正確只作為排除要件。這種立法技術將取得人的善意看作是默認的前提條件,而不是作為主張善意保護的要素。〔33〕Vgl.Reinhold Johow,Sachenrecht,Teil 1,Allgemeine Bestimmungen,Besitz und Eigentum,Walter de Gruyter&Co.,Berlin,New York,1982,S.360-361.
(二)絕對的交易保護
1.客觀善意要素與主觀善意要素
一般認為,在德國法上的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善意要件由主觀善意要素和客觀善意要素組成。前者是指取得人是否知道不動產登記簿的不正確,而后者指的是不動產登記簿的可信賴性 (Verlaesslichkeit des Grundbuchs),即公信力。客觀善意要素體現在不動產登記簿的設置規程上,它包括了登記機關的設置、登記簿的設置和登記范圍的確定。如前所述,取得人對不動產登記簿的具體信賴 (konkretes Vertrauen)與善意保護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這就決定了主觀善意要素不是善意保護的必備構成要件,而只是排除要件,取得人知道不動產登記簿的不正確就不能獲得保護。〔34〕BGHZ NJW 1980 2414.因此,對善意持有異議的人也不能夠通過證明取得人對不動產登記簿不具有主觀信賴而否定其善意。這樣一來,就排除了取得人因未盡到必要注意義務而被認定為非善意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德國法上的善意推定可看作是一種不可反駁的法律擬制。導致這種具體信賴與善意保護相分離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國法上物權行為的抽象性。取得人即使知道了不動產登記簿的基礎行為無效的原因,也不影響他根據不動產登記簿取得物權。從主觀善意要素和客觀善意要素的關系來看,客觀善意要素在善意保護中居于核心地位。由此,學者們將善意要件稱為制度性的信賴 (institutionellesVertrauen)。〔35〕Vgl.Hermann Eichler,Die Rechtslehre vom Vertrauen,Privatrechtliche Untersuchungen ueber den Schutz desVertrauens,J.C.B.Mohr(Paul Siebeck),Tuebingen,1950,S.97-98.
瑞士法之所以規定了不同于德國法的善意要件,學者們的解釋是,德國法上不動產登記具有形式上的絕對效力的做法夸大了公示思想的作用,而未充分考慮處分行為的原因。因此,對于瑞士法上的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而言,除了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的客觀條件以外,取得人主觀上必須因為信賴登記而為法律行為。否則,對于第三人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權利外觀,由權利外觀產生的信賴保護更無從談起。這就突出了取得人對不動產登記簿的具體信賴的重要性。這種具體的信賴一方面體現為取得人應當相信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表現為他沒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否則,他將被認為缺乏對不動產登記簿的具體信賴,對他的善意的推定也將被推翻。〔36〕Vgl.Oskar Leumann,Rechtsschein und Offenkundigkeitsgedanke im schweizerischen Recht,Druck von Huber&Co.AG,Frauenfeld,1933,S.45-46.這種做法實際上強調了主觀善意要素的決定性作用。
2.動產與不動產的二元論
德國法上對動產和不動產善意要件的區分做法體現了其對動產和不動產進行區分的二元論(Dualismus)思想。這種動產和不動產之間的二元論思想是繼受日耳曼法的結果。中世紀的日耳曼法認為,不動產較之動產不僅是更具經濟價值的財產權利客體,而且從社會功能角度來看具有不會枯竭的財產價值。德國在繼受羅馬法的過程中受到了這一思想的影響。自 19世紀 70年代以后,動產和不動產的區分在德國日益明確。隨著動產和不動產的區分,主觀善意要素在不動產領域的重要意義日漸式微。動產和不動產的區分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體現,有關不動產的規定顯示出與羅馬法的重大差異,展示出動產無可比擬的優越的法律地位。德國法對不動產進行特殊保護的做法較之羅馬法在經濟意義上具有明顯的優勢。德國人認為,土地及其他不動產不僅是每個人生存和自由發展的基礎,也是人類共同生活和特殊公共利益的基礎。雖然它的流通能力較弱,但鑒于其巨大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意義必須對其規定特殊的形式要求,以平衡由此產生的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沖突。而動產從功能價值上則與不動產完全不同,難以從總體上對其價值進行衡量。因此,立法者在制定民法典時便根據這種二元論的思想對動產和不動產進行了區別性對待。〔37〕Vgl.CarlButz,Der gute Glaube auf dem Gebiete des Liegenschaftsrechts,Universitaets-Buchdruckerei von J.Hoerning,Heidelberg,1906,S.24-25;Juergen F.Baur,Rolf Stuerner,Sachenrecht,18.,neu bearb.Aufl., Verlag C.H.Beck,Muenchen,2009,S.9-10.立法者考慮到動產和不動產之間在功能上的差異,除了對一些具有共同性的問題進行統一規定外 (如占有、所有權的內容、種類以及保護),對其他部分都進行了區別性規定(如所有權與限制物權的設立、轉讓和廢止)。〔38〕Vgl.Juergen F.Baur,Rolf Stuerner,Sachenrecht,18.,neu bearb.Aufl.,Verlag C.H.Beck,Muenchen, 2009,S.10.
動產和不動產的二元論不僅體現在實體法規定上,更表現在程序法規定方面。不動產登記簿制度的建立為不動產交易提供了一種客觀上值得信賴的基礎,由此建立起了不同于其他國家的不動產登記制度體系。德國法的不動產公示制度雖受到羅馬法的影響,但在糅合了日耳曼法理論之后,便呈現出與羅馬法完全不同的面貌。眾所周知,羅馬法上物權及其變動為外界認知的方式是占有交付,即使抵押權的設定也不例外。由于羅馬法沒有建立公開的、制度性的公示方式,因此,不論是動產交易,還是不動產交易,當事人對物權的信賴均僅局限于對相對人個人信用的信賴。這種物權公示方式無法為大宗的和經常性的物權變動提供公開、便捷的安全性保障。〔39〕Vgl.Ludwig Kuhlenbeck,Von den Pandekten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Band 2,Carl Heymann Verlag,Berlin,1899,S.477-480.中世紀以后,德國吸收日耳曼法思想,在不動產交易中要求不動產的轉讓和設定負擔應當具有公開性,因為唯有如此,方能為善意第三人提供交易安全的保障。起初,不動產讓與交易雙方必須在法官面前表示讓與合意,隨著不動產登記簿制度的建立,這種讓與合意還必須進行登記。這就要求所有與不動產權利變更有關的登記都必須制作成公開的書證。由于法院在不動產交易程序中作為國家公權力的代表出現,因此,不動產登記簿制度具有的公開性和權威性使不動產轉讓程序產生了合法性效力,這種效力逐漸演化為不動產登記簿的公信力。〔40〕Vgl.CarlButz,Der gute Glaube auf dem Gebiete des Liegenschaftsrechts,Universitaets-Buchdruckerei von J.Hoerning,Heidelberg,1906,S.24-25.
建立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登記給不動產交易創造一個值得信賴的基礎。使不動產物權的產生、變更、消滅都通過不動產登記來實現,讓不動產登記成為不動產轉讓行為的實質構成要件。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成為決定法律關系的基礎,這就明確地切斷了主觀信賴與善意保護之間的聯系,實現了對不動產登記簿的客觀信賴保護。這樣一來,每個人都可以信賴不動產登記簿,而對不動產登記簿的信賴并不是他取得不動產物權的構成要件。這也為注意義務的免除提供了基礎,取得人既不需要因為信賴不動產登記簿而為法律行為,也無須在對此持有疑問時負有調查義務。因為,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對善意第三人的保護作為法律擬制具有不可反駁性。而在不動產登記簿之外使第三人負擔調查義務的做法,則違背了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的絕對性。〔41〕Vgl.Hermann Eichler,Die Rechtslehre vom Vertrauen,Privatrechtliche Untersuchungen ueber den Schutz desVertrauens,J.C.B.Mohr(Paul Siebeck),Tuebingen,1950,S.97-98.因此,德國學者將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的善意保護稱為絕對的交易保護,因為它的基礎并非是個人的具體的信賴,而是客觀的、擬制的信賴。〔42〕Vgl.MarcusLutter,Die Grenzen des sogenannten Gutglaubensschutzes im Grundbuch,ACP164,S.124, 166.
四、善意要件與注意義務
我國也有學者注意到了德國法在善意要件上以客觀信賴取代了主觀信賴,但是他認為這是一種對善意界定的純客觀化方法。在這位學者看來,支持這種純客觀化的論據是查閱義務的免除和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擬制。〔43〕程嘯,見前注〔11〕,頁 79。如前所言,德國和瑞士同樣規定了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擬制,并且德國法上的善意要件不要求取得人負有注意義務。那么,查閱義務是否與善意要件的判斷標準存在聯系,瑞士法上注意義務的范圍包括哪些?下文將就此展開論述。
(一)查閱義務
德國法免除取得人查閱義務的原因,并不是因為歷史上人們形成了信賴不動產登記簿的傳統,或是不動產登記簿的記載與事實的吻合度高而值得信賴,而是因為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不要求對不動產登記簿的登記有具體的信賴。這一方面表現為取得人無需知道登記簿的內容,也不需要信賴該內容;另一方面體現為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和權利取得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取得人不需要基于信賴該內容而做出取得的決定。因此,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的善意要件完全是一個獨立的、從不動產登記簿特性中發展出來的否定性的概念。取得人不需要積極地信賴不動產登記簿,也不需要基于這種信賴而積極地行為。由此可見,德國法上關于善意要件客觀化的理論并不是建立在取得人的信賴之上的,恰恰相反,它超越了個人的具體的信賴。主張德國法對善意界定純客觀化的學者認為,我國大多數當事人并不信賴不動產登記簿,并認為這是我國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和德國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在善意要件上的一大差別。這種看法說明他并未領會德國法上善意要件客觀化的真正含義。不僅如此,他也忽略了德國法上支持善意標準客觀化的制度基礎,而從法解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制度基礎正是查閱義務得以免除的原因。
德國法之所以不要求取得人查閱不動產登記簿,主要原因在于善意推定和不動產登記簿的公開性。《德國民法典》第 892條不僅規定了善意推定,而且規定了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的善意保護效果只能對取得人有利。基于善意推定,取得人無需知道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也能夠獲得信賴保護。這一條文還有一個功能,那就是將取得人根據生活經驗對不動產登記簿內容的信賴視為不可推翻的假定,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將取得人的善意作為默認的前提條件。因此,不論取得人是否事先查閱了不動產登記簿,對他來說,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作為客觀的權利外觀只會產生對他有利的法律后果。
不動產登記簿具有公開性,這一原則一方面構成了公信力的基礎,即不動產登記簿形式上是公開的,有關的不動產交易當事人可查閱不動產登記簿;另一方面使取得人保有其所獲得的權利。因為不動產取得行為只能依據不動產登記簿所表明的主觀和客觀權利狀況來進行,即使取得人沒有查閱不動產登記簿,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也被視為對其是已知的并且對其有效。這就促使取得人實際上必須要去查閱不動產登記簿,因為取得人不得以沒有查閱不動產登記簿為理由作為主張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保護的抗辯。因此,取得人無需查閱不動產登記簿構成了客觀信賴的表現形式,但并不是客觀信賴產生的原因。
在瑞士,取得人無需查閱不動產登記簿的原因與德國法類似,同樣是基于善意推定和不動產登記簿的公開性。只不過,在立法技術上,這兩個方面不是通過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規定的,而是分別在《瑞士民法典》第 3條第 1款的善意推定條款和第 970條不動產登記簿的查閱條款中規定的。對取得人而言,善意推定的好處在于,法律假定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要求的前提條件都已經具備。基于善意推定,取得人可以認為不動產登記簿的登記是正確的和完整的,他不必通過查閱不動產登記簿的憑證來核對債權行為是否有效,也不用證明自己對登記簿內容的明知。這種推定完全符合第 970條關于登記簿查閱的規定,取得人不必表示他實際上查閱了不動產登記簿的各個組成部分,因為登記簿的內容原則上被視為是已知的。雖然第 973條要求取得人“出于善意信賴不動產登記簿的登記”,但是結合善意推定和登記簿的公開性來看,這樣規定顯然假定取得人已經知道了登記的內容,并對其善意進行保護——即便他實際上并不真正知道不動產登記簿的內容。為了防止這種做法帶來的不利后果,第 970條第3款也要求任何人不得提出其不知不動產登記簿上登記的抗辯,此外,如果原權利人能證明他有理由懷疑取得人的善意,那么這種善意推定將被推翻。〔44〕Vgl.Heinz Rey,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3.,ergaenzte u.ueberarbeitete. Aufl.,StaempfliVerlagAGBern,2007,S.388;HenriDeschenaux,Das Grundbuch,SPR,V/3,II,Helbing&Lichtenhahn Verlag,Basel u.Frankfurt am Main,1989,S.790.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瑞士法也基于善意推定和不動產登記簿的公開性免除了取得人的查閱義務,但是由于瑞士法要求取得人必須信賴不動產登記簿并且強調信賴和善意保護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它并沒有像德國法那樣實現信賴保護的客觀化,而是對取得人提出了注意義務的要求。由德國法和瑞士法對查閱義務的規定可以看出,善意要件無論在德國法還是瑞士法上都不是作為積極要件出現的,而是從法律技術角度被推定的。這種推定的技術在免除了取得人對善意的證明責任的同時,也達到了免除其查閱義務的效果。由此來看,善意推定、不動產登記簿的公開性以及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三者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聯,它們之間通過立法技術的方式實現了邏輯上的銜接。總的看來,這兩個國家對取得人的信賴進行保護的基礎均建立在善意推定的規定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取得人實際的查閱行為和查閱結果之上。所不同的是,瑞士法仍然強調取得人對不動產登記簿的具體的、個人化的信賴,強調個人的行為(包括了注意義務的履行)與善意保護之間的因果關系;而德國法所突出的是一種對潛在信賴的保護,強調的是不動產登記簿內容的可靠性、可信賴性,不要求個人的行為與善意保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也因此免除了所有的注意義務。
(二)調查義務
瑞士學者認為,要證明取得人明知或應知不動產登記簿不正確,明顯過于困難。因此,法律只要求,如果取得人盡到一定情勢所要求的注意義務,那么就應該能認識到不動產登記簿的不正確。注意義務的依據是《瑞士民法典》第 3條第 2款。雖然從字面意義來看,該條款可以解釋成善意應當排除輕過失,但法院并沒有用過錯作為善意的衡量標準,也沒有采取嚴格的過失劃分標準。學界和司法界普遍主張,應以客觀化標準來衡量注意義務,而不應直接采取無過失標準來界定善意的范圍。其原因在于:有時只要行為明確地偏離了一般的行為標準,就可以排除善意,并不要求行為人有重大過失;而在另一些情況下,行為人只有在具有重大過失時,才能被排除善意。這說明,過失程度與善意要件之間缺乏規律性的聯系。實踐中,法院一般也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掌握輕過失和重過失的程度,而沒有對注意義務的程度做出嚴格區分。學界和司法界公認的衡量注意義務的客觀化標準為,在特定的情況下經常采用的一般標準(Durchschnittsmass),其常根據生活經驗和專家意見來確定。它要求行為人具有通常的理解力和勤勉程度,其行為符合一個正常的、并且是正直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對待他人利益的方式。〔45〕Vgl.Peter Jaeggi,Berne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recht,Einleitung,Art.1-10ZGB,Verlag Staempfli&CIE.,Bern,1962,S.411f;Rudolf Pfister,Der Schutz des oeffentlichen Glaubens im schweizerischen Sachenrecht,Verlag Schulthess&Co.AG,Zuerich,1969,S.68f.
根據學術界對客觀化標準的理解,司法界通過判例確立了注意義務的標準:如果取得人獲悉了一個事實,而這個事實足以引起一個具有通常的智力和注意程度的人對不動產登記簿正確性的懷疑,那么此時取得人應負有對這一事實進一步調查的義務。取得人履行調查義務的目的,在于消除自己對不動產登記簿的懷疑,并由此確立對不動產登記簿的信賴。那么,他的調查義務應當涉及哪些內容呢?學術界的看法是,調查的范圍不應當僅局限于不動產登記簿的主簿(Hauptbuch)所記載的內容,還應當包括其他可能導致不動產登記簿之登記不正當的憑證、登記日志,必要時應進行實地察看。進行實地察看的依據是《瑞士民法典》第 676條第 3款規定的自然公示 (natuerliche Publizitaet)。〔46〕該款規定:“前款的地役權,如管道未暴露于地面的,依不動產登記簿的登記產生;其他情形,依該管道的安置而產生。”雖然這一條款本來的適用范圍是外在的管道,但對這一條款的適用范圍可以進行擴展,使其也適用于不動產的外在物理狀況。依據自然公示的法理,與不動產外在狀況有關一些情況可能在不動產登記簿中并未被登記為物權,但這些情況的存在可能會對不動產物權造成重要影響。取得人如果沒有通過調查去查知這些不動產的外在狀況,那么他不能主張自己是善意的。此外,還有一些問題并不適用自然公示的法理,因為這些情況的存在與不動產本身并無直接關系,但有可能構成不動產周圍重要的環境,例如過道、圍墻等外圍設施,這些設施的存在無法運用自然公示來確定其物權歸屬。如果根據一般交易習慣的要求,這些設施的存在可能對不動產物權交易產生重要影響的,那么取得人也應當盡到相應的調查和詢問義務。否則,取得人不得主張自己為善意。〔47〕Vgl.Basler Kommentar ZGB/Juerg Schmid,II,3.Aufl.,Helbing&LichtenhahnVerlag,Basel,2007,S. 2368.
取得人不僅要關注與不動產登記簿有關的登記材料和不動產的實際狀況,還應當對與不動產交易有關的其他登記簿(如商事登記簿)的登記有充分的了解。此外,對于夫妻一方處分共同財產的問題,取得人也應履行一定的調查義務。〔48〕Vgl.Heinz Rey,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3.,ergaenzte u.ueberarbeitete. Aufl.,StaempfliVerlagAG,Bern,2007,S.390.《瑞士民法典》第 228條第 2款規定,只要第三人不知或理應不知(wissen sollte)缺少另一方處分共同財產的同意,允許其以該同意為先決條件。從這一條款的規定來看,取得人雖然可以假定另一方已經同意對共同財產的處分,但他必須對此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
五、關于我國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體系性思考
從德國、瑞士法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規定來看,善意要件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物權變動模式和不動產登記程序法的規定。這些法政策選擇背后既有經濟和道德因素,也有一定的交易習慣和法律文化背景。以下將對我國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進行系統分析。
(一)物權變動模式
關于我國物權法規定的物權變動模式,有兩種代表性學說:債權形式主義說和物權形式主義說。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將登記機關的登記行為看作不動產登記效果發生的生效要件。區別之處在于,債權形式主義否認物權行為的獨立性,認為不動產登記是履行債權意思的結果;而物權形式主義則認為,不動產登記的結果是履行物權意思的效果,承認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抽象性。
這兩種學說均系舶來品,前者以奧地利法為藍本,后者以德國法為淵源。這兩種立法模式的爭議在我國由來已久,在《物權法》頒布之后仍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筆者認為,我國學者對奧地利和德國法上物權變動模式的理解不夠全面,主要體現在對登記行為性質的認定上。在我國學者看來,這兩種學說都將登記效果看作是實體法上的意思表示 (債權意思或物權意思)加登記行為的結果,然而,這種解讀方式忽視了不動產登記程序的獨立性。這兩種學說都將不動產登記過程看作是當事人的法律行為與不動產登記機關的登記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卻未對不動產登記過程中當事人登記申請行為的性質給予足夠關注。換言之,在這兩種物權變動模式中,登記機關的登記記載行為替代了當事人在登記過程中可能的意思表示行為。
由前面對德國和瑞士不動產物權變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德國法上的不動產登記過程為登記申請(程序行為)+物權合意(或登記同意)+登記記載,而在瑞士法和奧地利法上,不動產登記過程可概括為債權行為 +登記申請 (或登記同意)+登記記載,而登記申請 (或登記同意)被視為單方物權行為。〔49〕參見常鵬翱:“另一種物權行為理論——以瑞士法為考察對象”,《環球法律評論》2010年第 2期,頁 101;Bernhard Eccher,Kurzkommentar zum ABGB,hrsg.von Helmut Koziol,PeterBydlinski,Raimund Bollenberger,2.ueberarb.u.erweiterte Aufl.,Springer,W ien,New York,2007,S.389,S.405;Franz Bydilinski,Rechtsgeschaeftliche Voraussetzungen der Eingentumsuebertragung,in Festschrift fuer Karl Larenz,Hrsg.Von Gotthard Paulus,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Muenchen,1973,S.1028.瑞士法和奧地利法并非不承認(單方)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只不過它們均不認可物權合意的獨立性,而使得物權變動效果仍然依賴于債權行為的效力。遺憾的是,我國的兩種學說都沒有注意到德國法、瑞士法和奧地利法對不動產登記程序中登記申請或登記同意的規定。
(二)不動產登記申請行為
關于登記行為的性質,我國學者主要有三種見解:債權行為外在形式說、行政行為說和物權合意外在形式說。債權行為外在形式說和行政行為說的基礎都是物權變動模式上的債權形式主義。這兩種學說均認為,物權變動以“債權行為加登記 (交付)生效主義”為特征,否認物權行為的獨立性。不同的是,債權行為外在形式說只是將登記行為看作債權行為的外在形式,未對其作進一步的定性。〔50〕參見梁慧星:“對物權法草案(第四次審議稿)的修改意見”,載吳漢東、陳小君主編:《私法研究》(第 6卷),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頁 75;崔建遠,見前注〔9〕,頁 49。而行政行為說則認為,登記行為是不動產登記機關的依法而為的公法行為,并非民事行為。〔51〕參見王澤鑒,見前注〔10〕,頁 79;王利明,見前注〔8〕,頁 262,這位學者對不動產登記行為的性質和物權變動模式的理解前后有不一致之處。在同一本書的頁 305,他認為登記有民事行為屬性。在此書的頁255-256,他贊同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債權形式主義說,而在頁 305,他又認為不動產變動之實體法上法律效果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當事人之間的物權合意,而非登記機關的登記行為。物權合意外在形式說認為,物權法采取的是物權合意加登記行為的物權變動模式,登記行為是物權合意的外在形式,不動產登記機關應視為民事司法機關,登記行為應看作民事行為。〔52〕參見孫憲忠:“我國物權法中物權變動規則的法理評述”,《法學研究》2008年第 3期;孫憲忠:《中國物權法總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頁 334。
這三種學說皆以不動產登記機關為主體來分析登記行為的性質。這種做法雖關注了登記結果,卻忽視了登記申請人的申請行為。前已述及,與物權變動模式直接相關的是登記申請人申請行為的性質。根據我國不動產登記程序法,登記申請以雙方共同申請為原則,以單方申請為例外。就不動產善意取得而言,主要涉及雙方登記申請的情形。此時,雙方當事人必須到場,在不動產登記機關面前就不動產物權的處分達成一致意思,并共同填寫書面的登記申請書。以《北京市房屋所有權轉移登記申請書》為例,該申請書共分三個部分:一是房屋位置、權屬證書號以及房屋狀況;二是房屋買賣有關的價款、契稅、購房時間;三是雙方申請人的信息及簽名。如何認定登記申請書的性質,成為認定登記申請行為性質的關鍵。登記申請書雖然形式上是雙方為了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而向登記機關提交的格式文件,但從法律關系來看,其實際上構成了對申請登記的不動產的處分行為。根據登記申請書直接發生不動產物權設立、變更和消滅的法律效果,而不是產生債權性質的請求權。不動產登記機關進行登記所依據的正是不動產登記申請書。因此,在共同申請登記的情況下,登記申請書應視為雙方當事人對不動產進行處分的物權合意。
不動產登記申請在德國和瑞士法上均以單方行為出現,且德國法上僅具有程序法意義,與之相比,我國關于雙方登記申請行為的規定具有獨特性。不過,從要求提交的登記申請材料來看,我國不動產登記的效果仍依賴于債權行為的效力。申請人在提交不動產登記申請時需要提供權屬證明和債權合同。不少地方不動產登記實施細則和登記收件辦法等也將債權合同列為必備申請材料。不僅如此,多數法院在審理不動產善意取得案件時,也以合同的有效性作為判定不動產善意取得的基礎。這充分說明,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效果雖源于法律規定,但其仍受到債權合同效力和前手登記行為瑕疵的影響。這一點集中地體現在對取得人注意義務的要求上。
(三)關于注意義務的規定
從《物權法》和不動產登記程序法的規定來看,在進行不動產登記時,取得人必須盡到一定的注意義務,這體現在不動產物理狀況、不動產權屬狀況和不動產實地調查三個方面。
就不動產物理狀況而言,申請人應提交與不動產物理狀況有關的證明材料,如地籍調查表、宗地圖及宗地界址坐標、房屋平面圖、房屋勘測報告等。〔53〕參見《物權法》第 11條、《土地登記辦法》第 9條第 4款、《上海市房地產登記技術規定(試行)》2.9等。這些屬于與土地登記密切相關的其他證明材料,或者現場勘查材料。這間接地體現了取得人在進行土地登記時應履行的注意義務。
登記機關對申請人進行詢問體現了對處分權限的審查。不動產登記簿具有權利推定效力,處分人的處分權無需通過詢問程序加以確認。但是,不動產登記的規范性文件均將對處分權的詢問列為不動產登記機關的職權。〔54〕參見《物權法》第 12條第 2款、《房屋登記辦法》第 18條。根據《珠海市房地產登記詢問表填寫說明》的規定,申請人需對與其處分權有關的問題進行回答,如是否存在其他共有人、申請登記的房地產是否不存在產權糾紛、不存在查封或者預查封等權利限制等。若存在這些權利限制情形的,登記機關可不予受理。
由于我國沒有關于善意推定的規定,不動產登記機關的詢問程序顯然暗含了要求取得人盡到查閱義務的意義。與不動產處分權有關的事項屬于實體權利狀況,取得人在進行不動產交易時是否知道這些情況,并不應構成取得人善意取得的前提。只要取得人信賴不動產登記簿的記載,就應該受到善意保護。關于詢問和查閱義務的上述規定,起到了進一步確認不動產的權屬狀況,從而保證登記權利與實體權利一致的目的。這些規定的實際目的在于,“規避因當事人提供虛假、隱瞞真實情況所引發的行政及法律風險”(《珠海市房地產登記詢問表填寫說明》二、表格制定目的)。這些規定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將一般交易中的查閱義務等注意義務法定化的作用,登記機關扮演了督促、協助申請人履行注意義務的角色。此外,不動產登記機關還具有實地查看的職權,其目的仍是為了保證登記權利與實體權利的一致性,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幫助當事人履行了注意義務。
我國之所以在注意義務方面做出了不同于德國和瑞士法的規定,是出于以下原因:第一,我國土地實行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因此不動產物權的變動不能完全視為是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私法行為。至少就土地權利而言,土地是否存在閑置、是否應當收回等不動產登記的實質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國家和集體的利益。不動產登記機關為了保證實質合法性而規定這些審查程序,實際上超越了登記機關的中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以往的行政管理職能。第二,我國房、地分離登記的二元制的登記體制決定了不動產交易主體必須履行更多的注意義務,例如查閱、核實房屋和土地權屬證書、登記簿等,以規避登記體制本身帶來的風險。第三,交易習慣使然。農村的房屋長期不進行登記,家庭共有、夫妻共有的房屋常常登記在一人名下,這些現象非常普遍,也屬于基本的交易常識。這就要求取得人在進行不動產交易時,應當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而不是閉目塞聽,對可能是共有的房屋不進行查證。這事實上對真正的權屬狀況的不知起到了間接放任的作用。
(四)關于借鑒瑞士法關于善意規定的意見(代結語)
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兼具了依法律行為和依法律規定發生物權變動這兩種方式的特征。該制度法律效果的法定性通常會排擠其在法律行為方面的特征。從形式上看,善意要件的判定與善意推定、不動產登記簿的正確性擬制密不可分,就實質上而言,善意要件的確定始終以物權行為的抽象性或有因性為根基。在善意要件賴以存在的法律行為中,與善意要件相伴生的注意義務體現的正是法律行為所具有的特征。只不過,在法政策的選擇上,德國法采取了不動產和動產的二元論思想和物權行為的抽象性理論,實現了善意要件和注意義務的分離;而在瑞士,物權變動效果始終與債權行為的效力相聯系,這就使得善意要件的判定與注意義務緊密相連。
由于我國并未明確規定善意推定和不動產登記簿正確性的擬制,因此,對于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判定必須以法律行為 (不動產交易行為)作為切入點。結合不動產交易程序法和不動產交易的習慣來看,不動產登記程序法關于雙方登記申請和登記申請材料等相關規定體現了物權行為的有因性和對注意義務的要求。綜上所述,在理解我國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時,應結合法律行為和注意義務進行系統性思考。可適當借鑒瑞士法不動產登記簿公信力制度關于善意要件的規定,來進一步明確我國法關于善意的范圍和判斷標準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