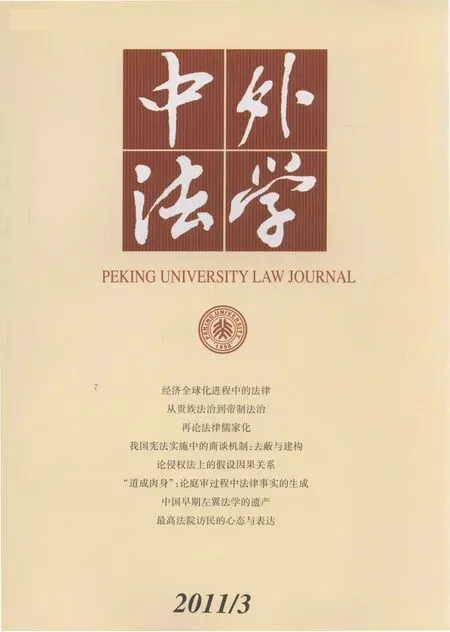我國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問題研究
張 鵬
保證債務作為一種債務,理當受訴訟時效的約束。然保證往往附有保證期間,一定情形下,隨著保證期間的屆滿,保證債務也隨之消滅。那么,保證期間和同為期限性質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此外,一般保證中,保證人通常享有先訴抗辯權,即保證人通常僅在債權人起訴并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仍不能實現債權時,方才承擔剩余部分的清償責任。這必然又牽涉到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起算與保證人先訴抗辯權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對于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及其和保證期間、先訴抗辯權之間的關系,學術界多有論述,但一直未形成共識。〔1〕近年來的一些參考文獻如:奚曉明:“論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中國法學》2001年第 6期;張谷:“論約定保證期間——以《擔保法》第 25條和第 26條為中心”,《中國法學》2006年第 4期;鄒海林:“論保證責任期間”,《民商法論叢》(第 14卷),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崔建遠:“保證債務與訴訟時效”,《人民法院報》2003年 6月 6日;蘇號朋:“論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載沈四寶主編:《國際商法論叢》(第 7卷),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曹士兵:《中國擔保制度與擔保方法——根據物權法修訂》,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民法通則》(1986年)、《經濟合同法》(1982年,已廢止)均未涉及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等問題。最高法院《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1994年)、《擔保法》(1995年)、最高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年)對于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及其保證期間、先訴抗辯權等問題均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但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國相關法律法規還沒有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問題做出科學、合理的規定。甚至于,依照最高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34、36條,竟然出現了“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尚未起算卻已經中斷”的荒唐結果。相關司法解釋起草者也不得不承認“實際上是不會存在的,這是一個紕漏”。〔2〕奚曉明:“論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中國法學》2001年第 6期,頁 64。
基于以上理論和實踐中的爭議,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及其和保證期間、先訴抗辯權等相關制度之間的關系竟被稱之為擔保法領域中“最為復雜”的問題。〔3〕有趣的是,最高法院相關人士似乎將問題歸咎于《擔保法》,“保證期間是擔保法規定的最為復雜的一個概念,司法實踐對保證期間的法律適用爭議紛呈,有些爭議還涉及到擔保法本身的錯誤。”(參見曹士兵:《中國擔保法諸問題的解決和展望》,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頁 132。)然梁慧星先生則將問題歸咎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就此問題反反復復地進行一些不可理解的解釋,形成今天看起來最為復雜的保證期間問題。”(參見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 32卷),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卷首語,頁 3。)
本文試圖從我國相關法律法規著手,在厘清現有規范立法原委的基礎上,比較不同立法例,正本清源,廓清相關概念、制度之本來含義,以期能夠對該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重構相關制度。
一、保證期間的法律效力和法律性質
對于保證期間的性質,學術界主流觀點曾一度認為是訴訟時效,〔4〕參見李明發:“論 <擔保法 >關于保證制度之若干新規定”,《法律科學》1996年第 6期;龍衛球:《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頁 693。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則一直將其理解為是除斥期間。〔5〕在最高法院《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1994年)和最高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年)中,最高法院都是將保證期間性質理解為除斥期間。參見李國光等:《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頁 146-147;最高法院經濟庭編著:《保證合同糾紛案件審判實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4年版,頁 32。目前,這兩種觀點均受到了嚴厲批評。〔6〕參見崔建遠主編:《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頁 182以下。當下主流觀點認為,保證期間是一種訴訟時效期間和除斥期間以外的獨立期間,然具體的法律性質,尚未有定論。在此,本文不直接探討保證期間的法律性質,而將更“現實”地研究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存續之間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關系,學界稱之為“保證期間的法律效力”,〔7〕參見高圣平:《擔保法論》,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頁 132。而后再依研究結果判斷保證期間的法律性質。
對于保證期間的法律效力,我國學界似乎并未引起足夠重視,我研究認為,此問題實際上存在不同立法例。根據本人研究心得,對不同立法模式概括如下:
(一)模式一:保證債務請求權存續期間模式——以臺灣地區為例
臺灣地區民法典第 752條規定:“約定保證人僅于一定期間內為保證者,如債權人于其期間內,對于保證人不為審判上之請求,保證人免其責任。”
臺灣地區民法認為,“所謂約定保證人僅于一定期間內為保證者,乃指就已確定之債務為保證,而對保證債務本身定有存續期間,約定債權人應于保證債務存續期間內向保證人為請求,期間經過,保證債務當即消滅,通稱之為定期保證。”〔8〕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年版,頁 408。“于保證附有期間,依當事人之意思得為負責之期間,于其期間經過后,保證即行消滅。”〔9〕史尚寬:《債法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頁 936。
依上所述,所謂保證期間者,乃保證債務的存續期間,即保證債務僅在保證期間內存續。申言之,債權人只能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保證期間屆滿,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即告消滅,債權人當不可以再向保證人主張權利。其法律效果類似于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隨著期間屆滿,保證債務之實體權利即告消滅。
但是,若嚴格按上述思路,立法將過于偏向保證人,對于債權人過于苛刻,故第 752條在遵循上述認識的基礎上,又適當限制了保證債務隨保證期間而消滅,即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為“審判上之請求”〔10〕依臺灣地區學界通說,與起訴具有同一效力之行為,如送達支付命令、申報破產債權、開始執行行為、申請強制執行、申請法院調解、申請拍賣擔保物等,亦為“審判上之請求”。參見歐陽經宇:《民法債編各論》,漢林出版社 1978年版,頁 319。的,保證債務將特例不因保證期間屆滿而消滅。正如此條立法理由所稱,“至保證債務,其自己定有期限者,若使保證人于其期限經過后,即時可以免責,于保護債權人利益,未免過薄。故特設本條,債權人不于期限內向保證人為審判上之請求者,保證人始能免責。”
上述第 752條系關于一般保證之規定。依臺灣地區學界通說,連帶保證亦準用該條。〔11〕參見錢桐蓀:“保證責任研究”,載鄭玉波主編:《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84年版,頁 1423。因此,連帶保證中,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亦只在保證期間內存續,將隨著保證期間的屆滿而消滅。
上述立法例中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一般保證中,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在保證期間內,若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保證人往往可以先訴抗辯權相對抗。若如此,如何要求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為“審判上之請求”呢?又如何能夠規定因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為“審判上之請求”而使保證債務消滅呢?對此,臺灣地區民法認為,保證人存在先訴抗辯權并不排斥債權人對于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因此,債權人完全可以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權利,要求其承擔保證債務。然鑒于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故法院在裁判時,必須明確保證人的保證債務需以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為前提,否則,保證人可以拒絕承擔責任。如臺灣地區學者邱聰智先生所言:
債權人未經強制執行主債務人之財產,即徑向保證人為訴訟上請求,而保證人行使先索抗辯權(即先訴抗辯權——本文作者注)者,亦不生否認債權人請求之效果,法院亦不得對債權人徑為駁回之敗訴判決,但亦不得為保證人應當然為給付之敗訴判決。換言之,于此情形,亦有如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援用,法院應依先索抗辯權行使,對原告為限制勝訴之判決,至其判決主文內容則為“被告(保證人)于原告 (債權人)就訴外人 (主債務人)之財產執行無效果時,應給付原告……”。如原告對主債務人及保證人同時起訴者,于此情形,其判決主文內容略作調整而為:“被告 (保證人)于原告 (債權人)就其他被告 (債務人)之財產執行無效果時,應給付原告……。”〔12〕邱聰智,見前注〔8〕,頁 383。
前蘇聯民法似乎采用了和臺灣地區相同的立法例。《蘇俄民法典》第 250條規定:“債權人在主債務到期后的三個月內不對保證人提起訴訟的時候,保證就算消滅。如果主債務沒有規定履行期限,也沒有其他協議的時候,保證人的責任在訂立保證合同一年后就消滅。”〔13〕鄭華譯:《蘇俄民法典》,法律出版社 1956年版,頁 58。此處,前蘇聯民法未采納約定的保證期間,而將保證期間一律法定為三個月,逾此期間,債權人未對保證人起訴的,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即告消滅。〔14〕參見(前蘇聯)B·Ⅱ·格里巴諾夫、C·M·科爾涅耶夫主編:《蘇聯民法》(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經濟法研究室譯,法律出版社 1984年版,頁 485。〔15〕現今《俄羅斯民法典》有關保證期間的性質還是采用相同見解。但是,其已經允許當事人首先約定保證期間,而在沒有約定保證期間的情況下,法定保證期間為一年。(參見《俄羅斯民法典》第 367條第 4款)
從以上內容可見,該立法例認為,保證期間法律性質為“保證債務的存續期間”,指債權人對(一般或連帶)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僅在保證期間范圍內存續,隨著保證期間的屆滿,保證債務將消滅。我大陸學者亦有持相同看法的,如蘇號朋先生認為,“保證期間就是普通的權利存續期間,與其他的合同履行期間并無區別。”〔16〕蘇號朋,見前注〔1〕,頁 411-412。類似觀點如:周愷先生認為,“保證責任期間就是保證合同所附的終止期限。保證責任期間屆滿則保證合同失效。從這個意義上講,保證責任期間也是保證效力的存續期間。”(參見周愷:“保證期間及保證中的相關問題辨析”,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 32卷),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頁 547);陳貴先生認為,“保證期間就是保證合同當事人的約定或依法律推定在主債務履行期屆滿后,保證人能夠容許債權人主張權利的最長期限。”(參見陳貴:“論保證期間”,《清華法學》(第三輯),頁286);鄒海林先生認為,“保證期間極為類似于附期限(終期)的債;但保證債務又不同于附期限的債。保證期間為保證人能夠容忍債權人不行使權利的最長期間。”(參見鄒海林,見前注〔1〕,頁 150-151)
(二)模式二:保證債務請求權附解除條件模式——以德國為例
《德國民法典》第 777條規定:
①保證人為現存的債務、針對確定的時間做出保證的,除債權人依照第 772條不遲延地收取債權,在無顯著遲延的情況下繼續程序,并且在程序終結后不遲延地通知保證人,謂其將向保證人提出請求外,在確定的時間過去后,保證人即免除責任。保證人不享有先訴抗辯權的,除債權人將這一情況不遲延地通知保證人外,在確定的時間過去后,保證人即免除責任。②債權人適時地進行通知的,在第 1款第 1句的情況下,保證人的責任限于程序終結時主債務的范圍;在第 1款第 2句的情況下,保證人的責任限于確定的時間過去時主債務的范圍。
依照上述條款:(1)一般保證中,債權人若想延續對保證人的保證債權,則必須在約定的保證期間內,依照第 772條〔17〕《德國民法典》第 772條:“①保證為金錢債權而存在的,必須嘗試在主債務人的住所強制執行其動產;主債務人在另一地有工商營業所的,也必須嘗試在該地強制執行其動產;既無住所也無工商營業所時,必須嘗試在其居留地強制執行其動產。②債權人享有主債務人的動產上的質權或者留置權的,債權人也必須尋求從該動產中受清償。對于另一債權,債權人也享有該動產上的此種權利的,只有在這兩項債權被以該動產的價額抵償時,才適用前句的規定。”對債務人提起(注意:無需提起并結束)相關司法程序,并“在程序終結后不遲延地通知保證人,謂其將向保證人提出請求”。〔18〕Palandt,Buergliches Gesetzbuch,66.Auflage,2007,S.1137.換言之,只要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依第 772條啟動相關程序,即可“避免保證因期間屆滿而消滅”。〔19〕(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等譯,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頁 426。此外,保證債務將限于上述債權人對債務人程序終結時主債務的范圍。反之,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向債務人提起相關司法程序的,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將消滅。
(2)連帶保證中,債權人若想延續對保證人的保證債權,則必須在約定的保證期間內“將債務人未清償債務這一情況不遲延地通知保證人”。〔20〕見前注〔18〕,S.1137.換言之,只要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及時通知保證人,即可“避免保證因期間屆滿而消滅”。此外,保證債務將限于上述保證期間屆滿時主債務的范圍。反之,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向債務人為上述通知 (即未向保證人主張權利)的,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將消滅。
德國民法中的保證期間制度雖沒有臺灣地區那么簡潔明了,但其兼顧各方當事人利益的架構,還是十分精巧的。①一般保證中,考慮到保證人存在先訴抗辯權,故借助于保證期間的督促,債權人將不得不及早對于債務人提起強制執行程序,從而及早明確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并以此固定保證債務范圍,防止加重保證人負擔。同時,和前述模式不同,債權人并不需要在保證期間內必須對保證人為訴訟上請求,而可在保證期間屆滿后自由選擇行使時機,亦不失為對債權人利益的兼顧。②連帶保證中,為了保護保證人利益,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對保證人為通知,以及早明確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及其范圍。同時,債權人也無需限定于保證期間內必須提起對保證人的訴訟上請求,以兼顧債權人利益。
從以上內容可見,該立法例認為,保證期間實質上僅是要求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一般保證)或對保證人 (連帶保證)為一定行為,否則,將因為未具備相應條件而消滅保證債務。如此,保證期間法律性質上當屬于“保證債務所附加的一個解除條件”,即未在相應期限內實現某種條件者,保證債務將因此消滅。對此,亦有大陸學者持相同看法。如秦鈺先生認為,“如果當事人約定了保證期間,那實際上就是當事人特別約定的一個保證債務的解除條件;當事人未約定而法律規定的 6個月期間,就是一個法定的期間,它的內容是:在該期間內,如果債權人不為一定行為,則保證人免責。”〔21〕秦鈺:“論保證期間”,載《民商法論叢》(第 26卷),香港金橋文化出版公司 2003年版,頁 480。
(三)我國保證期間的法律效果和法律性質——以解釋論為中心
我國法律法規中最早出現保證期間概念的是最高法院《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1994年)(以下簡稱“《保證規定》”),其思路顯然是借鑒了臺灣地區和前蘇聯立法例。《保證規定》第 10條規定:“保證合同中約定有保證責任期限的,保證人在約定的保證責任期限內承擔保證責任。債權人在保證責任期限內未向保證人主張權利的,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從該司法解釋起草者的表述中,我們似乎可以認定,保證期間就是保證債務的存續期間,保證期間屆滿,保證債務即告消滅,且無任何例外事由。如“保證責任的期限是指依法律的規定或依當事人的約定,保證人只在一定的期限內承擔保證責任”;“保證合同明確約定有保證責任期限的,債權人應在約定的期限內主張權利,若超過該期限而主張權利的,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保證責任即告消滅。”〔22〕最高法院經濟庭編著:《保證合同糾紛案件審判實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4年版,頁 31、35。1995年 11月 6日《最高法院對安徽省高院關于借款擔保合同糾紛請示問題的答復》中,曾經有相同的表達。這也是和當時學界的通說相吻合的,“如果保證合同約定保證人僅在一定期間內負保證責任,債權人在此期間沒有向保證人提出履行請求,保證人可免除責任。”〔23〕王家福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法律出版社 1991年版,頁 106。
從以上內容可見,《保證規定》是將保證期間法律效果理解為“隨著保證期間屆滿,保證債務即告消滅”,相應地,保證期間的法律性質應當理解為“保證債務的存續期間”。但問題是,如前所述,為何最高法院一直將保證期間法律性質定性為“除斥期間”呢?我認為,這是因為當時法學研究水平較弱,以致誤認為所有的權利存續期間都應稱之為“除斥期間”,而非僅形成權的存續期間稱為“除斥期間”。此種誤解,數年后,在最高法院相關人員的意識中仍然存在,“所謂除斥期間,是指法律規定的某種權利存續的期間,當期間屆滿時該權利消滅。……保證期間是法律規定債權人行使請求權的效力存續期間,是保證合同的效力存續期間,保證期間屆滿即發生權利消滅的法律后果,債權人在此期間內沒有行使請求權,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這完全符合除斥期間的特點。”〔24〕奚曉明,見前注〔2〕,頁 58。
《擔保法》(1995年)延續了《保證規定》的思路。根據起草者的解釋,“保證的期間,是指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起止時間,保證人在規定的期間內承擔保證責任,過了該期間,即使債務人未履行債務,保證人也不再承擔保證責任。”〔25〕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釋義》,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頁21。
但是,這里存在一個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權利和一般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之間的沖突問題。由于法學研究水平滯后,當時普遍認為,一般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并非指保證人享有對抗債權人的抗辯權,而是指向一般保證人主張權利的先決條件是,債權人必須先向債務人主張權利,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
一般保證的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保證人只有在主合同糾紛經審判或者仲裁,并就債務人財產依法強制執行仍不能履行債務后,才承擔保證責任,所以,在一般保證的法律關系中,債務人是債務履行的第一順序人,債務人首先應當對債務承擔責任;保證人則對債務履行處于第二順序,保證人在債務人不能或不完全承擔責任時,對債務承擔補充責任。〔26〕同上注,頁 21-22。此思路和《保證規定》思路是一致的,《保證規定》第 7條規定:“保證合同沒有約定保證人承擔何種保證責任,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保證人承擔賠償責任。當被保證人不履行合同時,債權人應當首先請求被保證人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被保證人的財產仍不足以清償其債務的,由保證人承擔賠償責任。”
因此,我們當時根本沒有前述臺灣地區立法例中債權人可以在保證期間內起訴一般保證人(或和債務人一起列為共同被告)的觀念。如此,即產生了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向一般保證人主張權利,否則保證債務消滅,然若主張權利,則又因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而欠缺請求權基礎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擔保法》引入了一般保證保證期間可因債權人向債務人起訴或申請仲裁而適用訴訟時效中斷的規定。〔27〕參見李國光主編:《擔保法新釋新解與適用》,新華出版社 2001年版,頁 286。
如此,我們方才可以理解《擔保法》第 25條第 2款規定:“在合同約定的保證期間和前款規定的保證期間,債權人未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債權人已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期間適用訴訟時效中斷的規定。”(一般保證)第 26條第 2款規定:“在合同約定的保證期間和前款規定的保證期間,債權人未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連帶保證)
但是,《擔保法》第 25條第 2款在規定“一般保證保證期間適用訴訟時效中斷的規定”后,沒有將其意思表達完全,而是戛然而止。也正是這種不清晰的表述,變成了此后一般保證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糾纏不清的“潘多拉盒子”。也許,若《擔保法》第 25條第 2款清楚地繼續規定“如果債權人已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保證期間中斷,在重新計算的保證期間內,債權人未請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28〕武靖人等主編:《中國擔保法律與實務》,中信出版社 1997年版,頁 94。相同觀點參見鄒海林等:《債權擔保的方式和應用》,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頁 73。則此后的爭議要小得多。
(四)我國保證期間法律效力和法律性質立法建議
筆者認為,“保證債務請求權附解除條件模式”更值得借鑒。
保證期間系為保護保證人利益而設,但也必須兼顧債權人利益。〔29〕參見李明發:《保證責任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頁 108。相較而言,“保證債務請求權附解除條件模式”(以下簡稱“附解除條件模式”)比“保證債務請求權存續期間模式”(以下簡稱“存續期間模式”)更能衡平各方當事人利益,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具體而言:
第一,“存續期間模式”將債權人對保證人的權利存續期間僅僅局限于保證期間內,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對保證人提起訴訟,對于債權人過于嚴苛,特別是在保證期間通常約定期限較短的情況下。
第二,“存續期間模式”對于債權人過于嚴苛,反而有可能損及保證人利益。如果保證債務僅僅在一定期限內存在,逾期將不復存在,則必將實質上刺激債權人及早對保證人行使權利,甚至于動用公權力強制執行。然反之,考慮到一定條件下,保證債務在保證期間后將繼續延續,債權人也許就不會過于匆忙對保證人主張權利了,可以對保證人寬以時日。要注意,履行期限對于保證人而言,也是一種重大利益啊。
第三,“附解除條件模式”已經起到了保護保證人利益的效果。參照德國立法例,借助于保證期間制度,已經起到了督促債權人及早對債務人強制執行,從而確定保證人保證債務以及限制保證債務范圍的效果。對于保證人而言,在明確其保證債務以及范圍的前提下,一種是債權人受制于較長時間的訴訟時效,故而未必急于對保證人主張權利;一種是債權人受制于較短時間的保證期間,故可能不得不急于對保證人主張權利,顯然,還是前者對其更有利。
第四,我國法中,也許理論或立法初衷是采用“存續期間模式”,然實質上卻似乎采用的是“附解除條件模式”。從《保證規定》到《擔保法》,直至最高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年)(以下簡稱“《擔保法解釋》”),均未徹底貫徹保證期間為保證債務“存續期間模式”,并沒有規定,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對保證人為訴訟上請求的,保證債務即告消滅。以《擔保法》為例:①連帶保證中,《擔保法》第 26條雖規定,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對保證人主張權利的,保證債務消滅,但根據《擔保法解釋》第 36條第 2款,其只要主張了權利,保證債務在保證期間屆滿后即不會消滅。這一處理和“附解除條件模式”何其相似!②一般保證中,受制于當時對先訴抗辯權概念的錯誤理解,《擔保法》第 25條第 2款規定,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債務消滅。雖然和立法動因相差甚遠,但該表述結果和“附解除條件模式”何其相似!如此規定,也許是考慮到強令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對保證人為訴訟上請求的不可行性,樸素地為了追求公正的司法實踐效果。但是,無論如何,其結果造成了我國當前有關保證期間相關立法表述與“附解除條件模式”的暗合。
綜上,就我國保證期間法律效力的重建問題,我建議:①就一般保證而言,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起訴或申請仲裁的,保證債務消滅;反之,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起訴或申請仲裁,并在相關執行程序結束后及時通知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在保證期間屆滿后繼續存在,然保證債務范圍以債權人對債務人相關執行程序結束時范圍為準。②就連帶保證而言,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通知保證人主債務未受清償,并主張權利的,保證債務消滅;反之,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在保證期間屆滿后繼續存在,然保證債務范圍以債權人向保證人通知時范圍為準。
相應地,我認為,應當將我國保證期間法律性質理解為“保證債務所附加的一個解除條件”,即“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起訴或申請仲裁”(一般保證)或“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權利”(連帶保證),則保證債務將因此消滅。且考慮到該情形屬于以一定事實的不發生作為消滅保證債務效力的條件,故此條件應當屬于“附否定的解除條件”。
這里要附帶強調的是,參照各國或地區立法例,并非所有的保證中均附有保證期間。如法國、日本民法典均未涉及保證期間制度;德國、臺灣地區民法典也僅僅是作為當事人特別約款而予以承認。且各國或地區民法以未約定保證期間保證為原則,以約定保證期間保證為例外。〔30〕參見周愷,見前注〔16〕,頁 552;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頁 875。而我國《擔保法》及其司法解釋受制于前蘇聯立法例,強令所有的保證必須有保證期間,當事人未約定的,依法定保證期間。保證期間乃為平衡保證人利益,及早了結或固定保證債務而設,若當事人自愿設立,當并無不可。反之,當事人亦可能不愿約定保證期間,而自愿對主債務作出長期的、完全的擔保 (當然,此也要受訴訟時效期間的約束),此當亦無不可。因此,無論當事人是否有意愿,法律均強行擬制當事人意愿而法定保證期間,從而為保證人開脫保證責任提供方便,此是否有強差人意之嫌?特別是考慮到債權人、債務人、保證人三方利益的復雜性,如此強迫,是否有失偏頗,過于武斷?學術界和實務界對此也多有反思。〔31〕參見曹士兵:“清理保證期間的法律適用”,載奚曉明主編:《中國民商審判》(總第 2卷),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頁 272;高圣平:“‘保證期間約定不明’的處理——兼評保證期間法定主義”,載王利明主編:《合同法評論》,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年版,頁 162以下;張谷,見前注〔1〕,頁 134。然考慮到我國《擔保法》及司法解釋的立法現狀,故本文還是將保證期間作為一整體概念進行研究。
然上述立法狀況對研究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問題有重大影響。由于我國所有的保證均伴隨著保證期間,故我國許多學者在思考該問題時總是以保證期間的存在和適用為前提。然在傳統民法中,相關制度設計均是以未約定保證期間保證為藍本的,約定保證期間保證反只是一種例外。注意到此點,對于我們理解我國現有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制度中的種種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起算點
(一)訴訟時效的起算點——我國和傳統民法〔32〕眾所周知,我國民法深受前蘇聯以及臺灣地區民法影響,而后者又直接承繼德國法傳統,故學理多認為,我國法律亦屬于德國法系之列。為了使立法例的比較有一個更為相近的前提,故本文用“傳統民法”一詞指稱德國、日本、臺灣地區等德國法系民法的一些共通性制度。之差異
我國《民法通則》第 137條前段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然傳統民法中,訴訟時效更多地是從“權利可行使時起算”。〔33〕《日本民法典》第 166條第 1款規定:“消滅時效,自權利可以行使時起進行。”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需要說明的是,《德國民法典》此處多使用“請求權產生時起算”的表述 (如第 199條),但其實質仍然是指“從權利可行使之時起算”。如 Ehmann und Sutschet,a.a.O., S.294指出:“時效原則上不得因請求權發生起算,而應自其屆至時起算,因為在此時點之后,債權人才有機會主張其權利,并避免罹于時效。”(轉引自黃立:“德國民法消滅時效制度的改革”,《政大法律評論》第 78期(2003年 12月),注釋 59)其間差異不在本文考察范圍內,不多敘,但就具體債務的訴訟時效起算而言:〔34〕我國資料參見顧昂然:《民法通則概論》,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 1988年版,頁 144;謝懷栻:《民法總則講要》,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頁 203。傳統立法例資料參見鄭玉波:《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頁 504;(日)三本敬三:《民法講義Ⅰ總則》,解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頁 362。
①約定有履行期限的債務,我國和傳統民法一般均認為,應當自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算。
②未約定有履行期限的債務,傳統民法一般認為,應當自債權產生時起算,然我國民法認為,應當自債權人請求債務人而債務人不履行時起算。
就未約定有履行期限的債務的訴訟時效起算點的差異,謝懷栻先生解釋稱:
從債權成立時起算,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是這樣規定的。從債權人請求而債務人不履行時起算,蘇聯是這樣規定的。第一種觀點的理由是:沒有規定履行期,債權人隨時可請求履行。可以行使權利而不行使權利,所以應從債權成立時起算訴訟時效期間。第二種觀點的理由是:既然沒定履行期,如從債權成立時起算,會損害債權人的權利。我們應取哪一種呢?我看我們的時效規定的很短,只有兩年,一成立馬上計算時間,很容易使債權人喪失利益,蘇聯的規定還是比較可取的。〔35〕謝懷栻,見前注〔34〕,頁 203-204。
對于上述我國和傳統民法就未約定有履行期限的債務的訴訟時效起算點的差異,孰優孰劣,本文不做評價,但必須指出,這一觀念上的差異直接導致了有關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上的差異。
(二)保證債務請求權何時產生、何時可行使
《擔保法》第 6條規定:“本法所稱保證,是指保證人和債權人約定,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保證人按照約定履行債務或者承擔責任的行為。”據此,保證債務是指,保證人和債權人約定,在債務人不清償債務時,保證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債務或者承擔責任”。該保證債務隨著保證合同的成立即告產生,但其是否實際可行使,尚需視債務人的行為而定。債務人及時履行債務者,債權人自不能對保證人主張保證債務;債務人未及時履行債務者,債權人自可以主張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正如學者所言,“保證合同一旦有效成立,債權人即取得對于保證人的保證債權,保證人的給付義務也隨之發生。只有在主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對于保證人的請求權才能行使,一般保證、連帶保證,概莫能外。”〔36〕參見張谷,見前注〔1〕,頁 134。
這里需要討論的是,一般保證中,先訴抗辯權的存在是否會妨礙債權人于主債務期滿時起即對保證人行使保證債務請求權呢?如前所述,我國法律理論和司法實踐曾經認為:一般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并非指保證人享有對抗債權人保證債務請求權的抗辯權,而是指向一般保證保證人主張權利的先決條件是,債權人必須先向債務人主張權利,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而后,債權人方才可以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然現在學界通說否認了這一觀點,認為,先訴抗辯權是保證人對抗債權人要求其承擔保證債務的一種抗辯權。〔37〕參見程嘯:《保證合同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頁 264。由此,我們可以當然地推導出:既然保證人是利用先訴抗辯權對抗債權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那么,該保證債務請求權肯定在保證人行使先訴抗辯權之前就已經產生了。〔38〕實際上,保證人是否行使先訴抗辯權還處于一種兩可狀態。根據立法通例 (如《德國民法典》第767條第 2款、《擔保法》第 21條),保證人要對債權人追索債務人的訴訟費用承擔責任。因此,在債權人追索債務人無任何意義的情況下,保證人完全可能雖有先訴抗辯權然卻最終放棄行使。參見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頁 97。實際上,目前的司法解釋也已經承認了此點,如《擔保法解釋》第 125條規定:“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向債務人和保證人一并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將債務人和保證人列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但是,應當在判決書中明確在對債務人財產依法強制執行后仍不能履行債務時,由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既然債權人可以不先行起訴債務人,而是將債務人和保證人一并起訴,〔39〕最高法院相關人士甚至進一步認為,債權人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之前,僅僅起訴保證人,在程序上也是可以的,當然,實體上能否勝訴另當別論。參見曹士兵:《中國擔保制度與擔保方法——根據物權法修訂》,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頁 136。那也就說明,在對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終結,保證人先訴抗辯權消滅之前,自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債權人已經可以行使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了。
綜上,可以得出結論:不論是一般保證,還是連帶保證,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自保證合同成立時即產生,但需自主債務期滿而未得清償時方可行使。
(三)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的確定
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屬于未約定履行期限的請求權,因此,在訴訟時效起算點問題上,我國和傳統民法出現了分歧。
傳統民法中,如前所述,多遵循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債務的訴訟時效從請求權“產生時起算”的觀點,然考慮到保證債務請求權的特殊性,故認為,其訴訟時效應當從保證債務請求權“可行使時”,即主債務履行期滿時起算。如在臺灣地區,史尚寬先生指出,就保證債務履行期而言,“當事人得就保證債務另定履行期。當事人未定保證債務之履行期者,其履行期依主債務之履行期。……從而,時效期間對于保證人依保證契約所定期限屆滿之日起開始進行。”〔40〕史尚寬,見前注〔9〕,頁904。就此點,筆者求教于臺灣地區中正大學謝哲勝教授,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復。在德國,學者認為,債權人針對保證人的請求權的訴訟時效,在 2001年前,從該請求權能夠行使,即主債務履行期滿起算,而在 2001年后,依據第 199條第 1款,則從該請求權能夠行使的當年年底開始計算。〔41〕Palandt,Gesetz ZurModernisierung des Sehuldrechts,61.Auflage,2002,S.387.《德國民法典》2001年修改后統一規定,訴訟時效從請求權產生之年的年末開始起算。(參見《德國民法典》第 199條)
在我國,遵循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債務的訴訟時效從權利人要求義務人履行而未得到履行時起算的觀點,認為,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應當從保證人拒絕債權人履行請求時起算。故《保證規定》第 27條規定:“保證合同約定有保證責任期限的,債權人應當在保證責任期限屆滿前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保證人拒絕承擔保證責任的,債權人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其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適用民法通則的有關訴訟時效的規定。”《擔保法解釋》中,連帶保證也堅持了這一思路,其第 34條第 2款規定:“……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而對于一般保證,由于對《擔保法》第 25條第 2款以及債權人保證債務請求權與一般保證人先訴抗辯權之間關系的錯誤理解,《擔保法解釋》做出了背離這一思路的規定,其第 34條第 1款規定,從主債務“判決或者仲裁裁決生效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具體原因,詳見后文)〔42〕對于未約定履行期間的債務,最高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2009年)第 6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債權人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的寬限期屆滿之日起計算,但債務人在債權人第一次向其主張權利之時明確表示不履行義務的,訴訟時效期間從債務人明確表示不履行義務之日起計算。”這一司法解釋的思路實質上和前述“從權利人要求義務人履行而未得到履行時起算”的觀點是相一致的。相較于上述一般規定,《擔保法解釋》屬于特別規定,故本文還是以《擔保法解釋》相關內容作為分析對象。
綜上,我認為,在重建我國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問題上,可以有兩種選擇:(1)若延續傳統民法思路,即應當規定:(一般或連帶)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算; (2)若延續我國《民法通則》觀念,即應當規定:(一般或連帶)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時起算。〔43〕我國也有學者注意到了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應當從主債務期滿未得到清償時即可行使,并且,也均認為,先訴抗辯權的存在并不影響債權人對一般保證人保證債務請求權的行使。但是,其似乎未注意到我國在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債務的訴訟時效起算點方面和傳統民法的差異,進而認為:我國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應當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算。例如,“先訴抗辯權不能阻止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起算,《司法解釋》第 34條中所持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筆者主張,無論一般保證或連帶保證,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都應從主債務人不履行債務之日起開始計算。”(秦鈺,見前注〔21〕,頁 478)本文作者也曾經持相同見解。(拙文:“論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計算——兼評《最高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內容”,《政法論叢》2004年第 4期)
三、先訴抗辯權和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
(一)問題的提出
依前述觀點,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或者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算 (傳統民法),或者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時起算(《民法通則》)。這一觀點適用于連帶保證中,不存在任何疑義。但適用于一般保證中,則可能存在爭議。具體而言,一般保證中,若債權人在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之前即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 (《民法通則》),或者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起算 (傳統民法),然受制于保證人先訴抗辯權的存在,勢必會給債權人主張權利造成麻煩。在此訴訟時效期間內,若債權人對保證人主張權利,則保證人完全可以先訴抗辯權對抗。債權人若不想放任訴訟時效的經過,則只有通過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以使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中斷,從而延續訴訟時效期間。由此,債權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為了延續訴訟時效,雖明知向一般保證人主張權利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保證人有先訴抗辯權),但也只能不斷重復這一不可能實現的“權利主張”。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法律體系的差異,傳統民法面臨著比我國《民法通則》更為尷尬的窘境。其一,和我國《民法通則》不同,傳統民法雖承認向義務人“主張權利”可以導致訴訟時效中斷的效果,但均強調,此所謂“主張權利”并非一般的自行主張,而必須是通過“訴訟方式”進行主張,〔44〕參見《德國民法典》第 212條;《法國民法典》第 2244條、第 2245條;澳門地區民法典第 315條。或者必須“配之以訴訟方式”進行主張,方才有效。〔45〕如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29條規定:“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①請求;②承認;③起訴。”第130條規定:“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于請求后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日本民法典》亦有類似規定,如第153條。法律如此規定,必將給債權人設置一個大大的難題。若不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將屆滿;若向保證人主張權利,則必須提起訴訟,而由于保證人還存有先訴抗辯權,即便勝訴,也只能獲得一個以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無效果為生效條件的將來得以履行的判決。“當提出抗辯權時,它能暫時地阻止法院執行該項請求權,即請求權人提出的給付之訴會被認為無理由或現在無理由而被駁回。”〔46〕(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頁 330。花費無數精力,債權人僅僅獲得這樣一個需待得主債務強制執行無效果而方才生效的判決,顯然是沒有意義的。其二:在債權人對保證人提起訴訟并獲得生效判決后,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15、230條,債權人只需在法定期間內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即便當時保證人沒有財產可供執行,但只要債權人發現保證人有其他財產,可以隨時請求強制執行。換言之,此后,債權人對保證人的權利將無期限地受法律保護,不存在需要再次主張權利以中斷訴訟時效的問題。但是,在傳統民法中,如德國、日本、臺灣地區,債權人在獲得生效判決后,仍然要從判決生效之日起重新計算訴訟時效。〔47〕參見張登科:《強制執行法》,三民書局 1998年版,頁 63。換言之,債權人對保證人進行訴訟并取得勝訴判決后,并不能一勞永逸。判決生效后訴訟時效又開始計算,債權人還要不斷以司法程序主張權利,以中斷對保證人的訴訟時效。如此,對于債權人而言,可真是不厭其煩了。
(二)立法例比較:先訴抗辯權與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中止、中斷
針對上述問題,為了補救一般保證中債權人利益,各國或地區立法例有三種不同做法:
第一,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
如《日本民法典》第 457條規定:“因對主債務人的履行請求及其他事由導致的時效中斷,對保證人也發生其效力。”再如《法國民法典》第 2250條規定:“向主債務人進行的傳喚,或者主債務人承認債務,對保證人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再如臺灣地區民法典第747條規定:“向主債務人請求履行,及為其它中斷時效之行為,對于保證人亦生效力。”澳門地區民法亦有類似規定。〔48〕澳門地區民法典第 632條第 1款規定:“對債務人發生之時效中斷不對保證人產生效力,而對保證人發生之時效中斷亦不對債務人產生效力;然而,如債權人使時效對債務人發生中斷,并將該事實通知保證人,則對保證人之時效自通知日起中斷。”澳門地區民法沒有讓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著主債務訴訟時效的中斷而當然中斷,而是強調債權人必須將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事實通知保證人方才產生上述效果。考慮到“將主債務時效中斷事實通知保證人”要比“對保證人進行司法上權利主張”方便得多,我認為,澳門地區民法雖有差異,但基本還是體現了讓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著主債務訴訟時效的中斷而中斷的思想。
立法之所以做出如此規定,多數學者解釋為保證債務的從屬性,“主債務存在時,從債務不可能因時效而消滅。”〔49〕徐滌宇譯注:《最新阿根廷共和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頁 864。另參見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三民書局 1981年版,頁 875。但也有學者否認此為保證債務從屬性的表現,認為“此效力非由保證債務附從性當然所生之結果,乃為推測當事人之意思所設保護債權人之規定。”〔50〕史尚寬,見前注〔9〕,頁 917。史尚寬先生進一步認為,此既然是為保護債權人利益而設,故不妨允許債權人依意思表示“另為訂定”規則,使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因此而中斷。然無論怎樣,這種立法例的實際效果是:在一般保證人還存在先訴抗辯權的情況下,債權人可以專心致志地向債務人主張權利,而完全無需顧及其和一般保證人之間訴訟時效期間的進行,因為其向債務人主張權利時,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亦當然地隨之中斷。如此,有效地避免了債權人單純地為了中斷對一般保證人的訴訟時效而無任何意義地向保證人以訴訟方式主張權利的困境。〔51〕參見拙文:“論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計算——兼評《最高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內容”,《政法論叢》2004年第 4期。
特別考慮到,傳統民法中多以未約定保證期間保證為原則,債權人因為沒有保證期間的約束,很可能拖延許久方才在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無果后再向一般保證人主張權利,因此,規定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當然隨之中斷,顯然更具現實意義。
第二,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受影響,繼續計算。
《德國民法典》2001年以前沒有類似《法國民法典》“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的規定。〔52〕參見戴修瓚:《民法債編各論》,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8年版,頁 220。換言之,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受影響,繼續計算。債權人若想延續對保證人的訴訟時效,則只能無奈地對保證人進行一場無意義的訴訟,以求訴訟時效的中斷。但考慮到原《德國民法典》一般訴訟時效長達 30年(第 195條),因此,即便如此,應當來說,對于債權人利益也并沒有過多影響。
這一做法也得到了我國某些學者的贊同,“保證債務請求權的時效與債權人請求主債務人履行債務的請求權時效并不相同,二者分別基于不同的事由開始起算、發生中斷或中止、甚至完成。保證債務請求權的時效有其自身獨立的中斷事由,與主債務時效中斷與否不發生關聯;不論是一般保證還是連帶保證,主債務時效中斷的,保證債務請求權的時效并不因之而中斷。”〔53〕鄒海林、常敏:《債權擔保的理論與實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頁 83。
第三,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保證人以先訴抗辯權對抗的,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中止。
一般認為,債權人對保證人主張權利 (這里的主張,可以是訴訟中的主張,也可以是訴訟外的自行主張),保證人以先訴抗辯權對抗債權人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并不能產生中止效果。因為訴訟時效為強制性規定,其中止事由應當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54〕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頁 537。而各國或地區立法例均未有此規定。甚至于,原《德國民法典》還對此予以了特別強調。〔55〕原德國民法典(2001年修訂以前)第 202條規定:“時效因給付遲延或者義務人由于其他原因暫時有權拒絕給付而停止。上述規定不適用于對留置權、合同不履行、擔保欠缺、先訴抗辯權,以及保證人根據第770條的規定享有的抗辯權和繼承人根據第 2014條、2015條的規定享有的抗辯權。其原因在于,“債權人不僅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消除這些抗辯權,債權人甚至對消除這些抗辯權負有義務。”〔56〕迪特爾·梅迪庫斯,見前注〔38〕,頁 101。
但有趣的是,2001年《德國民法典》修改之后,在原第 771條(該條原文為:“只要債權人未嘗試對主債務人強制執行而無結果,保證人即可以拒絕向債權人清償 (先訴抗辯權)”)后面,又加了一句話,即“保證人提出先訴抗辯權的,債權人對保證人的請求權的消滅時效停止,直到債權人嘗試對主債務人強制執行而無結果之時。”〔57〕需要說明的是,《德國民法典》中的“消滅時效停止”(Hemmung der Verjahrung)與我國民法中的“訴訟時效中止”并非同義,但內容有相當近似之處。(參見陳衛佐:《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頁 81以下)據此,本文為了和我國民法相銜接,故直接表述為“訴訟時效中止”。據此,《德國民法典》修改了以前債權人對一般保證人主張權利而遭到先訴抗辯權對抗時并不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計算發生任何影響的做法,而是賦予了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止的效果。〔58〕參見迪特爾·梅迪庫斯,見前注〔19〕,頁 423。
那么,《德國民法典》為什么要做出如上修改呢?我們研究發現,這和《德國民法典》2001年修改時縮短訴訟時效期間有關。根據《德國民法典》(2001年后)第 195條的規定,一般訴訟時效期間已經從原來的 30年大幅縮短為 3年。考慮到一般訴訟時效期間大幅縮短可能給若干權利當事人造成的不公正,《德國民法典》修訂時不得不在若干制度中進行了配套的修改工作。〔60〕BGB2002,Sonderausgabe Schuldrechtsreform,Neues Recht/Altes Recht,Mit Einfuehrung von Prof. Dr.Stephan Loreng,Verlag C.H.Beck,Muenchen 2002,S.6.原 30年訴訟時效期間情況下,考慮到時效期間很長,在債權人對一般保證人主張權利而遭到先訴抗辯權對抗時不賦予訴訟時效中斷或中止的效果,對債權人而言,恐利益影響不大。然在 3年訴訟時效期間情況下,時效期間已經大為縮短,若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還是不能因此而中止,則很可能出現不公正的結果:債權人對保證人主張權利,遭到先訴抗辯權對抗后,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繼續進行,而債權人因此只能起訴并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但等到相關程序結束時,3年的訴訟時效期間已經屆滿,如此,顯然對于債權人不公平。正是基于此點考慮,《德國民法典》(2001年后)修改了第 771條,新增了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因此中止的規定。〔61〕Palandt,見前注〔41〕,S.388.
(三)我國現有司法解釋之紕漏及將來之選擇
在我國,司法解釋似乎一直熱衷于規定類似“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的條文,這也許是因為法國、日本、臺灣地區立法例均有相關規定的緣故吧。但問題是,上述各立法例如此規定的前提是: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算。如此,考慮到保證人存在先訴抗辯權,為了平衡債權人利益,故規定“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各制度相互匹配,相得益彰。然我國司法解釋由于未能正確把握保證期間的法律效力以及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的相關問題,竟將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確定為“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判決或仲裁裁決生效之日”(《擔保法解釋》第 34條第 1款)。在此前提下,《擔保法解釋》第 36條又規定“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中斷”,如此,怎能不出現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尚未起算卻已經中斷的荒唐結果呢?
正本清源之后,面臨的問題是,我們應當如何重構我國的相關制度呢?我認為,對應各立法例,有以下三種方案可供選擇:①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受影響,繼續計算。②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③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保證人以先訴抗辯權對抗的,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中止。
第一種方案,各國或地區立法例較少采用,因為其不能為債權人受制于一般保證人先訴抗辯權而遇到的種種困難提供任何救濟。但需要注意到我國法律體系和傳統民法之間的差異,雖債權人無法借助于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而當然中斷對保證人的訴訟時效,然債權人完全可以輕松地憑借“自行主張權利”而中斷對保證人的訴訟時效,此點和債權人需以“訴訟方式主張權利、中斷時效”有巨大差別。此外,若債權人對保證人取得訴訟判決后,可一勞永逸,無需再反復主張權利、中斷時效,此點也和債權人在取得訴訟判決后還需不斷中斷訴訟時效,也有較大差異。總之,在我國,即便不賦予“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的效果,對于債權人而言,亦不會有失公允或增加過多負擔。
第二種方案,雖是各國或地區的立法通例,也有利于保護債權人利益,但需要注意的是,其立論的前提是: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從主債務履行期滿開始起算。如此,“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在邏輯上才不會出現矛盾。但是,若堅持《民法通則》中訴訟時效起算點的相關規則,將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定義為從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之時起。而如果債權人在對債務人主張權利之前并未對一般保證人主張過權利,則可能又會出現“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未起算卻中斷”的荒唐結果。因此,如果我們一定要延續傳統民法立法例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的慣例,那么,我們只能讓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也相應地回歸傳統。
第三種方案,其是德國民法因為未規定“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以及債權人對保證人“自行主張權利”不能產生訴訟時效中斷效果的不足而采取的補救措施。考慮到我國民法中,債權人對保證人自行主張權利,完全可以產生訴訟時效中斷效果的現狀,我認為,我國將來立法應當無需借鑒第三種方案。
綜合以上情況,在我國今后重構先訴抗辯權和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以及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和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等方面的關系時:
(1)若我們選擇傳統民法的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則第一種方案和第二種方案均具可操作性。但是,一方面,考慮到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是從主債務履行期滿自動起算的,債權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該訴訟時效的起算;另一方面,考慮到我國訴訟時效期間較短,只有兩年,因此,為了更好地保護債權人利益,減輕債權人負擔,我還是傾向于第二種方案。即,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62〕需要說明的是,臺灣地區通說認為,臺灣地區民法典第 747條中的“向主債務人請求履行,及為其它中斷時效之行為”“應僅以債權人向主債務人所為請求、起訴或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之事項為限,若其系由于主債務人之行為所致者,例如,‘民法’第一二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承認,性質上乃主債務人向債權人所為之行為,既非民法本條所指債權人向主債務人所為中斷時效之行為,故主債務人所為承認以致時效中斷者,對于保證人自不生效力。換言之,于此情形,保證債務之消滅時效仍然持續進行,而且主債務因而消滅時效之不利益,保證人亦毋庸承受。”(參見邱聰智,見前注〔8〕,頁 371)但是,在法國民法典第 2250條中,則明確規定,“主債務人承認債務”也“對保證人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同時,日本學者也認為,“債務人承認”應也屬于《日本民法典》第 457條所稱的導致時效中斷的“其他事由”。(參見(日)我妻榮:《我妻榮民法講義Ⅳ新訂債權總論》,王焱譯,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頁 431)因此,就債務人對債權人承認債務,能否發生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效果,法國民法、日本民法和臺灣地區民法之間存在著差異。我認為,從更好保護債權人利益,減輕債權人負擔角度出發,應當借鑒法國和日本立法例,故建議規定“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而非“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因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權利而中斷的,保證債權訴訟時效隨之中斷。”如此,也可以和目前已有司法解釋相銜接。
(2)若我們選擇《民法通則》的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則只能選擇第一種方案。因為選擇第二種方案,如前所述,可能又會出現“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未起算卻中斷”的荒唐結果。〔63〕這似乎也證明了法律是一個有機組成的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們也許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傳統民法中總論部分的“訴訟時效起算點”和債法分論部分的“主債務和保證債務之間的關系”兩個看似不相關的問題之間卻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民法通則》在訴訟時效起算點方面的一點創新(此點創新又是因為《民法通則》所規定的訴訟時效期間較傳統民法為短而引起的),導致了我們不能再延續傳統民法中保證部分的相關條款,而只能繼續創新下去。這也許教育我們應當對傳統民法體系更為虔誠,切不可肆意妄為,隨意“創新”。依第一種方案,債權人只能通過向一般保證人自行主張權利的方式來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這樣可能會加重債權人負擔,但考慮到此時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是從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時起算(而非如傳統民法自主債務履行期滿自動起算),故而在債權人已明確關注一般保證債務的前提下要求其繼續保持注意,必要時再次向保證人自行主張權利以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期間,應當說也不算為過,可以接受。
四、保證期間與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之關系
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對此,論著多有涉及,但似乎均未將其單列出來而專門進行討論,然此問題對于明了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具有重大關系,故本文此處將專門討論這一問題。
總結目前已有相關成果,學界對此大致有三種觀點:
(1)擇優說
此說認為,“無論訴訟時效還是保證期間,其指向的對象都是債權人對保證人的請求權,而訴訟時效和保證期間對待債權人的請求權的處理方式并不相同,從而不可能發生兩者并行不悖的情形,只能選擇其一。”“擔保法在債權人對保證人的請求權的保護上沒有采取訴訟時效保護的方案,而采取了保證期間的保護方法,其意圖在于,在保證期間屆滿后,債權人喪失的不是勝訴權,而是實體權利,也即其法律后果對債權人更為不利,而對保證人較訴訟時效為利。”〔64〕孔祥俊:“保證期間再探討”,《法學》2001年第 7期,頁 58。據此,此說認為,考慮到保證期間較之于訴訟時效更能保護保證人利益,故擇優選擇保證期間,因而在保證債務問題中將不復存在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問題。
(2)繼起說
這種觀點一直為司法解釋所贊同。這種觀點是為了將《民法通則》第 137條所稱“訴訟時效期間從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的規定落實在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起算上。〔65〕參見崔建遠,見前注〔6〕,頁 184頁。具體而言,一般保證中,加之受制于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是指債權人必須先對債務人強制執行未果后才對保證人享有保證債務請求權的觀念,故必須等債權人對債務人強制執行無效果后,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遭到拒絕時,債權人方知自己權利受到侵害,故起算訴訟時效;連帶保證中,必須等到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遭到拒絕時,債權人方知自己權利受到侵害,故起算訴訟時效。當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根據法律規定的方式,向債務人(一般保證)或者保證人(連帶保證)主張了權利,保證期間作用完結,訴訟時效制度開始起作用,保證期間與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相互銜接。〔66〕參見曹士兵,見前注〔31〕,頁 275。
這種觀點也得到了國內許多學者的贊同,為了徹底貫徹《民法通則》第 137條的精神,他們進而認為,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起算點應當是“對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之日起”。〔67〕參見崔建遠,見前注〔6〕,頁 185頁;鄒海林、常敏,見前注〔53〕,頁 83。因為,一般保證中,保證人在債權人對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之前,均享有先訴抗辯權,均可以據此拒絕債權人的履行要求,故在此之前,債權人無法獲知自己對保證人的權利是否受到了侵害。但最高法院認為,若如此起算訴訟時效,“時間拖得如此之長,對保證人過于不利”,且“在(主債務)判決生效后的兩年訴訟時效期間內,執行活動一般是可以完成的,債權人完全可以在此期間內起訴保證人。債權人還可以通過非訴訟的形式,要求保證人履行保證責任,使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中斷。”〔68〕奚曉明,見前注〔2〕,頁 63。因此,最高法院作出了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從“主債務訴訟判決或者仲裁裁決生效之日”起算的規定。
基于以上考慮,《擔保法解釋》第 34條規定:“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從判決或者仲裁裁決生效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連帶責任保證的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
(3)平行說
該說認為,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雖都是為保護保證人利益而設的法律上的期間,但屬于兩個并行的、互不相關、互不影響的期間。在具體實踐中,就保證人而言,其可以選擇“保證期間屆滿”進行抗辯,也可以選擇“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屆滿”進行抗辯。只要其中一個抗辯成立,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的權利即因此落空。正如張谷教授所言:
如果債權人對保證人的請求權,其訴訟時效完成時,而約定保證期間尚未屆滿的,那么保證人取得時效抗辯權;約定保證期間屆滿與否,已無實際意義。如果約定保證期間屆滿時,此前債權人未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義務的,那么保證人保證義務消滅;債權人對保證人的請求權,其訴訟時效完成與否,也不重要。如果債權人對保證人的請求權,其訴訟時效未完成,且約定保證期間亦未屆滿的,在一般保證中,于強制執行無效果后,或者在連帶責任的保證中,于主債務履行期屆滿后,債權人不遲延地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義務的,那么保證義務仍然存續,不過嗣后發生保證義務范圍固定之結果。〔69〕張谷,見前注〔1〕,頁 135-136。
對于上述三種觀點,我贊同第三種學說。
第一種觀點顯然不妥。從理論上說,該說將保證期間性質理解為債權人對保證人保證債務請求權的存續期間,這種理解本身并無可厚非,但作者并不能由此推導出:既然規定了請求權的存續期間,就無需再規定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了,因為前者的實施效果更有利于保證人。請求權依當事人約定也許可以附設存續期間,但并不能由此代替訴訟時效的功能。此完全為不同性質的法律制度,不可混同、替代。從實踐中看,該說也沒有可操作性。通常情況下,如約定保證期間為六個月,而訴訟時效為兩年,顯然適用保證期間比適用訴訟時效對保證人更為有利。但是,若當事人約定保證期間為一個月,或者為四年時,〔70〕目前學界通說認為,約定保證期間短于六個月或長于二年,應當都是有效的。參見曹士兵,見前注〔39〕,頁 147。若此時僅僅適用保證期間制度,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在一個月情況下,債權人根本來不及向保證人為訴訟上請求,在四年情況下,恐還是適用兩年訴訟時效制度更有利于保護保證人利益。
第二種觀點是源于《擔保法》第 25條立法條文的模糊性,以及最高法院對于保證債務產生時間、一般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和先訴抗辯權之間關系等的不正確理解而造成的。如前所述,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從主債務期滿未得到清償時就可行使了,同時,一般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并不影響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起算。受制于保證期間的約束,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或保證人為一定行為,否則將產生保證債務消滅的效果。但是,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和保證期間是兩個相互獨立,各自發揮功效的制度,完全不存在什么繼起的關系。
第三種觀點值得贊同。如前所述,保證債務作為一種請求權,當然應當受到訴訟時效制度約束,債權人未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對保證人主張權利的,保證債務因此落空。且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遵從訴訟時效起算點的一般規則,或者從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傳統民法),或者從權利人要求義務人履行時起算(我國民法)。保證期間是保證債務所附加的否定的解除條件,若保證期間內,債權人未為一定行為,保證人保證債務消滅;若債權人為了一定行為,則可以起到及早明確保證人保證債務以及范圍的效果。由此可見,保證期間是法律考慮到保證制度的特殊性而特設的一項制度,目的是為了在訴訟時效制度之外給予保證人以額外保護。據此,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和保證期間是兩個并行不悖的制度,在各自構成要件情況下,獨立發揮功效,互不影響。
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未約定保證期間的保證中,保證人將只能受惠于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制度,而無法接受保證期間的顧眷。
五、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中斷、中止和完成
保證債務作為一種獨立的債權債務關系,其當然適用訴訟時效的相關規定,在滿足法律所規定的中斷、中止、完成等條件時,自然發生相應的后果。對此,無需多加論述。
這里需要討論是,在主債務發生中斷、中止、完成時,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是否也應當發生相應的中斷、中止、完成的法律后果?抑或還是應當區別不同情況而具體分析?
(一)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中止、完成,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影響
1.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影響
根據《擔保法解釋》第 36條,“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中斷。”國外也多有類似立法例。就此規定之背景及其我國將來可能之立法選擇,前文已有論述,不再贅述。
需要說明的是,最高法院《關于貫徹實施 <民法通則 >若干問題意見》第 173條第 2款規定,“權利人向債務保證人主張權利的,可以認定訴訟時效中斷。”此條不符合主債務和保證債務之間主從關系的事實和原理。保證債務是主債務的從債務。如果說債權人對債務人主張權利,效力及于保證債務,還可以說是保證債務從屬性的體現的話,債權人對保證人主張權利,效力無論如何是不應及于主債務的。這是根本違反保證債務從屬性的,目前遭到學者的強烈批評。〔71〕參見程嘯,見前注〔37〕,頁 556。
2.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影響
《擔保法解釋》第 36條第 2款規定,不論一般保證或連帶保證,“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的,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同時中止。”(《保證規定》第 30條也有類似規定)
《擔保法解釋》相關起草人員給出的解釋是,“訴訟時效的中止,則是因非當事人所能控制的客觀原因而產生,如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這些情況往往對主合同當事人或對保證合同當事人,都同樣產生影響。因此,無論對于主債務還是保證債務均應一律對待,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也應當同時中止。”〔72〕奚曉明,見前注〔2〕,頁 64。對于《保證規定》第 30條,起草者也給出了類似的解釋,“在一般情況下,債權人不能行使對被保證人請求權,也就同時不能行使對保證人的請求權。在這種情況下,保證合同完全附隨于主合同,主合同訴訟時效中止的,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同時中止。”(參見最高法院經濟庭編著,見前注〔22〕,頁 52。)
我認為,上述解釋值得商榷。訴訟時效中止是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阻礙 (如法定代理人未確定等)不能行使請求權”而造成的。依照上述解釋,債權人對債務人主張權利時遭遇不可抗力、法定代理人未確定等事由而中止時,在對保證人主張權利時也會當然地遭遇類似情況,“同樣產生影響”。這種推理似乎難以成立。債權人和保證人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怎能同時遭遇法定代理人未確定的情況?債權人和保證人未必在同一地方,怎能同時遭遇不可抗力?參照各國立法例,我們也沒有發現類似規定。〔73〕澳門地區民法典第 632條第 2款更是明確規定,“對債務人發生之時效中止不對保證人產生效力,而對保證人發生之時效中止亦不對債務人產生效力。”
因此,我認為,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是否構成中止,應當參照訴訟時效中止的相關法律規定,獨立適用,不應當因主債務訴訟時效的中止而當然地認定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亦中止。
3.一般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完成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影響
主債務訴訟時效完成后,債務人取得相應的時效抗辯權。基于保證債務的從屬性,保證人亦可以行使債務人的抗辯權,故保證人當然可以據此對抗債權人保證債務請求權。各國或地區多有類似立法例,如臺灣地區民法典第 146條、第 742條,《德國民法典》第 217條、第 768條。
在我國,《擔保法》第 20條規定,“一般保證和連帶責任保證的保證人享有債務人的抗辯權。債務人放棄對債務的抗辯權的,保證人仍有權抗辯。”據此,完全可以得出主債務訴訟時效屆滿,保證人得援引此抗辯權對抗債權人的結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2008年)第 21條又予以了特別強調,“主債務訴訟時效期間屆滿,保證人享有主債務人的訴訟時效抗辯權。”
(二)連帶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中止、完成,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影響
1.連帶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影響
《擔保法解釋》第 36條規定,“連帶責任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中斷。”
《擔保法解釋》的上述規定和日本、臺灣地區民法之間存在差異,后者通說認為,雖然民法典沒有明確規定,但依據連帶保證的從屬性,連帶保證也應準用一般保證制度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的相關規定。〔74〕參見錢國成:“被保證之主債務與保證債務之關系”,載鄭玉波主編:《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84年版,頁 1406;(日)我妻榮,見前注〔62〕,頁 443。
對于上述境外立法例,我認為需加以仔細研判。連帶保證的特點在于,主債務履行期屆滿,債權人可以選擇債務人承擔主債務,也可以選擇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此時,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完全不存在一般保證中先訴抗辯權的干擾。我認為,上述境外立法例的合理性只能在于:①這些立法例中,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是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自動起算的,如此規定可以防止債權人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放任了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進行;②這些立法例中,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只能以訴訟方式進行,較為繁瑣,如此規定可以減輕債權人負擔。
就我國將來立法選擇而言,在《民法通則》規定權利人自行主張權利亦可以中斷訴訟時效的前提下,①若依《民法通則》,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時起計算連帶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考慮到債權人對于保證債務請求權已經予以關注的事實,加之債權人若想中斷時效也較為方便,我認為,可以不規定該規則;②若依傳統民法,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計算連帶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考慮到此時債權人可以獨立、方便地向連帶保證人主張權利的情況,若債權人卻對自身權利未予以起碼的關注,以致訴訟時效未中斷而屆滿,債權人也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法律保護。加之依《民法通則》,債權人若想中斷時效也較為方便,故我認為,此時亦可以不規定該規則。
綜上,結合我國法律體系特點,同時考慮和已有司法解釋相銜接,我建議,連帶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隨之中斷。
2.連帶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影響
和上文一樣,我認為,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應當當然中止。
3.連帶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完成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影響
和上文一樣,我認為,基于保證債務的從屬性,連帶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完成的,連帶保證人應當亦可以援引此抗辯權而對抗債權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
六、結 論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重構我國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有關制度時,應當貫徹如下幾點:
1.保證期間是保證債務中所附加的一個“否定的解除條件”:①就一般保證而言,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起訴或申請仲裁的,保證債務消滅;反之,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起訴或申請仲裁,并在相關執行程序結束后及時通知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在保證期間屆滿后繼續存在,然保證債務范圍以債權人對債務人相關執行程序結束時范圍為準。②就連帶保證而言,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通知保證人主債務未受清償,并主張權利的,保證債務消滅;反之,保證人的保證債務在保證期間屆滿后繼續存在,然保證債務范圍以債權人向保證人通知時范圍為準。
傳統民法中,一般而言,當事人可以約定附保證期間,也可以不約定附保證期間。我國目前相關法律僅僅承認附保證期間的保證,當事人未約定的,依法定期間。但我認為,將來亦不妨承認未約定保證期間的保證。
2.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從主債務期滿未得清償時可以行使。作為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債務,依傳統民法,(一般或連帶)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應當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算(方案一);依《民法通則》,(一般或連帶)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應當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時起算(方案二)。
3.在附有保證期間的保證中,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是兩個獨立的為了保護保證人利益而設立的平行的、互不相關的、互不影響的期間。其有各自的消滅事由,以及相應的法律后果。在具體實踐中,就保證人而言,其可以選擇“保證期間屆滿”進行抗辯,也可以選擇“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屆滿”進行抗辯。只要其中一個抗辯成立,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的權利即因此落空。
4.先訴抗辯權的存在并不否認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債權人對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請求權從主債務履行期滿時可以行使。在存在一般保證人先訴抗辯權的情況下,債權人為了實現保證債務,既可以單獨起訴債務人,也可以同時起訴債務人和保證人,只需要法院在判決時言明首先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即可。
5.一般保證中,若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時起算 (方案一),則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隨之中斷;若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時起算(方案二),則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隨之中斷。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隨之中止。主債務訴訟時效屆滿的,保證人可以援引此抗辯權對抗債權人。
6.連帶保證中,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隨之中斷。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不隨之中止。主債務訴訟時效屆滿的,保證人可以援引此抗辯權對抗債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