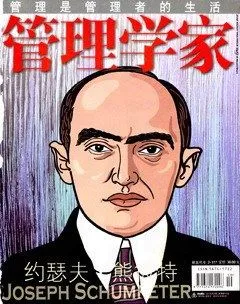創(chuàng)新與管理
“創(chuàng)新”一詞,已經(jīng)聒噪到耳朵生出繭子來的程度。然而,到底什么是創(chuàng)新?如何看待創(chuàng)新?如何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新?卻依然懵懂。“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人們一股腦兒涌向創(chuàng)新,贊美創(chuàng)新,但又不得不感嘆創(chuàng)新的神奇和稀缺。在這種背景下,管理學(xué)界也鐘情于創(chuàng)新,試圖以創(chuàng)新走出困境,解答疑惑。
綜觀國(guó)內(nèi)管理學(xué)界關(guān)于創(chuàng)新的論述,有四個(gè)問題不可不辨。
一是把創(chuàng)新等同于發(fā)明,這是最常見的偏差。發(fā)明可以從屬于創(chuàng)新,但不能等同于創(chuàng)新。世界上的發(fā)明多了,一位婦女,發(fā)明了一種穿襪子的新方法,你不能不說這是發(fā)明,但是,當(dāng)它不能創(chuàng)造新的價(jià)值時(shí),就不是創(chuàng)新。反過來,一位商人,完全采用模仿和跟進(jìn)的方式,沒有任何發(fā)明,卻獲得了巨大的商業(yè)成功,這就無疑屬于創(chuàng)新。在一定意義上,對(duì)于企業(yè)家而言,做出一項(xiàng)發(fā)明與把這一發(fā)明轉(zhuǎn)化為商機(jī)相比,后者要比前者更重要。當(dāng)然,對(duì)于科學(xué)家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科學(xué)家可以藐視商機(jī),而企業(yè)家也跟著科學(xué)家學(xué)樣,豈不是錯(cuò)位?看看熊彼特的書,這個(gè)問題就不難解答。
二是把創(chuàng)新作為管理職能,這在管理學(xué)界已經(jīng)有所表現(xiàn),而且有人言之鑿鑿。實(shí)際上,這涉及到管理學(xué)的學(xué)科界定和內(nèi)在邏輯。從法約爾以后,管理職能基本上有了大家都認(rèn)可的術(shù)語(yǔ)和范圍,盡管相關(guān)的爭(zhēng)論至今不息,然而,這種爭(zhēng)論基本不涉及創(chuàng)新。把創(chuàng)新列進(jìn)管理職能,會(huì)在邏輯上產(chǎn)生謬誤。固然,管理要激發(fā)、促成、鼓勵(lì),推動(dòng)創(chuàng)新,但創(chuàng)新本身卻不屬于管理。對(duì)此,尚有待于進(jìn)一步論證。
三是把創(chuàng)新與維持對(duì)立起來,這幾乎是最常見的思維偏差,而且往往是無意識(shí)的偏差。比如,國(guó)人常說的“創(chuàng)業(yè)難,守成不易”,前提就是把創(chuàng)業(yè)和守成看作對(duì)立的,起碼是“攻守之勢(shì)異也”。所以,一說創(chuàng)新,就是改弦易張,而把因襲傳統(tǒng)排除在創(chuàng)新之外。這種創(chuàng)新觀,極易流于偏激。而沒有保守主義的牽制,一味贊揚(yáng)激進(jìn)主義,很容易走上“改天換地”的折騰。這種思維往往不屑于“舊瓶裝新酒”,結(jié)果打爛舊瓶也釀不出新酒來,只能唱一曲“從頭再來”,低水平重復(fù)。
四是把創(chuàng)新的外延無限擴(kuò)大,幾乎無所不包。只要是變個(gè)新花樣,就是創(chuàng)新。這種所謂的創(chuàng)新幾乎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走向了趙本山賣拐式的忽悠。好一點(diǎn)。僅僅是追求言辭上的新穎和動(dòng)聽,而不管實(shí)質(zhì)上能不能增加價(jià)值。差一點(diǎn),就可能把好人變成瘸子,架上拐杖來表現(xiàn)與眾不同的新意。不但有可能在新幌子下原地踏步,而且有可能產(chǎn)生打著創(chuàng)新旗號(hào)萎縮后退,只是把倒退改名為“轉(zhuǎn)進(jìn)”而已。
正因?yàn)槿绱耍鼙颂睾涂死锼闺睦碚摚陀辛瞬豢珊鲆暤膬r(jià)值。熊彼特的貢獻(xiàn),是從理論上解釋了什么是創(chuàng)新,賦予創(chuàng)新這一概念的學(xué)術(shù)地位。我們不需要把熊彼特硬性拉到管理學(xué)界來充數(shù),但掌握熊彼特關(guān)于創(chuàng)新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論證,卻是管理學(xué)家必須要做的功課。如果說,早期管理學(xué)的理論發(fā)展,離不開亞當(dāng)’斯密的經(jīng)濟(jì)人假設(shè)和分工理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支持,那么,當(dāng)代管理學(xué)的理論發(fā)展,就離不開熊彼特的企業(yè)家概念和創(chuàng)新理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支持。經(jīng)濟(jì)學(xué)和管理學(xué)是應(yīng)當(dāng)有界限的,然而卻不能自守畛域而走向封閉。沒有熊彼特,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管理,就難以得到清晰的解析。克里斯滕森的貢獻(xiàn),是在操作層面解釋創(chuàng)新,對(duì)創(chuàng)新的生成、發(fā)展以及所需的組織變革,做出了管理學(xué)的回答。如果說,德魯克、漢迪等人,更重視對(duì)價(jià)值觀的變化進(jìn)行哲學(xué)式思考,那么,克里斯滕森就是對(duì)價(jià)值觀變化與運(yùn)作程序變化的關(guān)系、現(xiàn)實(shí)中這種變化應(yīng)當(dāng)怎樣促成做出了規(guī)范式呼應(yīng)。了解和掌握熊彼特與克里斯滕森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澄清關(guān)于創(chuàng)新的疑惑與誤解,進(jìn)而推動(dòng)真正的創(chuàng)新。
如果視野再開闊一點(diǎn),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克里斯滕森所說的維持性創(chuàng)新和破壞性創(chuàng)新,同科學(xué)哲學(xué)家?guī)於魉f的建立范式與打破范式的關(guān)系極為相似,在邏輯上高度吻合。再進(jìn)一步,有助于我們思考管理學(xué)科的革命問題,管理學(xué)本身,是否也存在破壞性創(chuàng)新?對(duì)于管理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研究來說,哪些地方是顧客(企業(yè))所不滿足的?哪些地方是顧客過分滿足的?還有哪些非消費(fèi)者實(shí)際上存在著學(xué)界未能提供的服務(wù)?這種思考,對(duì)管理學(xué)本身的發(fā)展,具有極大的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