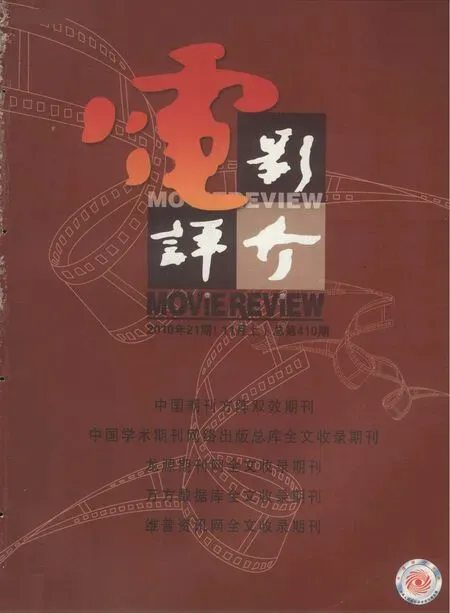先秦和同之辨的源流及思想史意義
首都師范大學 于占杰
先秦和同之辨的源流及思想史意義
首都師范大學 于占杰
當我們考察“和”字之意義來源,著眼于“和”、“龢”、“盉”字之分合時,就會發現,史伯、晏嬰由“和”字之“調音”、“調味”義出發,推而衍之,得出世間萬物相異、相反而適足以相成之理,單一事物的世界是不可能長久的。約與晏嬰同時的古希臘哲學家亦提出萬事萬物相異相反而和諧的思想,而他們所強調的“和諧”一詞亦本之于音樂,可謂異曲而同工。
和同之辨 語源學 儒家 古希臘哲學
一、和同之辨的內容解析
對“和同”問題的最早探討見《國語?鄭語》鄭桓公與史伯對話:
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將。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而欲無弊,得乎?” [1](p.1419~1420) ①
二百余年后春秋時代齊國之晏嬰亦有關于和同之辨的精彩論述,可與史伯的論述相互發明。《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2](p.470~473)
史伯和晏嬰嚴格區分“和”與“同”,主張去同而取和。所謂“同”就是單一要素或相同事物構成的狀態,即“以同裨同”。“和”則不然,是“以他平他”,是容納了多樣性的狀態。這種容納了多樣性的“和”的狀態又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相異相成,二是相反相濟。如晏嬰所舉的音樂之例: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這是相異而相成;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這是相反而相濟。
為什么史伯和晏嬰主張去同取和?我們當然可以說他們是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樸素的觀念。但如果從語源學的角度進行考索,就會發現,他們的這種觀念也與“和”字復雜的字義譜系有關系,而這是研究者較少注意到的。②
關于“和”,《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和(《說文解字》作‘咊’),相應也。從口,禾聲。” [4] (p.57)《說文解字》中,“和”字排在“唱”字之后,“唱,導也。” [4](p.57)而“和”字為“相應”之意,與“唱”意相對,其意為應和、附和等。如《荀子?樂論》:“唱和有應,善惡相象。”[3] (p.381)如果僅看這條解釋,就很難理解“和同有別”的觀念。但《說文解字》對“龢”、“盉”等解釋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線索。對于“龢”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龢,調也” [4](p.85),“調”字下的解釋則云:“調,龢也”[4](p.93),即“龢”“調”互訓。《說文解字》于“龢”字接著解釋道:“從龠禾聲,讀與咊同。”段玉裁認為,“龢”與“和”僅音同而已,其意則別,經傳多假“和”為“龢”。[4](p.85)“龢”之為“調”意,即調聲也。考“龢”所從龠部之“龠”字,《說文》曰:“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4](p.85) ③則“龢”與音樂的關系很明顯。而“盉”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調味也。”段玉裁注曰:“古器有名盉者,因其可以盉美而名之盉也。”段玉裁認為:“調聲曰龢,調味曰盉。” [4](p.212)故后來“和”之訓為“調”者,大抵非調味即調聲也。可見,先秦時,在表示“調(音、味)”等意時,“龢”、“盉”與“和”并用。只是在可用“龢”、“盉”的地方可以假借為“和”,反之則不然。總的趨勢是,“和”字行而“龢”、“盉”字漸漸少用④,于是“龢”、“盉”字之本義亦并入“和”字中,使“和”字呈現出了豐富的涵義,并發展出了和同有別的觀念。
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看出,齊侯(齊景公)所說的“和”,為“相應”之義,即“唱和”之和,齊景公認為梁丘據(子猶)的附和就是和諧。晏子則引音樂與調味的道理來闡發“和”字的哲學意涵,認為真正的“和”應當是不同因素(在君臣之間則為不同的聲音)的協調統一。梁丘據這種應聲蟲式的應和其實不是“和”,而是“同”,因為他不敢提出異議。從開篇的兩段引文猶可見“龢”、“盉”字之漸廢而為“和”字所替代,“龢”、“盉”其義亦并入“和”字之中。史伯、晏嬰關于“和”的哲學思想,顯然與為“和”字所假借的“龢”、“盉”有關:“和五味”之“和”,本字當為“盉”;“和六律”、“和五聲”之“和”,本字當為“龢”。而通假的結果是,“和”字多意化,為“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提供了語源基礎。調聲是將不同的音階按一定的韻律進行排比,形成美妙動聽的音樂。如果只有一個音調,那就是噪音了,所謂“聲一無聽”。調味是對不同的味道進行調劑,方能做出可口的佳肴,如果只有一種味道,勢必難以下咽,所謂“味一無果”。由音樂和美味的道理推而論之,則萬物皆如此:和諧的事物是不可能由單一元素構成的。只有多元素甚至相反的元素構成的事物,才是健康的事物。
史伯、晏子由音樂和調味出發所闡明的相異相成、相反相濟、去同取和的道理,最終還是落實到政治層面上。況且,史伯與鄭桓公、晏子與齊景公對話的背景本來就是政治議論。史伯認為,周幽王去和取同,“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如虢石父乃讒諂巧從之人,而周幽王卻立以為卿士,這就是“剸同”。晏子則明確告訴齊景公,君臣之道應當是“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即統治者應當聽取臣子的不同意見,特別是相反的意見,進行綜合判斷;而臣子則應當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見,這樣就像把不同的味道調成美味佳肴一樣,這才是真正的“和”,這樣才能減少決策失誤,“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梁丘據則不是這樣,而是“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完全從一己之私利出發,一味迎合統治者的心理,不肯提出異議。這種的政治局面是有危險的。
二、和同之辨的思想史意義
“和同之辨”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義。去同取和的觀念為先秦諸子廣泛接受,甚至用語也頗為相近。如《管子?宙合》亦舉音樂與味道而論君臣之道:“五音不同聲而能調,……五味不同物而能和”。[5] (p.211)錢鍾書在《管錐編》中又引《淮南子》、《孔叢子》等證之。⑤東漢荀悅對此總結道:“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6](p.23)
“和同之辨”最重要的思想史意義是其對儒家的影響。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7] (p.296)即源于此。孔子繼承史伯、晏嬰的去同取和的思想,又進一步發展了和同有別的思想,將其作為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內容,明確將“和”與“同”作為君子、小人人格之分際。縱觀《論語》全書,孔子對“和”(與“同”相對的“和”)的肯定、對“同”的警惕是很明顯的。孔子特別強調君子的獨立人格,有定見,對于是非有明確的判斷,不人云亦云,處朋友之道,則規過相諫。“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7](p.357)對直、諒品格的肯定,在《論語》中屢見,如:“人之生也直;罔子生也,幸而免。”[7](p.125)故“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7](p.75)儒家強調中庸之道,告誡過猶不及,但倘不得中道而與之,則寧取其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馮友蘭解釋道:“狂狷之行為,雖不合中行,要皆真性情之流露,故亦可取。” [8](p.314) ⑥相反,對于貌似行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四面討好,八面玲瓏的“鄉原”,則深惡痛絕,認為是“德之賊”。因為“鄉原”這種人表面上與人和睦相處,誰也不得罪,“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而且“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表面顯得寬宏大量不計較,看似是在踐行中庸之道,但實際上自己無主心骨,沒有自己的堅定意見,一意取悅于他人,博得眾人歡心,故“眾皆悅之”。劉寶楠所謂“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托,故以是亂德”。“鄉原”類似于今天所說的“老好人”、“濫好人”,人緣極佳,但無原則。強調行中庸之道的儒家,對此似是而非的行為自然最為警惕。類似的說法還有: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7](p.297)
朱熹的解釋是,“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倘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固“其無可好之實”,但如果“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有其茍合之行”[9](p.147),此即“鄉原”也。“巧言令色”者亦與此相仿佛。一個人給他人留下的印象,有毀有譽才是正常的。故孟子強調“反經”,經者,常也,即回到正常狀態,有自己的原則,有愛憎,能好惡,表里如一,則“無邪慝矣”。孔子還告誡:“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7] (p.345)這句話可以做兩種解釋。一是認真考察眾人所以好惡之緣由,好在哪里,以此為上進之動力;惡在哪里,以此為戒懼,有“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之意。其二是如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引衛瓘所說的:“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惡人與時同好,亦則見好也,兇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10] (p.163)如此,“眾好之,必察焉”亦有警惕鄉原之意。而程樹德在《論語集釋》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注解“余論”中引陳天祥《四書辨疑》也特意指出:“和則固無乖戾之心,只以無乖戾之心為和,恐之未盡。若無中正之氣,專以無乖戾為心,亦與阿比之意相鄰,和與同未易辨也。中正而無乖戾,然后為和。”[11](p.936)蓋“同”為“和”之似是而非者,而“和”如果處理不好,亦易流于“同”。是否有“中正之氣”是區分“和”“同”的重要標志。
總之,孔子等儒家將“去同取和”的君臣之道推及于君子人格塑造方面,成為個人修身行事、朋友相處之道的一項重要原則,豐富了和同之辨的內涵。
三、與古希臘哲學的比較
無獨有偶,當中國先秦時代的思想家探討和同問題的時候,約與此同時的古希臘哲學家也提出了類似的相異相成、相反相成的思想,甚至在語源學方面也有相似之處。錢鍾書指出:“古希臘哲人亦道此,亦喻謂音樂之和諧,乃五聲七音之輔濟,而非單調同聲之專壹”。[12] (p.237)約與晏嬰同時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鼎盛年約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即認為,“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D8)[13](p.23~24) ⑦還說:“他們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對立的統一,如弓和豎琴。”(D51)[13](p.24)此派即引音樂為例來闡發其相反相成的道理,與史伯和晏嬰引音樂等闡發其去同取和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亞里士多德對該派學說的描述是:
自然也追求獨立的東西,它是用對立的東西制造出和諧,而不是用相同的東西,例如……音樂混合音域不同的高音和低音、長音和短音,造成一支和諧的曲調。(D10)[13](p.23)
亦是闡發其相異相成、相反相濟之理。再如,比赫拉克利特稍早但與晏嬰仍差不多同時的畢泰戈拉(Pythagoras,鼎盛年約在公元前530年左右)學派也引音樂為例,以不同的樂符奏出和諧的樂章來闡發其相異及相反相成的道理。在政治領域,亞里士多德即反對蘇格拉底追求的整齊劃一的城邦,認為城邦應當是由不同品類的要素組成的。[14](p. 44~53)
有趣的是,希臘語中“和諧”(αρμονια,harmonia) 的原始意義就是關于音樂的,即將不同的音調調和在一起,成為音階。這種音樂意義的和諧在公元前五世紀就已經建立起來了。這與中國先秦時“和”(“龢”)最初作為調音之意相同,由此引發的哲學思想也是相通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古希臘的哲學家都不約而同地由音樂等出發提出了相異相成、相反相成的深刻思想,但其中亦有不同之處。雖然東西方的哲學家都注意到不同的音調在一起可奏出和諧的樂章,但至于為什么不同的音調在一起方能和諧的問題,史伯、晏嬰等沒有討論這個問題,而畢泰戈拉派則不僅注意到和諧的音調是由不同的音符奏出的,其中有高有低,有緩有急,有徐有疾,還注意到不同的音調之間存在著比例的關系。“畢泰戈拉是第一個洞察到音樂關系的人,他洞察到這些可以聽見的差別是可以用數學來說明的,——洞察到我們對于協調和不協調的聽覺乃是一個數學的比較”。他認為,“在音樂中,音調的差別表現為不同的數的關系;數的關系是唯一規定音樂的方式。”[15] (p.238)不僅如此,畢泰戈拉派認為,萬物之所以可以相異相成、相反相成,不同的事物在一起之所以可以達到和諧的效果,就是由于其中存在著數量上的關系。他們認為,萬物皆數,“數是一切事物的本質,整個有規定的宇宙的組織,就是數以及數的關系的和諧系統。”[15] (p.218)畢泰戈拉派還把數當作萬物的始基或本原,認為“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個本性來說都是以數目為范型的,數本身則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13](p.19) 。而史伯、晏嬰等在引音樂為例時,他們或許也意識到音樂中的各音符之間存在著數量上的關系,但并未由此推衍形成數本原的觀念。
總之,當我們考察“和”字之意義來源,著眼于“和”、“龢”、“盉”字之分合時,就會發現,史伯、晏嬰所談的“和”有其語源學上的根據,在闡述“和”“同”有異時,談到了“調味”、“調音”等問題,猶可見“龢”、“盉”等字漸不用而漸為“和”字所代之軌跡。史伯、晏嬰由“和”字之“調音”、“調味”義出發,推而衍之,得出世間萬物相異、相反而適足以相成之理,單一事物的世界是不可能長久的,而落腳點卻在君臣關系上,強調君臣之間當允許有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見,政治上只有一種聲音是危險的。這種強調去同取和的思想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則不僅繼承了史伯、晏嬰關于和同問題的政治上的重要意義,更將其作為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內容。儒家強調君子應有自己的獨立人格,有明確的是非判斷,反對隨波逐流、四面討巧、八面玲瓏、俯仰于他人。在見不到能行中道者時,對狂狷人格亦有所肯定,因為狂狷者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不隨便附和他人,而對于左右逢源、誰也不得罪的鄉原(鄉愿),則深加痛斥,因為他們貌似行中庸之道,實為無原則地同于他人,是“德之賊”。
約與晏嬰同時的古希臘哲學家亦提出萬事萬物相異相反而和諧的思想,而他們所強調的“和諧”一詞亦本之于音樂,可謂異曲而同工。只是史伯、晏嬰所關注的重心乃是政治問題,而古希臘的畢泰戈拉派由此發展出數本原的觀念,是為同中有異。
注釋
①《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與此同,見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諸子集成》1954年,第181~182頁。
②臺灣學者盧瑞容教授從“相對關系”的角度出發,從文字溯源開始,對“和”的音樂性本質、“和同”之辨、“和合異同”及“和”的宇宙論和身體觀等哲學觀念進行了系統梳理。筆者基本同意盧的觀點。見氏著《中國古代“相對關系”思維探討——“勢”“和”“權”“屈曲”概念溯源分析》,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
③ 這里的“和”即是“相應”之意。
④ 先秦之時,“龢”、“盉”與“和”字尚并用,如《呂氏春秋?孝行覽》:“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慎行覽》:“夔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但總的趨勢是“龢”、“盉”漸為“和”字替代。越到后來則誠如段玉裁所言“今則和行而龢盉皆廢矣”。
⑤《淮南子?說山訓》:“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陸處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后成。”《孔叢子?抗志》篇:“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
事是而臧之,猶卻眾謀,況和非以長乎?’”錢鍾書指出,子思之“和”,正史、晏之“同”也。其實這里子思所說的“和”即齊景公所認為的“和”,亦即附和、應合之意。見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37頁。
⑥ 馮友蘭自注系引錢穆《論語要略》并采美國學者德效騫(Homer H. Dubs)所作之“The Conflict of Authority and Freedom in Ancient China Ethics”文之意。
⑦D代表第爾斯輯本《蘇格拉底以前哲學家殘篇》的代號,數字即該書該章編碼,下同。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2] 徐元誥.國語集解[M]. 北京:中華書局,2002.
[3]〔清〕王先謙.荀子集解[M]. 北京:中華書局,1988.
[4]〔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黎翔鳳.管子校注[M]. 北京:中華書局,2004.
[6] 〔東漢〕荀悅.申鑒[M].上海:上海書店,1986.
[7]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M].上海:上海書店,1986.
[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 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疏.論語集解義疏[M](見《論語注疏及補正》).臺北:世界書局,1990.
[11] 程樹德.論語集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12] 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86.
[13]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14]〔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15]〔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10.3969/j.issn.1002-6916.2010.21.043
于占杰(1979——)男,漢族,山東文登人,首都師范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2007級博士生,研究方向:先秦哲學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