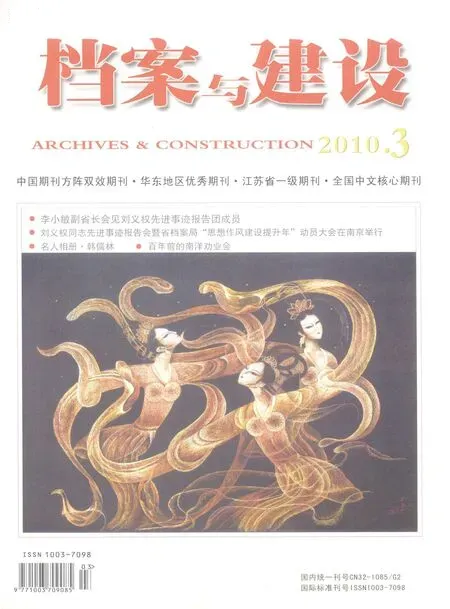那年我十六歲
□武明劍口述 黃劍寶整理

翻開《江陰市志》,有這樣的記載:1968年7月25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至1969年7月,全縣有老三屆(66、67、68屆)高中畢業生共5813名,全部動員去農村插隊插場務農,其中600人插隊至吳江縣農村。1971年,又800名知識青年去蘇北濱海農場和東辛農場插場。徐霞客鎮《峭岐志》中也有記載:1971年5月,峭岐14名知識青年去連云港東辛農場落戶。
武明劍對我講,他就是這14名中的一個。那年,他虛齡16歲,兩年制的初中剛畢業,人生得小模小樣,在當時的所有插場青年中是最小的,乍一看還是個少年。記得到農場報到時,有位南京的“插兄”開玩笑說,這小孩身上還有奶腥味。按理說,他當時的年齡還不到下鄉插隊的歲數,但在多次強烈要求下,公社民政科還是批準了。
筆者問:你為什么會有如此決心呢?武劍明嘆了口氣說:啊呀!你勿曉得,當時家中兄妹五人,哥哥在上高中,妹妹和弟弟都在上小學,就靠父母上班那點收入,要負擔五個孩子上學,還要維持生活,你說容易嗎?再說那時上學也是和和調,不是學工,就是學農學軍,整天轉在工廠車間或田頭,能學到什么?還是早點出去自謀生路,還可減輕家里的負擔。更何況那時上山下鄉的熱潮搞得轟轟烈烈,大街小巷到處貼滿了宣傳標語,廣播里整天在大力宣傳鼓動。自己還有一個迫切的愿望,就是想先插隊落戶后再去參軍,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解放軍,這是從小就有的志向啊!
他一口氣說了許多,同時也斷斷續續地講起了農場的一些經歷。百聞不如一見,要展現他當年的那些生活情景,莫過于去東辛農場實地走一走、看一看。于是我征求他的意見,能否去趟連云港東辛農場。他爽快地答應我:好啊!反正我現在下崗在家,常常靜坐下來就要回憶那些難忘的歲月,真想去故地看一看啊!于是約了個日子,決計去連云港東辛農場。在征得江陰市檔案局領導的同意和支持后,10月12日,我們自己駕車前往,同行的還有1968年我縣首批插隊到吳江的老知青孫可立。
我們沿著沿海高速公路一路向北,上午十點半左右,在一個名叫新浦的地方下了高速公路。再循著“東辛農場”的路標一路向東,約20分鐘的時間,來到了不似心目中想象的東辛農場。
東辛農場坐落在連云港市東南方向的沿海邊上,極目遠眺,良田萬頃,茫茫一片。由西向東的主干道兩旁高樓林立,各類商店鱗次櫛比。遠處高高矗立的建筑架和大吊車,昭示著東辛農場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武明劍跨下轎車,雙目凝視著遠方,由衷地嘆了口氣說:啊!38年啦,全變啦!眼前寬闊的水泥大道,當年只是一條泥土郵路,也是我們農場唯一的一條大路,每逢下雨泥濘一片。那時的大路兩邊,分散駐著我們各個知青連和零星幾個破舊的小村莊,我們的連部就在附近。因為當時此地曾是一個小集鎮,有郵局、百貨店、食品站、飯店、理發店等,歪歪斜斜地分布在這條破街上,與其他遠離集市的連隊知青相比,我還算運氣好的。走,去尋找我們當年連隊的駐地。他領著我們一邊穿街走巷,一邊講述著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往事……
1971年5月20日下午,是我們出發的日子。那是一個春光明媚,鳥語花香,彩蝶紛飛,令人神往的日子。我沉浸在對新生活憧憬和向往的興奮里,全不顧母親的悲傷、父親的沉默和兄弟姐妹的依戀。兒是娘的心頭肉,兒行千里母擔憂!這幾天母親為我的遠行一直在作著準備,替換的衣服、鞋襪、日常生活用品等,還為我專門做了一些粽子,以便路上充饑。那些天母親整天以淚洗面,常常用呆呆的目光注視著我,嘆著氣。眼看就要出發了,全家人緊緊地跟在我的身后,父母幫我拿著行李,要送我到輪船碼頭。峭岐中學的李淑英校長(當時叫主任)也專門來送行。和我同行的還有徐兆紅、湯珍珠、黃亞荷、徐挺、黃美郎、汪玉仙、沈炳南、吳丁慶、陳振祥、姜德勝、王靜健、徐正敏、丁國良,共14人。14個家庭組成的送行隊伍浩浩蕩蕩,行走在窄窄的老街道上。記得那時的輪船碼頭就在峭岐街的南沿河邊,對岸就是建國前大地主吳齊波和吳林寶叔侄倆的近400畝的大果園(現已被徐霞客鎮人民政府建成了一個旅游景點)。輪船碼頭極其簡陋,用幾根大木頭伸入河中,搭成一個“門”字架子,再在架子上擱上幾根木頭,形成一個直角形的木架。輪船靠岸后,船工用一塊跳板往木架上一擱,乘客就依次排著隊,一個一個搖搖擺擺地上船。
父親幫我提著行李,緊跟在我的身后,他要送我到江陰。到了輪船的甲板上,我轉身朝岸上一看,只見母親淚流滿面,嘴里還在不停地告誡我一定要注意身體。父親一聲不響地站在我的身邊。我看著父母和家人沉重悲傷的神情,似有一種酸痛涌上心頭,便一溜煙鉆進船艙。然而,到了船艙還是忍不住從船窗里偷看了一眼母親,只見她一邊用左手不停地擦著眼淚,一邊舉起右手對著輪船向我招手,張著嘴,說著我聽不見的話,我想一定是臨別時的再三囑咐。我再次別過頭去,似有一股男子有淚不輕彈的勇氣。少頃,只聽“嗚”的一聲長鳴,輪船要起航了,又聽得“”的一聲哨子聲,輪船便慢慢駛離了碼頭。從此,我離開了生我養我16年的故鄉,開始我漫漫八年的插場生涯。
憑著武明劍對38年前的記憶,我們繼續走街串巷地尋找,終于在轉了幾個弄堂的居民住宅后,找到了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江蘇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三團七營五十連二排六班”的老房子。可惜,當年一式六排的老房子經歷了近40年的變遷,早已面目全非,但當年女插青居住的一排還在。我一看,典型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用石塊和紅磚砌成的矮平房,前檐高不過三米,后檐高不過二米五,間長為小八步約六米,間寬三米余,總約20平方米的面積,每間朝南開了一個門。后墻有一個長寬不過70公分的雜樹木窗,也許是為了御寒,所以后墻的墻身較厚,以致內窗臺上可以放一些東西,住在靠窗的可以放些書籍或其他生活用品,女插青還可以放上一面小鏡子,每天照著梳妝打扮。屋頂均為水泥桁條,桁條上釘上雜樹椽子,鋪上蘆席,上面蓋上紅色或青灰色洋瓦,雖然簡陋,倒也整齊好看。

武明劍描述,當年五十連插青和連部家屬的生活區是這樣布局的:一式小平房一律六間一排,左一排,右一排,前后各三排,中間有一條寬約三米的小通道,前后排之間有一片十米開闊的場地,供我們洗曬衣被和活動。右前排六間是女插青宿舍,右后排六間是我們連隊的食堂和豬舍,其它均是我們男插青和連部家屬的宿舍,我住在左后排。在食堂的西北角,有一條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河,小河邊長滿古樹柳木,一年四季能聽到樹上的鳥語和看見清清河水中游的魚兒,小河上有一座小橋,走過小橋就是一所小學校。在我們生活區的周圍和場地上,栽著一排排整齊的白楊樹,白楊樹的枝丫一律向上,英姿颯爽,就像我們這些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在生活區的西南方向約二百米處,有一個前后兩排平房組成的小院子,那是五十連連部辦公處。
我們根據武明劍的描述按圖索驥,在女宿舍前面的場地上找到了當年唯一的公共廁所。我一看,那用大小石塊堆砌而成的廁所,極像放在公眾面前的一件“老古董”,也像東北深山老林里的蘑菇屋,被后來自由建造的各種大小建筑物圍在不起眼的地方,30年前用水泥和手工做成的“男”、“女”兩字還清晰可見,我趕緊用相機拍了下來,雖有點不雅,但它倒是一個完整的歷史物證。武明劍說,這就是我們連上百號人唯一的“出口公司”,夏天來方便吃勿消蚊子蒼蠅的叮咬,到了冬天,有時深夜上廁所,裹了一件大棉襖都凍得發抖,還要從后排一溜煙跑到這里,蘇北平原的嚴冬寒風刺骨,現在想想還有點后怕。

武明劍接著對我說,那天我們離開峭岐后,先到江陰縣委黨校住了一夜,縣里還組織我們進行了一次學習培訓。21日,我們從江陰乘汽車去無錫上火車,臨別時,身邊的父親眼看著小小的兒子即將與自己分別,呆呆地看了我一眼,便痛苦地雙手抓住自己的鬢發,流著眼淚蹲下身去。我第一次看見父親有這樣的慈心,因為父親是峭岐街上有名的嚴父,平時我們兄妹五人無論哪個淘氣或惹事,父親二話不說舉手便打,且不是用手打,而是有一根專用棍棒,我們幾個沒少挨父親的棒頭。所以,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父親是我們家里的“老虎”,善良慈愛的母親才是我們溫暖的港灣。此時此刻,我突然感覺到了人間偉大的父愛,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也是突然醒悟的。我熱淚盈眶,強忍著別過頭去,似有千言萬語要對我的父親傾訴,然而終究一句也說不出來。也難怪,那時的我畢竟還小,對人間的冷暖和親情的體會只是淺顯的感覺,真正要用語言表達卻沒有達到理性認識的程度,所以自己背起行李與同伴們一起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現在想起來,別怪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這樣“殘酷”,在那個時代,靠他和母親吃辛吃苦負擔我們五人成長是多么地不易,經濟和精神的壓力有多大!非要到自己為人父母后,嘗盡了人間的甘苦才有深刻體會啊。
那天我們在江陰西門車站登上大客車直達無錫火車站,坐火車兩天一夜經南京、徐州后,直達連云港的新浦車站,再坐公共汽車到達目的地——東辛農場,記得是1971年5月23日的傍晚。初去有兩件事至今難忘,一件是那天晚飯時第一次吃到藥芹炒肉絲,因我在老家從未吃過這菜,一般濃濃的藥腥味叫我惡心得直吐。另一件事是那時我確實還小,貪睡的毛病加上一路的疲勞使我一夜睡得像死狗一樣,以致清早起床的哨子都沒有聽到,醒來后一看,臨時用稻草鋪就的大通鋪上只剩下我一個人四仰八叉地躺著,不知天南地北,還以為是睡在家里,趕緊起床穿衣奔出去,同志們早已端著飯碗在吃早飯了。現在想想真的好笑。
憑著武明劍的記憶,我們離開了當年的居住地,向西南方向尋找當年的連部。果然,在一條新筑的大路東面,發現了當年的連部所在。只見在圓圓的月形門里邊,掛滿著絲瓜藤蔓,場地上種滿各類綠瑩瑩的蔬菜,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正在細致地侍弄著。發現身后有人,老人直起身來,用審視的目光打量著我們。武明劍仔細辨認了一下之后,欣然大聲喊道:“茅場長!”老人先是一驚,然后打量起來:“你是?”“我是武明劍呀。”“啊呀,小武啊!”老人恍然大悟,緊接著相擁相抱,緊緊地握住了武明劍的雙手。“啊呀!多少年了啊!想不到今天能看見你啊!”老人感動萬分,帶著那濃濃的蘇北口音敘述起當年的往事……
武明劍對我說:老人名叫茅青山,是當年五十連的指導員。大約1976年,建設兵團劃歸地方管轄,茅青山擔任分場的副場長,專管農業生產。在漫漫八年的插場生涯中,老人沒少對我關心。剛來農場時,連部領導體諒我人小,就安排我在連部抄抄文件,抄寫大字報,使我遠離繁重的體力勞動。我的一手鋼筆字和毛筆字,就是在那時打下的基礎,直至現在,筆墨紙硯是我人生最好的“伴侶”,雖自我感覺難登大雅之堂,但它使我的業余生活充滿了樂趣。
在農忙季節,我除了在連部做些類似文書的事情外,還是要參加勞動的,如割草、放牛、看青等。割來的草主要是喂牛,那時農場的牛車是主要運輸工具,每逢收割季節,一輛輛的牛套車穿梭在田間場頭,上千畝的莊稼果實都得靠牛車拉到倉庫場上,然后脫粒、揚谷、曬干、入庫,再繳給國家。還有那潔白的棉花、鮮嫩的甜菜等等,總之,每個季節都有豐收的果實,都得靠人力和牛車去完成。說起割牛草與我們家鄉的割草是不同的,那時家鄉生產隊一般只有一頭至兩頭牛,割草只要一個人就能完成,而我們連隊共有十幾頭牛,每天的用草量是很大的。割草的工具不是竹編的筒籃和短柄鐮刀,而是套著牛車和手持類似大草原牧民的長柄鐮刀,那鐮刀像一輪彎彎的月牙,刀刃磨得飛快,割草時手握長約二米的刀柄,利用右大腿和腰部扭轉的力量,“唰唰唰”地將草齊齊地割倒在地,然后一捆捆地裝到牛車上,堆成一個小山型,再駕著牛車往回趕。這時我可以悠然自得地躺在草堆上,那藍天白云和高高的白楊林伴隨著我,閉上眼睛,哼著歌曲享受一番勞動后的快樂。
看青除了是一種責任,還有另一番情趣。那時每個連隊都有一二千畝地的莊稼,不是稻麥就是棉花或甜菜等,一年四季都不歇著,一年四季都有人專門看護,一防野獸及飛鳥的侵害,二防階級敵人的破壞。其實所謂的“階級敵人”也不過是一些愛貪小便宜的農民,或順手撈點稻草、樹木,或隨手拿一點成熟的作物之類,但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看青是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的。看青的時間是白天田野里無人勞作的時候和晚上九點之前,常常是白天我一個人手握著木棍轉戰在廣闊的田野,跑累了就挑個沒人的地方,頭枕草地、面朝藍天睡上一覺,晚上手握著雪亮的手電筒,繼續轉田頭直到休息時回駐地。在那個正長身體又充滿饑餓的年代,有些知青乘看青的機會,做了一些至今想起來都感到難為情的“壞事”。如順手偷些老百姓的白菜、山芋、蘿卜、雞蛋等,拿回宿舍煮熟了大家一起分享。特別是雞蛋,為了避免留下“罪證”,他們悄悄地在雞蛋殼上用針鉆出一個小洞,然后仰起脖子將里面的蛋黃和蛋白吸個精光,再悄悄地放回到雞棚里。現在想想真是缺德,因為那時的老百姓要靠雞蛋在市場上換取油鹽醬醋的啊。我也做過一件缺德事的,記得是一個夏天,我和沈炳南、姜德勝三人借著游泳的機會偷過林場的蘋果。當時正下著大雨,路上無人,便悄悄地游至對岸的蘋果園,狠狠地偷了大半蛇皮袋的蘋果,回宿舍飽餐了一頓。

也難怪,在那個艱苦和饑餓的年代,每月的糧食定量只有28斤,月工資先是15元,后來逐步加到17元、19元、23元,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日日見長的身體,那點糧食好似木樨花喂牛,那點工資只能扳著指頭一點點地花,難得吃個葷菜是最大的享福。還有就是盼望著過年,因為每年的除夕有一頓聚餐,連部就會殺一頭大豬。每到那天兄弟姐妹們異常興奮,早早地等待著開飯的鐘聲。一盆菜端上來,十雙筷子一齊下,猶似風卷殘云,不消幾分鐘就盆子朝天,連汁湯汁水都掃得精光。1973年連隊分紅,我第一次分到113元,這是我靠自己辛勤的勞動得來的一筆巨款,長到那么大還是第一次看到這么多錢。記得我激動地將錢塞到枕頭底下,然后雙手護住枕頭臥倒在床頭,美美地享受了一番。年底回鄉,還給妹妹買了一雙紅布面塑料底的新鞋子,讓妹妹在街上風光了一下。后來聽說妹妹穿了幾天后再也舍不得穿,藏了起來,到有喜事時才穿出來。
眼看就到中午飯的時間,茅青山老場長非得請我們用餐不可,后來經我們再三推辭,也就作罷。我們三人就近找了家飯店,僅僅花了50元便飽餐了一頓,四大盤佳肴讓我們撿了個地區消費差價的大便宜。
中午的秋陽和秋風給人一種既溫暖又涼爽的感覺。午飯后,我們三人來到當年五十連的田野里。田野里一片金黃,沉甸甸的稻穗在秋風的吹拂下頻頻向我們點頭致意,寬闊的灌溉渠道兩邊是寬寬的機耕道,機耕道兩邊又是高高的防護林,整整齊齊,向遠方延伸。在防護林的遠處,當年兄弟連隊的營房猶在,遠遠望去像一排排整齊的鴿子棚。我想,當年的知青就像一只只的鴿子,清晨上工哨一響就飛出棚去,傍晚收工哨一吹就飛回巢中。那里是他們唯一的歸宿,那里是他們帶著疲憊的身體休息的地方,那里是他們含著眼淚思念家鄉思念親人的地方……
我們徜徉在田埂上、果林間,還有掛著幾個枯萎凋零棉果的棉田旁,更多的是沒有盡頭的稻田小路上……
武明劍說:我在連部干了三年,1974年開始我當上了營部通信員,在四十八連至五十二連的幾十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我整天和自行車、郵包、報刊、信件在一起。那時能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村間田頭,就像開著小轎車一樣神氣,更何況我是為這么多人服務的通信員,所以我愛自行車就像騎兵戰士愛戰馬一樣。騎車的技術也十分嫻熟,單把上下車,邊騎邊發信件等只是小菜一碟,特別是那時沒有石子路或水泥路,窄窄的泥路上有被牛車或郵車壓成的一條深坎,我可沿著那條坎不差分毫地一路騎過去。但通信員也很辛苦,每逢下雨天自行車不能發揮作用,就只能靠自己的雙腳步行,有時深夜送加急電報要來回跑幾十里路。
也是在這一年,我終于盼來了報名參軍的機會,這是我從小就有的志向啊!以我民兵訓練射擊的水平和強壯的身體,都說我沒問題。踴躍報名,參加體檢,一關,二關,幾個關口過去了,可在胸透上查出了小毛病,結果被刷下來,我茫然若失,以致一段時間吃飯睡覺都不香。1976年又有一次機會,結果還是這樣,我也就死了這條心。
我當了四年通信員。1977年,連部辦了家燈管廠,連部又調我到廠里當出納會計,一直干到1979年1月離開農場回鄉。
秋陽從樹梢慢慢下垂,我們在田野里漫步了近兩個小時。走一走當年江陰插青曾經戰斗過的地方,我們感慨萬千。
當年,他們懷著無限忠誠,憑著自己一顆紅心兩只手,誓叫荒灘變良田。寒冬臘月,他們在這里開渠引水,清理淤泥,筑路整田;夏日炎炎,他們播種收割,揮灑汗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整整八個春秋,度過他們的青春年華。
當然,還有那無休止的政治學習,無數次的露天電影,大會堂的文藝演出,學唱樣板戲的高漲熱情,打賭一口氣吃一斤饅頭的歡樂,刻骨銘心的初戀等等。如今回憶起來還歷歷在目……
太陽西垂,眼看時候不早,我們抓緊時間又走訪了幾位當年的老領導和老鄉家,看了一眼當年的農場醫院、人民大會堂、農場場部。我說回家吧,武明劍回過身去,向東辛農場投去深情的一瞥,然后打開車門,跨上汽車,踏上了回江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