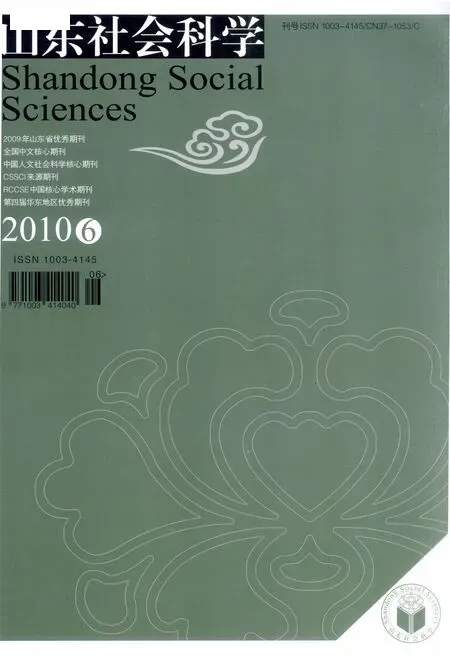唐詩中“草”的隱喻認知解讀①
2010-04-12 21:58:26林麗君
山東社會科學
2010年6期
林麗君
(山東廣播電視大學,山東濟南 250014)
唐詩中“草”的隱喻認知解讀①
林麗君
(山東廣播電視大學,山東濟南 250014)
當代隱喻理論認為,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修辭現(xiàn)象,更是一種認知方式。人們往往通過具體的、熟悉的、有形的概念去認知和體驗抽象的、復雜的、無形的概念。隱喻與詩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是詩歌重要的表現(xiàn)形式,隱喻在詩歌中普遍運用。唐詩中關(guān)于“草”的隱喻可以說比比皆是,并且隱喻豐富;與其它時代詩詞中“草”的隱喻相比有其自身特點。
唐詩;草;隱喻;認知解讀;時代特點
中國是一個講究語言藝術(shù)的國家,尤其善于運用隱喻來含蓄地進行語言表達。俗語有“聽話聽音,鑼鼓聽聲”,即指語言中有言外之意,文人講究說話含蓄,不能太直白,其實就連村婦吵架也有“指桑罵槐”,這其中都有隱喻在起作用,可見隱喻是多么普遍地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我國古詩詞更是把這種隱喻發(fā)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從《詩經(jīng)》到楚辭再到唐詩宋詞,幾乎每個時代的詩歌中都大量存在著隱喻現(xiàn)象,而“草”的隱喻就占了很大比例,在古詩詞中俯拾皆是,且隱喻豐富。本文僅對唐詩中“草”的隱喻現(xiàn)象進行簡單分析,以期對“草”在唐詩中的隱喻規(guī)律及特點進行簡單歸納,文中涉及的語料均來自 198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鑒賞辭典》。
一、隱喻的本質(zhì)與內(nèi)部結(jié)構(gòu)
人類對隱喻的研究已經(jīng)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修辭學中隱喻一直被理解為辭格——比喻的一種,是“比明喻更進一步的比喻”。……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