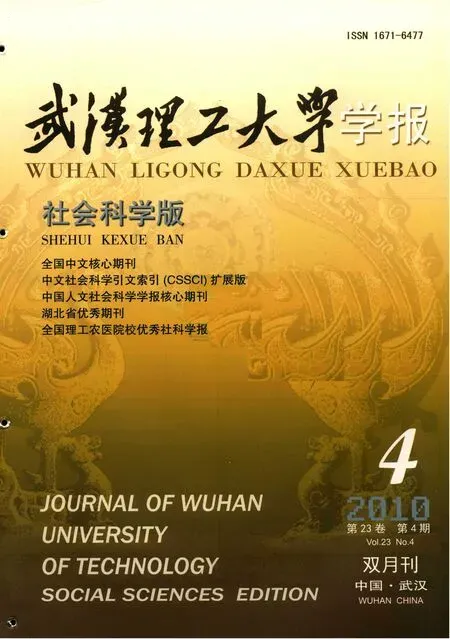“比較熱”下的冷沉思——中西比較法在法律史研究中運用狀況之評析
段曉彥
(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政法系,福建福州350002)
“比較熱”下的冷沉思
——中西比較法在法律史研究中運用狀況之評析
段曉彥
(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政法系,福建福州350002)
中西比較法在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表現為籠統定性,力證西方的法律制度或因子已存在于中國傳統法中;二是表現為簡單地以西法為模式,而苛責中國傳統法的簡陋。這都悖離了比較的原理和要求,而落入了“比附”的俗套。在創造和構建今天中國的法文化中,法律史研究需發揮文化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遵循比較的原理和要求,竭力探尋和破譯中華法系的社會文化遺傳密碼,摒棄“比附”,尋求中國法律史的“自我”。
法律史;中西比較;比附
一、“比較熱”的興起
比較法學是對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進行研究的學科,既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法學的一種研究方法。自1900年第一次國際比較法大會在巴黎召開以來,比較法的發展已逾百年。對中西法律制度進行比較,不僅是學術研究的需要,更是法制改革和法治建設的需要。中國法治求索百年,實際上是探索如何比較的百年。自清末法制變革起,中華法系傳統的律令和律例體制開始解體。中國法制的近現代化運動走的是學習歐美的路線,這就需要力求“今西”和“古中”的會通。思想家和學問家們,諸如梁啟超、嚴復、沈家本、吳經熊、陳顧遠、梅仲協、楊鴻烈、蔡樞衡、瞿同祖等,通過政論、演講和學術文章的形式,用比較方法探究中西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區別和聯系,構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政壇學壇經久不衰的課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西法文化比較持續升溫,也相繼出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成果。如張中秋先生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第一次從文化學或文化史角度全面系統地分析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八大差異以及導致這些差異的成因和歷史后果[1]。公丕祥先生等完成了《法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一書,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分析論證了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西方法律文化東進,滲入及中國傳統文化轉型變革的歷史規律[2]。張培田先生所著《中西近代法文化沖突》一書,從中西近代法文化沖突的角度,透視了鴉片戰爭以來到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法制演變[3]。范忠信先生的《中西法文化的暗合與差異》[4]2-4,從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用歷史分析的方法和比較分析的方法 ,通過對“親親相隱”、“親屬相犯”、“親屬相奸”、“無夫奸”、“重點治吏”等制度的研究,來“尋找和闡釋中西法律文化的深層共性”;崔永東先生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較》[5],從法律文化、道德與法律之關系、治國方略、司法思想、私人財產權觀念、法律自然主義六個方面對中西法律文化進行了比較。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專門編著《比較法律文化論集》,收錄了1980-2006年關于中西法律比較的論文30篇,可以說是這一時期中西法律比較成果的一個凝結和濃縮[6]。在法學研究中——無論是理論法學、還是部門法學,若沒有比較法的出現,其研究必然是低層次的。
勿容置疑,中國法律近代化和現代化之進程基本是在學習、比較和借鑒西方法律理論和制度的過程中展開或完成的。“比較熱”的興起自有其合理原因。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通過對中西法律進行比較,其優勢在于可以拓展學術視野,幫助我們突破一些陳舊和可能錯誤的思維框架;從法制建設實用或功利主義的立場來看,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地區不同法系的經驗,以完善自我,為法制建設提供制度和文化資源支持。但是,在掀起“比較熱”的同時,我們需要反思的是,中法與西制畢竟屬于不同的法系,其制度設計、文化觀念、思維模式、價值取向、法律方法與技術等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加上作為交流載體的語言和文字又截然不同,我們進行比較的初衷是為了完善自我甚至是拯救自我,但卻又往往落入“比附”的俗套,結果卻迷失了“自我”,這與中西比較的運用失當不無關聯。那么,中西比較法的運用究竟存在哪些主要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何在?我們的法律史研究應如何調適中西比較法的運用?本文試圖對以上問題作簡析。
二、中西比較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認為西方的法律制度或因子已存在于中國傳統法
自清末法制變革起,中國法制的近現代化運動是以西方法律理論和制度為標桿推動的,這就需要力求“今西”和“古中”的會通。在此,我們分別以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著稱的“冰人”——沈家本和“言論界的驕子”——梁啟超對會通中西的態度為例說明。
1.“對號入座”,將中國傳統法納入西方法律體系解釋。在中國法律史上,當歐美法律話語在近現代中國法律生活中取得壓倒性的話語權時,“古中”之法制和法理必須納入這一法律體系中來解釋,沈家本作為“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7],也免不了簡單的對號入座現象。他“舉泰西之制而證之于古”,認為,“西法之中固有與古法相同者”[8],西方的法治學說,并非西方之獨創。《管子》提出:“立法以典民則祥,離法而治則不祥。”又提出:“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還主張:“先王之治國也,使法不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8]當然,沈氏的“古已有之”之說,不純粹是,甚至主要不是一種學術見解。他抬出三代圣人之法,說是與泰西之法相合,其直接的意圖是想減輕法制改革的阻力,類似于康梁的托古改制。這些不成熟之處,反映出他借古喻今,以期減少修律阻力的良苦用心。
2.以中學比附西學,“以中證洋”。作為一代學術驕子的梁啟超,維新變法時期,大量地運用“以中證洋”的手法,“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謂彼之所長,皆我所有”[9]106-111,進行革新思想宣傳。《古議院考》一文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梁氏遍引先秦及漢代典籍、制度,證明議院之意在中國早已有之:
“于古有征”。其言曰:問子言西政,必推本于古,以求其從同之跡,敢問議院,于古有征乎?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議院之名,古雖無之,若其意則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書》曰:“詢謀僉同。”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其在《周官》曰……其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后殺之。”《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諸大夫,上議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國人,下議院也。雖無議院之名,而有其實也[9]94-95。
在戊戌政變后的政治宣傳活動與講學中,梁氏仍不時地比附中西學,如認為霍布斯的學說與荀學、墨學相類似,“其所言哲學,即荀子性惡之旨也;其所言政術,即荀子尊君之義也”,將荀學與霍氏學說作了簡單的比附與比較[9]94。墨子論社會起源與霍布斯“同一見解”,國家成立后,“上同乎天子”,就此點論,與霍布斯輩所說,“真乃不謀而合”[9]127-128。其他如將井田制度與社會主義的比附,等等,不一而足。總之,西人的觀念或制度,在中國皆古已有之。筆者認為,沒有具體制度的比較,只是籠統定性,缺了名實之辨,有點指鹿為馬的味道,因此,盡管這些研究的出發點或有可取,但學說本身卻不能服眾。
(二)以西方法為模式,苛責中國傳統法簡陋
1.中國人眼中的“傳統法”。梁啟超于1896年寫成的《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明言,“文明野番之界雖無定,其所以為文明之根原則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備而愈公者,則愈文明”,而中國“今日非發明法律之學不足以自存矣”[9]93-94。顯然,梁啟超的文明標準是西方的“繁備”且“公”的“法”,因而西方自希臘、羅馬時便法律日益發達,而中國自秦漢以來法律卻日益衰敗。
即便是當前法學界,一些研究者用現代法的標準去要求古代法,認為古代法的規則、體系、精神與現代法格格不入,構成了現代法發展的阻礙。許多人甚至將現實中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法律制定的不完善、法律執行中的誤差、司法中的腐敗等,歸咎于中國古代法的傳統不如西方優秀。總是習慣地將自己的“老祖宗”和“老祖宗之法”作為批判的靶子,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中國法律缺乏好的傳統和基因。
2.外國人眼中的“傳統法”。中國人尚且如此,西人更是以“帶色的眼睛”來審視中國傳統法律。近代社會科學發展史上世界公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馬克斯·韋伯將中國傳統司法審判稱之為“卡迪審判”①,認為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體現。并將其作為西方現代司法審判的對立面,而后者則是西方(主要是歐陸)法律文化“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具體呈現。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韋伯認為:
“中國的法官——典型的家產制法官——以徹底家長制的方式判案,也就是說,只要是在神圣傳統所允許的活動范圍內,他絕對不會根據形式的律令和‘一視同仁’來進行審判。情況恰恰根本相反,他會根據被審者的實際身份以及實際的情況,或根據實際結果的公正與適當來判決”[10]。
這是韋伯作為一個西方人用二元對立的理念型——“形式的—實質的”與“理性的—不理性的”范式分析中國傳統法律時得出的結論。立基在清代司法審判制度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我們發現他的這種論斷是令人質疑的,而其最大的問題在于“以西論中”,帶著規范性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11]。麥克雷曾經不無嘲諷地說:“幾乎所有寫韋伯的書,都是帶著敬畏之感落墨的。”[12]特別是韋伯的方法論和由這種方法論得出的結論導致很多的漢學家和中國研究者的誤解,這其實是對中華文化整體性的誤解。
三、中西比較法律史研究存在問題的原因歸結
一百多年來我們是以西方近現代法律術語、法律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來釋讀,解構中國古代法,來建構中國現代法的。它使法律史研究別開生面,使之從過去的律學、經學中解脫出來,建立起近代科學思想和學術規范的法律史學科,這無疑是一個莫大的進步。但是,由以上幾種傾向可以看到,中國法律史正在喪失“自我”,所謂的“中西法律比較”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比較”,而只是一些簡單的牽強的“比附”。
(一)混淆了“比較”與“比附”
比較是確定事物相同點或相異點的方法。是根據一定的標準,把有某些聯系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事物加以對照,從而確定其相同或相異之點,便可以對事物做初步的分類。然而只有在對各個事物的內部矛盾的各個方面進行比較后,才能把握事物的內在聯系,認識事物的本質[13]。比附是指拿不能相比的東西來勉強相比[14]。“古中”和“今西”的“會通”之所以偏離方向,失去自我而變得非驢非馬,從方法論的角度進行審視,是我們混淆了兩種方法的運用,或者沒有按照比較學所倡導之模式“運行”,意在“比較”,實在“比附”。
第一,“比較”之首要前提是兩對象之間具有可比性,否則就會落入“比附”的俗套。如沈家本先生提出,我國《周禮·秋官》中的“三刺之法”與《孟子》“國人殺之之旨”相吻合,“實為陪審員之權輿”[15]。這顯然有比附之嫌。陪審制度是古代西方“奴隸民主政治的產物”,是在古代審判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具有民主性質的訴訟制度。因民主高漲而確立或興起,因中央集權或專制而削弱或廢止。陪審制度及其變革承載著司法民主和權力制約理念。“三刺”是中國古代審判官吏聽獄斷訴的一種方法。其含義是指在審判案件時,經詢問群臣、群吏、萬民三方面意見后才能決定處罪犯死刑。其是和“明德慎罰”思想、親貴合一與家國一體的國家制度密切聯系的,是中國古代司法審判制度中的一種民主形式,更確切的說是一種“慎刑”制度。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實行的都是封建專制政體,根本沒有陪審制度生存和發展的土壤。
第二,“比較”必須持同一的對比標準和立足點,避免兩種或幾種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法價值論或思維方式,否則就會歪曲原義或者無法理出比較對象相同或相異的真正根源所在。如“親親相隱”制度,以往的學界認為其是“三綱五常”或封建宗法主義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的具體體現,該制度成了中華法系的殊相之一。有的學者認為,“容隱制”不但是古羅馬法中的重要內容,而且仍被法國、德國、意大利等現代西方國家所采用。由此認為,這是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之一[4]73-75。我們在嘆羨這一“驚人”結論同時,不能忽略另一深層次的問題,即中西法律中的“親親相隱”,其價值取向和立足點是不同的。前者屬于中華法系的古代血緣親情倫理立法,后者屬于現代意義上基于人性的親屬權利立法。血緣親情倫理立法的宗旨是家庭本位,基于人性的親屬權利立法的宗旨在于維護人權。
第三,“比較”必須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事物持價值等觀的態度,避免“文化一元論”或“歐洲中心主義”。韋伯之所以將中國傳統司法審判描述為“卡迪審判”。他過度強調了西方現代社會的法官在無漏洞的法律下嚴格依法審判的一面,而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事實存在刻意忽略。在他的眼中,中國古代的司法幾乎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因為它們都不是將一般性、概念性的法規適用在某一個事實之上,而是取決于裁判者對一個具體案例的公正感與價值判斷”[16]。細究,韋伯的論斷事實上并非僅是針對帝制中國時期的法律運作所下的一個概括性論斷,一旦將觀察視野擴展至他那整套理論,我們就可以發現,帝制中國的這個形象,在韋伯那里其實是被等同于西方中古社會的傳統法階段,從而被置入西方發展史的序列之中[17]。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
(二)對古代法的“原貌”認識困難
其實,中西法律比較之所以會在“古已有之”、與“一無是處”、“文明落后”之間游離,方法運用的缺陷當其首要原因。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如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代法的解體,人們對古代法原貌的認識日益模糊,加之研究者對國學的疏遠,把握傳統文化與古代法成為愈來愈困難的事情。對中國法律史而言,目前研究中的最大難題是已經無法尋覓原汁原味的古代法,而對古代法的認識愈模糊,比較法研究中的誤解和偏見就會愈多愈深,也就愈難發掘傳統法的精華和真正尋找到法的傳統動力。
(三)文化背景和語言能力制約
文化背景的不同也是導致中西比較運用失當的又一原因。在“古中”和“今西”的對接中,我們往往是以現代西方舶來的法律術語來闡釋中國古代的法律現象、用現代漢語去翻譯西方法律詞匯,即所謂“法言法語”概括“彼水彼土”的法律現象,由于從文化背景、語境到法的體系、特征等各方面 ,中國古代法與西方法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使得對兩者的認識產生無窮的謎障。
語言能力的欠缺也不能忽視。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中國比較法研究曾達到很高的程度,這與當時研究者精通數國外語是分不開的。著名法學家楊兆龍便掌握了8國外語,今天很少出現具備這種能力的學者了。研究外國法而不精通外國語,自然無法真正理解外國法。甚至可以這樣說,語言方面的不足,制約了比較的深度和廣度,也制約了大師的出現。
四、中西比較法律史研究的三個趨向
其實,古中與今西的沖突,絕非僅僅是話語系統的不同所致,隱在話語背后的本質問題,是現代法與傳統法的關系問題。長期以來,在“古中”法與“今西”的關系問題上,“今西”法屬于強勢的法文化系統;同樣,在傳統法與現代法的關系上,“現代法”占有強勢地位。然而,在文化多元和對話的今天,不是強勢吃掉弱勢。在創造和構建今天中國的法文化中,需要的恰恰是文化主動和自覺:現代法批判傳統法,傳統法批判現代法,為此,我們應努力尋求中國傳統法的“自我”。
(一)提煉和構建中國法律史固有的范疇體系和話語系統
中華法治求索,“既需廣采它山之石,又應悉心尋求自我,破解文化遺傳之密碼”。法的社會遺傳密碼和法的文化遺傳密碼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法的價值取向、法的思維方式、法的智能和藝術的奧妙所在。而破譯她是十分艱巨的工作,僅僅簡單地再現歷史上的法制度、法思想是無法達到的。它還要一種內心的體認,一種歷史高度的洞察,一種敏捷而準確的把握。只有長期潛心于斯,反復地入于史又出于史的人,才有望成為獲得打開密碼鑰匙的幸運者。為此,扎扎實實地深入到記載思想文化的典籍之中,認認真真地梳理傳統法中的基本概念,諸如禮、法、禮制、禮治、禮義、法制、法治、刑、律、刑律等等,與歷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律家進行交流和對話,理解他們思想,并運用當代的科學、方法和智慧識讀其中的精髓,逐步擺脫用西方法律概念為主闡釋中國傳統法,也許是我們當下應有的開始[18]。
(二)將法學類國學引入法律史教材
我們既然要尋求中國法律史的自我,就必須了解這一“自我”的內涵和特質,從這一意義上講,通過追尋法學國學的歷史和成就,來展示中國傳統法學,可能是有價值的一種路徑。如《中國傳統法學述論——基于國學視角》一書,就是一部以國學的體例、方法來敘述中國傳統法學的作品,可以說是致力于這方面工作的可貴嘗試。全書分為中華法系學、禮法學、刑名學、律學、唐律學、刑幕學、宋(慈)學、沈家本學,最后又附上了簡牘學。該書前言中所論及了該嘗試的初衷。其給我們的啟迪在于,主要以律令刑典制度為研究對象的中國法制史是不夠完整的,而注意禮法關系但忽略了禮法整體性的中國法律思想史也是不夠完整的,禮制研究、禮法制度整體研究,將會成為中國法律史的發展趨向[19]。
(三)用史料說話,重視司法檔案在研究中的運用
在倡導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多元化、思維邏輯多值化的今天,法律史研究在“與時俱進”,豐富“自我”的同時,避免迷失“自我”,必須要固守其最基本的“根魂”——用史料說話。比如,要對對韋伯關于中國傳統司法的誤解性的論述進行比較到位的辨正,遠非僅是粗略地指出韋伯的論斷并不符合中國的事實那樣簡單,更重要的是要以具體可靠的史實來證明韋伯的論述與作為事實的中國法律傳統的落差,進而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說明韋伯所感知到的,也許只是在西方映照下的一個對極面,其并沒有全面深入地洞察中國法律傳統豐富的真實面相。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林端教授,在其《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一書中所做的,有很多地方(尤其是第四章的內容)都可以被看作是這樣的努力。如在該書第四章第三節,林氏整理了現藏于臺灣大學圖書館的“淡新檔案”中222宗民事案卷,并以此基礎批駁了美國學者 M ark·A·A llee所謂的清代縣官民事斷案時甚少引用律例的論斷,后又選取了“淡新檔案”中的數宗“祭祀公業”案件,以史實為例證明國家法律與民間習慣同為法源[20]。林氏在這里所運用的,其實正是典型的法律史研究方法。
總之,我們在開展中西比較的同時,要慎重對待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研究。否則,如果在中西法律史、文化史方面的學養和研究歷練不足,抓到一些西法的概念和名詞來解構、詮釋中國傳統法的做法,或者輕易做出優劣評判的話,就失去了比較的意義,而落入“比附”的俗套。當然,慎重對待比較不是不要比較。正如俞江先生在浙江嘉興召開的“比較法在中國”學術研討會上(2007年11月24日)所說,從長遠來看,研究法律之間精神、文化的差異當是比較法領域的重點,但這種研究應從細微處著手,以微觀切入的方式來幫助我們思考宏觀問題,此亦為研究的方向之所在。文化、精神、理念的研究并非意味著寬泛,相反,我們正需要對文化本身進行更加細致的探索。
注釋:
① “卡迪審判”本來是被用來描繪回教法官的審判制度,后來卻被韋伯非常寬泛地借以指稱西方傳統社會的專權君主的“王室審判”,教權審判或家產制君主的審判,古雅典的“人民法庭”審判,革命法庭審判,陪審制審判等等。
[1] 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序言.
[2] 公丕樣.法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1-2.
[3] 張培田.中西近代法文化沖突[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內容摘要.
[4] 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與差異[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5] 崔永東.中西法律文化比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37.
[6]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比較法律文化論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序言.
[7]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0:872.
[8] 沈家本.寄簃文存[M].清光緒33-34年(1907-1908)鉛印本,卷六.
[9]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9:106-111.
[10] 馬克斯 韋伯.儒教與道教[M].洪天富,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123.
[11] 林 端.中西法律文化的對比——韋伯與滋賀秀三的比較[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6):26-40.
[12] 金耀基.韋伯、海德堡、社會學[M]∥金耀基.金耀基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45.
[13]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3839.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Z].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69.
[15] 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呈訴訟法擬請先行試辦折(1906年)[M]∥大清法規大全·法律部(卷十一).高雄:考證出版社,1972:1907.
[16] 林端.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M].臺北:三民書局,2003:18.
[17] 尤陳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重新解讀與韋伯舊論的顛覆[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2):154-160.
[18] 俞榮根.尋求“自我”——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傳承與趨向[J].現代法學,2005,(2):166-174.
[19] 俞榮根,龍大軒,呂志興.中國傳統法學述論——基于國學視角[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8-9.
[20] 艾馬克.十九世紀北部的臺灣: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M].王與安,譯.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125-149.
The Cool Meditation of“Comparison Method Boom”——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Study of Legal History
DUAN Xiao-y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Fujian Cadre College of Economical Administration,Fuzhou 350002,Fujian,China)
There are two harmful trends in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study of legal history:one of them holds that all western laws have already been included in ancient Chinese law s;the other holds that all Chinese law s can be reduced to nothing for its extreme simplicity and believes that only the western ones are the best model.The two trends both deviate from the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comparison,which tends to become blind analogy.In creat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a’s legal culture at p resent,the study on legal history should p lay a positive and conscious role in the endeavor to explore and decipher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eretical code,get rid of blind analogy,and look for the true meaning of China’s legal history.
legal history;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blind analogy
D908;D909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4.015
2009-12-29
段曉彥(1981-),女,河南省南陽市人,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政法系教師,主要從事法律史學研究。
(責任編輯 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