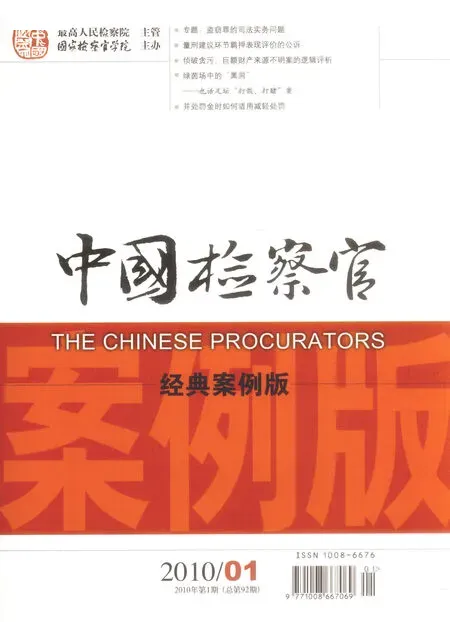誤盜自己的財物能否構成盜竊罪
文◎康紀強
誤盜自己的財物能否構成盜竊罪
文◎康紀強*
對于類似“對象認識錯誤”的行為,很多人認為應定性為犯罪未遂;筆者認為這種看法與刑法理論和司法解釋不符。
王某大擺酒席賀兒子滿月,同事紛紛前來捧場,觥籌交錯至深夜方散,王某大醉,送同事小張出門,同事發現自己騎來的摩托車不見了。到處找也沒找到。此時,王某見旁邊另有幾輛摩托車,將其中一輛摩托車撬開,小張將此車騎走。第二天,王某弟弟發現王某的摩托車丟失,遂向公安機關報案。經查,王某的摩托車正是被王某、小張前夜盜走的那輛摩托車。
有觀點認為:王某偷盜自己的摩托車,未侵犯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不構成盜竊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四項規定:“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
也有觀點認為,本案中王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未遂)。理由是:
其一,本案中,王某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且明顯不同于“偷拿自家財物或者近親屬財物”。“偷拿自家財物或者近親屬財物”,所指的行為是行為人在“明知”所竊取的是自己家所有或者其近親屬的前提下,對財物實施的竊取行為,其主觀惡性小,故對其“一般不按犯罪論處理”。而本案中,王某并不“明知”摩托車是自己的。
其二,本案中王某的行為屬于行為人對犯罪對象的認識錯誤,這種認識錯誤并不影響對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追究。本案中王某把自己的摩托車當作他人的,就是一種對犯罪對象(摩托車)的認識錯誤,這種認識錯誤并不影響其行為構成盜竊罪。
其三,本案中王某的行為屬于盜竊罪未遂(不能犯未遂)。犯罪未遂可分為能犯未遂與不能犯未遂。所謂不能犯未遂,是指罪犯人對有關犯罪事實認識錯誤,而使犯罪行為不可能達到即遂的情況。本案中,王某誤將自己的摩托車當他人的摩托車加以盜竊,犯罪目的不可能達到,即成立盜竊罪未遂(不能犯未遂)。
本文認為王某的行為不能構成盜竊罪。
一、誤盜自己的財物,不可能侵害所有權
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盜竊罪的客體為公私財物所有權。所有權屬于絕對權和對世權,具有排他性,排斥其他任何外來的非法妨害;反過來說,所有權并不排除權利人自己的“妨害”,因為自己的行為不可能對自己的“所有”造成任何有意義的妨害,不論這種行為是合法或非法,有意或無意。與此相聯系,現代刑法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就是“市民刑法”觀念的不斷成熟,它要求刑法必須反映市民社會的價值觀念,而所有權的絕對原則正是市民社會的基礎。如果刑法對權利人處分自己的所有物的行為進行打擊,就違反了“市民刑法”的基本要求,就是盲動而無效的,在正義上無憑,于功利上無據。所以,行為人對自己物權的侵害只是一種假想。充其量我們只能將盜竊罪的對象延伸至“他人合法占有的屬于行為人自己的財物”,而不能毫無限制地擴大到“自己的財物”,即使存在認識上的錯誤,其行為的實際指向仍然是“自己的財物”。正確理解盜竊罪的對象,符合刑法謙抑性原則,也是現代文明刑法的必然要求。
二、一般的盜竊未遂不具有可罰性
很多人認為,在誤盜自己的財物這種認識錯誤情況下,應當成立盜竊罪的未遂。這種說法沒有看到盜竊罪在犯罪停止形態上的特殊性,實為不妥。盜竊罪的成立以“數額較大”為標準,達此標準犯罪成立。如果盜竊數額不大或分文未得就不構成犯罪,沒有存在未遂的余地。但同時,盜竊罪又是結果犯,即只有出現財物被行為人盜竊,所有人或保管人失去控制的結果,始能既遂。當行為人已經著手實行盜竊,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沒有完成時,在理論上應該能夠成立未遂,這就出現了兩難問題:一方面,盜竊罪作為結果犯,存在成立未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盜竊行為沒有“得逞”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認定可能盜到的財物是否達到 “數額較大”的標準?這種法律適用上的困境其實來源于我國刑事立法的缺陷。
在未遂犯的處罰范圍問題上,各國刑事立法大致采取三種做法:①概括主義;②列舉主義;③綜合主義。我國《刑法》第23條明確規定:“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可見,我國刑法在未遂犯的處罰范圍上采取的是“概括主義”,即對分則中規定的所有犯罪的未遂,原則上都應處罰。我們認為,采取這種立法模式,在哲學上犯了“一刀切”的錯誤,難以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法律上,隨著國際刑法潮流漸趨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這種處罰輕罪未遂的做法已經失去來自于正義維持的支持。針對這種弊端,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未遂犯的處罰模式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缺口,其第1條規定“盜竊未遂,情節嚴重,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重要目標的,應當定罪處罰”。言下之意,只有符合“情節嚴重”的盜竊未遂才應該論罪處罰。何為“情節嚴重”,第6條又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如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盜竊金融機構、流竄作案危害嚴重、累犯、出現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等加重結果、盜竊特定款物后果嚴重等具體情形。這兩條規定的內容說明:我們開始意識到概括主義之弊端,實際上對刑法總則的“概括處罰主義”做了一次微調,對盜竊未遂的處罰開始采取列舉主義,這樣才能避免矯枉過正。此舉可謂是一個明智且意義重大的選擇,對一般的盜竊未遂,大可收起刑法這柄“雙刃劍”。法律必須切合社會需要,否則就會成為一紙空文。
三、事實認識錯誤可阻卻違法性
事實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與自己有關的事實情況所產生的不正確認識。它大致可以分為三類:①積極的錯誤,即犯罪事實本來不存在,而行為人誤以為存在。②消極的錯誤,即犯罪事實雖然存在,但行為人誤以為不存在。③行為人認識到了犯罪事實,但卻將此種犯罪事實誤認為彼種犯罪事實。這一問題關系到是否阻卻行為之故意和減輕行為人之刑事責任。古羅馬法諺云:不容許法律的錯誤,但容許事實的錯誤。意在有事實認識錯誤時,行為具有某種程度的可恕性,應當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及至近現代,這種觀念更是突顯其重要性,成為刑法公正性、謙抑性價值的重要體現。
誤盜自己財物這種對象認識錯誤,應當屬于積極的錯誤,即把本來并不存在的“可盜取”的財物當成現實的存在。顯然,這種行為不具有任何實在的社會危害性,也不具備承擔刑事責任的實質根據。我國臺灣地區有學者主張行為具有侵害群體法益之“害他性”,始能具有違法性,可資為借鑒。“事實錯誤阻卻違法”的原則,強調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在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時的重要作用,使刑法更具有人情味,成為一國刑法成熟、完備的有力象征,應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根據此原則,行為人誤把自己之物當作別人之物進行占有就會阻卻違法性,不應認定為犯罪。
四、現代刑法的運行需講求效益
市場經濟的全面建立,使我們有必要對刑事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近年來,我國犯罪的絕對數量一直處于高位徘徊的態勢,而國家所能投入的刑事資源是有限的,一個高投入、低產出的刑法運行體系,將無法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所以,我們對刑法的評價不應囿于“善惡”之爭,而應多一種新的標準:是否具有效益性。
綜上所述,對誤盜自己財物、數額不是巨大的行為定罪處刑,將徒增刑法自身的成本。從主客觀相統一的角度考慮,誤盜自己財物的社會危害性不是很嚴重,且沒有實質意義的受害人,西方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也均在嘗試“無被害人犯罪的出罪化運動”。對這樣的行為進行處罰,既無受害人的“報復”情感要滿足又無被打破的社會秩序要恢復。若是僅僅為了預防犯罪,又有單純將行為人作為實現目的之手段的嫌疑,必將為人權刑法所不齒。
刑事訴訟活動必須符合訴訟經濟原則,尤其在刑事追訴意義不大時,應優先考慮程序的經濟性。誤盜自己財物的行為,由于沒有相關的受害方,調查、取證將非常困難,這是行為人逃避懲罰的天性使然。綜合實體與程序兩方面可以看出,對誤盜自己財物的行為論罪處刑很不經濟,只能使刑法的效益更低。事實上,刑事干預的必要性首先是與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和法律文化程度相統一的。我國眼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財物的流動性大大加強,使盜竊行為有更多的機會,面對大案、要案層出不窮的局面,國家實際上已沒有精力去懲罰誤盜自己財物這種輕微的行為了。
*湘潭大學法學院刑法學碩士研究生[41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