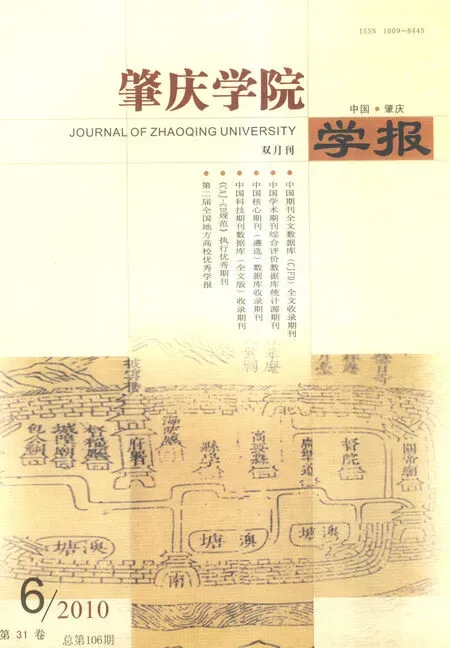一種嶺南文化詩學的重構
——論鐘道宇的端硯敘事
賴翅萍
(肇慶學院 文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一種嶺南文化詩學的重構
——論鐘道宇的端硯敘事
賴翅萍
(肇慶學院 文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端硯敘事”是鐘道宇試圖重構嶺南文化詩學的切入點。他在有關采硯、雕硯、藏硯、養硯等系列故事的講述中,重新挖掘嶺南先民對自然、社會、歷史、道德、人格、情趣、韻致等諸多方面的心靈體驗、情感訴求與價值評判,并重構了一種天人合一、道器并重、實用與審美并存的多元的嶺南文化。
鐘道宇;端硯敘事;嶺南文化詩學;重構
任何一種敘事都是一種文化理解方式,都是對文化的一種透視。鐘道宇在他的端硯系列敘事如 《持守》、《大水魚》、《硯癡》、《老硯》、《硯村紀事》、《走馬燈》、《渡》、《雙聲恨》、《百鳥歸巢》等文本中,試圖通過對歷1 300多年而不衰的“群硯之首”——端硯的歷史敘述,重新闡釋嶺南文化的豐富內涵與精神意韻,重構一種新的嶺南文化詩學。
在已有的闡釋中,嶺南文化通常被描述為一種務實、創新、開拓、包容、進取的海洋文化。其中,務實常常被描述為嶺南文化的主要特質,而與務實相對的務虛文化,如強調性靈、情調、趣味等非功利的審美文化則被排除在嶺南文化之外。事實上,位居嶺南要塞的端州,其得天獨厚的靜山柔水,厚重的歷史積淀,豐厚的文化底蘊更有可能孕育出非功利的審美文化,它們與嶺南的務實文化一道構成了獨特多元的嶺南文化景觀。
“端硯”便是鐘道宇試圖重構嶺南文化詩學的切入點。他以端硯作為敘事的基本物象,在有關采硯、雕硯、藏硯、養硯等系列故事的敘述中,融入嶺南先民對自然、社會、歷史、道德、人格、情趣、韻致等諸多方面的心靈體驗、情感訴求與價值評判。在他的筆下,端硯與嶺南的人文相通,成為嶺南文化的載體。
在《大水魚》里,鐘道宇這樣敘述端州藝人對制硯手藝的看法,“硯村人通常把制硯這門手藝比喻成一件老棉衲。他們說,制硯是一種謀生手藝,學會了,就等于掌握了一門可以養家糊口的本領,不管外面世道如何變化,只要尚能操作,便可生存。程家良說,這件老棉衲呀,雖然不是錦衣,然而天氣轉冷時,取出來披在身上,還是可以取取暖的,不至凍死。”不管世道如何變化,手藝始終是人們御寒取暖的老棉衲,養家糊口的手段。硯村人在長期的生存實踐中,因參悟了制硯手藝所蘊藏的生存大“道”,而視手藝為神靈,在《持守》里,端州百姓把姑蘇巷里技藝高超的硯匠顧二娘尊稱為顧二神;在《硯村紀事》里,制硯祖師伍丁更是位居天、地之后,受到端州歷代制硯匠人的祭拜。不僅如此,這種生存大“道”作為一種信仰,早已滲透到端州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就連硯村百姓的擇偶,也以選擇匠人為首選:“阿妹無心嫁街面,要嫁黃崗白石村。羨哥會打石賺錢,愛妹能雕并蒂蓮。不披綾羅不坐轎,花傘迎郎到村邊。接到新郎回家轉,拜天拜地拜祖先……”(《硯村紀事》)。可見,鐘道宇的端硯敘事首先承載了嶺南先民務實的生存理念,他們視生存為第一要義,尊重謀生,并敬重賴以謀生的手藝。
嶺南先民雖然看重謀生的技能,注重生存的“器”與“藝”,但當“器”與“道”,“藝”與“德”發生沖突時,他們絕不允許“器”與“藝”對“道”與“德”的凌駕。鑒于端硯材質溫潤,硯石精光內斂,其品格與中國傳統文人的道德與人格理想不謀而合,鐘道宇以硯喻德,并以君子比德的審美觀念燭照端硯敘事,從而使端硯成為高貴、典雅、堅貞等美德的隱喻,成為堅強、剛正、清白等人格的象征。在《持守》中,岳母為兒子岳飛刺字“精忠報國”,岳飛在端硯上篆刻“持堅守白,不磷不淄”,人與硯兩相輝映,人格與硯格相融相通。在鐘道宇布滿歷史年輪的端硯敘事中,中華傳統文化人格薪火相傳的歷史畫卷也隨之徐徐展開:先人岳飛不受逆賊之聘,鄙視榮華富貴,誓死效忠宋室江山;謝枋得雖身陷囹圄,生命奄奄一息,卻堅持絕食為宋守節;制硯大師阿滿敬重抗金英雄,神情凝重肅穆雕刻英雄硯;文天祥誓死不降元軍,效忠宋朝;后人吳鐘善縱使生活困頓也絕不出賣祖傳的端硯;吳旭霖在“文革”中冒著生命危險收藏端硯(《持守》);匠人程細蝦不愿為了效率和金錢偷工減料,堅持要雕刻名副其實的百鳥歸巢硯(《百鳥歸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敘述表明,如端硯一般堅強、剛正、清白、貞潔、高貴的美德,早已內化成嶺南先民的一種道德自覺與人格訴求,成為嶺南文化的重要表征。
在鐘道宇獨具匠心的敘述下,端硯不僅承載著嶺南先民務實的生存理念,成為嶺南道德與人格文化的象征,同時,還成為嶺南超功利的審美文化的載體。
得益于端硯的制作、鑒賞與收藏,端州有著深厚的賞玉和賞石文化傳統。受這種文化傳統的長期濡染,嶺南先民和中原先民一樣,有著發達的審美意識,他們對意象、意趣、情趣、自然美、形態美、視覺美等的審美能力,絕不遜色于中原先民。有感于此,鐘道宇一方面滿懷著詩意表現嶺南先民這種發達的審美意識,“愛硯成癡”是鐘道宇端硯敘事中常見的一種情感形態。在 《持守》里,宋高宗、岳飛、謝枋得、文天祥等中原先民在激烈的抗金斗爭中,仍然保持著對端硯的癡迷與喜愛;在《硯癡》里,黎八、金櫻、黃莘田等嶺南先民也和中原先民一樣,愛硯成癡:黎八愛祖傳硯石勝于愛自己新婚貌美的女人;黎八家的幾代女人每晚都以自己鮮嫩的胴體滋養著硯石,使硯石鮮亮如初;“十硯老人”黃莘田辭官歸隱,回鄉建造雕梁畫棟的“十硯軒”,醉心于把玩硯石詩酒酬唱的詩意生活。當嶺南先民沉醉在對端硯的鑒賞和把玩中時,他們并非玩物喪志,而是審美意識充分覺醒,人生充盈著詩意,心靈獲得了空前的自由。正如錢穆所言,“此心自由自在,不為物縛,不受物占,清明在躬,虛靈不昧,也自會領略到人生尋樂的真諦。”[1]
另一方面,鐘道宇在把握和處理人與端硯的審美關系時,他或移情入物,用心智和情感去充盈端硯,將喜愛與癡迷的情感投射到端硯上,從而使端硯脫離了死寂和無生命的物質特性,成為有著騷客形骸、文人風骨、通靈爾雅、詩意曼妙的嶺南文化精靈,在歷史發展的長河里跳起空靈的舞蹈;或把端硯幻化為一位天生麗質、豐滿圓潤、潔凈無瑕且深情款款、情趣盎然的柔媚女性,讓她訴說歷史滄桑與世紀風雨,見證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經由物世界和人世界之間的相通相融,鐘道宇的端硯系列敘事文本便呈現出一種溫暖的情感氛圍與浪漫舒展的自由氣象,折射出古老的嶺南先民對自然所懷抱的詩意審美觀念、物我相通的物象觀念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因為,物我相通與天人合一的前提是,認同自然的生命是自在的,認同它像人一樣具有生命,具有喜怒哀樂的情感。
一方硯臺,一座城市,一種文化。鐘道宇的端硯敘事告訴我們,視硯為神的嶺南文化,其實包括對自然的崇拜,對人格、物格的敬重,對工藝的尊重,對情趣、意趣的追求等。因此,鐘道宇通過端硯敘事所致力構建的嶺南文化其實是天人合一,道器并重,實用與審美并存的一種多元文化。
[1] 錢穆.晚學盲言[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62.
(責任編輯:杜云南)
I207
A
1009-8445(2010)06-0003-02
2010-10-03
賴翅萍(1964-),女,廣西陸川人,肇慶學院文學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