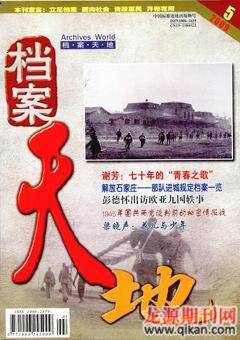自留地
劉慧鑫 谷 欣
隨著“三農”政策的逐步推進,中國農村改革不斷推進,農村正在變得日益美好。使得在喧囂、擁擠中痛苦掙扎著的城里人有時都無比羨慕農村,那里有靜謐并且糅合著野花清香的空氣,蔚藍色的天空,山清水秀的景致。那么在農村,哪里的風光又是農民兄弟姐妹眼中的仙境呢?答案既簡單而又統一,那就是他們自留地的無限風光。大凡來到農村,最鮮艷的花開在自留地,最壯碩的果實結在自留地,最辛勤的汗水滴在自留地。自留地就是農民心中的終身依戀,永不言棄的美人。但這美人卻曾聲名狼藉,背負著最惡毒的詛咒,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是歷次政治運動的活靶子。也不知她被打倒了多少回,卻仍然花枝招展,人見人愛,幾乎受到每一個鄉親的吹捧與呵護。
自留地,顧名思義是自己留下的地,是我國在實行農業集體化以后留給農民個體經營的少量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產品歸個人所有。是相對于公有或集體所有產生的,是很具有中國特色的產物,在別的國家恐怕很難找到雷同版本,地位相當特殊。自留地曾有國家的鼎力支持,自留地,就是這么一種在保障農民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為適當地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由國家給予的支持農村副業發展的土地保障形式。
自留地,這個讓人又愛又恨的歷史名詞,因其頑強的生命力,在中國解放后50余年的土地制度中大放異彩,我想不止農民對它熟悉,想必所有中國人也并不陌生。它承載了太多的歷史與改革變遷,在目前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中,仍然存在著作為農村集體經濟補充的自留地產權制度。由于這部分土地在全部可耕地面積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而社會各界對它的經濟效應的研究并不是很充分,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如果說過去的農村自留地在計劃經濟時期,滿足了農民生活多元化需求的話,那么今天的自留地就成了農村經濟產業化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了。
時光在流逝,歷史在創造,事物在發展,萬事適者生存,存在即因為需要,自留地也不會例外。在這半個世紀的歷史變革中,自留地制度經歷了什么?它是怎樣在多次重創中頑強留存下來的?種種疑問的謎底即將揭開,請聽我們的慢慢分解。
自留地的產生——全國第一次土改后留下的小尾巴
新中國勝利后,以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大綱》頒布為標志,在全國的新解放區開始進行如火如荼的第一次農村土地改革運動,通過剝奪地主土地并向農民分田的形式,消滅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占有土地、農民被迫務工的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分配制度,使得廣大農民第一次當家作主,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在當時百廢凋零的條件下,新型的土地分配方法不僅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還鼓勵了農民革命的積極性,為實施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至此我國農村土地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轉變為農民土地所有制。為自留地制度和自留經濟(自留經濟是在合作化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允許社員利用剩余時間和假日,從事農村集體允許的自留地、飼料地、小片荒地、手工業等家庭副業生產經營,它被認為是集體經濟的補充部分。)的產生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一次土地改革后,全國開始組織初級社(即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實行的一種勞動組織形式),農民個人所有的耕地和農具全部入社,并且在短時間內在全國各地“遍地開花”,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到了1955年年底,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掀起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運動,國內大量的初級社轉為高級社(即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初級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集體農莊式的集體經濟組織。)在初級社轉為高級社的過程中,農民的土地被收歸集體所有,但是每戶人家還是保留了一段小尾巴,即從高級社中抽出5%的土地分給社員種植蔬菜,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留地。自留地相對于集體用地來說面積很小,平均每人不到一分田,一個五口之家自留地也只有那么三四分田,最多的人家也不會超過半畝地。然而,現實是大部分的地都是公家的了,只有自留地是自家的,所以每家農戶都在這一小塊地上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大家對于這塊地更是十分地愛惜。農戶為了保證自留地的豐收,在自留地上栽種的,也都是由最好、最飽滿的種子發起來的秧苗。自留地的各項工作,如翻土、插秧、拔草、打藥、施肥,灌水等,這些也都馬虎不得。農戶每天清早爬起來的第一件事便是去自留地上看看,看苗長得怎樣了,有沒有雜草,有沒有蟲子。有雜草就要趕緊除草,有蟲子了趕緊噴農藥(一般從隊里拿的),要不然,就不辭辛勞地下田一個一個地捉。至于施肥,由于農具基本上都交給生產隊了,因此農戶在自留地施的肥都是農家肥,這個對土壤好,有利于保養土質,農作物也長得好。白天在隊里干活時,一有空就溜回自留地了。傍晚回家,也要去自留地上轉轉,盼望那些秧苗長好點,就像疼惜自己的孩子一樣。而對于公家的地,就沒有這么細心了,秧苗倒伏、肥料不濟、灌水不足等現象時有發生。這樣區別對待的最終后果就是,公田的每年畝產量只能收個700-900多斤谷子,而自留地平均一年(早晚稻)畝產量可以收獲1000-1200斤,自留地上的產量比生產隊的產量每畝平均可以高出200-300斤。這些“高產”的自留地上所生產出來的糧食,便能保證一家人4-6個月口糧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戶的生活水平。
1958年自留地的第一次取消——小尾巴歸入大堆
1958年8月,毛澤東主席在河南新鄉七里營視察時說“人民公社好”。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便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中寫道:“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變為集體經營。”一些主張保留自留地的干部,例如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楊玨和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自此,從1958年開始,自留地逐步也被納入集體,小尾巴于是歸了大堆,土地也都劃歸集體所有。同年開始興辦“大食堂”,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多干少干一個樣,致使大家沒有了生產勞動的積極性,集體土地的耕種也荒廢了,不多久“大食堂”就辦不下去了,最終以解散食堂告終。于是,農民再次以戶為單位進行分配,但是農村財產制度由農民個人所有變成生產大隊或生產小隊集體所有。農民的土地、生產工具全部歸大隊和生產小隊所有,變成了集體財產,私人與自己的農具和土地的聯系中斷。相對于集體化時期,農戶雖然失去了對其生產的絕大部分糧食的控制,但是,仍有一小部分糧食是可以利用的——那就是自留地上產的糧食。這部分糧食成為農戶生活的“救命稻草”,農戶能通過這一小部分自己能夠左右的糧食,來解決其生活上的難題,不至于餓死。而這種“大包大攬”的集體耕種、集體經營的土地制度,大大地制約了農業的良性發展,致使1958年秋收之后,由于國內主要農產品供應全面緊張,外交上又與蘇聯的國際關系日益惡化,在雙方面的夾擊下,直接導致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三年大饑荒,數千萬農民在煎熬中餓死。大饑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的慘狀,評論說:“如果把自留地堅持下來,小自由多一點,即使是反革命破壞,人也要少死好多。”
自留地的再次萌芽——農民開始“兩條腿走路”
1958年,毛澤東開始糾左。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已決定恢復自留地。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糾左中止,極左派得勢。1960年11月3日,在大饑荒籠罩全國的危急時刻,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其中第五條說:“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場,再加上生產隊內部實行的小包工,這就是“文革”中被稱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三自一包”。)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被視為人民公社憲章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俗稱“農業六十條”),其中第四十條說:“自留地一般占生產隊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到七,歸社員家庭使用,長期不變。”草案把自留地經營的權利重新還給農民,農民開始“兩條腿走路”。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穩定下來,直到大包干在20年后將所有集體耕地都變成“自留地”。
自留地的再次夭折——文革期間,全國“農業學大寨”,割資本主義尾巴,自留地被收回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陽縣,是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解放前,這里窮山惡水,七溝八梁一面坡,自然環境惡劣,群眾生活十分艱苦。然而,1963年8月,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幾乎給了這個原本貧窮的小山村毀滅性的打擊,暴雨造成山流地沖、房倒屋塌,七成以上的農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這無異于雪上加霜。但是大寨的人民沒有被困難壓倒,他們拒絕了政府的救濟扶持,而是在陳永貴、郭鳳蓮的帶頭下,堅定不移地把戰勝災害、克服困難的基點定在依靠群眾、依靠集體力量上。他們沒有像其他社隊那樣因遭災而向上、向外伸手,而是響亮地提出堅決實施“三不要”(不要國家救濟糧、救濟款、救濟物資)、“三不少”(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集體庫存不少)的救災方案。他們艱苦奮斗、治山治水、積極自救,因地制宜地、開創性地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層層梯田,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最終帶領大寨走出災后困境,奪取了當年的好收成。
為了大寨這個災后自救的奇跡,1963年11月,山西省委號召全省各級黨組織,特別是農村的基層組織向大寨黨支部學習,黨員要向陳永貴學習。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大篇幅地介紹了大寨大隊同窮山惡水進行斗爭,改變山區面貌,發展生產的事跡。同日發表的社論指出,學習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學習他們遠大革命理想和對未來堅定不移的信念;學習他們敢于蔑視困難、敢于同困難作斗爭的頑強精神和實干苦干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優良作風和嚴格要求自己,以整體利益為重的共產主義風格;學習他們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的作風。由此,全國農業戰線開展“農業學大寨”的運動。
自此,1970年因洪水取消了自留地的大寨成為農業學習的典型,開始全國性的推廣,一個又一個“大寨”在全國涌現。文革期間把自留地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復辟地,割資本主義尾巴,大搞所謂國有制升級,取消農村私有經濟成分,全面取消農村自留地、家庭副業,自留地被收回了,“小荷剛露尖尖角”的自留地再次夭折。“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寨這個曾經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成了中國農村的圣地,“文革”的十年中,雖然很多東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學大寨村、舉大寨旗”的活動在中國沒有停止過。1975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發出“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斗”的號召。當時的意圖很明顯,欲造成一個由大寨村到大寨縣,再到大寨省、大寨國的滾雪球效應,以徹底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四人幫”被粉碎后,華國鋒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繼續高舉“農業學大寨”旗幟。1976年12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陳永貴作了《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這次會議,由于“極左路線”的延續,將學大寨運動推上了極端。不僅農業學大寨,而且教育、衛生、司法、財貿等行業和部門都要學大寨。
但是,全國的“農業學大寨”沒有科學的因地制宜,而是照搬過來,不適應當地情況的發展,使農民的日子更加難過了,負擔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貧困境地。肖東連在《一個時代的終結》中寫道:“農民收入20年間幾乎沒有提高,1976年全國農村人均口糧比1957年還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產隊占38%,全國有1.4億農村人口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農民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問題日益顯現,從1978年春天開始,“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呼聲漸漸蓋過“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各地在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同時,強烈要求糾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極“左”的做法,如要求歸還農民的自留地、自留樹,開放集市貿易,允許農民養豬、養雞、搞家庭副業等等。
自留地的新生——改革開放,土地家庭聯產承包
在現實狀況面前,黨中央認識到了自留地的重要性,認識到了自留地是農民的“救命稻草”。在我國農業集體化時期,廣大農村地區實行土地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經營、統一分配勞動產品的土地經營方式。與此同時,國家還允許農戶依法經營一小塊自留地,以彌補集體經濟的不足。自留地經營不是一種獨立的經營方式,它只是集體化時期集體經濟的補充和附屬。自留地經營存在的歷史條件就是單靠集體經濟不能滿足社員家庭對日常生活消費品的多種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補充辦法。自留地經營作為集體經濟的補充,它的生存和發展不能不受到集體經營的制約。同時,歷史經驗證明,保護農民經營自留地的權利是正確的。
我國在經過1967年、1968年的“全面奪權”,至1968年底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以及基層政權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雖然“九大”堅持了錯誤的政治路線,但是“九大”以后我國的政治局勢出現了相對的、暫時的穩定局面。隨后,國民經濟因“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于1968年跌入“低谷”后,經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努力于1969年開始回升。但是直至1970年下半年中央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政策調整,才給奄奄一息的個體經濟主要是農村自留地、家庭副業、家庭手工業,以及與此相關的多種經營、集市貿易帶來了一線生機。
這一政策調整,首先從1970年8月25日國務院召開的北方地區農業會議開始,會議認為“農業六十條”中有關現階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適用,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同年10月5日,國務院就這次會議的主要精神,給中共中央寫了《關于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報告》,明確指出:(1)農村人民公社現有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關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變動”;(2)在服從國家統一計劃的前提下,“要允許生產隊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3)在保證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4)既要堅決肅清“物質刺激”、“工分掛帥”的余毒,“又要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反對平均主義”。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并強調:“望各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參照執行。”這些政策和措施,對有效地穩定農村個體經濟,進一步推動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值此之際,1978年全國農村發生了兩件大事,使“農業學大寨”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第一是,四川省將自留地擴大到了總耕地面積的15%,還開放了自由市場,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第二件事就是,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支持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并波及全省農村的包產到戶。(1978年以前,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只是一個有20戶、115人的生產隊。小崗作為“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而聞名,當時二十戶人家個個當過隊干部,“算盤響,換隊長”已成為這里特有的規律。到1977年底,小崗隊社員已是一無所有,不論戶大戶小,戶戶外流;不論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討過飯。1978年10月的一個晚上,小崗村的18戶農民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在秘密開會,會議的中心內容就是要把集體耕作的土地包產到戶。到會的18位戶主冒著坐牢的危險,賭咒發誓在一紙分田到戶的“秘密契約”上按下了紅手印,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土地大包干”。小崗人用18個鮮紅的手印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最為壯觀的一頁。這艱難的第一步,帶動了全國億萬雙農民的腳步。“大包干”這種家庭聯產承包制度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最終上升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制度,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由此小崗村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農村六十條”的第四個版本:其中提到“社員耕種的自留地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自此,各地開始全面恢復農民的自留地,恢復農村集市貿易,鼓勵生產隊搞多種經營,鼓勵農民發展家庭副業。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并于當年實施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特點是土地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徹底廢除了人民公社和大鍋飯的消極影響,得到了廣大農民的堅決擁護和支持,極大的鼓舞了農民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促進了農村地區發展。隨著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全面實施,自留地的實際作用并不大了,但是集市貿易、農村副業經濟卻開始蓬勃發展。農村勞動力解放后,大量農民進城了,靠自己的勞力賺錢,回家蓋了新房,買了拖拉機等生產工具。經濟發展后,大家都開始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城市居民開始搞個兼職,賺些外快,買個汽車,同時社會上也依然存在著低收入人群,依靠兼職以解決生計問題。人們在“自留地”上的辛勤耕耘為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從此,由土地改革緣始,近3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把中國帶入了欣欣向榮的城鎮化、工業化、現代化時代。
自留地的淡化——第三次土地改革,面臨農村土地流轉
2008年10月12日,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以此為標志,通過關于農村改革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主要特點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自留地制度在這種新型的土地改革模式下開始淡化。
30年前,小崗村村民嚴俊昌冒死帶頭簽下分田的“生死契約”;30年后,他兒子嚴德友簽下了合地的“市場契約”。從“分田”到“合地”,嚴家父子走的路似乎南轅北轍。但嚴家父子的不同舉動,或許暗合了不斷變化的農村狀況和社會背景。在當時,國家實行集體經濟的人民公社體制,分田單干、包產到戶是政策所不允許的。小崗村的農民們顯然意識到這樣做的危險,但嚴俊昌等18戶不愿再挨餓的農民,還是暗室密謀,在一張“生死狀”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并以中國最傳統的方式按了手印。而現在的這份契約,是嚴德友和20多個村民簽的,帶有明顯的市場經濟色彩。他們約定,在不改變家庭聯產承包的大前提下,簽訂為期20年的土地租賃合約。同時,租賃價格并不是一成不變,它會隨農作物的市場價格進行相應浮動。目前,一畝地的年租金為500元。現在,嚴德友以這種方式租來的土地,不是種莊稼而是種葡萄。同時,出租土地的一方還可以給承租方打工。這樣,不僅出租土地掙到了錢,打工還能掙一份錢。頗具意味的是,當年冒死“分田單干”的嚴俊昌,對這種土地流轉的做法卻很支持。
距小崗村40公里左右,有一個叫趙莊的鄉村。眼下,他們正在運作一場看似遠離當年小崗分田模式的新變革。村里把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并與村民們簽訂合同:在12年內,租用村民1萬多畝土地,總投資3000多萬元,實施綜合開發。在鳳陽,像這樣敢于進行制度創新的農民還有很多。縣里因勢利導,本著依法、自愿、有償原則,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將土地這一最古老、最原始的農業資源逐漸盤活。
這種新的土地流轉制度還在逐步的推進中,想必會為農村土地制度帶來新的生機。從1955年11月公布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規定: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過當地人均耕地的5%。到2007年11月29日四川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的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實施辦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已劃定到戶的自留地、自留山由農戶長期無償使用。”自留地制度已經歷經了半個世紀的時光,卻頑強地保留下來。只是隨著時間和中國的土地改革制度在與時俱進的調整,來適應中國解放后日新月異的農村改革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