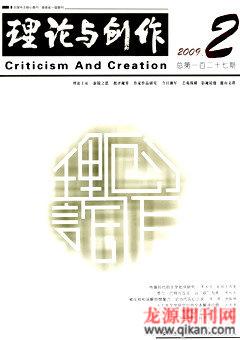傳媒時代:受眾批評的興起和文學批評的泛化
周興杰
一
我們一直生活在傳媒之中。從遠古口口相傳的聲音傳播時代,到當今無往弗界的網絡傳播,人類一直依賴各種傳媒而被聯系在一起,傳媒也一直或隱或顯的影響和制約著人類歷史的變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波斯特提出,“歷史可能按符號交換情形中的結構變化被區分為不同時期”。不過,由于報紙、雜志、廣播、電影、電視和網絡行業等傳播產業對當代社會肌體的全面滲透,更由于傳播媒介對蕓蕓眾生的生活理念的支配性影響,我們更有理由給這個時代貼上“傳媒時代”的標簽。然而,當這個傳媒時代來臨時,我們卻常常聽到這樣的抱怨:正是由于當代傳媒的推動,文學批評話語在一片眾聲喧嘩中變得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故此,文學批評正在失范,文學批評出現危機!
難道傳媒是文學批評的阻拒性力量?回顧歷史我們發現,正是現代印刷傳媒的發展,促使文學批評成為了一門獨立學科。有學者在進行了一番歷史考察后指出,“我們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中國近現代的文學批評,是以報刊作為其出發基地的。”從這里開始,文學批評不再是象牙塔尖端的少數精英自我陶冶的玩物,而是成為更廣大的知識分子群體改造社會的武器。正如陳曉明所說:“新文化運動就是推動中國經典化的文學平民化和普及化,文學批評正是借助大眾媒體完成了偉大的現代白話文轉換運動。同時,也展開了現代性的社會理念、知識和審美感知方式的傳播和普及。”由此,一個專業的文學批評隊伍出現了,一整套相應的文學批評準則也確立起來。照此邏輯,傳媒與文學批評并非對立關系,而應是促進關系。
那么,似乎是天作之合的文學批評與傳媒,為什么會在傳媒時代出現了感情裂痕?問題在于我們的傳媒時代其實不僅是一個傳媒發達的時代,而且是一個信息傳播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轉型的時期,即印刷傳播向電子傳播的轉型,因而我們說的傳媒時代,實際上是電子傳媒主導的跨媒體時代。而這種媒體轉型也帶來了文學批評形態的多層面轉型。
以我之見,印刷媒介時代文學批評的主導形態是專家批評。首先,這與印刷媒介時代的文學生產方式有關。由于媒介因素和社會體制的共同制約,印刷傳媒之前的文學是一種貴族化的文學,新文化運動者對此的激進批判已使我們耳熟能詳,勿需多論。進入印刷傳媒時代,新文化運動同仁力圖推行的是一種平民“能懂”的文學。1949年之后,傳播方式沒有發生根本變革,但傳媒的管理方式更為嚴格,此時的文學必須是能給“人民”的文學。然而無論是“能懂”還是“能給”,內在的文化權力結構方式則基本一致:文學創作是少數人的事,文學的普通受眾(平民)都被置于從屬地位。
與之相應,印刷媒介時代文學批評的目的雖不可否認是平民化的,但它的結果卻是文學批評的專業化,其突出表征即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如果說中國古典的文學批評還只是貴族精英對作品的感悟式評點,那么現代文學批評則越來越需要強大的學理支撐。在當前的文學批評文本中,哲學、精神分析學、社會學、語言學等諸多人文學科知識紛紛涉足其間,各種批評理論流派此起彼伏,批評話語也思辨色彩日趨濃厚,感性印象日趨淡漠。這固然是文學批評獨立化、學科化的必然結果,但也使得文學批評成為專家圈子里的家常話,不為普通讀者這樣的初入大觀園的劉姥姥們所了解了。
其次,印刷媒介的傳播特性強化了這種專業化、理論化的傾向。印刷時代的傳媒雖然極大的擴展了受眾的數量,卻并未建立起信息施受雙方的即時聯系,更不用說同步的交流互動。由于印刷媒體的信息容量,讀者的批評意見必須經過報紙雜志的編輯們層層選拔。而批評話語的理論化程度已然成為鑒別高下的重要標準,這樣,現代印刷傳媒成了擅長理論化言說的專家們的后花園。由于無法如是言說,普通讀者則被擋在了門外。因而專家批評掌握了印刷媒介時代的文學批評話語權。
但是。隨著電子傳媒的發展,長期穩居文化權力結構上層的批評專家發現,他們正面臨失去對話語權掌控的危險。因為在電子傳媒時代,正在發生的是一種平民能寫的、甚至是平民直接提供的“文學”。在這種新的文學生產形態的推動下,不但有善于制造聲勢的媒體批評,而且長期默默無聞的媒體受眾群也開始對“文學”說三道四,在電子傳媒平臺上眾聲喧嘩。套用王朔的句式,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全體有批評能力的人民”。我們不妨稱這種以傳媒受眾為主體的批評為受眾批評。它的出現預示著文化權力關系結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解體和重構,必然給主導的文學批評形態造成嚴重沖擊。傳媒時代文學批評危機論的實質正在于此。
二
我以為,受眾批評的出現是傳媒時代的文學批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因為,文學批評本質上是圍繞文學作品展開的文學接受活動,對于一部作品,無論是專家還是普通讀者,他們都有自己的感受和認識,因而也都有表達這種意見的權力。然而,由于印刷媒介的局限性,廣大受眾的聲音被長期淹沒,這不能不說是重大的遺憾。所以,受眾借助當代電子傳媒優勢登上文學批評的舞臺,實際上是翻開了文學批評史的新的篇章。但是,面對剛剛興起的受眾批評,許多學者表現出了對它的不適應乃至蔑視。在他們看來,受眾批評喧鬧而粗俗,并無多少價值可言,而造成這種價值缺少的根源即在于面對強大的傳媒,受眾并不具備作為批評者的主體性。從而,認識受眾的主體性。或者說分析受眾在傳媒中究竟占據怎樣的主體位置,成為認識受眾批評的焦點性問題。
在這一問題上最富影響力的意見來自于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他們認定,傳媒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生產機構,在它的宰制下受眾淪為原子化個體。“從電話進到無線電廣播,作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每個人,每個主體都能自由地運用這些工具。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民主的聽眾,都可以獨立自主地收到電臺發出的同樣的節目。但是答辯的儀器尚未開拓出來,私人沒有發射的電器設備和自由。群眾被局限在由上面特意組織的‘業余愛好者的人為束縛的范圍內。”如此,大眾傳媒可以輕而易舉地生產日趨單面化的受眾和追隨者,大眾在一個自由的空間里失去的恰恰是思想的自由。在阿多諾式的批評視域中,受眾要么沒有批評,要么只能有盲從的批評。對當代受眾批評的蔑視遵循的正是這一理論邏輯。
但作為該學派的一員,本雅明則表達了更為辯證的見解。本雅明看到,機械復制技術的發展帶來的是藝術社會功能的轉換,即藝術由“膜拜價值”轉向“展示價值”,其實質是摧毀了藝術品的權威性,是由藝術品自主、藝術創造者主宰走向大眾的欣賞自治。同時,這一轉換過程也是人類感性認知方式的歷史性變異過程,大眾在對藝術復制品的體驗中形成的感性認知方式,實則充滿了不確定性與悖論性。因而本雅明使用了諸如光暈、震驚、凝神關注/心神渙散,獨一無二的/復制的等一系列對立性范疇來描述受眾認知方式的新形態。因此,本雅明不無憂慮的寫道,“觀眾成了一位主考官,但這是一位心不在焉的主考官”。對比兩種認識我們發現,本
雅明與阿多諾不但在傳媒的社會功能上存在認識分歧,更重要的是對受眾(或者說大眾)的主體性存在認識分歧。阿多諾站在總體性的主體觀高度俯瞰受眾,因為沒有看到他們的自律性而遮蔽了他們的能動性。本雅明看到的則是“心不在焉”的受眾,一種后現代化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主體形態。
現實地看,本雅明的認識更貼近電子傳媒時代的主體狀態。因為,當代電子傳媒的技術特點就在于信息生成的“即時性”和信息獲取的“即地性”。電視直播、網絡直播等手段使越來越多的信息的生成正在和傳播的過程重合起來,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以更為便捷迅速的手段獲取即時信息。此外,當代電子傳媒在信息交流上也體現出更大的互動性,受眾不但對接收的內容有更多的選擇權,而且能夠同步將自己的見解反饋在媒體平臺上。特別是進人了網絡時代,阿多諾等擔心的“答辯的儀器”已經開發了出來,這樣,“屈從性的受眾”的觀點已經從物質基礎上受到了挑戰。故此,我們可以說,當代傳媒技術客觀上提升了受眾的地位,并使普通受眾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
除了技術上的優勢,受眾進入媒體的方式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在網絡世界,人們普遍地以匿名的方式進入賽博空間,從而使虛擬實踐的主體成為有別于現實社會個體的匿名主體。在現實生活中。姓名是現代權力機構最便捷的追蹤符號,因此人們只有遵循這個姓名扮演指定的自我。但通過化名的方式,在線者可以在網絡世界重新塑造自己的全部或部分身份,甚至可以擁有多重身份。從而在線成為某種面具游戲、某種玩不同身份的游戲了,人們借此可以不出場而又在到場,能看到而不會被看到,走入未知世界而又不冒任何危險。這樣。網絡化名從心理上規避了現實權力的對主體的定位,這無疑使人們更加勇敢去嘗試日常生活中不敢嘗試的各種行動。故此,傳媒僅僅意味著宰制的強化的論點也是很難站得住腳的。
從上述兩個方面不難看出,電子媒介時代的受眾已經不是現代性意義上的以統一性、自主性為標志的主體,而是一種后現代性的在不同主體位置上位移的流動主體。正如馬克·波斯特在考察了人類傳播形態的變遷后指出的,在電子傳播階段,“即持續的不穩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因此,電子媒介時代的受眾的主體性不能以“能動/屈從”的對立模式進行簡單價值評判,而是應看作一種新的主體類型的生成。受眾的這種主體特性使他們得以分享文學創作與批評的主體位置。
三
因此,隨著受眾批評的崛起,傳媒時代的文學批評出現的既不是危機也不是鼎盛,而是形成一種不斷泛化的局面。
這種泛化,首先是指批評形態的擴大,即出現專家批評、媒體批評和受眾批評等多元批評形態共存的局面。我們有理由積極看待這種多元形態。因為,專家型的理論批評固然有諸多優點,如對文本形式的審美把握,文本結構的精細剖析,以及對作品的價值與意義從人文精神、終極關懷的角度進行觀照等等。這些優點使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將繼續存在并發揮獨到的社會效用。但它的一個突出問題在于:過度闡釋。常見的現象是,專家為揭示作品中的微言大義,不斷征調各種理論資源,對文本進行深度耕犁,到了巴特這樣的大理論家那里,文本更成為他自由闡釋的游戲對象,以至越說越玄,令人費解。因此,專家批評的這種闡釋的無度性已經將自身引向了某種歧途,以至于蘇珊·桑塔格這樣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批評家發表《反對闡釋》,倡導向“新感受力”——閱讀的感性經驗的某種回歸,來作為對過度闡釋傾向的匡正。而受眾批評盡管無法具備專家批評的優勢,發揮同樣的功能,卻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上述缺陷,使得這種多元形態體現了某種互補性。
其次。這種泛化是指批評對象的擴大。傳統文學批評、或者說專家批評的主要對象是歷史上的文學經典,和同時代的有可能成為經典的作品。但受眾文學批評的對象則完全是彌散性的。人們可以從“關關雎鳩”談到安妮寶貝,從荷馬扯到郭敬明,完全不受“雅”與“俗”、經典與流行的文類區分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它能面對當下不斷涌現的、普通人自己創作的作品作出及時反應,真正做到“評價老百姓自己的創作”。顯然,這樣的文學批評體現的是文學觀念的深刻嬗變。人們不再像專家那樣關注這是不是“文學”,而是關注這是怎樣的“文學”。
再次,它還是指批評形式的泛化。專家批評是一種以文字為主要媒質的理性分析。而在電子傳媒時代,文學批評的形式大大突破了文字表達的單一形式。在一些學者看來,廣播電視的訪談、座談節目和一些以文學藝術為對象的專欄節目都是文學批評的新形式,像媒體的炒作也可看作某種批評,此外,配樂詩朗誦、電視散文等都可視為邊緣化的文學批評形式。而我以為,更能體現電子傳媒特性的文學批評形式包含在這樣一個事件當中。2008年,花城出版社推出全新修改版的《金庸全集》,在新版中,金庸聽取專家意見對小說內容做了多處修改。雖然出版社多有溢美之詞,廣大“金迷”卻不買帳,聲討聲勢從網絡一直蔓延到平面媒體,而且維護舊版的“金迷”更在網上結成聯盟,對新版小說進行抵制。這一事件既體現了大眾文化受眾的能動的抵抗意識,也很好地展現了當代跨媒體傳播的互動性,因而不能不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學批評形式。
那么,是不是像另外一些學者說的那樣,電子傳媒時代的文學批評,特別是網絡文學批評,使文學批評進入了自由境界呢?我以為這一論斷過于樂觀。傳媒文學批評自由論的論據之一是,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媒體既不為統治者宰制,也不為知識精英控制,由于身份選擇的自由。媒體甚至率先消滅了“階級”,在網絡面前人人平等。故而,以網絡傳媒為代表的新傳媒是話語權的全方位解放。這種論斷顯然忽略了現代傳媒網絡的構建是以巨大的資本投入為前提的,因此,且不說進入當代傳媒沒有免費的午餐,即使我們承認每一個受眾是平等的,我們也無法否認資本方在當代傳媒的文化權力結構中仍然占據更有利地位。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打開任何一個文學網站,簽約寫手的作品都處在更醒目的位置。論據之二是言說方式的任意性和非功利性,這只要看看被封殺的網址和網上流行的以吸引眼球為目的的出位之語,就勿需再做更多的議論了。
因此,與其說傳媒時代的文學批評是自由性的,不如說這種來自廣大受眾群體的批評是自發性的。只要我們拿受眾批評與專家批評做一番比較,這一點就顯露無疑了。首先,傳媒時代的文學批評主要是受眾直面作品,有感即發。在專家批評那里,某一批評意見的形成往往需要一定的研究基礎,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思考。而受眾批評則往往省略了這樣長時期的理性沉淀,只隨著興致所至,對作品作直觀感悟式的評價。其次,傳媒時代的文學批評表述隨意,體例不拘。專家批評講究思維縝密,因為總是動輒千言的長篇大論,布局謀篇都有一定的規矩和講究。受眾的批評話語卻無需如此,不但是有一說一,而且是說到哪里算哪里,甚至一個鬼臉,一串符號。都可以拿來表達對作品的好惡。此外,我們還可以說受眾型的批評更重趣味,而專家型批評則更追求深度。等等。總之,當前傳媒文學批評的這種直接、感性而隨意,決定了其批評形態的自發性。認清傳媒時代文學批評的這種自發性,有助于我們既不要把傳媒時代的文學批評看得過低,也不要看得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