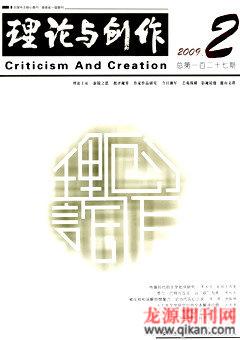楚文學的現代回聲
任美衡
新時期以來,無論從口號、理論或者流派,還是從創作的實際而言。湖南文學都取得了豐厚的實績,特別是作為具有標志性意義的茅盾文學獎而言,莫應豐的《將軍吟》和古華的《芙蓉鎮》雙雙獲獎,更使湖南文學在當代文學格局中不可替代;1985年,韓少功發表《文學的根》,掀開了文學尋根的熱潮,《爸爸爸》《女女女》《火宅》等作品也成為當代文學史上不可忽略的經典;以及“文學湘軍”的出現;等等。這種文學創作的繁榮自然也吸引了眾多文學研究者,本土評論家胡良桂也積極地投身其中。他與當代湖南文學共呼吸,體會著他們的潮漲潮落,共同和他們向廣闊的領域開進,對于他們的失誤,他予以深刻地揭露和毫不留情地批判,并且提出許多非常中肯的建議;對于湖南文學取得的任何些微成就,他都為之歡欣并加以大力推薦。在近三十年的文學研究道路中,盡管經歷不斷的坎坷和曲折,胡良桂始終沒有放棄過對湖南文學的關愛。
一、在細讀中理解作品的真義
新時期以來,湖南當代文學作品精彩紛呈,爭奇斗艷,在全國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然而,如何真正認識這些作品的價值,使之呈現出應有的文學史意義,已成了一個難解之題。同時,也由于這些作品本身帶有時代的特點,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巨大的爭議,因此,如何“估定”它們的價值,評論界見仁見智。
作為密切關注并跟蹤當代湖南文學發展的胡良桂而言,他不是對任何作品進行簡單地、輕易地否定或者肯定,也不任意拔高或者貶低,而是采取一種細讀策略。這種細讀既結合了西方新批評文論的若干優勢,細致地進入文本里面,把文本當作一個生命體,在它的空白與狹縫之中尋求真義。當然,這種細讀更帶有陳思和所說的那種探究性與投入性。“細讀文學作品的過程是一種心靈與心靈相互碰撞和交流的過程,我們閱讀文學,是一種以自己的心靈為觸角去探索另一個或為熟悉或為陌生的心靈世界。”這樣才能真正地使自己,使主體進入文學作品。胡良桂也正是神會了這種細讀對于文學批評的重要性及其意義,所以他充分調動了自己的全部積累、全部情感和全部智慧,對作品進行生命的投入,這樣,在他面前,批評對象就成為了一種豐富的、有意義的“生命物體”。胡良桂還借鑒自己所受到的湖湘文化之深刻和強烈的熏陶,所承受的八十年代西方文學批評的八面來風,以及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形成了自己獨具個性的閱讀期待。憑藉于此,胡良桂對許多湖南的當代文學如孫縫忠的“湘西系列”小說、任光椿的長篇歷史小說、譚談和唐浩明的小說創作,以及《戊戌喋血記》、《曠代逸才·楊度》等不但進行了精彩點評,同時還進行了深入地鑒榷。
盡管他采取的是現實主義方法的批評外殼,然而對于其中的主題、人物,對于其中的藝術技巧他都進行了細筆勾勒,這樣的閱讀不但帶有獨特的個性生命色彩,而且又契合了時代的閱讀需求。所以,他的細讀既發人所未發,在別人爭鳴之外洞開了作品的秘密和作者創作所蘊含的深刻苦心;同時,這種細讀也蘊含了胡良桂強烈的激情,正如法郎士所說的“靈魂與杰作的遭遇”。當胡良桂用全副身心來閱讀作品的時候,他仿佛成了一個靈魂的天使,遨游于作品的浩瀚大海之中,他不斷地去挖掘,不斷地去探索,不斷地去破壞,不斷地去尋求,一部看似簡單的作品在他的批評之下往往能夠帶給我們最為豐富的聯想、思考和哲理。他對于文本的細讀在程序上是這樣的:首先,借鑒了西方新批評的一些理論經驗,從文本的機制人手,探討文本的語言、節奏、象征,探討詞語之間和意義之間的張力、縫隙,探討在主流意識形態所主宰的意義之上文本所可能顯示出來的叛逆、裂痕,把現代人的生活經驗充分地融入到他對作品的解讀之中,使這種閱讀往往充滿了一種陌生感,他極力地阻止著我們深入。但是又強烈吸引著我們深入,這種“悖論”使得胡良桂的文學批評充滿著深刻的魅力。但他又時刻不忘自己作為一個批評家的責任與使命,對于諸多文本,他在主體強烈侵入其中的同時,又不忘提醒讀者某些方面出現的瑕疵和偏失,所出現的某個黑洞,這種情況主要出現在對當代文學史上一些名著的解讀上,比如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楊沫的《青春之歌》、田漢的《關漢卿》等等作品,胡良桂努力推開文學史上的慣性閱讀,通過細讀去尋找到這些作品在時代的宏大敘事之外所具有的生命美學。當然。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胡良桂在把作品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閱讀的同時,他又出乎其外,把文本架構于時代之中,梳理它與時代絲絲縷縷的關系,它所帶來的時代啟示、讀者的誤讀,以及這些作品本身還具有的未被認識的內涵。胡良桂充分尊重并預示著這種深奧性與移動性,預示著這種由破壞帶來的無窮性。所以,在注重文本的同時,胡良桂也不忘文本外面所具有的可能性。
通過這些途徑,胡良桂逐步地找到了作品的真義。但胡良桂從不諱言,這種真義是絕對的;在他看來。這種真意可能是讀者最需要的,也可能是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最富于時代性的內涵。當然,無論如何,胡良桂畢竟不是一個由異域理論武裝起來的批評者,他的根基深藏于湖湘文化或者傳統文化的土壤里,他更為深刻的還是接受了現實主義美學的熏陶,所以他的閱讀讓我們既感覺到輕松,往往又有意外之美;既帶給我們閱讀的流暢,往往又帶給我們哲思。他非常反對把作品當作理論的證詞,因此,他往往是通過對孫健忠的“湘西系列”小說、任光椿的長篇歷史小說、譚談和唐浩明的小說創作、以及《戊戌喋血記》《曠代逸才·楊度》和古華的《貞女》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之閱讀而找到了文學的規則與法律。這種細讀總體來說是以生命體驗作為出發點,以生活經驗包括文化積累作為主導,以對作品的契合作為途徑,以對意義的發現作為目標,以對作品經典性的確立作為細讀的宗旨,因此他的細讀是很有特色的。
當然。在具體的批評過程中,盡管胡良桂希望找到一條通達的大道,但也正是局限于這種理論儲備,他的閱讀和批評往往又帶有一種由和諧帶來的某些地方的矛盾性,細讀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蔽了它的深刻性。比如他對于描寫歷史的觀點給予一種消極性的認同,對于某些話語進行一種慣性的接受,對于某些作品的解讀形成一種內在的結構,由此形成了一種閱讀的惰性。同時,這種細讀畢竟是來自于他的靈感,有時候往往停留在某種感性的闡發而缺乏一種理論的提升,所以這種細讀在整體上會給我們帶來若干驚喜,但相對于他自己或本身的批評語言又不免帶來了某些俗套。這種細讀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成為他的柵欄,使他難于對作品形成一些帶有尖銳性的觀點。當然,這種細讀因為依靠湖湘文化深厚的人文底蘊又有別具一格的實踐魅力。
二、著眼于文本的創新
新時期文學努力強調創新,八十年代以來,各種新的文學技巧手法紛紛涌進中國,意識流、反諷、拼貼、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等等,都在中國大陸得到了極大的回應和廣泛的傳播。它也像一股巨大的神秘的力量促進著湖南文學的向前發展。然而,如何判定這種創新更有價值,如何判定這種創新是否更符合于文學的規律。
更能夠促進文學的發展?胡良桂以湖南文學為考察對象,提出了文學的創新標準:
第一,創新不等同于西方文學。西方的進化論往往以極端的、絕對的和斷裂的姿態看待文學的傳統,他們以否定一切來否定文學創作,因此造成了文學本身的斷裂、失誤和陷阱;由于以歐洲中心論為基礎,因此它往往居高臨下地看待別的文學,以致潛在地拒絕與其他文學的交流,從而導致本身的封閉性。在胡良桂看來,這種創新肯定是行不通的。創新,首先要立足于當前的文學現實。因此,他對許多作品的批評都看它是否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傳統,是否真正地延續了傳統。創新是“有限”的。也就是說他看重這部作品是否有經典性。首先看它對傳統繼承了多少又發揚了多少。比如《詩詞大國推盟主》一文對毛澤東一些詩詞的解讀,就更看重于這些詩詞是批判地繼承了屈原、李白、蘇軾、辛棄疾等人的優秀藝術傳統。盡管是“舊體”,但并沒有生吞活剝的缺點,也沒有勉強拼湊的矛盾,毛澤東用它來表現新的革命生活,融洽自然。所以,他對于這種“舊瓶裝新酒”充滿了推崇之情,這不僅僅是一種形式,更是一種對于文學的觀念。
第二,這種創新是否更新了文學的慣性思維。我們往往可以通過許多技巧、手法、形式等發現文學的某些陌生化傾向,但在我們深入閱讀之后,卻又發現它們經常經不起推敲,甚至給我們帶來許多失望。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文學的思維沒有更新,它依然守持的是那種機械的、僵化的、簡單的思維。在胡良桂看來,只有打破文學的那種思維框架、思維模式,我們才能真正地推陳出新。《湖南文學界的一面旗幟》一文就深入到了周立波之《山鄉巨變》在文學思維方面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忠誠于生活,忠誠于自己的藝術感覺,所以,他在創作中顯得靈動,充滿了天才性,又充滿了巨大的創造力量;然而當他回到時代,回到現場,他又對自己這種來自于生活所賜予的思維靈感感到困惑,感到矛盾,感到急躁,感到疑慮,這樣也就導致了他的批評在某種方面又不免趨于僵化。胡良桂也考察了唐浩明能夠在《曾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等小說中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功,乃在于他在創作思維方面充分地、狂放地、恣肆地運用了多種文學思維,如審美的、靈感的、理性的、普遍的、科學的思維貫穿其中,而且各種思維互相激蕩,又滋生出一些邊緣化的思維形式,使得無論是《曾國藩》還是《楊度》,盡管它敘述的是某些歷史事實,但往往讓我們常讀常新,就在于這些思維成分不同地混合給我們所帶來的新景觀。第三,創新又是一個慢慢地剝離公共經驗,走向個性化的過程。正如麥家所說:“文學的創新決不是為了盡可能多地分享公共的經驗,而是要在公共經驗的叢林里,找到一塊屬于我自己的地方,以及一個屬于我自己的觀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文學的創新也不是為了承認、贊美已有的文學現實,而是要在已有的現實之中,敞開一種新的寫作可能性。文學創新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我們學習如何在人群中成為那個面目清晰、風格鮮明的‘個人”。應該來說,這也道出了胡良桂對于文學批評的心聲。所以,盡管許多文學作品被大家叫好,甚至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但胡良桂并不是盲目地附和,而是從作者是否形成了個人經驗出發對他進行評價,這就使得他保持了一種清醒的批判意識,充滿了辯證性。如《夢土》與《玩古》等長篇小說曾經引起文壇的巨大轟動,也造就了湖南文學的輝煌,然而它有沒有缺陷呢?在胡良桂看來是有的,如缺乏大家風范,在對長篇小說的整體把握、敘述風格和語言韻味方面,都出現了“半部杰作”現象,但胡良桂在指出它的缺陷之時并不否定它真正的內在價值。
第四,在胡良桂看來,創新相對于湖南文學來說,還要看湖湘文化是否成為文學創作的內在精神,它滲透的程度往往也決定了作品的高度。然而,這并不是作者一廂情愿地將所有湖湘文化都囊括進去就顯示了它的成功,應該來說,湖湘文化的正負、好壞、高低、陰暗、光明、價值往往也考驗著作家的水平和能力。有些作家往往從標新立異或者獵奇的角度來肆意展示湖湘文化的負面,這往往引起了胡良桂的反感,他對此不屑一顧,如某些尋根文學作品。當然,對于湖湘文化比較好的方面他是贊頌的。
總體來說,胡良桂對于湖南文學的研究以創新為標桿,方方面面地考慮了創新帶給湖南文學的影響,從而表現了他自己的批評觀。然而,當今湖南文學也面臨著深刻的危機。正如雷達所言:它正在成為時尚和口頭禪。如存在復制化與批量化的現象。在他看來,湖南的作家們正面臨著一個更新庫存、擴大資源的迫切問題,作為一個與新時期湖南文學共同走過來的人,胡良桂深刻地辯析了它的癥結所在。所以,他在批評中又不失冷靜地提出,無論我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創新畢竟是湖南文學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湖南文學唯一存在的理由。他希望湖南的作家們應該發揚勇于探索的精神,把創新的火把永遠傳遞下去。
三、努力建設自己的評論文體
從本質的意義上來講,胡良桂并非一個理論主義者,他更多地是通過自己的批評實踐來體現自己的批評方法,并勉力地建設著自己的評論文體。
第一,他始終尊重文本。任何批評必須來自于文學現場,它不是空中樓閣式的闡發,也不是以某種理論作為判斷視角對文本進行閹割,它必須要尊重作品本身的價值。胡良桂對湖南的許多代表性文本都進行了反復研讀,對整個作品都了然于心方敢下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的評論中,對知識的運用、對文本的批判所舉的例子都隨手拈來,交錯復雜,仿佛形成一個迷宮,但只要我們遵循他的思路,會發現其實井然有序。
其次,他始終尊重自己的藝術感覺。胡良桂對湖南文學的研究從不牽強附會,也從不亂點鴛鴦譜,他始終忠實于自己的藝術感覺,好的說好,壞的說壞,絕不違著良心做虛偽的判斷。所以,在他的批評中,可以看到意象派的靈光往返、徘徊、閃過,可以發現法朗士所說的靈魂與作品的相遇。對于作品中閃光的方面或有突破的方面,他從不掩飾自己的好感,甚至也從不掩飾自己的判斷,甚至不諱比較高的評價。同時,這種藝術體驗、藝術感覺還灌注了他的生命的張力,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胡良桂的文學評論往往也是他對生命的一種闡發。
第三,他嚴格遵循自己的批評經驗。不是有了自己的藝術感覺就可以信馬由韁,可以海闊天空。這表現了他的一種理性與節制的原則,即遵循自己的批評經驗。這種批評經驗既來自于他自己的批評實踐,也來自于古今中外其它研究者的批評經驗,如魯迅所說的“知人論世”。在評論中,胡良桂對已有概念、范疇進行了重新評估、清理、揚棄、辯證地分析,然后再將其運用到自己的批評實踐之中,這既使我們在規范中發現了批評的魅力,也使我們在熟悉中找到了陌生的感覺。如他對于批判現實主義,對于許多形象、典型,對于美、真、善等概念的闡發,評《夢斷帝鄉路》與《鐵血霸業魂》的悲壯與崇高,讀《秋霧漾漾》所形成的一個歷史時代的縮影,讀《“公仆”三部曲》得出的一幅當代官場的政治生活畫,讀《芝城風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