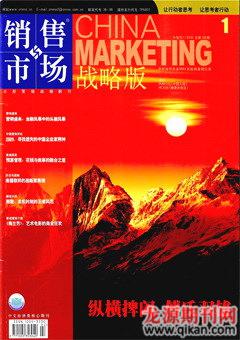站在歷史的分水嶺
姬大鵬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個睿智的年月,那是個蒙味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時期,那是疑惑重重的時期;那是陽光普照的季節,那是黑暗籠罩的季節;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那是讓人絕望的冬天;我們面前無所不有,我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們大家都在直下地獄。
——英·狄更斯《雙城記》
每一個人都是自我歷史的囚徒和特定經驗的人質,深入其中可能被情緒和偏好綁架,置身事外則容易被輿論和宣教蒙蔽。在舉國上下巨浪排空般的煽情報道中,剛剛抽身遠去的30年改革開放歷程——這段注定成為中國最難以復制的經濟崛起和文明復興的歷史——對于中國近代歷史的揚棄、原生文明的激發和普世文明的勾兌,使得任何一種力圖完備解釋它的社會科學理論都顯得蒼白空洞;它提供了一個最復雜也最完整的歷史切片,讓喜歡宏大敘事的歷史學家和自認洞察了文明演進軌跡的社會學家有了皓首窮經的研究對象,而其恢宏的標本學價值可能需要參與者用更大的耐心來等待時間的仲裁。
1919年的中國站在了如何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十字路口,1949年的中國站在了如何構建全新發展范式的十字路口,1979年的中國站在了如何追趕先進文明體的十字路口,2009年的中國站在了如何打造“中國世紀”的十字路口。在篳路藍縷地跨越式發展之旅中,“1840情結”始終是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主流文明試探與互窺、融合與摩擦、協同與對抗的文化深層誘因。既要學習師傅之制度技術又要否定師傅之道德價值的心理沖突,對國人道術一體的評價傳統構成了真正的挑戰,它不僅蘊含了以往我們的社會變革中大喜大悲的所有秘密,還將在未來漫漫的征途中長久地扮演著道德天平,
而在上述幾個轉型節點中,1979年以來的變革最為復雜多元,它完全不同于1919年和1949年強勁清晰的線性整合戰略——在與西方強國的對抗中獨立自主地壯大文明實力——而是在堅持制度優勢的前提下強力變革發展模式,在自我矛盾和中外矛盾錯綜復雜的糾纏下“摸著石頭過河”,也正因為如此,1979模型的魅力在中國歷史上也許只有商鞅變法可以比肩。這兩個偉大的試驗都解決了一個文明發展史上最古老的難題:在力挺國家原有骨架的基礎上猛烈創新血脈,既避免了文明的代際更新所帶來的斷代黑洞與撕裂破壞,也防止了文明在功能體的共同體化和麻痹僵化中被異體文明整合,
故而,在巨大喜悅和充滿憂傷的二極氛圍中以足夠的冷靜重新審視1979模型的約束條件、突破層次、路徑抉擇與遺留問題,是我們這代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將成為下一個30年模型主角的同仁們不能回避的功課。
一、1979模型的約束條件:存在“三個割裂”、老一輩革命家生活在一個由信仰構成的英雄主義的年代,資本主義的掠奪性和舊中國腐朽政權的反動性在那代人的心靈深處造成了巨大的創傷。1949年建國后的冷戰大局迫使中國選擇了一個在政治上模仿蘇聯的一元化管理、在經濟上偏重國家集體建設的大頭小尾的發展模型,但在現實地解決了國家對抗性實力需要的矛盾后,組織和成員之間的差距逐步拉大,因此到了改革開放前夕,中國面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割裂(生產關系高于生產力)、城市與鄉村的割裂(剪刀差)、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割裂(冷戰及意識形態對立)。
二、1979模型的突破層次:實現“三個突破”。發軔于1978年年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在1979年開花結果,小崗村的農民從這年試驗成功,開啟了中國獨特的“突破在地方、規范在中央”的基層戰略主導范式;蛇口招商局終于呱呱墜地,奠定了中國改革實踐大于理論的嶄新格局;皮爾·卡丹和霍英東的破冰之旅昭示了開放與改革同樣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確立了中國雙引擎驅動而非改革帶動開放的單極增長模式。因此,思想突破中的“市場導向”,唯真務實,制度突破中的擱置爭論、實踐大于理論,模式突破中的執行層先行、管理層升華、改革開放雙引擎驅動的策略,成為1979模型中擺脫約束的三駕馬車。
三、1979模型的演進路徑:抉擇“三個優先”。組織管理和組織變革有著三個訴求,道德優先、秩序優先和目標優先,分別對應著組織高層、中層和基層。在組織變革中是否能恰當選擇其路徑、將是變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為變革型管理和和慣例型管理不同,需要組織高層關注目標優先——鄧小平的“貓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恰恰把控了這個最為關鍵的戰略要害,一舉屏蔽了當時大而無當的道德優先和僵化保守的秩序優先,給中國改革提供了一幅扎實可靠的演進路線圖。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歷史的大河在過去的30年回旋激蕩,浪潮滾滾,但2008年的食品行業危機宣告了中國商業文明的缺失,透射出我們軟實力的孱弱。當面對經濟戰略的實用主義——這個歷史留給我們的最大資產和負債時,當寄生型經濟體在金融風暴的拍打中瑟瑟發抖時,重溫歷史先賢們大爭于世、奮發求強的故事,將給我們不一般的勇氣和智慧,不一般的長策與戰略,不一般的世界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