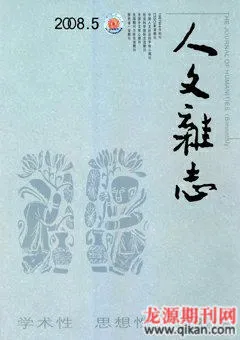比較語境與中國文學研究的自我意識
內容提要 徐復觀力圖在比較語境中對古典作出現代的闡釋和研究,但他反對用西方的文學體系作為標準來衡量中國文學。他強調文學研究要走出進化論的觀念,采取歷史的整體視角。他認為,要以中國文學自身的傳統為脈絡來建立研究的基點,而避免那種以西方某種理論概念為先在體系的研究方法。基于這種學術的自我意識,他提出了中國文學的實用性,將其作為傳統文學的主要特征加以表彰,從而構建出與一般從純文學角度出發建立的中國文學史觀念。
關鍵詞 徐復觀 比較語境 自我意識 實用文學傳統
〔中圖分類號〕I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08)05-0108-07
中國現代學術是在西學影響下形成的,是以西學作為參照系,或者運用其方法作為工具來分析中國的傳統學術。現代傳統文化研究里,西學是一個或明或潛的比較。對我們來說,比較是使中學獲得新的意蘊的有效途徑,現代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也是在比較視野下進行的。
一
在中國文藝研究中,徐復觀自覺吸收西方的文藝理論,以之作為觀照中國文學的一面鏡子,他力圖在中西的比較語境中對中國傳統文藝思想作出現代闡釋和研究。他說,“我常常有一個想法,希望能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來講中國文化。所以我在東大開文心雕龍的專書以前,最大的準備工作,便是摘抄了約三十萬字的有關西方文學理論批評的東西。”
①徐復觀的中國文學研究貫穿了現代意識,他認識到中國文學的審美特性與特征只有在西方理論的參照下才能獲得現代的闡釋。應該說,西方文學理論的引入使得我們的眼界比以前更加的開闊,比如以往中國人重視的是詩歌和散文,對戲劇和戲曲并不重視,由于西方敘述文學的發達,讓我們重審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小說與戲曲,對小說、戲曲的發掘可以說大大豐富了以往中國人的理解,更讓傳統的雅俗觀念具有文學意義。但是,徐復觀認識到,我們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必須符合中國文學自身的發展,我們必須在中國文學的歷史語境中闡發它,從而凸現出中國文學自身的特性。西方理論作為參照可以啟發我們打開視野,卻不能代替我們對自我問題意識的研究。就文學研究而言,徐復觀認為,在對具體的古代文學闡釋中,西方的理論難以對中國文學進行有效的闡釋,很難將中國文學的獨特魅力展現出來。任何簡單照搬西方理論,將中國文學納入其中做比附的闡釋方法,都是一種偷懶的行為,這忽視了中西文學的差異遠比其共同性多。對西學理論的生搬硬套,其結果是使得中國文學經驗被遮蔽,僅成為西學理論普遍性的一個注腳。
徐復觀認為,我們應通過置身于歷史情境之中來獲得關于文學的具體感受,還原中國文學發生的本來面貌,從歷史變化的角度來理解文學觀念。這正是他一直強調的,思想史文學史的研究必須用“動的觀點”來研究,所謂“動的觀點”,就是說,任何的文學現象并不是從天而降,而是有源有流的,它是文學歷史的產物,帶有歷史的烙印。因此不能孤立的研究文學現象本身,而應該同時關注文學現象的歷史根源及其發展,這樣對文學研究才是動態的,符合文學現象的歷史性。而現代許多“研究文學史的人,多缺乏‘史地意識’,常常是以研究者自己的小而狹的靜地觀點,去看文學在歷史中的動地展出。不以古人所處的時代來處理古人,不以‘識大體’的方法來處理古人,也不以自己真實地生活經驗去體認古人。常是把古人拉在現代環境中來受審判”。(注: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自序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因此,徐復觀強調采用一種內部視角的方法,即從歷史文本出發來闡發歷史本身,用中國文論本身的話語來闡釋中國文學,他極力避免用現代科學實證方法,他力圖把握中國文學的內在特征,這正是徐復觀對中國文學解釋研究的核心所在。最能體現徐復觀這種闡釋方法的是他對“文學”概念本身的理解,因為這是任何研究中國文學首先遇到的問題:在中國歷史文化的語境中,文學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如果要復活中國文學就必須對“文學”在其原初的語境中自身的涵義做出符合其自身的理解。
“五四”之后,中國文學研究較早開始了建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科的現代學術化努力,可以說,中國文學的審美特征和特性是在西方藝術理論的啟發下才作出了系統的理論化闡釋,中國文學的價值和特征在這種比較的語境中獲得較清晰的了解。但是這種啟發又容易使得研究者有意無意之中將西方文學的發展模式以及藝術的審美趣味視為文學發展的普遍模式和藝術審美的最高標準。“五四”以來,西方文學理論中影響中國文學最深遠的就是純文學觀念,用現代的純文學概念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成為之后的文學研究主流,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史就是純文學史。
但是,文學是一種生存的文化經驗,它不應該存在任何先驗的文學或者文學的本體理念,任何將西方文學經驗視為文學普遍性的看法,就是已經將西方的文學經驗和實踐預設為文學的本體,從而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先驗理念。不同地域國家的文學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文學模式,中國的文學研究,中國文學的經驗如果不僅僅是為世界文學提供一種新的地方性經驗,而是豐富我們對文學的形態,文學性的理解。文學研究作為學科來說,也只能是經驗性的,文學的概念應該由文學的實踐中產生,文學的審美以及藝術的趨向也只有放在一個獨立的文學系統中才能獲得理解和認同。正如比較文學的理論家邁納所指出,文學理論體系產生于豐富的文學創作實踐及其作品分析中,而“當文學是在一種特殊的文學‘種類’或‘類型’的實踐基礎上加以界定時,一種獨特的詩學便可以出現”(注:〔美〕厄爾?邁納:《比較詩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學的具體經驗不是用來證明西學的正確與否,或者為其理論提供一個東方的注腳。即使從世界范圍的文學發展來說,純文學觀念也不過是西方文學發展到近代以來才出現的,徐復觀指出,所謂藝術的自覺,純粹藝術的觀念直到康德才出現。他說,“古希臘的藝術模仿說,一直支配到歐洲的十七世紀。及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出,對美的成立、藝術的成立,才開始了真正地反省”。(注: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序》,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頁)他較準確的把握住了西方美學的發展的史實。藝術自覺的理論淵源來自于康德,康德系統地闡發了審美活動的無功利性和相對獨立性,為藝術劃定了自我的獨立地盤。而在19世紀中、后期歐洲的唯美主義運動中,“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更標明了以藝術自足性和獨立性為特征的“純文學”的藝術追求。
文學的觀念與理論首先來自于具體的文學實踐,先驗的文學本體性并不存在。即使就西方文學而言,“文學”觀念的形成也不過幾百年的歷史。文學理論家喬森納?卡勒指出:“文學就是一個特定的社會認為是文學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來裁決,認為可以算作文學作品的任何文本。”(注:〔美〕喬森納?卡勒:《文學理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他說:“文學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數作品似乎與通常被認為不屬于文學作品的相同之點有更多的相同之處,而與那些被公認為是文學作品的相同之處反倒不多。”在西方,現代的純文學觀念實際上也是遲至19世紀才誕生。喬森納?卡勒指出:“如今我們稱之為literature(著述)的是20個世紀以來人們撰寫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現代含義:文學,才不過200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這個詞和它在其它歐洲語言中相似的詞指的是‘著作’或者‘書本知識’。……如今,在普通學校和大學的英語或拉丁語課程中,被作為文學研讀的作品,過去并不是一種專門的類型,而是被作為運用語言和修辭的經典學習的。……比如維吉爾的作品《埃涅阿斯紀》,我們把它作為文學來研究。而在1850年之前的學校里,對它的處理則截然不同。”(注:〔美〕喬森納?卡勒:《文學理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頁)可以說,這種對文學的看法與中國古代對“文”的看法就比較接近。可見,純文學觀念只是現代西方文學發展的一種觀念,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文學本身是一部流動的歷史,文學的觀念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文學的概念是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地形成的,文學的概念本身就表明文學實際上是一個在歷史中不斷演化和建構的過程,它是在與其它知識的不斷區分之中被表述出來的。純文學的觀念只有在科學、道德、藝術分治的現代性知識景觀中才能建立和凸顯出來。因此,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只能是一定時期的產物,并不具有先驗的合法性。既然文學的觀念并不是先驗的,文學在中西方都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文學的觀念隨著文學的變化發展而逐步形成的。那么僅僅用今人的純文學觀念來衡量文學史的材料,以之貫穿文學史研究,其結果就是大量文學史上的文學作品排除在文學研究之外,這樣的文學史不過是一種單一觀念史的產物,它不能對文學發展的歷史情形作出真實的描述以及合理的評價。
二
徐復觀認為以莊子影響的“為藝術而藝術”與以孔子影響的“為人生而藝術”構成了中國藝術精神的兩種范型。徐復觀對繪畫和文學在審美上的分野,從美學上說,暗合于康德關于審美的論述,繪畫(視覺藝術)是一種純粹的藝術,比較接近康德所說的“純粹美”;而文學藝術本身因為形式因素比繪畫要弱,而作為“依存美”的特征比較明顯,從康德那里以純粹美為基礎的審美論對文學的解釋效用也就更低了。因此對這兩種美的藝術,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審美理想,繪畫是氣韻生動的空靈之美,是神韻之美,是偏向虛的美;文學是偏向實的美,是充滿了內容的美;這和康德美學有驚人的相似。錢鐘書先生說:“中國傳統文藝批評對詩和畫有不同的標準,評畫時賞識王士禎所謂‘虛‘以及相聯系的風格,而評詩時卻賞識‘實’以及相聯系的風格。”(注:錢鐘書:《七綴集》,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5頁)錢鐘書用美學的所謂“虛實”來區分中國文藝在文學和繪畫上的審美區別,而這種審美區別,根源恐怕就是徐復觀所闡述的,中國文學具有實用性的傳統,這就使得中國文學的美學上偏于“實”;而中國繪畫則是秉承莊學的精神,構成了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一書對莊子影響下的中國繪畫構成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精神進行了深度闡發,而他關于“為人生而藝術”實用文學傳統的構建,則是貫穿其《中國文學論集》的文學觀念核心。但在目前徐復觀的文藝思想研究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主要是因為以往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太狹隘,被西方的文學及其理論觀念所束縛。而徐復觀實用文學傳統的提出,是建立在對“五四”以來文藝研究深入反思基礎上的。
中國文學里面純文學的概念實際上是“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影響的結果,文學并不是先驗存在的。在五四一輩的學者中,純文學觀念與進化論糾結在一起,文言文學與白話文學,雜文學與純文學,構成了古今中西,落后與進步的關系。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設置了進步與落后的文學設想,將古代文學設想為落后的文學,白話文為新時代文學的代表,終結了文言文學的時代,這種進步論的思想觀念下,文學研究的核心中民間文學成了中心。在這種進步論的視野里,俗文學與純文學成為文學研究的中心,它們體現了進步論中的文學性觀念。但是這種中西比較,恰恰造成對中國文學特征的遮蔽。徐復觀指出:“進化的觀念,在文學、藝術中,只能作有限度的應用。歷史中,文學、藝術的創造,絕對多數,只能用‘變化’的觀念加以解釋,而不能用‘進化’的觀念加以解釋。可是時下風氣,多把個人的文學觀點,套上未成熟地進化觀念的外衣,無限制地使用,結果,文學史中十之八九的人和作品,都在這些人的心目中變成了過時的肥料。”(注: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自序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由這種中國文學的自我意識出發,他重新評價了在純文學視野下被貶低了的中國文學的非審美中心的散文,突出了實用性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我們不能夠用現代文學的純文學概念來規范中國文學的類別,不能將中國傳統的文學中很多的樣式通過純文學這一概念被排除在文學研究之外。徐復觀實際上通過對中國文學史一種實用的文學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以敘事小說為主體的文學史的論述,闡明了中國文學的獨特性與個體性特點。唯有如此才能闡明中國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正如海外華人學者劉禾指出,現代的“文學”這一概念通過把小說、詩歌、戲劇和散文視為“純文學”,而把所有其他形式降到非文學的地位。在小說、詩歌、戲劇和散文被命名為“文學”的同時,其他古典文類則被重新分配到“歷史”、“宗教”、“哲學”以及其他的知識領域,而這些知識領域本身也是在西方概念的新譯名基礎上被創造出來的。這種“文學”的概念與古典的“文學”概念大相徑庭;然而,今天的“中國古典文學”也被迫按照現代文學的觀點被全新地創造出來。“他們按照自己時代對歐洲現代文學形式和體裁的理解,實際上對中國文學進行了重寫。……不論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發現了什么東西,它們都不可能擺脫一種總是有歐洲文學參與的學術史和合法化過程。人們總是能夠提出這樣的異議:為什么一談到體裁形式,就要用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形式來限制人們對漢語寫作中可能存在的其他體裁類型而被排除在文學史之外呢?”(注: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63-307頁。(另參見劉禾:《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上海三聯書店,1999。)因此,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必須站在歷史的角度,恢復中國人對文的看法。徐復觀指出:“研究西漢文學,首先應在西漢人之所謂文學的范圍內探索。西漢人的所謂‘文學’,姑且以《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為基點。”而“由詩賦略而可以了解西漢人所承認的文學范圍,不僅后世之所謂古文(散文)未包括在內,且諫謚箴銘等有韻之文亦未包括在內,其范圍較東漢及后之所謂‘文學’為狹。”③徐復觀:《西漢文學論略》,《徐復觀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398頁)實際上,中國古代的文含義十分豐富。最早的“文”字,在甲骨文中是紋身的人像的縮寫。其后,《易?系辭下》云:“物相雜,故曰文”。意思是指凡由線條與色彩構成的事物的美的外表形態,都稱為“文”。可以說,從自然界的森羅萬象到人類社會的禮儀道德、典章制度、言論著作、詩樂舞蹈、工藝美術等 都屬“文”的范圍。正如劉師培《廣阮氏文言說》所云:“三代之時,凡可觀可象,秩然有章者,威謂之文”。“文學”也不是指今天的文學作品,而是泛指學術文化。文學一詞最早出現在《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 楊伯峻《論語譯注》說:“指古代文獻,即孔子所傳的《詩》《書》《易》等。”最典型的莫過于《詩經》,今天我們自然視為文學作品,但在先秦,尤其春秋以前,人們是把它作為政治、道德和文化的百科全書來看待的。如《左傳信公二十七年》載趙衰云:“《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論語?泰伯》云:“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則說明它是進行政治、倫理和道德修養教育的重要手段。也就說,從先秦開始,文學所包含的內在的純粹審美的要求并不是很突出,文學更多的與廣闊的社會生活相聯系。
因此,就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而言,我們應該擺脫近代以來西方文學的影響,“文學”觀念應該以中國文學自身的文學發展來界定,如果按照西方文學的標準,則會將很多中國的傳統文學排除在研究之外,這無疑就會造成對古代文學的偏見,造成中國古代文學不如西方文學的判斷。只有立足于傳統的文學觀念,才能真正了解中國文學本身,了解中國文學有著自身的審美特點、追求與發展規律。“研究西漢文學,首先應在西漢人之所謂文學的范圍內探索”。
③這表明徐復觀有著鮮明的本土意識,認為在中西比較中,中學不應成為西學理論普遍性在中國的一個注腳。中西之間應該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但在五四以來很多的學者看來,現代的學術研究往往意味著斬斷傳統,中國的現代學術必須要建立在與傳統的斷裂基礎上。這常常表現在在中西文學比較中存在這樣一種問題的情境:中國為什么沒有史詩,中國為什么沒有悲劇,以及與西方文學相比中國文學的想象力比較的貧乏等等問題。徐復觀指出這種中西比較里隱藏的西方中心意識,他說:“有的研究西方文學的人,曾倡言‘中西文學之不同,在于中國文學中的想像力的貧乏’。應分兩方面來了解。一方面是,在中國傳統文學中,實用性的文學——序傳、論說、書奏等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這類文學中,當然不容許有豐富的想像活動。民初以來,因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許多人把這一類的文學評價得很低,而另標出或 ‘美文學’或‘純文學’,以資與西方文學較一日的長短。但西方因報紙雜志等的發達,實用性的散文,在文學中已日居于重要地位,這已被西方的文學史家、文學理論、批評家所注意到了。文學保有實用性的文學傳統,并不是壞事。凡是拿西方文化中一時的現象、趨向,以定中國文化的是非得失,我愿借此機會指正出來,這是相當危險的方法”。(注:徐復觀:
《中國文學中的想像與真實》,《徐復觀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頁)在這里,徐復觀明確地提出了中國文學的實用傳統是中國文學區別與西方文學的最重要的特征。
三
中國文學的實用傳統首先體現在中國文學的文體較西方復雜,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不同之點,在于西方文學只順著純文學的線索發展,而中國則伸展向人生實際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所以西方文學的種類少,而中國文學的種類繁,因此,在作品的整理與把握上,中國文學分類的重要性過于西方文學”。
③
徐復觀:《文心雕龍》淺論之七,《中國文學精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頁)因此用純文學的觀念來研究中國文學必然會將中國文學的傳統截斷,從中抽離出能夠符合純文學觀念的作品,將具有中國文學本身特點的文學或者排除在文學史研究之外,或者沒有給予合理的評價。中國文學的類型比西方復雜,很多實用性的文章也是屬于文學,不僅僅只有詩、小說之類近代以來所謂的純文學的作品才有文學的價值。而中國文論家“自西漢之末迄東漢之初,已經有人注意到奏議、書論等的文學價值”。③就文體而言,如果按照西方文學的分類標準,他們只有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幾類,那么漢賦該歸入哪一類呢?它是詩歌呢?還是小說?由此,按西方文學的標準,詔、策、令、教、表、啟、書、檄等等,均不在文學研究的范圍,收錄這些文體的《昭明文選》就不能算做純文學總集,討論這些文體的《文心雕龍》也不能算做純文藝理論的著作。而在徐復觀看來,這些作品恰恰構成中國文學史的實用傳統。
更深一層次,以西方關于小說“有一定長度的虛構的故事”的定義,中國史志著錄的小說都不合標準。而用西方文學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將中國古代文學思潮分類的方法也從根本上忽視了中國文學思潮的自身發展。西方美學中關于審美的概念諸如悲劇、喜劇、崇高、優美等在我們的藝術當中并不能夠找到相應恰切的作品,而我們固有的比、興等藝術手法也在西方藝術理論的框架里面無所適從。“至于中國文學中人文化成的觀念、原道宗經的思想、比興寄托的方法、風神氣韻的話語,都因為與西方文學思想、文學觀念、文學方法、權力話語不諧而沒有得到文學史家的足夠關注和深入研究,以致中國的文學史實只能用來說明西方理論的正確,卻不能用來作為建筑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學科體系的基石。”王齊州:“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史觀的現代意義,武漢大學“中國近代化史與社會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2000年11月18-19日)
因此,徐復觀批評蕭統的《文選》,就是因為《文選》的所謂美文抹煞了中國文學的實用文學,“對西漢文學的誤解,實始于《昭明文選》。蕭統以統治者的地位,主持文章銓衡,他會不覺地以統治者對文章的要求,作銓衡的尺度,而偏向于漢賦兩大系列的‘才智深美’的系列,即他所標舉的‘義歸乎翰藻’。”(注:徐復觀:《西漢文學論略》,《徐復觀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頁)也就說,文學的經典的確立無疑應該根據藝術標準,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文學史上經典是一個不斷的確立的過程,這就意味著文學性本身就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每一次文學經典的重新確立都是基于一定的文學觀念的改變,文學的觀念決定了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衡量價值的標準。文學的文學性其實仍然是受著時代和政治的因素影響,文學性離不開政治思想的背景。以漢代文學為例,從東漢初年,已把文學的范圍擴大到散文這一方面,而王充《論衡》中對劉向、匡衡、谷永這些人的奏議,從文學觀點再三加以推重。曹丕《典論?論文》分文學作品為四科,四科中首推奏議。爾后陸機的《文賦》、劉彥和的《文心雕龍》,無不以奏議在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究其因,徐復觀認為,“蕭統《文選》中收集了許多散文作品,但因統治者厭惡諫誨,可謂出于天性。他的父親梁武帝晚年尤為顯著。所以蕭統竟然把奏議這一重要的文學作品完全隱沒,而僅在上書這一類中稍作點綴。于是西漢在這一方面許多涵蓋時代、剖析歷史的大文章,又一起隱沒掉了。這可以說是以一人統治欲望之私,推類極于千載之上。”(注:徐復觀:《西漢文學論略》,《徐復觀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頁)因此,徐復觀非常重視中國文學的實用性特征,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徐復觀因此批評文選派以《昭明文選》所體現出的文章的驕儷之美作為中國傳統文學的美的標準,他認為這不能完整地概括中國文學的整體特點,他們沒有真正地契入中國文學的內在精神。徐復觀認為這種實用性特征正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文學傳統,“所以《詩》大序說‘先王以是 ( 詩 )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種要求,一直延伸到后來的小說、戲劇中去。”(注:徐復觀:《中國文學討論的迷失》,《中國文學精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82-83頁)也就是說,中國文學的發展流變,雖然體式多有變化,但其詩學主張一直則是沿著《詩》大序的方向,一路都是具有實用色彩。
而中國文學的這種實用性根源,在徐復觀看來是根植于中國文化的性格,而“經學奠定中國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基線。中國文化的反省,應當追溯到中國經學的反省。”
④徐復觀:自序,《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從而,經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中國文學實用性特性的形成關鍵。所謂的經學就是經世致用之學,經學對歷史和政治闡述是以實用為目的,但其中仍然包含著文學的藝術性。通過經學,我們才能對中國文學實用與審美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的考察。例如,《詩經》的文學性就體現了文學的實用性與審美性的互動。而在《先漢經學之形成》一文中,徐復觀詳細考察了經學所給予《墨子》、《莊子》、《管子》、《韓非子》及《呂氏春秋》的影響。基于這種基本認識,徐復觀高度評價了劉勰的文學觀,認為劉勰把《原道》、《征圣》、《宗經》三篇作為文之樞紐,就是要把文學納入到“經”這個文化大流之中。他說:“《五經》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正如一個大蓄水庫,既為眾流所歸,亦為眾流所出。中國文化的‘基型’、‘基線’,是由《五經》所莫定的。《五經》的性格,概略的說,是由宗教走向人文主義,由神秘走向合理主義,由天上的空想走向實用主義。中國文學,是以這種文化的基型、基線為背景而逐漸發展的。所以中國文學,彌綸于人倫日用的各個方面,以平正質實為其本色,用彥和的詞匯,即是以‘典雅’為其本色。”在曹丕的《典論論文》和劉勰的《文心雕龍》中,“麗”只是詩和賦的審美要求,這僅僅是中國文學美感意識的一個方面。而其他諸如銘誄、奏章、書論等實用文體的美感意識則是不同于“麗”的“典雅”、“尚實”等。
在徐復觀看來,中國文學的實用傳統并不是浮淺的功利主義,而是基于人格修養的人文主義④,而這正是“經”的主要內容。正因為此,在討論作為現代文學較為推崇的想像和虛構的概念時,徐復觀認為,正是這種人文主義造成了中國文學崇尚對人世界的現實關懷。與西方文學以想像和虛構作為文學的本質特征不同,中國文學的根本特點不在于想像和虛構,而在于其人間情懷。中國文學并非沒有想像和虛構,但是中國文學的想像是一種關懷現實世界的想像,而非超絕理念世界的想像,也就是他說的“中國文學家生活在人文世界里”,這也正是為什么中國文學沒有西方悲劇之所在,他說:“中國從西周初年起,已開始擺脫原始宗教而走向‘人文’之路。印度佛教進入到中國后,也只發揮其無神論的一方面;并將印度的各種‘大地震動’這類的奇特表現,逐漸轉變而為‘平常心是道’的平常的表現。人文的世界,是現世的,是中庸的, 是與日常生活緊切關連在一起的世界。在此種文化背景、民族性格之下,文學家自然地不要作超現世的想像,不要作慘絕人寰,有如希臘悲劇的走向極端的想像。中國文學家生活于人文世界之中,只在人文世界中發現人生,安頓人生;所以也只在人文世界中發揮他們的想像力。中國不發展史詩(《詩經》中便有不少史詩),是因為中國的史學發展得太早。中國不出現悲劇,是因為中國民族的性格、文化的性格,不愿接受走向極端的悲劇。這其中沒有能不能的問題”。徐復觀:《中國文學中的想像與真實》,《徐復觀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頁)
因此,不理解中國文學的實用傳統,用純文學觀來審視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就不能真正把握中國文學精神。“中國文學,從歷史的發展上來說,有與西方文學不同的地方。在中國文學史上,敘事詩、戲劇、小說,雖然不是沒有,但未能得到適當的發展,所以過去用故事情節來批評文學的很少。”(注:徐復觀:《文心雕龍》淺論之七,《中國文學精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頁)在純文學的觀念下,文學的實用性與文學的道德教化作用被貶低了,甚至被認為是與文學的審美性相對立的。這種觀念如果說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偏離了文學史發展的事實。(注:在文學史中,即使是在西方文學里面,與純文學的審美主義宣稱相反,審美并不是文學的惟一目的。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指出,小說閱讀在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創造中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卡勒說:“在19世紀的英國,文學呈現為一種極其重要的理念,一種被賦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書面語言。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中,文學被作為一種說教課程,負有教育殖民地人民敬仰英國之強大的使命,并且要使他們心懷感激地成為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啟迪文明的事業的參與者。在國內,文學反對由新興資本主義經濟滋生出來的自私和物欲主義,為中產階級和貴族提供替代的價值觀,并且使工人在他們實際已經降到從屬地位的文化中也得到一點利益。文學對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懂得感激,培養一種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階級之間制造一種伙伴兄弟的感覺能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還起到了一種替代宗教的作用。”(〔美〕喬森納?卡勒:《文學理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至今,英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利維斯點評了兩百多年來的英國小說,疏理出以道德要義和興味關懷為基準的英國小說的偉大傳統。(參看利維斯(F. R. Leavis)著:《偉大的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事實上,在重新對這種文學觀念的反省之后,現代的研究者們已經認識到這種文學觀的局限性。近來,國內的文學史研究者們提出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史不是純文學的‘文學史’”(注:馬中紅:《多學科視角研究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國際研討會綜述》,文藝報2004,12月14日,2004年第140期),這種認為只有純文學才構成文學史的思維方式,是承接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受西方唯美主義影響的結果,這種文學史的敘述可以說是一種審美霸權,其結果是對中國文學本身產生隔膜,使中國文學史上喪失了很多有意義和價值的東西。這種文學史觀念是以西方文學標準衡定中國文學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潛在表現。
結語
徐復觀強調文學的中西差異,這是中西空間性的歷史文化差異。就文學來說,從來不存在一種普遍的文學和一成不變的文學觀念。徐復觀因而重視中國文學本土性特征,他關于文學研究“歷史的動態”的觀點,實際上構成其中國文學研究自覺的本體意識。他對進步論的反思,體現了文化上的本體意識,文學研究的本土意識。他指出進步觀是一種靜態的歷史觀,它否定文化的多元性與民族文化的個性,“由西方哲學的一元論而形成一元底歷史觀,拿一個東西作歷史文化惟一的測量尺度;在其惟一底尺度下,世界的文化,都是同質的;只有時間上的前進或落后,而無異質底個性文化之并存”。
(注:徐復觀:《文化的中與西》,《中國學術精神》,華東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頁)
中國文學的處境也是整個中國文藝的處境,中國文藝必須放在中西的藝術比較系統中才能有價值,這里包含這樣的一個深刻意識:中西文藝通過比較得以互相發明,這個過程里面,必須伴隨著中國文學的自覺意識。實際上,中國文學研究中自我意識的獲得乃是自我文化價值的認同,對中國文學價值的肯定實際就是對自我文化價值的肯定。而關注中國文學的自身經驗并不是希望通過中國文學的地方性經驗給西方人的視野提供一個奇觀,而是正視我們的文學傳統,發現我們文學中的有益經驗,從這種文學經驗中探討文學發展的規律,從而使得中國文學的經驗成為整個世界文學經驗中寶貴的財富,豐富我們對文學理解,拓展文學的內涵。因此,徐復觀并不因為中國文學的自我意識而忽視文學的普遍規律,否定文學性的存在。他認為文學的價值以及文學區別其它文章的就是文學性,但是這種文學性在中西之間有著區別。
徐復觀并沒將傳統與現代對立——也沒有將中西之間對立起來,在《中國藝術精神》以及中國文學的研究中,他大量運用西方美學文學的理論進行中西的比較互釋。但是,對他來說,西學只是作為參照系而存在,通過與西學的比較,使中西二者之間可以互相發明,從而使中學獲得新的意蘊。他對五四以來文藝研究的反思體現了他強烈的中國自我意識,他認為中國文學史的建立必須回到中國文學本身。把文學放回到歷史語境當中,恢復文學的中國意義,才能發現中國文學的自身特性對中國文學作出恰當的理解,那種以西方文論的模式來格式化中國文學的做法,往往讓我們喪失了自身的文學傳統,切斷中國文學的源頭。只有當我們恰當地理解了中國文學傳統,才能從這一傳統當中獲得有生命力的東西,一種活的精神。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楊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