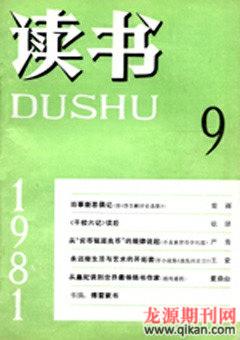“擠”
張重憲
一九二八年,關于無產階級文學革命,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有過一場論爭。凡是知道這場論爭的人大概都記得魯迅的一句有名的話,即:“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普力漢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閑集·序言》)但是大概人們還都不知道,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積極倡導者的郭沫若也是被“擠”的一個,和魯迅一樣。郭老在《自傳》中談到魯迅的被“擠”之后說:“其實就是我,也是實實在在被‘擠的一個,我的向中國古代文獻和歷史方面的發展,一多半也就是被這幾位朋友‘擠出來的。”郭老接著說:“我主要是想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反過來說,我也正是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這種工作的動向,雖然由于我的教養和所處的環境有以促成,但確實是經過后期創造社的朋友們的‘擠,我也愿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認的。”
談到這場論爭的意義,郭老說:“辯證唯物論的闡發與高揚,使它成為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業績存在的。”這一點,從魯迅和郭沫若的被“擠”,也可充分看出。當然,論爭本身還很復雜,其間也夾雜一些我們陣營內部的矛盾,但魯迅說得好:“對于為了遠大的目的,并非因個人之利而攻擊我者,無論用怎樣的方法,我全都沒齒無怨言。”正是這樣,“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魯迅語)
這場論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一些作家世界觀的轉變,將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而魯迅和郭沫若的坦白及闊大的胸懷,也將永遠傳為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