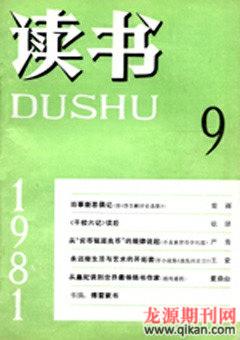一位“山野妙齡女郎”的出世
張啟祥
二十五年前,范文瀾同志在《介紹一篇待字閨中的稿件》一文中,高度評價劉堯漢同志的《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一個典型實例》(下簡稱《過渡》)未刊稿,把它形象地贊譽為“山野妙齡女郎”。范老在文中熱情洋溢地推薦說:
“我覺得這篇稿子的妙處,正在于所采用材料‘幾全是取自實地調查,無史籍可稽。
“我們研究古代社會發展的歷史,總喜歡在畫像上和《書經》、《詩經》等等中國的名門老太婆或者希臘、羅馬等等外國的貴族老太婆打交道,對眼前還活著的山野妙齡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視,冷淡無情。事實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難得出新的結果,而和妙齡女郎打交道卻可以從諸佛菩薩的種種清規戒律里解脫出來,前途大有可為。劉堯漢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許多妙齡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紹一下,摘出‘歷史輪廓一項,借《史學》的地盤和吉士們會面。”(載《光明日報》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學》專刊)
劉堯漢著《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文集》一書,已經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收錄了他建國以來所寫的包括《過渡》在內的十篇彝族民族學論文。這些論文題材廣泛,資料豐富,富于創見,引人入勝,對彝族社會歷史的發展,如彝族奴隸制的實質,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以及其社會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發展的諸形態,都作了深入的探討,這是建國以來出版的一部有分量的民族學論著,很值得大家一讀。
正如范老在上文中所贊譽的,收入本書的論文都有這樣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注重實地調查,主要是用實地調查得來的活材料,來印證歷史闡明問題。作者在把現實調查與歷史文獻相結合,利用現實生活中的民族學資料,去探索解決一些長期被湮沒或懸而未決的課題方面,開創了一個成功的范例。正因為這樣,他的調查研究工作,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引起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史學前輩的重視,并有幸得到他們的親切關懷和指導。
本書中發表最早的論文《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屬于彝族之新證》(原載《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就是在史學前輩們的關懷下寫成發表的。一九五三年,作者根據郭老、藹老的指導,到云南哀牢山南詔開國君主的故鄉深入查訪,終于發現了彝文宗譜、靈臺、巫畫等資料,有力地證明唐代南詔王室蒙氏家族是彝族人,從而糾正了許多中外學者長期認為南詔王室屬于傣族的舊說。這篇不見于史籍的《新證》,在郭老、翦老關注下發表后,引起國內外的廣泛反映。泰國前總理乃沙立和英國的一位學者看到此文后,都信服地表示放棄他們原先認為南詔王室屬于傣族的看法。
劉堯漢關于清代哀牢山區以彝族李文學為首的各族農民起義的調查材料,特別是他發現并搶救出夏正寅《哀牢夷雄列傳》殘稿一事,曾被范老譽為是對近代史研究的一大貢獻。由于這些不見于“正史”的調查材料的發表,才使這次歷時二十三年、以彝族為主體并有漢、白、哈尼、傈僳、傣、苗等民族參加的清代農民大起義,得以為世人所知曉,并引起史學界的廣泛注意。如郭老主編的《中國史稿》,曾多次引用這些資料,肯定了這次農民起義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收入本書的《太平天國革命的一支洪流》一文,就是作者關于這次農民起義的研究成果之一。
解放初期,我國史學界仍多習慣于單純依靠文獻資料,而對考古資料,特別是民族學資料重視不夠,甚至持有異議。針對這種情況,李亞農同志的《中國的封建領主制和地主制》一書,在援引劉堯漢《過渡》資料時指出:“拿中國現代的少數民族情況和古史作比較研究,在我們看來,這是極正常、極普遍的研究方法,因為誰都知道,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民族,其情況是大致相同的。”他并把《過渡》中收錄的清代地主劉宇清總結其祖先統治經驗的兩篇短文視為“寶貴無比的兩篇文獻”,對其史料價值給予很高的評價。(見《李亞農史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李維漢同志在《中國各少數民族和民族關系》一文中援引劉文上述資料時也指出:“從這篇文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彝族社會由奴隸制度經過封建莊園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演變情形。”(見李維漢《關于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若干問題》,民族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
摩爾根致力于“印第安民族學”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人類早期歷史的原貌”,為史學研究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途徑。劉堯漢對彝族民族學卓有成效的研究,也超出了彝族一個民族的界限,而具有著廣泛深遠的社會意義。
例如,他在《中華民族的原始葫蘆文化》一文中,通過對哀牢山彝族“祖靈葫蘆”以及彝巫咒辭等民族學資料的剖析,結合對我國近二十個民族有關習俗及傳說的考證,生動地闡明了我國各族原始先民曾有過母體崇拜——葫蘆崇拜的共同經歷。這種具有豐富內容的原始葫蘆文化,形象地表明我國各民族間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這是中華民族《創世紀》的神話傳說。我國許多民族,語言各異,住地不同,但
再如,對曾在我國許多民族中流傳的“十二獸”歷法,過去中外學者多主張西來說,認為它是從外國傳入的;雖有少數人認為應是中國的獨立創造,但苦于缺乏證據;至于它起源于何時?為什么要用“十二獸”這種形式?則更是無從談起了。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從歷史文獻考證“十二獸”歷法起源得不出結果時指出:“考證起源的意義,看來完全屬于考古學和人種學的范圍。”劉堯漢正是利用民族學也即人種學的資料,成功地解決了這一長期懸而未決難題的。前年他與嚴汝嫻合寫的《“十二獸”歷法起源于原始圖騰崇拜》一文,通過對彝族原始圖騰遺跡、紀日十二獸壁畫、彝文《母虎日歷》碑以及彝族祭祀、舞蹈等民族學資料的考證,令人信服地闡明了中國“十二獸”歷法產生于原始狩獵、牧畜、農耕等生產及以此為基礎的圖騰崇拜,是我國各族先民自己創造的早于夏代干支歷的原始歷法。從而為祖國天文歷法史研究做出了寶貴貢獻。
收入本書的其他論文,也同樣保持著“山野妙齡女郎”的青春魅力,讀來令人興味盎然,深受教益。例如在《羌戎、夏、彝同源小議——兼及漢族名稱的由來》這篇不到五千字的短文里,作者根據彝族現實生活中保留的虎圖騰崇拜和尚黑這兩個突出的古俗特點,結合史料令人信服地論證:這些古俗與“三皇”之首的伏羲和“三王”之首的夏禹的密切關系,進而闡明了彝族與古羌戎先民(伏羲部落)、夏部落及漢族祖先之間的親緣關系。本來,文獻中的這些神話和傳說,很多是真假難辨的,但作者憑借民族學資料這種“活化石”的幫助,就能使它們的社會歷史意義得到復活。這說明在研究有關民族起源、民族形成這類史料少、難度大的史學項目時,從民族學的角度去進行探討,是極為必要的。
劉堯漢同志是彝族人,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族學研究會理事。他從解放初期一個在民族學領域學步的青年,成長為有成就的民族學學者,這反映了在黨的關懷培養下,少數民族干部茁壯成長的一個側影。作為少數民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劉堯漢從解放初期參加工作時起,就立志要為祖國民族學的發展做出貢獻。三十多年來,他一直為此奮斗不息。過去由于極左路線的干擾和影響,我國民族學研究工作也走過曲折的道路,如曾出現過片面強調生產力、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而忽視其他方面研究的偏向,甚至曾一度否定了民族學這個學科,把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視為禁區,不準人們涉及。少數民族出身的劉堯漢同志,深知越是這些落后保守的方面,越較多地保留著原始因素和民族傳統,其中不少是真實的歷史資料,很有研究價值。因此,他一直排除干擾,頂住壓力,鍥而不舍地對這些資料進行搶救收集。即使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他雖身處逆境,也從未中斷過這種努力。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以后,他能很快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來。收入本書的十篇論文,有七篇是近幾年來寫成的。他這種不畏艱險、勤奮治學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作者在憶及范老等前輩對他的關懷和教誨時,滿懷深情地指出:這體現了黨和老一輩學者對民族學的重視,體現了他們對青年科學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精心培育。作者深切體會到:這是出人才出成果的一個重要條件,自己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績,是和黨的培養、前輩們的關懷分不開的。這一直是激勵他不斷向前攀登的動力。
在回顧自己的治學道路時,作者指出:“我在重視歷史文獻的同時,更側重實際調查,這對民族學的研究至關重要。……我們研究歷史,無非是依靠文獻、考古和現實調查這三種資料。現實調查——就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而言也就是民族學調查——所獲的資料,因與現實社會生活相關聯,較前兩種資料更為豐富、生動、充滿活力,足以彌補前兩種資料之不足。所以,范老把它形象地稱為‘山野妙齡女郎,認為同她打交道往往是發現新的問題,進行新的探索,得出新的結論的重要途徑。……也許有人認為,解放三十年了,哪里還有什么‘山野妙齡女郎呢?事實上,不僅在遠離交通線的深山密林中和海島邊境上,還有著未開墾的處女地;即使已經調查過的地區,也還有許許多多的‘妙齡女郎在向我們招手哩!”
在我國廣闊的民族學研究領域里,確實還有許多“處女地”和“妙齡女郎”,急待人們去開墾、去結識。在祖國向四化進軍的新長征中,這方面工作是很需要,也是大有可為的。劉堯漢同志目前正在川、滇交界的納西族、普米族地區,為此進行著新的探索和努力。我們預祝他在與新的“妙齡女郎”打交道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文集》,劉堯漢著,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第一版,0.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