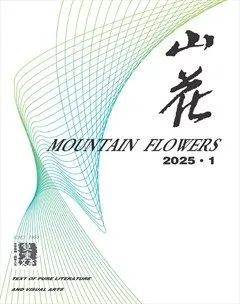亞當那根肋骨
1
像鳥兒一樣起飛,落地,用腳步去丈量從未踏足過的土地,呼吸氣味兒陌生的空氣,品嘗新鮮又吃不慣的食物,給身體以營養的同時,心靈似乎也獲得了不同于以往的滋養。這樣的人生,即便只是想象一下,似乎都讓人在灰暗單調的世間望見一絲亮光。而真正在路上了,各種困頓、不適和疲憊會像行走在叢林中被灌木劃到手腳,或被不知名的蟲子蟄到皮膚一樣,不期而遇。最痛苦的莫過于時差,本想打起精神好好享受眼前風光,磕睡蟲卻跳出來搗亂;明明躺在昂貴的酒店的床上了,睡眠卻像被誰偷走了一樣,沒了下落……
去年冬天是我行走最為密集的一個冬天。北京、漢堡、柏林、布拉格、魏瑪、布萊梅、阿姆斯特丹、洛杉磯。醒來還沒睜眼,先要下意識地問自己:我,這是在哪兒?然后,腦細胞漸次蘇醒過來,浮現出幾張在那個城市的熟人面龐。
“我也有同感呢!在我看來,如果只是重復熟悉的日子,活一年和活一百年有什么區別?經歷,而非占有,是活著的惟一有積極意義的目的。”在機場遇到剛從大溪地島寫生回洛杉磯的吉賽爾。這位女畫家,不僅走遍了七大洲,還漂過了四大洋。疫情期間我們結伴去新墨西哥州的荒山上尋訪原住民遺址,一路同行同吃同住,我才知道總是幸福地微笑著的她,十年前便患了乳癌,切除了兩側乳房。攝影,畫畫,騎馬,種樹,航海,烤點心,生女兒,她比以往活得更恣意舒展。她的作曲家丈夫是迪斯尼音樂總監,本不用她為生計奔波,可她除了偶爾賣幾張畫,還去一所社區大學兼課,堅持與丈夫平等負擔家里的開銷,說那樣能讓她感覺到作為partner(搭檔)的價值和尊嚴。在路上,在旅館,我們兩個成了話癆,聊文學、歷史、藝術、園藝、氣候,也聊人性。“Humansuck(人類挺差勁的)”,這句悲觀的話,被她眼里含著寬容的笑意道出來,竟讓我一下樂觀起來。“我們只能,也應當原諒彼此,因為各自的差勁背后都有難以言說的迫不得已。我父親,在我讀中學時自殺了,很嚇人的那種方式——他加足馬力,從山崖上直接把車開進了海里!越長大,我們越心疼他的不易,而非像小時一樣恨他自私。當年他內心藏著那座地獄,而我們又何曾伸出過援手?”那晚的對話,毫不夸張地說,照亮了我霧蒙蒙的世界。體格纖柔的吉賽爾,是一根暖暖緩緩燃燒的火柴。
“米歇爾好些了嗎?”在機場分手前,我倆幾乎同時脫口而出。我們知道,等見了探險家史蒂夫,他肯定會帶給我們好消息,正是他,介紹我們認識同齡女子米歇爾的。
“我聽說時差每增加一個小時,就需要多一天回到正常狀態。北京和洛杉磯差十四個小時,那就得花兩周調整。”史蒂夫聽說我回來了,特意從高速上飛馳一小時趕到。我們在冬日仍碧綠的灌木林中徒步。美其名曰幫我倒時差,其實,我知道,這位忘年交有一肚子話想說。
半年未見,他似乎更神清氣爽了,全然不像七十二歲的老人。“我不敢期望像我母親一樣能活到九十五歲,可至少,我想和她一樣不給親友添麻煩。”他拿出手機,給我看他母親。目光慈祥的老婦,在照片上沖著我微笑,滿臉皺紋像斑駁落葉,襯托著兩排貝殼般潔白的牙齒。那是史蒂夫疫情前飛到佛羅里達州去看她時拍的,也是老人最后的一張肖像照。“我父親當年總嫌她話太少,老了,她反倒比年輕時更幽默了,那次她跟我說,你知道在我們這些老女人眼里,什么樣的男人最受歡迎嗎?夜里還有足夠好的視力和體力,敢開車上路的男人!哈哈。”美國的佛州因氣候溫暖濕潤,是許多老年人退休后安度晚年的首選。
我不只一次聽史蒂夫跟我聊他的母親。“年過九旬了,還腰背挺直,那個小小的公寓總是被她打掃得一塵不染,那些老先生們沒事兒就愛去她那兒喝咖啡。報稅、還賬單、繳納水電煤氣費,她全都按時按點兒,票據疊放得整整齊齊。”她染上新冠后變得極為虛弱,甚至小便在了床上。“她難為情地打電話給我,說別讓那位女看護去了,她實在不好意思讓人家清理穢物,堅決要求住進臨終關懷醫院。”臨終關懷醫院是放棄治療的病人死前的最后一站。史蒂夫想去看她,被她阻止了。“墓地我早在十年前就給自己買好了。我這一生經歷豐富,很知足。兒子,我現在要跟你說再見了,我愛你!”她躺在病床上柔聲和史蒂夫道別,半小時后,她安祥地閉上了眼睛。
老人把薄薄的遺產分了四份。兩份給自己的親生兒子,兩份給她再嫁的丈夫與前妻生的兩個女兒。史蒂夫他爸年輕時的照片我也看到過,那退役少校是個外表俊朗的萬人迷。在史蒂夫十一歲時,父親丟下眼淚汪汪的妻兒跟別的女人走了。史蒂夫的母親被迫出去工作,在一所小學當打字員。不忍心看兩個兒子跟著她活得太拮據,她再婚嫁給了一個經營廚柜生意的男人。
“當然,沒有愛情。那人大概嫌我和哥哥是累贅,開始客氣過一段,后來就常對我們惡聲惡語。我哥受不了,一上高中就搬走了。我則患了抑郁癥,關在衛生間把毛巾撕爛過好幾條。我母親只得帶我去看心理醫生,直到我也去外地上了大學。后來那個男人死了,遺囑里所有財物都寫在他女兒名下。那兩個女孩很仗義,說太不公平了,主動跟律師協商分了一份給我媽。”作為猶太后裔,成年后的史蒂夫和哥哥都賺錢有道,生活優渥,但回首當年,他仍有些動容。
他母親在七十歲時再婚,十二年后那老先生去世了。“盡管兩人沒有任何共同子女和財產,可她說那是她這輩子最幸福的時光,她得到了一個男人的愛與平等對待。”
我也意外得到了老人的一件遺物,一套裝在精美小木匣里的中國麻將。“把我和哥哥送到學校,把家里打掃得窗明幾凈,約幾個軍官家屬在客廳里打麻將,是她年輕時不多的快樂時光……”史蒂夫給我看過一組母親的黑白照,那個扎著蝴蝶結眨著黑眼睛的小姑娘,那個穿著方格裙裝戴著長串珍珠項鏈的美少婦,定格在歷史里,像從未存在過一樣不真實。
那套麻將牌當然是由史蒂夫轉贈給我這中國人的,我從來沒玩兒過,放在書架上擺著,像一件祖母留下的傳家寶。偶爾拉開小抽屜,我會摸一摸那象牙的溫潤,像輕撫著老人骨感的手背。展開那張小小的紙片,筆跡工整,記錄著缺失的幾張牌:二餅缺一張,八條缺兩張……
從露珠晶瑩的清晨走至暮氣散漫的黃昏,哭過笑過,她最后平靜地走完了屬于她的里程,輕悄地融化了,像一片干凈的雪花;可她留給親人甚至一個陌生人的懷想,沉甸甸的,像剛從田間擔回家的稻谷,散發著熟透了的清香。
我想到在北京的一位好友的老媽,走時也是望九的人了。“那天她突然提出要去醫院住幾天。我們只當她是哪兒不舒服了,就帶她去了。第二天,她就在病床上去世了。”回到家,女兒們才發現她把衣柜里的衣服都已分類疊好,下面壓著紙條,注明哪些是她們可以接著穿的,哪些是嶄新的,可以送給外人。“她一輩子從不穿皮鞋皮衣不背皮包,說不能忍受讓動物為人類被剝皮。”
這兩位老人我都未見過一次面說過一句話,可想到她們,總讓我忍不住仰望天宇。如果有天堂,她們一定正在那瑰麗圣潔的所在沖我微笑。
2
臘月底了,洛杉磯正午的陽光仍熱烈溫暖。走了一會兒,史蒂夫指著不遠處一塊大石頭說他得坐下歇歇。半年前他去北加滑雪,一條腳后跟的韌帶斷裂,打了三個月石膏,現在走路仍有不適,可他已經作好準備,一周后要再去滑雪,雖然醫生極力反對。一想到那個名為猛犸的滑雪場,我腦海里閃過的是那張沉靜從容的東方笑臉,是那個帥氣陽光的牛仔和兩條矯健的大丹犬。
“快告訴我,米歇爾怎么樣了?上次你說她干細胞移植很成功……”我望著史蒂夫,有些急切地問。
“現在,我得告訴你壞消息了。三天前,米歇爾走了,從被確診到離開,剛剛半年。下星期,在帕薩蒂納有一個追思會……”史蒂夫帶著磁性的聲音一下鈍澀了,雙眼皮的大眼睛里透著無奈與悲涼。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麗的陽光一下子比那雪山還刺眼。
“天哪!你過幾天去滑雪,會多難過!每次你都住在他們家……”我嘴上說著,腦子卻是卡頓住了的,仍不肯相信那個漆眉星眸的女子已經從世間消失了。
“她和瑞本來已經從山里搬走了,他們半年前在波特蘭買了個漂亮的房子,瑞在法學院注冊的碩士課程也要開學了。米歇爾添置了成套炊具和種子,打算在家煮飯帶狗種花種菜……我怎么能不傷感?他們在山里租住了六年的家,我熟悉得像我的滑雪杖。”史蒂夫說著眼圈已經紅了。
米歇爾,我怎么能忘記她,那張友善似姐妹的笑臉!
那年去洛杉磯采訪,在史蒂夫的游說下,我打算跟他去滑雪。從洛杉磯到滑雪場的路很好走,向北,開五個小時的車,路上所見,除了自二百年前就立在那兒的三兩個凋敝小鎮,只是一望無際的荒野。好在史蒂夫愛聊天,我已經被他“灌輸”了即將見到的米歇爾的簡歷。她自小家境富裕,父母是第一代菲律賓裔移民,都是很有名望的心臟科專家,在帕薩蒂納富人區擁有一棟百年別墅。從醫學院畢業后,米歇爾成了一名婦產科大夫。她愛玩兒愛運動,在一個健身俱樂部與史蒂夫相識,兩人都參加了每周三次的越野晨跑,早上五點就起床跑五英里。家境好、生活如意的女人大都晚婚,因為她們不期待通過婚姻或愛戀改變人生。年過三十,她嫁了稱心如意的白人老公,是個帥氣儒雅,成功的企業家。婚后五年,命運跟她開起了玩笑。“很抱歉,honey(甜心),這是我為你慶祝的最后一個生日。咱們分手吧,我愛上了一個男人……”在她的生日晚宴上,遞上一塊新款的百達裴麗手表,丈夫帶著歉意坦然相告。她有些喘不上氣來,似乎一下明白了為什么結婚五年了她一直沒有懷孕。
離婚手續辦得很利索。這夢幻又奇葩的婚姻破裂了,碎殼下倒并非空無一物,銀行賬號里那長長一串數字像一串珍珠項鏈,至少令人欣慰。前夫不是沒良心的人,創立的新公司剛好上市,很慷慨地給了她一大筆錢,加上做醫生的積蓄也不少,米歇爾便辭了職,揣著一顆空蕩蕩的心和鼓鼓的錢袋,開始周游世界,同行者是她的愛犬彼得。有著運動員體型的她也許身手太矯健了,兩年過去了,丘比特之箭從來沒能射中她,直到某天倦累了回到洛杉磯。一個冬日,她決定去滑雪。
“她住在山腳下的威斯汀酒店,很快結識了一幫志趣相投的朋友,包括一對長年住在滑雪勝地的夫婦。某天他們說:‘你應該認識我們的朋友瑞,一個真正的西部牛仔,他也有一條大丹犬。’他倆一見鐘情,盡管她比瑞年長十五歲。”他倆帶著兩條大狗,租了一個二層樓的木屋,一住就是六年。每年十月開始飄雪,整個小鎮銀白一片,那在山腳下的房子被覆蓋上了潔白松軟的棉袍,像現實版的童話世界。
我聽了越發想認識這對情侶。
快到了,史蒂夫接到米歇爾的電話,說一會兒要接上我們一同去河邊餐館吃晚飯。她的聲音很干凈渾厚,隔著電話都能讓人感受到暖意,沒有一絲富家女慣有的嗲氣或甜膩。
剛辦好入住,在房間安頓好行李,他們就到了。
米歇爾在電梯邊迎到我們,與史蒂夫擁抱后,站在那兒目光暖暖地打量著我。她臉色微黑,濃眉大眼,一頭黑直的長發,加上真誠的微笑,在金發碧眼的人群中,讓我看著倍感親切。瑞從那輛舊舊的頂著雪的本田小車里出來,高大修長,濃密的棕發剪得極短,戴著金邊眼鏡。他安靜靦腆地笑著,像個在讀大學生。
路兩側是高高的雪墻,那是暴雪后由鏟雪機堆起來的。不同于用了除雪劑的主路,通往樹林深處的餐館要經過一條結著冰的窄土路。瑞把車開得極小心,嘴里仍熱切地和史蒂夫討論著洛杉磯棒球隊的排名。“你知道嗎,男人眼里的孩子氣真讓我受不了,我完全沒有抵抗力!”米歇爾拍一下我的肩,笑著說。這句話很有魔力,一下把我們倆拉近了。
“喝什么酒?如果都點紅肉咱們就要一瓶紅酒。如果吃海鮮,就來點白葡萄酒。”他們顯然是那餐館的老主顧,服務員大媽親熱地撫了一下瑞粉紅的耳朵。他是個地道的白人,兒時父親出走,母親在一個牧場當廚師。他十來歲就在牧場與牛馬廝混,獨自在山上放牧,為小牛犢小馬駒接生,嚼著草莖枕著雙肘躺著望天,在大自然中他像匹野馬一樣無拘無束地長大。
“你甚至可以不用馬鞍倒坐著騎馬?”都市生都市長的史蒂夫羨慕的驚嘆,讓米歇爾臉上泛起自豪的笑意。她側過臉望一眼身邊的瑞,抬手愛撫一下他的短發。是喝了酒嗎?燭光下,她的眸子越發黑亮,像注滿了幸福的幽泉。
開胃菜,湯,正餐,甜點,一道道地上來,全都美味可口。我們喝光了兩瓶紅酒。聊天的內容也是天南海北,包括旅途的見聞,正熱映的電影,更多的是聊他們即將迎來的新生活。房子看了好幾處,除了要給人和狗足夠的空間,他們最在意的是要有幾棵大樹。當然,幾位都是dogperson(愛狗人),狗狗是不可缺少的話題。
“我愛福克納,他是真的懂狗愛狗的好作家!”米歇爾給她的狗取名彼得,是因為福克納那篇《他的名字是彼得》,那條只活了十五個月便被汽車軋死在公路上的獵狗。“彼得還是原諒了這個司機。在彼得一年零三個月的一生中他從人類那里得到的除了仁愛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他甘愿奉獻出一生中剩下的六年、八年或是十年,以免有一個人趕不上自己的晚飯。”米歇爾在手機上找到那篇短文讀了起來,“可是他僅僅是一條狗。他沒有過去也絕不會永生不死,對于他來到的這個世界他所要求的并不多:食物(他不在乎是什么,也不在乎給他多少,只要是慈愛地給予就行)、手的撫觸、一個聲音(他認得這聲音,雖然不理解所講的話也無法回答),還有就是可以奔跑的土地、可以呼吸的空氣、四時八節的陽光雨露……聽聽!”
瑞剛要接話,米歇爾笑著輕拍一下他的手背,有些孩子氣地搶著告訴我們,“知道今年夏天我們四口去哪兒了?MontereyBay(蒙特利爾灣)!就是想感受一下當年約翰·斯坦貝克帶著他的狗——查理,在碼頭走來走去的場景。棒極了!聽聽這段,《斯坦貝克攜犬橫越美國》……”說著,她又快速在手機上劃著,揚臉讀起來,“他不識字、不會開車、對于數學一點概念都沒有。然而在他努力的領域里,也就是他現在正在做的事——緩慢而高貴地把整個區域聞個夠、留下足夠的氣味——則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當然,他的領域有限,但我的領域又有多寬呢?”聽說斯坦貝克也是我喜歡的美國小說家,以蒙特利爾灣為原型的《罐頭廠街》我更是百讀不厭,米歇爾開心地舉起右手在空中與我擊掌。“我和瑞說好了,等過些年,也和斯坦貝克一樣帶著狗去游歷,也許和他一樣,走上一萬英里……”
我們靠窗而坐,隔著一層玻璃,外面是雪堆成的白而厚的墻,房檐下錐形冰凌晶亮剔透,工整地豎成一排,讓人想伸手去摸或用舌頭去舔。戶外的冷冽和桌上的熱烈相映,讓人愈發覺得這把酒閑聊的夢幻。我不由暗想,人生有這樣的美妙時光,確實值得來過。
我和史蒂夫出門前已經約好,結賬時splitthebill(分攤賬單)。許多美國人約定俗成的規矩,再好的朋友相約吃飯,也是AA制,何況這個餐館的美味并不價廉,這樣全套地吃喝下來,至少得三百美元。賬單來了,瑞伸出長胳膊接過去,笑著遞給米歇爾,“Beourguests(當我們的客人)!”米歇爾柔聲說著,拿筆在賬單上寫小費,好像款待朋友是最自然且快意的事。
回酒店的路上,望向車窗外,山嶺與雪野一暗一明,線條壯闊又纖柔,像一幅中國古山水畫。一度,我們都靜坐著沒有說話。不記得是誰感嘆了一句瘟疫之下人類的脆弱。“我覺得人類應該放下面具,放下虛榮,像狗一樣,自由而忠誠地活著。”米歇爾與我坐在后排,輕聲說罷這句話,側臉望著我,目光篤定,像夜幕中剛掛起的星。
“是啊,所以我一到冬天就來滑雪,自1969年起,五十多年了,從沒間斷過。有人說不值得,往返開車十幾個小時,只為那幾小時的快樂。可我不在乎。有多少成年人還沒放棄孩提時的快樂啊!我希望自己能滑到八十歲。不過,也沒幾年了。”最后這句,史蒂夫的聲音低了下去。
“瑞還有些年頭,他還年輕……”米歇爾頑皮地笑著,邊說邊伸手搔了搔瑞的后脖子。“哦天,你嚇得我差點讓車撞到了雪墻上。”瑞驚叫著笑嚷。
雖然有個富足的女友,瑞仍在利用他的法學專業賺錢,不時受地方司法部門的委托,走訪、記錄和安撫家暴案件的當事人。
聽說我想去體會地道的美國牧場生活,他說可以幫我引薦,“我建議從幫廚開始,每天交幾十美元,吃住全包。慢慢地適應了,就可以接觸畜群,練習一下騎馬。到時候恐怕你就不想寫作了,那樣的田園生活既忙碌又放松,沒體會過的人永遠想象不出那感覺。”
“不過,你真要去那兒生活,需要額外地小心一點,laylow(低調)。那里方圓幾百公里全是白人,看到其他膚色,比如像咱們這樣的人,他們會不習慣,甚至會大驚小怪……”明明是在說種族差異,米歇爾仍是云淡風輕地笑著。
3
快到酒店時,瑞停車加油。
我和米歇爾說起了我十五年前剛到美國時第一次加油的經歷。
“在中國的加油站,只要把車一停,就會有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上前來招呼。熄火,你不用下車,只需從搖下的車窗大聲嚷一句加滿,無論是用加油卡還是現金,幾分鐘搞定。不像在美國,全是自助加油。”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個暮春的黃昏,剛參加了一個活動,看到油量很低了,便開進路邊一個空蕩蕩的加油站。我突然有些心虛,除了幾桿注油槍掛在那兒,看不到一個人影兒。我事先倒是聽同事指點過這里加油的規則——有加油卡或信用卡,可以直接刷卡;如果兩樣都沒有,就要走進那便利店交現金,說明車停在幾號加油槍旁邊,服務人員會收費遙控,你出去加夠預付的費用,加油機便會自動停止。
我是辦了加油卡的,按屏幕指示一步步操作,刷卡,快速取出,選擇加油型號,拉過油槍插進車的注油孔,楞是不出油!重新操作一遍,仍是沒動靜。
我有些急了,天色開始暗下來。不久前剛看到報上說有一個劫匪專門在加油站搶車,趁車門沒鎖,鉆進去開車就跑。他已經作案十幾起仍在逃。
“我聽說過那個劫匪,專搶女司機,當時的新聞很轟動。”史蒂夫道。看著油表在蹦數字,瑞也過來聽我說。
想求助吧,偏偏沒有其他人出現。我坐進車里,鎖好車門,焦急地等了十幾分鐘。暮色漸濃。終于,有一輛越野車很快速地開了過來,從上面跳下來一個人,還好,是位金色頭發的中年婦女。穿著牛仔褲和及膝馬靴的她像個中世紀騎士,利索地泊車,腋下夾著個男式公文包,走進旁邊的便利店。
“你不會加油?!Ohmygosh(哦,我的天哪)!”她臉上的驚愕比遇到劫匪并不遜色。
我只能有些難為情地微笑著說我試了,不行。
“以前都是誰為你加油?”她臉上浮現出友好的笑意,似乎想把驚訝藏起來。
“我丈夫。”我有點尷尬地應付道,不想跟她解釋中國的加油站有多方便。
“你丈夫?!親愛的,作為女人,不能事事指望男人活著哦。”她睜大了眼睛望著我,一字一頓地說,像母親在不放心地叮囑思想幼稚的孩子。
我點頭說好的。她接過我的加油卡,熟練地操作著,不到一分鐘,就有新鮮血液注入了我那老馬的胃。
“哈哈,我覺得你應該感謝這個看似有點女權主義的陌生人。我以前和你一樣,許多事都是父母和兄弟、丈夫來操心。后來我去云游四方,租住在意大利人家里,語言不通,買不到新鮮菜蔬,吸塵器壞了也要自己修,似乎是可憐的,可真學會了必需的生活技能,才感覺像魚在大海里游泳一樣的自由,以前的安逸不過是在泳池里打轉的小自在。”米歇爾從地上握起一團雪,揉成雪球朝一株松樹扔去,“《圣經》里說夏娃是由亞當的一根肋骨做成的。我沒有宗教信仰,即便如此,女人也可以選擇做一根堅韌的肋骨。”
我們都不相信那次的見面是唯一一次,臨別依依,約好他們來中國找我玩兒,或者我到了美國去投奔他們的新居。
“有錢有愛心不勢利不自私,米歇爾是多么難得的好女人!我就不理解為何英語會有misogyny(厭女癥)這個單詞。我生命中認識很多女性,看似柔弱,但即便遭生活凌辱,也挺直脊背活得磊落坦蕩。”在酒店電梯里,史蒂夫感嘆。
“米歇爾、吉賽爾和你母親,還有我北京那位朋友的老媽,都是可愛的肋骨!”我笑著贊同。
有好幾次和國內的男性朋友聊天,他們都好奇地問我對美國女人的看法。有人問我是否她們更傾向于淡化性別,活得更獨立更堅強。在我看來,美國女人確實往往更具“中性思維”,不因為性別下意識地讓自己先矮男性半頭。
自那以后,史蒂夫又去滑過兩次雪,而我則在摔傷了肘部后對滑雪失了興趣,但仍不時聽到米歇爾和瑞的消息,知道他們從雪山腳下搬走了,正熱火朝天地迎接人生新一階段。
后來我回了北京。時差還沒倒過來,半夢半醒中接到史蒂夫打來的微信電話,聲音低沉。“有個非常壞的消息我得告訴你。米歇爾病了!她早晨醒來,發現身上有許多瘀斑,瑞趕緊拉她去醫院,她被確診了白血病,而且是非常惡性的那種……”
我心一抖,怎么會?我們的老朋友彼埃爾得了白血病后抗爭了兩年,在春天仍是走了,但好歹他也活了八十二歲,而米歇爾才不過五十歲!我安慰著史蒂夫,也在安慰著自己,說別太擔心,一來現在科技發達,二來米歇爾年輕,有經濟實力,父母和她自己又都是學醫的,應該能有好轉。
此后不時聽到史蒂夫轉述的消息,還看到過一張米歇爾化療后包著頭巾的照片。照片中,她與瑞相依而坐,臉貼著臉,開心地咧嘴笑著,似乎她得的只是一場感冒。不久,聽說她哥哥特意從外州趕來,配合醫院為她做干細胞移植,進展順利。沒想到……
“那天瑞給我打來電話,帶著明顯的哭腔。”我從來沒見史蒂夫如此壓抑沮喪甚至氣憤,“命運太不公了。那么善良的人,沒有不良嗜好,竟然說沒就沒了。”
心酸化作淚水流了我一臉。米歇爾,人生若只如初見!
那場隆重的葬禮,地點選在加州理工大學那座古香古色的小樓,愛因斯坦曾在里面住過很長時間。吉賽爾也去了,發給我一些現場照片。“大家輪流發言,一會兒笑,一會兒哭,回憶當年和她在一起的點滴往事。”史蒂夫說到場的親友有二百多人,包括米歇爾的前夫,他獻上了一籃白色蝴蝶蘭——他是一位儒雅清瘦像哲學教授的男子。
我沒敢去,燃了三支香,默想著靈堂里米歇爾的那張照片。她側著臉,篤定專注地望著我,就像那晚坐在車里時一樣。
“她有遺言嗎?”我不甘心地問史蒂夫。
“瑞說她最大的遺憾不是不能陪親人多走一程,而是不能捐獻器官,雖然她十六歲第一次考取駕照時就在器官捐獻后打了勾。她沉著地把后事都作了交待,還手寫了這張紙片。我拍了發給你。”
那是一張巴掌大的橫條便箋紙,很流暢的筆跡:
Lessonsfromdogs
(從狗那兒學到的)
Getmessy
(去滾一身泥)
Run,jump,play
(去跑,去跳,去玩)
Donotbeafraidtorelax
(不要害怕放松)
Betruetoyourself
(真實地面對自己)
Getalittlegoodysomewhere
(在某個地方做點好事)
Giveeveryoneachance
(給每個人一個機會)
Greeteachdaywithexcitement
(帶著興奮迎接每一天)
Donotforgetfoodisawesome
(別忘了食物是了不起的)
Takecareofyourself
(照顧好自己)
Beloyal
(忠誠)
Donotholdgrudge
(不要懷恨)
Appreciatelittlethings
(欣賞小事)
Knowhowmuchyoulovesomeone
(知道你多么愛一個人)
我也看到了照片里的瑞,著黑色西裝的他似乎一下成熟了十歲,他對著鏡頭微笑,禮貌、努力地微笑。那張臉真誠依舊,笑容后是藏不住的心碎和哀傷,讓人不忍多看。米歇爾和那些桃李春風的印記,已經深深嵌進他三十五歲的生命底色中。那還沒焐熱的新家,那失去了女主人的狗,既是保護他的鎧甲,也是刺痛他的傷疤。
“C'estlavie(這就是生活).”史蒂夫遇到不如意的事,都愛用法語發出這句感嘆。“米歇爾沒錯,我也從狗身上學到過不少東西。我曾養過一條狗,它陪伴了我十八年。每天我和老鄰居喬治教授一起遛它兩趟,一月月,一年年,我們眼看著它脊梁塌下去,臉上長了突起的肉瘤,后來牙也掉了,下巴也松了。我和喬治說,從它身上就看到了我們自己,咱們也正走在這條老邁下去的路上……這就是自然的殘酷,任誰也沒有辦法阻止。”
幾天后,我接到了史蒂夫的電話,他正在開往猛犸滑雪場的路上,“我要像條狗一樣,去滾一身泥,去雪地上打個滾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