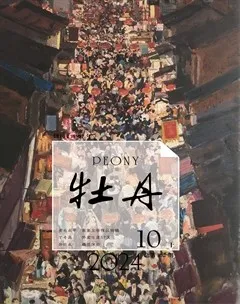客家紅背帶
邱裕華,江西省作協會員,作品發表于《人民日報》《讀者》《散文》等報刊。
我是在母親的紅背帶上長大的。
我的老家在贛中南的大山里,全村都是從外地遷移過來的客家人,落腳于此也不知有多少代了。猶如中國紅一般的紅背帶,在我們那里,每家每戶都可以見到。它是客家人代代相傳的摯愛,聯結著一個個孩子的幼年時光。
這樣的紅背帶,在客家每一個出嫁姑娘的嫁妝里都有。它的做工很簡單,擇一塊兩三米長、一兩尺寬的大紅棉布條,縫邊后擰起來即可,要是手藝熟練的裁縫個把小時就行了。但是,它質量上乘,能用好幾年甚至十幾年。更重要的是,在這滿滿的中國紅里,盛滿了濃濃的祝福:祝福白頭偕老,日子長長綿綿;祝福驅邪避兇,日子紅紅火火;祝福早生貴子,“背帶,背帶,帶子帶孫,子女滿堂”。
紅紅的背帶,一頭連著新娘,一頭連著新郎。結婚那天,新郎帶著親友,早早地出發,騎著自行車,翻山越嶺,來到新娘家。在陣陣嗩吶聲中,在鞭炮聲里,新娘哭著告別不舍的父母,戴著紅蓋頭,穿著紅嫁衣,帶上祝福,坐上婚車,開始向未來的生活出發。紅背帶的一頭,是新郎幸福的笑臉,真心的承諾。紅背帶的另一頭,是新娘的忐忑與期冀。窮也好,福也罷,新娘把自己的一生和新郎緊緊相連,許下對未來不變的夙愿與美滿。
紅紅的背帶,一頭連著母親,一頭連著孩子。新婚之后,孩子很快出生了。農村家務活多,家里家外,灶前灶后,樣樣都需女人到場。襁褓中的孩子沒人帶,怎么辦?紅背帶從嫁箱里拿了出來,年輕的母親背著幼小的孩子在廚房里忙碌,在小河邊清洗,在菜園里除草,在地里種莊稼,在圩鎮上叫賣……初為人母,一開始背的時候,動作生疏,甚至還需別人幫忙,而且兩個肩膀酸酸的,胸口也有些悶。很快,她就能熟練地應付了。她把紅背帶對中從孩子的兩腋下穿過,然后微轉身半蹲下,兩只手各抓住背帶的一頭,輕輕一用力,孩子就到了肩膀上,然后將紅背帶從自己的肩膀拉下到胸前交叉,再往后裹住孩子的小屁股,又回到自己的胸前打上牢牢的結。這樣,不管是上山還是下地,子心貼母背,冷熱相依偎。看到孩子一天天長大,猶如地里沐浴春風春陽的莊稼,她開心地唱著歌謠:“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唱著唱著,背后的小家伙打著細細的呼嚕又甜甜地睡著了。
紅紅的背帶,一頭連著艱辛,一頭連著希望。鳥兒大了,總要勇敢飛向天空。婚后的男人,理當成家立業。在農村,要是兄弟姐妹多,往往新婚不久,一對新人就需分家立戶,開枝散葉。面對簡陋的家舍,夫妻兩人手握手,心連心,開始小家庭的謀劃。紅背帶,牢牢地拴著一家人。盛夏時節,汗水濕了紅背帶,濕了母親的肩背,也濕了孩子的衣襟。到了臘月,寒風吹來,出門時母親給孩子蓋9iryK9uv58sWApmFA7NsqpjGyAgPcdaRs79u5b4TcK4=上厚厚的棉披風。孩子餓了,找個背風的地方,把孩子放下喂口奶,解泡尿。沒辦法,生活總得朝前走,活兒那么多,日子和希望就在前方,年輕的母親總要腳步不停息,才能趕上。要是夫妻慪氣吵架了,她氣不過,背上孩子就回了娘家。孩子他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過個一天兩天,記掛著家里的活計,她又背著孩子從長長的山路那頭回來了。寒暑交替,在母親的背上,孩子一天天長大,不再需要母親背著了。可是,又一個小生命出生了,紅背帶又出現在了母親的肩上。
我出生時,我的母親已經四十三歲了。那時,繁重的家務,讓母親天天都忙碌在生活的經緯線上。母親是如何把我養育大了,我自然知之甚少。可是,我結婚后,母親經常向我的妻子重復這么一個細節:冬天,母親背著我上山撿柴火,等母親手持柴刀砍好、捆好一大把柴火要回家了,只要母親把柴火扶立在地上,準備背上肩頭時,我總是立馬把小小的腦袋偏到一邊去,而且一路上都是如此歪著頭,沒有被那些粗糙的柴火弄破過臉頰。
我的母親每說一次,妻子就會取笑我一回,說我小時候蠻聰明的。我卻笑不出來。母親撿柴火的山我是知道的,我長大后經常跟她去。在我們那兒,冬天農閑時節每戶人家都要到山上撿好次年用的柴火,不然,開春之后沒有時間,而且天熱了山上也有蛇。那崎嶇狹窄的山路,處處都是纏繞交雜的灌木、荒草和野藤,有些地方又滑得很,空手都不好走,母親背著我,還要背著五六十斤重的一捆柴火,她是用了多大的小心和力氣才得以平安地往返一趟趟的?
一條紅背帶,一生養育情。紅背帶,就像是第二條臍帶,在嬰兒出生后又重新把母親和孩子系在一起。只是,在歲月的洗滌中,它漸漸褪色、破舊,不再那么紅艷得如早春的花、深秋的果。隨著紅背帶的褪色,母親窈窕的身姿漸漸變得臃腫,堅挺的脊背漸漸變得歪斜,年輕秀美的新娘成了蹣跚的老太太。大了的孩子,像鳥兒一樣飛向四方。
飛得再遠也不用怕,只要循著長長的紅背帶,就能回到母親溫暖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