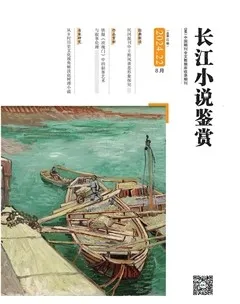論王西彥小說的女性書寫
[摘要]抗戰時期,作家王西彥創作了大量小說,其中的女性形象有相當分量,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女性人物長廊,也為女性文學的發展增添了一份力量。本文著重分析王西彥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即農民中的女性形象和知識分子中的女性形象,試圖通過小說中對女性人物的塑造來探究作家的文學創作觀及其對女性的認識。
[關鍵詞]王西彥" "農民" "知識分子" "女性形象" "女性書寫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2-0052-04
王西彥的創作始于20世紀30年代,其一生筆耕不輟,出版了十余部小說集及大量文藝理論著作,是抗戰時期東南文藝的代表作家。從抗戰初始到40年代,王西彥以一種“農民式的固執”進行創作,其小說數量之巨居戰時作家前列。
王西彥的小說主要涉及農民和知識分子兩類題材。作品塑造的主要人物譜系有農民、女性、知識分子三類。當然,女性可以劃歸到農民或知識分子之中,但因為其作品中女性形象所占比重較大,故將這一形象單獨劃分。本文著重分析王西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即農民中的女性和知識分子中的女性,試圖通過分析其對女性的書寫探究他的創作觀及他對女性的認識,更深入地發掘其小說的價值內涵。
一、農民女性
王西彥早期以浙東家鄉的人和事為題材,創作了大量關于農村女性苦難生活的文章,被冠以“鄉土作家”的頭銜。然而浙東家鄉給他的感覺是陰郁、凄冷的,誠如作家在作品選本自序中所說,“直到現在,回憶起自己童少年時代的家鄉生活,就會在腦子里展現出一連串令人戰栗的悲涼景象。”[1]因此,作家這一時期的創作也顯示出悲涼的基調,其筆下的女性人物也幾乎有著同樣悲慘的命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頑固封建勢力的壓迫,另一方面則是扭曲的宿命觀作祟。
1.封建勢力壓迫下的女性
《村野戀人》中的小金蘭為讀者上演了一出愛情的悲劇。人性天然的欲望讓小金蘭和庚虎這對青年男女心生愛戀,然而家庭的貧富差距和父母排斥外姓人的觀念使得這段愛情無疾而終。戰爭的爆發更加重了他們愛情的悲劇意味,庚虎被日本兵所虜并在逃跑時被擊殺,失去愛人的小金蘭在沉痛的心境之下孤苦地活著。《微賤的人》更是封建專制制度下農村婦女悲慘命運的真實寫照。銀花在生父的打罵下度過凄苦的童年,成年后被繼父賣到山里。銀花在山里成了家,雖然丈夫和婆婆對她愛護有加,但村里仍有一部分人對這個“來路不明的外地人”充滿敵意,銀花與牛二坤的戀愛也因她是外村人而遭到阻攔。最后女兒意外溺亡,牛二坤慘死,婆婆發瘋,銀花選擇投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古屋》這個封建大家庭中,悲劇也時時上演。陰暗的古屋里,掌權者(孫尚憲)利用封建家長制的權威對女性進行肉體與精神上的迫害,孫尚憲的妻子受不了封建大家庭抑郁的氣息和駭人的封建權威選擇投井自盡。啞巴侄子的媳婦兒被高價彩禮和謊言騙至孫家,過著精神與肉體極度壓抑的生活,她試圖逃跑卻被抓了回去,最后瘋瘋癲癲撞墻而死。值得一提的是,《古屋》和張愛玲的《金鎖記》幾乎完成于同一時期(1944年),但和張愛玲的創作不同的是,王西彥對啞巴媳婦兒悲劇命運的描寫更側重于分析造成悲劇的外部因素,而對于其身上的人格缺陷不做過多闡述。在塑造啞巴媳婦兒這一人物時,王西彥始終懷抱憐憫之心,同情其不幸遭遇,包容她身上存在的人性弱點,直接把矛頭指向封建家長制。
2.宿命觀麻痹下的女性
封建勢力的壓迫和病態的國民性在上述女性人物身上得到體現,而扭曲的宿命觀則較多體現在王西彥筆下的童養媳身上。這些童養媳都有著悲慘的命運,身處苦難之中的她們只能用宿命觀來慰藉自己,“這是繼魯迅之后又一幅中國婦女的另類悲劇圖———沒有抗爭的悲劇”[2]。
王西彥以自己母親的形象為原型,創作了小說《苦命人》,講述母親在姥姥家長權威的逼迫下離開“家”,最后郁郁而終。在故事中,作為童養媳的母親即使為這個家付出了全部精力,做足了兒媳的本分,但仍被婆婆無情打罵。在生命垂危之時,母親說:“不是姥姥的錯……是媽媽的錯,是媽命不好……”[1]童養媳不僅喪失了婚姻自主權,她們基本的生存權也得不到保障。《鳳囡》中,童養媳鳳囡成天在婆婆的辱罵和丈夫的毆打下討生活,遭受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可是她卻將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苦痛都歸咎于自身命運的不濟,“她想到命運的難以違抗,前世欠債的無法還清,被迫于一種深沉的絕望”[3]。還有《黃昏》中的福田媳婦兒,自做童養媳起她就過著凄慘的生活,二次成家后,突發的戰爭和天災又使她陷入絕境。丈夫失蹤、公公病倒、家畜也在瘟疫中死去。公公把一切的災難都歸于她這個“外來人”的不祥,她也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個不祥之人,于是認為“一切災難應該由自己一人擔受”,并“聽憑他把一切禍害歸嫁到自己身上”[4]。以上這些童養媳們,全都過著奴隸般的日子,她們不敢有怨言,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用“這就是命啊”來安撫自己。她們被生活壓扁,喪失了反抗意識,覺得自己理應是苦難的承受者,她們的靈魂已麻木,令人痛惜。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在所有的社會領域中,人們把婦女看成另一種人——他者。在此,“他者”是指那些沒有或喪失了自我意識,處在他人或環境的支配下,完全處于客體地位,失去了主體人格的被異化了的人[5]。童養媳們喪失了自我意識,屬于“他者”,她們變得麻木,沒有了反抗的能力,只能以宿命觀來慰藉自己的心靈。當然,作者在批判之余也極力為我們展示這些女性身上的堅忍、善良、勤勞等品質。童養媳們具有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但都被不公平的社會所傷害,因此,在作者看來,這些女性并不是可辱的,而是可悲的!這種宿命觀也不是天生就形成的,而是千萬受苦受難的農村婦女在無奈之下的共同選擇。總之,王西彥在這些作品中傾注了他全部的悲情,誠如學者張晉業所說,“不但寄予同情,而且在靈魂深處同她們打成一片”[6]。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學綱要》中指出:“在漫長的童年時期,正在逐漸成長的人依賴自己父母生活。這段時期在他的‘自我’中留下了一種‘沉淀物’,形成一個特殊的媒介,父母的影響便通過這一媒介而得到延伸。”[7]王西彥在他的回憶性散文中常常提及在童年時期見證過的農村女性的悲劇命運,這些悲劇人物在他的家中就有原型,即作為童養媳的母親和苦命的姐姐。王西彥正是從她們的遭際中感受到人間的不平,所以他要為與有同樣命運的人們訴苦,反映一個時代農村女性的悲慘遭際。
二、知識分子女性
王西彥在20世紀40年代進入創作的高峰期,他一方面繼續取材于鄉土并抒發自己對戰爭的沉思;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描寫戰爭中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形成了他又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小說系列。他認為“知識分子不僅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他們中間的先知先覺者”[1],在這一觀念的驅動下,他的知識分子系列小說創作愈發走向高潮。王西彥取材身邊的人事,并把自己對知識分子命運的體會、思索融進小說之中。本部分著重分析王西彥筆下的女性知識分子形象,發掘在特定時期部分女性知識分子的特質,并以小見大探析戰時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總的來說,王西彥筆下的女性知識分子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被黑暗淹沒走向沉淪的知識女性;還有一類是擺脫封建束縛,實現自我救贖并投身社會革命的知識女性。
1.被黑暗湮沒,走向沉淪
在近現代的社會改革中,知識分子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力軍。但同時,由于知識分子自身怯懦、易動搖的弱點,他們被貼上了“寧做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標簽。這些弱點在戰爭的背景下更大程度地顯現出來。王西彥基于這些弱點,塑造了一群在戰時被黑暗淹沒,走向沉淪的女性知識分子。
《家鴿》中的姚文英,從一位知識女性搖身一變成為全職太太,養尊處優的生活讓她逐漸忘卻了自己的“飛翔技能”。因感生活乏味,她即興參加了“三八”節慰問傷兵的活動,但在前行的路上卻因為一點挫折而選擇了退縮,逃回家后她宛如一個受委屈的孩子撲進丈夫的懷里尋求安慰。優裕的生活讓姚文英理想的翅膀退化,成為飛不遠的籠中鳥。在甜蜜的幸福中,姚文英甘愿沉淪,即使這幸福是以喪失自我獨立的能力為代價。姚文英這個人物極具代表性,代表著當時一部分嫁入豪門的知識女性,她們被包裝成華而不實的洋娃娃,再也走不出那個甜蜜的“家”。作者塑造這類人物旨在告訴讀者,姚文英們雖然是知識女性,但知識只是被她們當作精美的飾品,她們的靈魂早已在物欲享受中走向墮落。
同樣被黑暗勢力吞噬的還有《神的失落》中的高小筠。高小筠純潔、天真,是男主人公(馬立剛)心中的神女。但在邪惡面前她卻放棄追求,跳進黑暗的陷阱。她放棄與馬立剛的愛情,成為發國難財的表哥的側室,造成馬立剛的“神的失落”。但對于高小筠這個人物,作者并沒有過分譴責,反而投去憐憫的目光,甚至公開為其辯解,認為“她不是個懦弱的人,她‘是我們所生活著的這個時代或社會的創造物’”。因此,“我們不應該用一些空洞無言的言辭去責備她,我們應該低下頭來去看一看自己所站立的土壤,自己所處的環境”[8]。面臨愛情和生存的選擇,高小筠在經過一番理性的思考后最終徹底看清現實。如果說子君的選擇尚有反抗封建禮教的意義,高小筠的選擇則是金錢與愛情之間的選擇,即物質生存需要與精神追求之間的選擇[9]。在作者看來,她的沉淪不是墮落,而是清醒的生存之道。
2.擺脫封建束縛,實現自我救贖
王西彥小說中的男性知識分子大多是力弱者,相反,一些女性身上卻蘊含著巨大的力量。《古屋》中的洪翰真在戰亂時逃出封建大家庭并立志獻身于抗戰。她奉行獨身主義,認為女子應該接受教育成為一個獨立的人,而不是成為男子的附庸。她認為,女性的獨立“第一能擺脫男子出于自私的那種柔情的束縛,第二能夠解除家務和子女的糾纏。但這談何容易?這是必須在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之下才有可能”[10],尖銳地指出了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女性的生存困境。因此,她熱心教育事業,試圖通過教育來改革社會,試圖尋找到一條更公平的道路。她對改革事業的熱情與孫尚憲“伊壁鳩魯主義”的庸于安逸產生強烈的對比,成為黑暗中的一縷希望之光。
同樣追求理想并投身抗戰事業的知識女性還有《母性》中的黎敏和張志慧。黎敏原本是一位教師,擁有穩定的工作和美滿的家庭,戰爭使她放棄“小家”而成全“大家”。她與丈夫將自己剛出生的孩子送往保育院,決心獻身于抗戰事業。黎敏處于矛盾的心理狀態之中,天然的母性情感讓她認為把嬰兒拋棄是一種犯罪行為,但她又明白“這不是我們兒女情長的時代”[5]。面對喪子之痛,她“放聲哭將出來”以平衡內心的矛盾。和黎敏的矛盾心理不同的是,張志慧的心志則更加堅定。張志慧是一個有著不可捉摸性格的女子,在愛情上極其灑脫。她和一名實業家結婚兩年后,在愛國信念的驅使下毅然決然地拋下丈夫和孩子,全身心投入到抗戰中。當她得知黎敏為追求抗戰事業而選擇放棄剛出生的孩子后激動地抱住了黎敏,并認為“這真是一種崇高的犧牲!”投身抗戰,爭取早日解放正是王西彥心中完美又誠摯的理想,“那些在黎明的濃黑里忘我的戰斗者,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界的驕傲”[10]。這類知識女性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作者理想的寄托。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女性身上完美的人格不免帶有“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色彩。
《古屋》里的另一位知識女性廖慧君,堪稱新時代“成功”的“娜拉”。廖慧君聰明能干,“卻陷身在一所窒息的墳墓一般的古屋里,年復一年地守著一份無望的生活”[9]。她在陰暗無趣的現實生活和知識女性對實現自我價值的精神追求之間彷徨,過著極度苦悶的生活。終于,她在秦一冰的幫助下逃離古屋,到重慶參加有關婦女運動的工作。秦一冰是廖慧君出走的助推者,也是廖慧君之前的一位“成功”的“娜拉”。但她們又有著很大的不同,秦一冰在失去兩個孩子和家庭的“寵愛”之后才選擇出逃,她沒有家庭的牽絆。而廖慧君則是拋棄了自己的家庭和兩個年幼的孩子毅然決定出逃,選擇去過自己理想的人生。她們的進步性在于基本祛除了對男性的依附意識,勇于“出逃”并追求獨立與自由;精神上的獨立又讓她們和魯迅筆下的娜拉產生共鳴,她們都有著叛逆的個性和反抗傳統封建舊思想的勇氣。但是,王西彥在對這兩位女性或者說“成功出走的‘娜拉’”們的描寫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經濟獨立,她們的出走事實上也是不成功的,但是將作品放在當時的戰爭背景下去考察,又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抗戰到底”是王西彥創作的特點,但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寫作,秦一冰和廖慧君這兩位女性形象身上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事實上,作家是為抗戰寫女性,而不是為女性寫女性,從創作動機上看,王西彥的女性書寫略顯單薄。當然,如果我們因此去否定作品的全部價值,那對作家也不免過于苛刻。其實作者著力想為我們呈現的是這些“娜拉”們的反抗精神和勇于追求的品質。
三、結語
王西彥善于用感性的思維觀察女性世界,他在書寫家鄉女性的生存時常常融入自己對女性生存的理解,飽含對女性生命狀態的關注。王西彥的童年經歷令其塑造的遭受苦難的農村女性形象更為真實,“不但寄予同情,而且在靈魂深處同她們打成一片”,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中國現代男作家對鄉村女性的想象性書寫。此外,他還始終以平視的目光去理解和書寫女性,以細致溫柔的內心發現女性身上特有的品質,這多表現在他塑造的“童養媳”身上。“童養媳”們雖然深受宿命觀的荼毒,但作者無意于批判而旨在同情,對她們身上的堅韌品質給予欣賞。在書寫知識女性時,作者一方面延續之前的風格,一方面又將其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下進行考察,發現她們身上新的特質。對部分“沉淪”的知識女性,如高小筠,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而對擺脫封建束縛實現自我救贖的女性身上獨特女性意識的書寫,則讓讀者看到了黑暗中的希望。從“沒有抗爭的‘悲劇’”到成功出走的“娜拉”,王西彥在創作題材上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但不變的是他對于中國女性生命狀態的關注和真誠的寫作態度。
參考文獻
[1] 王西彥.王西彥選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
[2] 朱向軍.沒有抗爭的悲劇——論王西彥《悲涼的鄉土》上的女性[J].名作欣賞,2013(17).
[3] 王西彥.悲涼的鄉土[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4] 王西彥.王西彥選集(第二卷)[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
[5] 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6] 張晉業.試論王西彥的短篇小說創作[A]//艾以,等.王西彥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7]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綱要[M].劉福堂,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
[8] 王西彥.王西彥選集(第三卷)[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
[9] 周麗娜.被壓抑的個人現代性——以《夢之谷》和《神的失落》為例[J].煙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4(3).
[10] 王西彥.王西彥小說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特約編輯" 張" "帆)
作者簡介:王小鳳,寧夏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