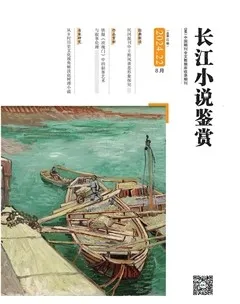對鄉村秩序重建的深切期望
[摘要]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趙樹理因其對鄉村問題的持續關注與洞察而聞名。他從自身過往的農村生活經驗和對時代政策的獨特領悟出發,將鄉村議題融入其創作中,經由小說的形式深入剖析鄉村社會的演變。他描繪出一條雖不明顯但飽含深遠意義的鄉村秩序恢復與構建的途徑。經由個體與集體的有機結合,趙樹理將社會主義理念逐漸滲透到傳統的熟人社會之中,構造出對鄉村共同體的全新的現代性想象。這種嘗試不僅是對鄉村現實的真實寫照,更是基于鄉村現實對未來的一種展望。盡管他的鄉村書寫存在難以整合的現代性經驗,但仍然體現了農民個體與鄉村集體之間的辯證關系,也體現了現代作家與其所代言的群體之間的復雜聯系。
[關鍵詞]趙樹理" "鄉村秩序" "現代性
[中圖分類號] I2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2-0103-05
趙樹理誕生于中國社會歷經滄桑巨變的時期,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度備受關注,亦不乏爭議。身為農民之子,他洞悉農民的艱辛與掙扎,對鄉村與農民懷有深厚的情感。這種情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創作立場和態度。趙樹理的寫作視角獨特,他自下而上地觀察鄉村社會,通過細膩的筆觸描繪出各色人物及新興社會力量的崛起。從20世紀40年代,趙樹理始終將創作焦點鎖定在鄉村社會。趙樹理將現實社會的紛繁復雜巧妙地植入文學作品之中,以此揭示鄉村社會的多元與矛盾,并再次復刻了鄉村社會秩序在演變與重構中所經歷的復雜過程。他的作品不僅是對鄉村社會的真實寫照,更是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深入反思。通過獨特的描寫手法,趙樹理將鄉村社會的復雜性、矛盾性和變革過程展現得淋漓盡致,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和文化視角。
一、鄉村社會的危機與鄉村固有結構的轉變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當中,從中央一級到縣一級皆屬于朝廷直接管轄的系統,到了縣以下的鄉村則不再由朝廷管治,而是由以地主、鄉紳為代表的鄉村精英按照儒家倫理道德秩序來負責鄉村社會的治理,即所謂“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1]。在儒家建立的血脈親情、長幼尊卑等一套完整的道德要求和行為準則之下,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雖不受中央集權的朝廷直接管轄,卻也經由鄉村內部傳統的行為規范形成了穩定存在并延續的生活秩序,成為傳統中國社會秩序超穩定結構的組成部分。然而,隨著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的強勢入侵,中國社會被迫進入現代化的進程,開啟了由“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專制社會向民主法制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及人民由臣民轉向公民的歷史變遷,并與相應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轉變”[2]。社會的轉型將建立國家統一、民族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作為目的,鄉村世界則面臨著如何完成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如何融入現代民族國家的宏觀建設等問題。
自民國以后,國家的政治體制雖然發生變化,但由于小農經濟的落后,鄉村社會仍受到傳統禮法和儒家思想的影響,權力主體并未產生較大改變。在鄉村社會的外部,戰爭與革命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對其進行著沖擊,西方的現代理念也開始進入鄉村。而與外部的沖擊同時發生的是鄉村內部掌握文化優勢的傳統鄉紳的影響力逐漸減弱,而新興地主和土豪劣紳開始崛起,他們借宗族的威望和自身的地位欺壓剝削著農民,“引路綁票,講價贖人,又做巫婆又做鬼,兩頭出面裝好人”[3],同時還利用長老統治及其教化權力剝奪家族結構式社會之外的人們的話語權,教訓外來者:“你們這些外路人實在沒有規矩!來了兩三輩子還不服教化!”[4]由于鄉村固有的封閉性和農民固有的保守性,他們難以憑自身的力量與土豪劣紳抗衡,大多只能維持一種無所適從的狀態。面對農民的無力反抗,土豪劣紳更是完全將農民作為自身盈利的工具,鄉村內部的階級矛盾日益加劇,鄉村社會的傳統內在秩序也逐漸瓦解。
面對外部環境的劇烈動蕩和鄉村社會的失序,新生政權和革命力量的介入對鄉村內部秩序的重組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趙樹理的小說當中,新生政權的引導使農民們團結起來,開始擁有了屬于自己的話語權,生活狀態逐漸變得正常,鄉間秩序得以重塑。在《三里灣》《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等小說中,個人的力量十分渺小,李有才被惡霸驅逐出外,宋秉穎也被逼迫遠離家鄉,而“只有多數的正派人都被發動起來、組織起來,都有了民主權利,有了組織力量,那才能有效”[5]。于是在趙樹理的小說中農民們紛紛以集體的面貌出現,李有才以自己的快板才能團結起一群不忍受壓的年輕人,在自己的土窯中聚集起鄉村領域的諸多個體。他們在遭遇欺壓和剝削時團結在一起對霸權予以質問和反抗,表現出集體力量的威嚴,初步顯現出鄉村現代化組織的形式。并且,這樣的集體并非烏合之眾式的群體,而是有了相當的反抗精神和一定獨立意識的群體,他們以自己的視角觀察審視著外在世界。
針對整合個體這一問題,趙樹理在他的小說當中給出了兩種規劃方案。在《李家莊的變遷》中,共產黨員小常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李家莊中發動群眾與強大的封建勢力和地主所建的犧盟會作斗爭;《李有才板話》里的老楊同志也主動了解地主掌權的情況,在假模范村的檢查工作中對鄉村的政治予以糾偏。這類具有清廉品質的黨員干部群體通過參與鄉村治理,為農民爭取利益。與此相對,另一種解決方案則是在鄉村內部選拔人才,在農民當中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干部,使之成為獨屬于鄉村的管理人才。在《三里灣》中,王金生作為土生土長的鄉人,能在國家的培養之下敏銳地發現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從大局的層面去思考,教育鄉村中的落后分子,堅定地帶領群眾由無知走向覺醒,由力量微薄的個體團結為堅強有力的集體。
傳統的中國鄉村既屬于血緣共同體,也是基于地緣關系的共同體,當傳統的血地關系面臨挑戰時,趙樹理在《三里灣》中探索著社會主義理念如何在鄉村進一步落實,尋求在鄉村建立一種精神共同體的可能。他將三里灣視為整體,把鄉村內部的諸多元素打亂重組,由封建的大家庭重建為進步的小家庭,在瓦解與重建當中生成新的內在機制,對鄉村共同體進行重塑。《三里灣》這樣一個敘述舊世界的滅亡和新世界的誕生、講述落后紛亂的鄉村社會更迭為理想社會的故事,正如陳順馨所說,是“通過虛構的革命歷史小說和反映一個大時代到來的社會建設小說……讓一個新的、屬于未來的‘想象的’社群或國度能夠呈現在讀者面前,發揮進一步的想象效果”[6]。趙樹理在把握時代主旋律的同時結合鄉村的現實狀況,在小說當中清晰地描繪了一個雖仍具傳統色彩但也顯示出現代風貌的鄉村社會,彰顯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獨特氣象。
二、農民主體性的萌發與鄉村權力秩序的重建
農村和農民是趙樹理筆下最主要的兩個書寫對象,農村在由舊向新變化,農民也在隨之不斷領悟自身境遇、了解社會現狀而逐漸成長。在小說《有個人》中,主人公宋秉穎雖勤勉勞作,忍饑挨餓,絲毫不敢對村長做出反抗,最后還是被逼到離開家人和故鄉的境地。他雖對自己的命運做出了反省,卻仍未在行動上對自己遭遇的不公進行反抗。而趙樹理后來的作品《福貴》中,主人公福貴不止停留在思考自身悲劇這一步上,而是在新政權的統治之下勇敢把悲劇的來源歸屬到剝削自身的地主之上,并成為鄉村社會的新人。由此觀之,只有在意識到自己可以為自己發聲,改變現有的生活狀態的情況下,農民才開始敢于為自身辯護,其主體性才能萌發。
鄉村秩序的構建與農民對自身命運的掌控密不可分。革命政權若要重構鄉村秩序,就必須把具有主體性的農民作為依賴的對象。只有具備精神上的開闊與樂觀,農民們才能擁有投身于鄉村秩序建設的動力,進而把握和改變自己的人生。在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中,小二黑敢于反抗,堅決掌握自己的命運,展現了強烈的主體性。《登記》中的艾艾同樣堅守婚姻自主權,堅決選擇與戀人小晚結婚,體現了她的獨立和堅定。在構建農村社會新秩序的過程中,培養農民對農村新秩序的深厚情感認同不可或缺,激發他們參與秩序構建的自主意識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首位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與農民緊密相連、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作家,趙樹理在作品中展現出農民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和地位,也表現出農民對自己命運的思考和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熱情。
同時,趙樹理小說中新一代農民相較于老一代農民還表現出更為顯著的主體性意識的提升。老一代農民常常在家庭內部全方位展露他們的家長權威,而在面對外部世界時,他們又會表現出過分順從、膽小謹慎的特點。這種陳舊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使得農民群體在某種程度上顯得缺乏自我意識。他們習慣于封建統治,將生活中的種種境遇視為命運的安排,認為自己無法改變既往的現實和已定的命運,只能寄希望于“清官老爺”或“菩薩下凡”式的外部力量的出現。《李有才板話》中的老秦就是這類形象的典型之一,面對壓榨自己的惡霸勢力,他們只能表現出卑微的服從,缺乏反抗的勇氣。與之相比,新一代農民不再呈現出這種軟弱無能的愚眾面貌,而是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展現了創造歷史的主動性。他們不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參與者,更是推動鄉村變革的重要力量。這些鄉村新人的“新”,體現在他們為鄉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現了敢于創新、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如《三里灣》中描繪的進步女性王玉梅、范靈芝等,她們勇敢追求進步,成為鄉村變革的積極推動者;《三里灣》中的王玉生等人物,善于團結各方力量,為鄉村發展付出艱辛努力;還有《套不住的手》中的陳秉正、《實干家潘永福》中的潘永福等形象,他們以勤勞的雙手和不懈的努力,表現著鄉村勞動人民的堅韌和拼搏精神。
趙樹理深刻認識到青年在重塑鄉村秩序中的核心地位。通過文學創作,他將政策引導和集體關懷下的新生青年群體塑造為推動鄉村建設、重塑鄉村秩序的生力軍。他們積極投身于鄉村建設之中,為鄉村的繁榮發展而不懈努力。在趙樹理的小說中,這代掌握知識的青年農民群體身上既散發著飽滿激昂的革命熱情,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自己的個人欲望。在《〈三里灣〉寫作前后》一文中,趙樹理明確表達了自己對知識青年的看法:“這些人,不一定生在貧農家庭,自己對農業生產工作也很生疏,然而他們有不產生于農村的普通的科學、文化知識(例如中國、世界、歷史、社會、科學等觀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氣,很少有、甚而沒有一般農民傳統的缺點。一個由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組織逐漸向著完全社會主義化方面發展,對這樣的新生力量是應該重視的——因為社會主義事業的任何部門都是需要一般知識的。”[7]趙樹理相信,新一代鄉村青年應具備勤勉刻苦的素質,同時還應堅守實事求是的原則,將個人所學的文化知識與鄉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發展的統一。在小說中如是,在生活中亦如是。趙樹理不斷鼓勵他的女兒趙廣建到基層去實踐,并在《愿你決心做一個勞動者》一信中表達了他對女兒的深情教誨,以及作為老一代作家對知識青年投身鄉村建設的熱切期望。
趙樹理的作品不僅是對鄉村變遷的細致刻畫,更包含著對舊有鄉村秩序弊病的深刻剖析。他站在人文主義的立場上深入探討了封建勢力對農民的壓迫,并努力挖掘農民內在的主體性和發展潛力。在趙樹理筆下,農民的精神覺醒與成長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他敏銳地捕捉到農民在生存狀態和精神需求上的變化,展現出他們在長時間的積累與努力下逐漸覺醒、擺脫封建思想束縛的歷程。同時,趙樹理還關注到了鄉村社會外部的新興力量,認為只有整個鄉村社會的共同進步,才能真正實現鄉村的繁榮與和諧。趙樹理的小說語言平實易懂,人物形象豐富多彩。他從民間視角出發,以樸實的語言揭示鄉村秩序重建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這種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使得他的作品更加貼近生活、貼近人民,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真實而生動的鄉村世界。
三、趙樹理筆下鄉村書寫的現代性內涵
傳統的鄉村社會中長期存在著無序的狀態,在革命力量的引領下,鄉村的個體村民才開始被整合成為有覺悟的群體。他們積極參與斗爭與反抗,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團結與力量。這一重大的歷史性變革,象征著鄉村社會從無序到有序的深刻轉型。在有序的社會環境下,趙樹理深刻認識到鄉村社會的熟人關系與新型社會秩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理想的鄉村共同體圖景。為了維護鄉村社會公共秩序的平衡,趙樹理在小說中采納了“私序”的社會規范,結合鄉村共同體的精神引入了一系列新理念。在《三里灣》的第25章中,畫家畫出了中國農村發展的三張畫:第一張畫作描繪了三里灣在合作化初期的景象,展現其原始風貌;第二張畫作則展示了三里灣在水渠修建完成后的新面貌,突顯了集體力量的偉大;第三張畫作最為引人注目——它所呈現的是一種在當時條件下可能實現的“準共產主義”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不僅體現了高度的集體協作精神,也預示了未來社會發展的可能方向。這樣的書寫無疑“蘊含著鮮明的鄉村共同體意識,這一現代群體觀是趙樹理的敘事動因之一,這種看似傳統又超越傳統的自在寫法,一方面沖破了傳統的敘事方式,同時也給‘五四’以來西方為中心的現代觀帶來了一種新的思考維度”[8]。
趙樹理所構想的鄉村社會以集體為核心,與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相一致,描繪出一種切近而實際的共產主義愿景。與之相應,趙樹理的敘事手法也獨具匠心。他巧妙地采用了獨特的鄉村內部視角進行創作,主要由一位或數位敘述者來講述故事。敘述者與故事中的人物之間建立了一種特定的關系,從而形成了獨特的敘事視角。這種手法不僅豐富了故事的層次和內涵,也使得讀者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鄉村生活的真實面貌。并且,這種敘事視角始終扎根于鄉村內部,與《暴風驟雨》中黨代表的外部視角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自我“改造”的知識分子外部視角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趙樹理的早期作品中,歐化小說的影響還很明顯,情節構造偏向于復雜,而后期的作品卻越來越彰顯出鮮明的農民化創作風格。這種創作風格的轉變不僅是他個人藝術追求的結果,也是時代變遷的反映,深層次地揭示了作者思維方式的變革——由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逐漸轉向農民的思維方式。這一轉變體現了趙樹理對農民生活的深入理解和關注,也展示了他作為一位文學家對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敏銳洞察。趙樹理小說的敘事視角獨特,既未受外界審視目光的影響,也未采用內部自省的方式。盡管敘述者或隱含作者具備全知的能力,但他們只通過角色的有限視角,冷靜地觀察并敘述事件的演變。由于故事中的角色生活在鄉村環境中,缺乏現代個體的主體性和獨立精神,因此在摒棄了古典全知視角的敘述者后,小說并未對農村變遷進行直接評論。事件的發展和解決、農村的變革與重組,均源于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這種特定的敘事手法,對小說敘事與民族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得鄉村成了一個獨具特色且富有深刻內涵的空間,展現了作者對理想鄉村生活形態的憧憬。
趙樹理因其對鄉村立場的堅守和熱愛被一些啟蒙文學家貼上了“不現代”的標簽。又因其語言風格通俗易懂,部分“現代”的五四式批評家也對其頗有微詞,將之與張愛玲和“鴛鴦蝴蝶派”歸為一類。然而,日本學者竹內好卻從趙樹理的“古”和“俗”中洞察到了他的超越性:“我認為,把現代文學的完成和人民文學機械地對立起來,承認二者的絕對隔閡;同把人民文學與現代文學機械地結合起來,認為后者是前者單純的延長,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因為現代文學和人民文學之間有一種媒介關系。更明確地說,一種是茅盾的文學,一種是趙樹理文學。在趙樹理的文學中,既包含了現代文學,同時又超越了現代文學。”[9]賀桂梅也認為,趙樹理的作品是“超越了西方現代性的‘另類’的現代文學”[10]。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當中,鄉村一直是一個難以書寫的對象。許多作家和學者自詡為人類前途的深刻思考者,但實際上,他們的探討往往淪為文字游戲,無法為弱者發聲。而趙樹理的寫作卻展現出與眾不同的特質,他的文字始終扎根于鄉村的土壤,以真實的觀察和深刻的思考為基石,而非空洞的抽象或自我滿足。
在《三里灣》等作品中,趙樹理展現出對鄉村社會的細致洞察與深入關懷。他將視線聚焦于鄉村與農民的生存和發展之上,以實際行動為文學創作界樹立了體察式思考農村農民的典范,表現出對全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反思與洞見。他基于深切的理解和尊重為弱勢群體發聲,“是在創造典型的同時,還原于全體的意志。這并非從一般的事物中找出個別的事物,而是讓個別的事物原封不動地以其本來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規律性的事物之中……因此,雖稱之為還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發點上,而是回到比原來的基點更高的新的起點上去”[9]。他所描繪的鄉村進化體現了個體與集體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理想鄉村社會中“遠”與“近”的辯證張力。這種辯證關系不僅表現于農民個體和鄉村集體之間的互動,也體現在現代作家與其所代言的群體之間的復雜聯系。趙樹理的社會地位屬于精英階層,卻始終把鄉村和農民的福祉置于首要位置,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對鄉村秩序重建的構想,對塑造未來幾十年乃至幾百年中國文化的發展與走向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趙樹理對鄉村世界的構想都未得到啟蒙知識分子的接納。因為在具有文化想象和社會實踐需求的啟蒙知識分子看來,啟蒙應當以城市為主體,針對具備一定公民素養的民眾而展開。這也自然而然地導致農民和農村難以成為知識分子們啟蒙構想的出發點,趙樹理的鄉村共同體理想難以被理解。但從現實意義上考量,趙樹理作品中農民個體的啟蒙和對鄉村秩序及其內部組織的改造雖仍屬于一種難以自生的輸入型機制,但“從趙樹理開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才第一次出現了活潑、朗健、正面的中國農民形象,中國最底層的民眾才真正成為書寫的主體對象”[11]。并且,趙樹理小說中的語言書寫明顯超出了現代文學舊有的基本經驗,在鄉村共同體的想象中進行了具有前瞻性的自覺創造,呈現出開放性的特點。趙樹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善于發掘其優點,摒棄其缺點,他的思想在當時雖未得到廣泛的認可,卻在實際意義上創建出一套更加貼近中國實際的鄉村理想社會體系,表達了自己對鄉村秩序重建的深切期望。
參考文獻
[1] 秦暉.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2] 鄭佳明.中國社會轉型與價值變遷[J].清華大學學報,2010(1).
[3] 趙樹理.小二黑結婚[A]//董大中.趙樹理全集(1)[C].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
[4] 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A]//董大中.趙樹理全集(1)[C].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
[5] 趙樹理.發動貧雇要靠民主[A]//董大中.趙樹理全集(3)[C].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
[6] 陳順馨.1962:夾縫中的生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7] 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A]//董大中.趙樹理全集(4)[C].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
[8] 劉旭.趙樹理文學的敘事模式研究[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
[9] 竹內好.新穎的趙樹理的文學[A]//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外國學者論趙樹理[C].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10] 賀桂梅.趙樹理文學的現代性問題[A]//唐小兵.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1] 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溫瑞鑫,湖北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