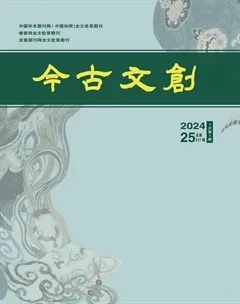明代戲曲“教化論” 中的載道與娛人
2024-07-25 00:00:00黃文欣
今古文創
2024年25期
【摘要】明代文人在戲曲中寄寓現實批判與倫理教化,這類創作提出利用戲曲進行教化的理論,如高明《琵琶記》中“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及丘濬《五倫全備記》中“備他時世曲,寓我圣賢言”等。而明代戲曲“教化論”的強調,是否降低了戲曲的藝術性與娛樂性?本文以《五倫全備記》為例,試論證戲曲“教化論”實際在于客觀上提升了戲曲的文學地位。
【關鍵詞】明代戲曲;《五倫全備記》;教化論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5-009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5.029
中國戲曲發端于民間歌舞、說唱和滑稽戲,在民間文化土壤中逐漸成長、分化。王國維《戲曲考原》中以“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對“戲曲”進行了界定,1912年又在《宋元戲曲考》中進一步以“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戲劇之意義始全”完善了這一定義。這里將戲劇與戲曲的概念劃分清楚,即戲劇是“演故事”,戲曲則是“以歌舞演故事”。
戲曲中作為故事載體的“戲”包含著“虛假不實”“謔樂游戲”的屬性觀念,其精神與儒家為代表的崇實尚理的正統文化相悖。因此,自原始歌舞中的戲曲萌芽,到宋金時期形成較為完整的戲曲藝術,戲曲一直以非正統的“俗樂”存在,受到正統文化的壓抑,基本上沒有文人士大夫等精英階層參與創作。及至金元雜劇,文人精英階層因現實原因介入創作,開始了對“戲”的傳統與現實的重新審視,從而賦予“戲”以正統文化價值和功能。
文人士大夫出于主體情感體驗和欲望的表達,利用戲曲發憤抒情,表達對社會現實的批判。……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