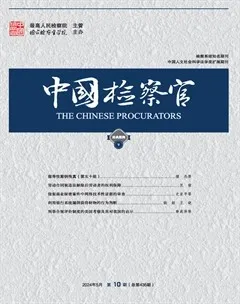涉區塊鏈數字藏品案件罪與非罪辨析
張云東 熊輝
摘 要: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涉區塊鏈數字藏品新型案件不斷出現。此類新型案件可能涉及詐騙罪、非法經營罪等罪名。審查認定時,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剝絲抽繭,在把握可能涉及罪名犯罪構成要件的基礎上,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結合嫌疑人供述、數字藏品是否真實、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的區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是否違反國家規定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從而準確認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
關鍵詞:區塊鏈 數字藏品 罪與非罪
一、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至8月期間,趙某伙同他人成立某空間技術公司,該公司取得EDI許可證(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ICP經營許可證(互聯網信息服務業經營許可證)以及公安機關網絡備案,開發一款名為“某空間”的手機APP,在APP上銷售數字藏品[1],招募客服人員建立微信、QQ群等進行客戶推廣,客戶在APP上注冊后,通過微信、支付寶、銀行卡轉賬等方式進行充值,充值之后賬戶上顯示余額,通過余額在APP上選購數字藏品,每份數字藏品售價1-99元不等。趙某在銷售數字藏品過程中,通過虛假的廣告推廣宣傳,夸大數字藏品收藏價值,發布相關的回購公告、進行虛假空投(空投就是指將數字藏品免費贈送給客戶)、開展抽獎活動并偽造抽獎人數,開通二級寄售市場(二級寄售市場系app內用于用戶與用戶之間交易平臺),制造虛假繁榮交易假象,引誘被害人購買數字藏品,“騙取”被害人資金463萬余元,后趙某將該二級寄售市場關閉,并將“某空間”技術公司連同公司APP等一同賣給另一家公司,關閉所有推廣客戶的微信群、QQ群,將錢款提出轉賬至個人賬戶,后因被害人報警案發,案發后,趙某并未將錢款退還被害人。
2023年6月18日,公安機關以趙某涉嫌詐騙罪向檢察機關提請批準逮捕。
二、分歧意見
針對本文案例的定性,第一種意見認為趙某構成詐騙罪。趙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開發“某空間”手機APP,進行虛假營銷及廣告宣傳、承諾回購、開放二級交易市場、進行虛假空投、開展抽獎活動、偽造抽獎人數等方式,營造二級市場虛假繁榮假象,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購買數字藏品進而遭受財產損失。因此,趙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趙某構成非法經營罪。趙某違反國家規定,未經許可非法經營數字藏品業務,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應該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三種意見認為趙某不構成詐騙罪、非法經營罪。趙某雖然在銷售數字藏品過程中使用虛假宣傳、虛假營銷等欺騙手段,但是趙某的上述行為無法直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排除其存在民事欺詐的合理懷疑。被害人是基于對數字藏品未來增值預期的考量而自愿購買數字藏品,并非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物進而遭受財產損失。數字藏品的銷售并未有相關法律規定屬于特許經營的范圍。因此,在數字藏品法律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將銷售數字藏品的行為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于法無據。
二、評析意見
筆者贊成第三種意見。趙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非法經營罪。從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角度分析,構成詐騙罪應同時具備以下四個要素: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實施了詐騙行為、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物、行為人取得財物與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物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本案中,趙某所實施的客觀行為無法直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實施的欺詐行為非刑法意義上的詐騙行為,而是一種民事欺詐行為,被害人并非是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的財物。趙某經營數字藏品的行為并未“違反國家規定”,也不屬于《刑法》第225條第1款第4項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具體分述如下:
(一)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非法占有目的是詐騙罪的首要判斷要素。構成詐騙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實踐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有兩種情形。一是行為人對非法占有目的供認不諱。例如,行為人供述自己就是為了想要占有被害人的錢款而實施的詐騙行為。這種情況一般比較少見,即便是出現這種行為人對自己非法占有目的完全供認的情況下,還需要結合其他客觀證據對行為人供述的真實性進行印證。二是行為人自己對非法占有目的拒不供述的情形,即提出許多辯解。這種情形下,應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及在案客觀證據進行綜合判斷,允許采用推定方式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既要》(以下簡稱《審理金融犯罪紀要》)明確了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七種情形。[2]司法實踐中,如果行為人采取詐騙方式獲取資金后,不能返還,并且具有上述七種行為之一的,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允許行為人提出反證。在行為人提出辯解且辯解合理,有其他證據能夠印證行為人辯解的情況下,則無法推定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2.本案趙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趙某對于自己構成詐騙罪拒不認罪,辯解自己屬于合法經營,是一種市場行為。根據上文論述,本案的情形屬于司法實踐中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第二種情形,即行為人對于自己非法占有目的拒不供認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需要結合《審理金融犯罪紀要》中規定的非法占有目的推定情形、行為人辯解、在案客觀證據進行綜合認定,司法實踐中,主要圍繞行為人取得被害人財物是否具有非法性、在取得被害人財物的過程中是否具有詐騙行為、事后表現等方面進行實質性審查認定。
(1)本案從行為人取得財物是否具有非法性來看,行為人取得財物的行為不具有非法性。本案中,趙某通過設立公司、開發銷售數字藏品的APP銷售數字藏品。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數字藏品國內市場的情況,國家是允許銷售數字藏品的,且國內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數字藏品市場。趙某成立的公司開發APP銷售數字藏品,取得EDI許可證(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ICP經營許可證(互聯網信息服務業經營許可證)以及公安機關網絡備案,屬于合法經營,其通過向市場主體售賣數字藏品獲取對方錢款,屬于一種合法的市場交易行為,其取得財物具有對價性,不具有非法性。
(2)本案從趙某在取得被害人財物過程中是否具有詐騙行為來看,不可否認,趙某取得被害人財物過程中存在一定的欺詐行為,但是該欺詐行為并不能推定趙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排除合理懷疑。一是趙某銷售的數字藏品具有真實性。從數字藏品的定義來看,數字藏品是將現實中的藝術品或者作品等數字化,并將其在區塊鏈上進行上鏈,具有唯一性、可驗證、可流通等特性。數字藏品只有上區塊鏈才具有唯一性。判斷數字藏品是否真實的依據主要有兩個方面,該數字藏品是否上鏈和該數字藏品是否取得原作品的版權授權。數字藏品區塊鏈一般有公鏈和聯盟鏈。公鏈主要是國外鏈,聯盟鏈主要是國內鏈。公鏈和聯盟鏈均屬于上鏈。在審查判斷數字藏品是否上鏈時,應審查是否在公鏈或聯盟鏈上鏈,如果在任意一個上鏈,即為上鏈的數字藏品,具有唯一性、真實性、可驗證性、可交易性。本案中,趙某銷售的數字藏品均在區塊鏈上進行上鏈,以永久儲存該圖片,且獲得鏈上的唯一標識和合約,能夠在區塊鏈上查詢到圖片,并且上鏈后圖片會有一個通證編號(Token ID),通過通證編號可以進行驗證。此外,本案中數字藏品的原版權作品為劇本殺圖片以及找設計師設計的圖片,均支付了版權使用費,數字藏品原始圖片來源具有合法性,也進一步證實數字藏品的真實性。二是從趙某的客觀行為分析,雖然趙某實施了虛假廣告、回購公告、虛假空投(空投就是指將數字藏品免費贈送給客戶)、偽造抽獎人數,開通二級寄售市場后關閉等行為,上述行為存在一定的欺詐性,但是趙某銷售的數字藏品系真實的,被害人對于數字藏品的真實性是有認識的,也能夠認識到自己購買的是數字藏品,并沒有陷入到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物。本案中,趙某雖然實施了上述行為,但僅以上述客觀行為認定趙某構成詐騙罪,則將違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造成客觀歸罪。此外,也不能排除上述行為屬于民事欺詐的范疇,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的結論。三是趙某并沒有承諾高價回收數字藏品。在數字藏品的銷售中,如果在案證據能夠證實行為人在銷售數字藏品時,行為人在銷售平臺發布以后高價回收數字藏品的許諾,而被害人正是基于該許諾才購買的數字藏品,在售出后行為人攜款潛逃,則可能構成詐騙罪。數字藏品本身只是一個鏈上的數字憑證,其本身的原作品并非具有價值,也可能一文不值,在行為人不回購的情況下,被害人無法將其轉手賣出去,對被害人來講,則遭受了損失。本案中,趙某雖然發布過回購公告,但是其回購公告并未承諾一定會高價回購數字藏品,并且回購公告中明確了回購需要滿足的條件,趙某也確實回購過一部分其銷售出去的數字藏品。
(3)本案從趙某事后表現來看,趙某雖然事后將公司賣掉,關閉客戶微信群、QQ群,并將錢款提出轉至個人賬戶,但上述行為并不能必然推導出趙某的行為符合《審理金融犯罪紀要》中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七種情形。趙某將公司賣掉,該行為屬于一種合法的市場行為,其將公司賣給另一家公司,將APP平臺轉移到另外一家公司,并且支付給對方公司相應費用,簽署相關協議,由對方公司負責對原平臺進行運營維護,趙某的上述行為有相應的客觀證據能夠證實,其將公司賣掉是通過合法途徑進行,且與對方公司有約定,原APP的運行維護由對方公司繼續運行。并且在案證據證實趙某并未逃跑。從趙某的資金情況來看,其銷售數字藏品所得,大部分費用用于技術開發、圖片版權、服務器數據庫、工資等費用開支,并沒有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行為,也沒有肆意揮霍資金的行為,也沒有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等行為。
(二)準確界定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的界限
1.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的區別。在司法實踐中,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行為很容易混淆,準確認定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一般可從欺騙內容、欺騙程度以及欺騙結果三個方面進行界定。一是欺騙內容方面。民事欺詐是部分或個別事實的欺騙,而詐騙犯罪則是全部事實的欺騙。二是欺騙程度方面。詐騙犯罪是采用欺騙手段使得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并交付財物,而民事欺詐雖然采用欺騙手段,但是沒有達到使對方無對價交付財物的程度。三是欺騙結果。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目的,這種利益是通過民事行為實現,詐騙犯罪中,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謀取的不是民事行為的對價利益,而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物。[3]
2.本案中趙某的行為屬于民事欺詐而非詐騙犯罪。從欺騙的內容來看,趙某是在銷售數字藏品的過程中采用的虛假宣傳夸大數字藏品收藏價值,在進行空投時進行虛假空投,開放二級交易市場、篡改二級交易市場數據、進行虛假空投、開展抽獎活動,偽造抽獎人數等方式,營造二級市場虛假繁榮假象,其主要目的在于吸引消費者來購買其數字藏品,是銷售前的一種民事欺詐的營銷手段,但是銷售的商品是真實的,屬于個別或部分事實的欺騙,而非全部事實或整體的欺騙。從欺騙的程度來看,趙某的欺騙行為并沒有達到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進而交付財物的程度。被害人認識到趙某銷售的是數字藏品,屬于其購買的數字藏品有充分的認識,其也是基于數字藏品未來能夠升值漲價的預期而購買的,只是對于購買數字藏品的風險缺乏必要的認識。從欺騙的結果來看,趙某雖然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但是是通過向消費者支付對價的方式,即通過民事行為和途徑進行的,不是無對價的獲取對方的財物。
(三)趙某的行為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1.趙某的行為并未“違反國家規定”。《刑法》第225條規定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之一是“違反國家規定”。《刑法》第96條對“違反國家規定”進行了明確規定。經對數字藏品相關規范性文件梳理,主要有中央層面的《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數字藏品應用參考》,其他則為地方性或行業性規范。上述規范文件均不屬于《刑法》第96條“國家規定”的范疇。一是涉數字藏品國家規定空白,則趙某銷售數字藏品的行為無從談起“違反國家規定”。二是即便趙某銷售數字藏品的行為違反上述數字藏品規范性文件,因上述規范性文件不屬于《刑法》第96條規定的范疇,趙某的行為也并不“違反國家規定”。
2.趙某的行為不屬于“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刑法》第225條非法經營罪第1款第4項是兜底條款,規定了“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筆者認為對于《刑法》第225條第1款第4項的規定應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對市場經濟秩序這一法益的破壞程度。非法經營罪規定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節,應當首先考慮對市場經濟秩序這一法益是否造成嚴重破壞。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趙某經營的數字藏品銷售業務,屬于數字經濟的重要領域,也是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并未對市場經濟造成破壞,對于拓展市場經濟新型領域的范圍起到積極作用,有利于市場經濟繁榮發展。二是經營行為有無實質的違法犯罪行為及其后果。目前數字藏品市場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國家也采取鼓勵發展數字經濟的政策,在相關法律規定不完善的情況下,鼓勵數字藏品相關行業進行嘗試和探索,趙某經營的數字藏品均為真實的數字藏品,均在區塊鏈上鏈,其經營數字藏品的行為經營行為無實質的違法犯罪行為及其后果。目前國內也有許多公司企業經營數字藏品業務,并且許多數字藏品頭部公司也開通二級市場供用戶與用戶之間交易。綜上,趙某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最終,檢察機關,上述交易并未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對趙某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