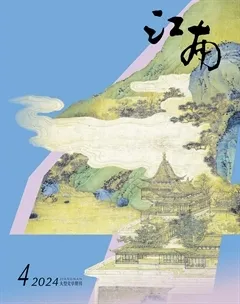無月之夜
2024-07-03 00:00:00吳文君
江南
2024年4期
一下午她都坐在旅館里。窗外就是沙灘,和她只隔了條小馬路。游人被棧道帶到這兒,穿過沙灘,變成越來越細小的黑點,在海岸邊來回移動。一棵樹拉長了枝葉,就像跳著沒有一個重復動作的舞蹈。正是這棵多少有點遮擋視線的樹讓她發覺風在變大,遠處的礁石擊起一層層白浪,之前興致勃勃爬到上面拍照的人不知什么時候已經消失了,路上一個游人都沒有了。云陰沉沉地壓在海面上方,隔著玻璃也能感到瑟瑟冷意。
她喝了暖壺里的剩茶,看了下時間。
四點。
也沒多久。一點不到住進來的。房間和手機訂單首頁顯示的一樣,白床,白床頭柜,床頭畫著海草、貝殼和魚。最好的當然還是這扇窗,從她坐下,就進入了既不想過去也不想將來連現在也一并消失的狀態。
連手機循環播放的大提琴曲都和這里這般渾然一體。
寂寞許久的路上又有兩個身影出現了。男人胸背寬闊,女人的長裙不時被風卷起露出白晳的小腿,腳后跟小小的粉粉的像兩顆櫻桃。
她看著他們,感覺著他們說話時的心不在焉,好像半小時前還在會議室里枯燥乏味地坐著,之后卻同時推開那扇門走了出來,渾身洋溢著一股自由自在的勁兒。即使漸漸小下去,小到只如兩根若即若離的火柴棍兒,仍有著奇異的黏性,讓她不肯舍棄地尾隨著他們走近礁石。女火柴棍兒找到平坦的地方坐下,男火柴棍兒則保持著微微勾頭的站姿,她看了他們有二十多分鐘,可還是讓他們不動聲色地消失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