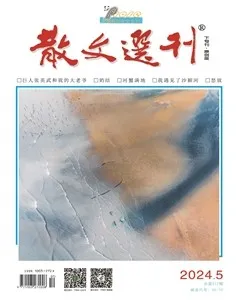這地上,河流縱橫
泥馬度
那些天然神造的河流,都淤積了,而得要給水一個出路。扒河成了秋收以后,整個冬天的勞動。卷著鋪蓋,堆起糧草,馬車拖拉機,一車車拉往扒河工地。
大路小路上,勞力坐在高高的糧草頂上,看得就頭暈。總有車翻在半路上,哪一年不死人啊。
冰封的平地挖出河流來。鐵锨一锨锨往下挖,一車一車往上推。河上看著河下的人就像螞蟻似的。萬物冬眠,只有人在不能再低的地方,靠著勞動取暖。
在冬天,挖到水,挖到流動。寒冷流成汗水的河。挖水掘汗成冰。一年年的冬天就是這樣過來的。無論多大的雪和雨,都沒有停止過。寸土傷人啊,河口,可是個鬼門關。
1958 年秋冬,祖父在河工地病了倆月,臥在工棚里,還有碗飯吃。而沒去扒河的人,在家鄉連個稀飯影子都照不到自己腫脹的臉。祖父被車拉回來時,兩腳生蛆,皮包著凍骨,鮮血還在動,眼在動。春天到了,有樹葉草根什么的了,活了過來。
而大老爺卻失蹤了,再也沒有回來,說是從河工地逃到蘇州去了。新鮮的水在動,從雙手里新生出來的河流,多么像打通的坑,坑的串連啊。
我沒有扒過河,但要給錢。我妹妹沒有去過那里也要給糧。上了大學,跳了龍門,就不挖河,不去工地了。
2000 年,我們村里有人在河底挖出一只壇子。人群騷動,壇口還沒揭開,就被督工的支書下到河底,拿走了。說是上繳了,壇里到底有什么,叫屈的人傳說是元寶,是寶玉。總之壇子沒露著個準確的風聲。岸上的人啊,看底下的勞動,就像密集的工蟻的蠕動。岸在升高,勞苦在一寸一尺地降低。把大地掏空,無數次上來下去,像無數只蝸牛蚯蚓把土方拉上岸。土平堆成大堰,也就是此岸和彼岸了。
東挖一條,西挖一道,按照圖紙勞動。挖出水的網絡,把洪水的病毒刪除。村莊一代代青春,把一年年的血汗發送到命定的遠方的信箱。多少糧食如泥牛入海。這些河啊溝的,都通向大海。
在1988 年的酷夏,說是天上什么黑子爆炸,熱得不能再熱了。母親和三妹去河邊洗臉,母親滑掉進河里,我聞聲瘋跑跳河,把她撈上岸,就埋在河岸的大堰下。那些土還是新從地下翻挖上來的呀。人工河,永遠淌走了我的秀發的母親。
大堰上,栽著白楊,長著高高低低的神奇的眼睛。這永不合眼的張望,日日夜夜,多么想讓人淚流滿臉。
河里的流動,白楊樹漸漸看不清楚了。河里淌來城市的黑水,散發連樹木都熏黃的味道。
大地里的河流,流動著工業和城鎮最黑暗的部分。黑夜的面目滔滔地流入村莊的生活,改變著村莊的味道。多少年一船船的公糧和稅費倒溯向上游,淌下來的,是污穢。光明在上頭,黑暗在下頭。河流像一張郵票,郵走太多的好東西。相信吧,這古老不變的地上,遲早也會傳來鴻雁的消息。
現在河流真的在變清了,也沒有任何的負擔。小漁船一身輕松。大堰上的白楊樹,又睜開美麗的眼睛,再也沒有人扒河了。冬天的河役早早地結束了。
大地和它的河流又恢復往常的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