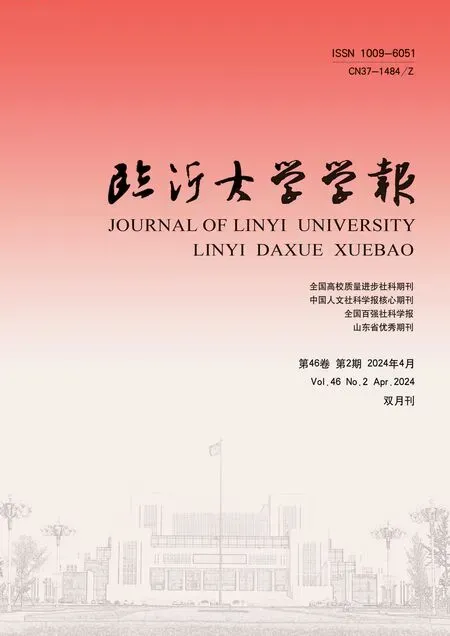阿多諾論“藝術介入”的實踐品格
2024-06-12 18:39:18劉秀哲
臨沂大學學報
2024年2期
劉秀哲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19 世紀初,黑格爾提出了“藝術終結論”,此后該命題被丹托、卡斯比特、漢斯·貝爾廷等理論家不斷地演繹與重構,時至今日仍然方興未艾。針對此種情形,我們不禁要問:藝術真的已經終結了嗎?或者何種藝術已經終結了?終結之后的藝術又將走向何方?面對諸如此類的問題,理論家們雖然紛紛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卻又莫衷一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薩特為代表的說教式、宣傳式的藝術必然走向了終結。“20 世紀上半葉出現了數百種運動:立體主義、野獸派、建構主義、至上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抽象主義。每個運動都有自己的宣言”[1],每個運動都對異于自己的運動形成一種解構,介入藝術也概莫能外。
既然現代藝術對介入藝術的解構已不言而喻,但非介入或零介入的藝術真的可能存在嗎?眾所周知,無論是作為介入藝術早期形態的“傾向文學”,還是作為介入藝術余續的“參與藝術”,均在不同程度上消解著藝術的意義與價值。介入藝術果真能夠獨善其身嗎?顯然這是一個偽命題。二戰結束后,資本主義獲得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工具理性取代價值理性大行其道,文化工業逐步滲入并掌控了大眾的生活,成為宣傳意識形態的載體。此時,西方知識分子開始對啟蒙理性進行反思,對具有社會屬性的藝術進行反思。在全面行政化的社會體系下,藝術何為?是如薩特所言,作家應“完全地介入,絕對地自由”[2],還是如羅蘭·巴特所言,“寫作絕不是交流的工具,它也不是一條只有語言的意圖性在其上來來去去的敞開道路”[3]。……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18期)2024-06-07 22:40:49
文苑(2020年11期)2021-01-04 01:53:20
兒童繪本(2018年22期)2018-12-13 23:14:52
讀者·校園版(2018年13期)2018-06-19 06:20:12
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 16:58:59
讀者(2016年7期)2016-03-11 12:14:36
現代計算機(2016年12期)2016-02-28 18:35:29
發明與創新(2015年25期)2015-02-27 10:39:23
爆笑show(2014年10期)2014-12-18 22:27:48
中國衛生(2014年12期)2014-11-12 13: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