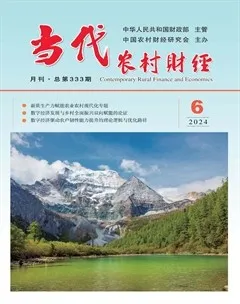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雙向賦能的論證
玉素甫·阿布來提 郭靜
摘要:2023中央工作會議中指出要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入全面發展階段。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的融合發展研究刻不容緩。本文以我國31省(市)為研究主體構建2010年—2022年的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的面板數據,運用修正耦合協調度模型和空間聯立方程模型探究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的耦合協調類型、時序演變趨勢以及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的空間交互效應。研究結論表明:在研究區域內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存在雙向賦能關系;在研究區域的鄰接區域內數字經濟發展單向賦能鄉村全面振興發展;鄉村全面振興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與提升未出現正向促進作用,即未實現雙向賦能。文章在根據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并綜合考慮現實情況為數字經濟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的雙向賦能提出四條政策性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 鄉村全面振興 修正耦合協調 空間交互效應
一、引言
202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鄉村振興進入全面發展階段。鄉村振興是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戰略。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城鄉發展協調,實現鄉村與城市的互補性,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17年G20峰會首次提出“數字經濟”一詞,隨著人們對科技的不斷依賴和數字化轉型的推動,以及2023年9月新質生產力的首次提出,數字資源成為新的經濟推動。我國的數字經濟在短時間內達到令人矚目的規模,發展數字經濟對鄉村全面振興具有不可小覷的推動力量。在數字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行業之間的融合和協同將成為關鍵。數字經濟的發展與農業的互相融合,通過數據共享和合作,實現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
現階段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關系論證大多集中于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單向驅動作用(張蘊萍等,2022和孟維福等,2023)而研究鄉村全面振興對數字經濟的賦能作用的研究較少,忽略兩者雙向影響關系研究可能導致研究結論的主觀偏差;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的耦合協調度的研究中,大多采用傳統的耦合協調模型(張旺和白永秀,2022),而傳統耦合協調模型在計算時會產生理解與計算誤差,對研究結論的真實性準確性產生一定的影響。如何將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相結合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而基于時空交互視角研究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水平也將為我國數字化發展和經濟由增速到提質的結合提供了思路與方向。因此,本文結合以往研究長處和考慮未涉及的交互關系基礎之上,對我國31省(市)層面的面板數據從時序演變趨勢和空間交互效應探究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是否是雙向賦能關系,意在貢獻邊際效應,為“數字經濟發展促進鄉村全面振興—鄉村全面振興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雙向賦能提供思路和建議。
二、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與指標體系的構建
文章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鄉村全面振興選為目標變量。基于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與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基礎與評價的全面性,綜合考慮對其發展水平的測度,參考王軍(2021)張挺(2018)等的研究方法構建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綜合指標評價體系,如表1。

為避免因其他變量對數字經濟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的影響偏差,選定影響數字經濟和鄉村振興的共同控制變量為:經濟發展水平(pgdp),以某省當年GDP與全國當年GDP比值表示;其中數字經濟的控制變量組為:政府支農干預度(gisa),以某省財政農業支出與GDP的比值表示;人口密度(den),以省人口數與省面積的比值表示;對外開放水平(ops),以某省當年的進出口貿易額與當年GDP比值表示;其中鄉村全面振興的控制變量組為:城鎮化水平(urbl),以當年省城鎮人口與總人口比值表示;人力資本水平(huml),以省高校在校人數與總人口的比值來表示;老齡財政負擔(fbe),以地方財政科學技術支出與地方財政教育支出之和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的比值表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文章選取2010年—2022年的31個省(市)的省級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有關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各省的統計年鑒、中經網數據庫;有關鄉村全面振興的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國泰安數據庫、EPS數據平臺等。由于港澳臺地區的數據獲取難度較大,文章不做研究。31個省(市)的數據中,其中西藏地區有關數字經濟的相關數據有缺失,缺失值已用Matlab軟件線性插值法補齊。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鄉村全面振興的測度綜合水平與得分進行權重的賦予與確定,基于準確性與客觀性的綜合考量,文章采用熵值法進行。
(三)修正的耦合協調模型與類型
由于常用的傳統耦合模型存在一定的主觀錯誤與計算誤差,因此文章參考王淑佳等(2021)對耦合協調度模型的誤區和修正后建立數字經濟—鄉村全面振興耦合協調度模型,如(1)(2)(3):

模型中的C表示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的耦合值,取值范圍是[0,1],越接近1,兩個系統耦合性越高;T表示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的綜合協調指數,αi為待定權重系數,文章參考張旺(2022)的方法,將兩者的權重系數都賦值為0.5;D表示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取值范圍[0,1],越接近1,兩者的耦合協調水平越高。文章仍然參考王淑佳(2021)的修正耦合協調模型中的方法,文章通過耦合協調度的取值范圍將耦合協調類型分為10個等級:0.0,0.1]為極度失調、(0.1,0.2]為嚴重失調、(0.2,0.3]為中度失調、(0.3,0.4]為輕度失調、(0.4,0.5]為瀕臨失調、(0.5, 0.6]為勉強協調、(0.6,0.7]為初級協調、(0.7,0.8]為中級協調、(0.8,0.9]為良好協調、(0.9,1.0]為優質協調。
(四)空間聯立方程模型
為驗證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鄉村全面振興水平是否存在雙向影響關系,文章參考張鵬和于偉(2019)基于地級市的數據對金融聚集和城市發展的研究,構建文章省級數據基礎上的空間聯立方程模型,如(4)(5):


公式(4)(5)表示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的空間方程式,其中dde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res表示鄉村全面振興指數、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w表示空間權重、α表示常數項、β和λ表示影響系數、η表示空間相關系數、X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方程的控制變量組、Y表示鄉村全面發展的控制變量組、ε和υ表示隨機擾動項。
三、時間演變格局分析
(一)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的發展水平分析
由于數字經濟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區域間受影響程度存在差異,因此文章參考潘方卉和陳淼(2024)的研究方法,將31個省(市)被劃分為七大地區對其的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鄉村全面振興發展趨勢進行闡述探究。(如圖1、圖2所示)。
1.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根據圖1顯示的數字經濟發展趨勢情況可以看出:全國七大地區數字經濟整體發展趨勢呈現為波浪式增長;其中華東地區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水平最高,可能原因在于政策積極推動、科技創新的資源積累。技術應用與產業優勢和高水平人才聚集度比其他六個地區優勢大;華北地區的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水平要高于華南、西南、華中地區,而西北、東北地區的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水平都較低,原因可能在于西北、東北地區的工業結構相對單一,科技創新和研發投入水平相對較低;七大地區在2017年開始后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增加幅度變大,原因可能在于2017年召開世界經濟論壇后我國大力推進數字技術和科技創新的發展促使全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快速提升。
2.鄉村全面振興發展水平

根據圖2顯示的鄉村振興發展趨勢情況可以看出:七大地區的鄉村全面振興發展水平整體呈現勻速增長的趨勢;華東地區鄉村全面振興發展水平位居七大地區首位,而華南地區和東北地區的鄉村全面振興發展水平于2010—2015年在七大地區最低,2016—2020年略高于東北地區,2021年開始東北地區鄉村全面振興發展水平反超華南地區,原因可能在于2021年國務院發布《東北全面振興“十四五”實施方案》的政策推動效應;西南和華北地區鄉村全面振興水平差異不大相繼發展,2017年西南地區鄉村全面振興發展增速明顯高于華北地區,原因在于西南地區的生態環境和自然儲備要強于華北地區的資源要素優勢因素。
(二)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耦合協調度的時序演變趨勢
時序演變是縱向時間維度去比較分析兩者的耦合協調度變化趨勢。利用修正后的耦合協調模型對2010—2022年31省(市)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水平耦合協調度進行測算,并根據各省測算結果對我國七大地區的耦合協調情況和類型進行分級,結果如表3。從耦合協調類型來看:全國整體的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耦合類型為勉強協調,具體劃分可以看出數字經濟與鄉村全面振興的耦合協調水平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性;從增長率來看:耦合協調度最高到最低的排名依次是華南地區〉西北地區〉華東地區〉西南地區〉華北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耦合協調度較高的地區卻表現出較低的增長率,表明七大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差距正在逐漸縮小,區域發展差異呈現出一定的收斂態勢。

四、空間交互效應分析
文章基于兩者可能并非單向驅動而是雙向賦能互為因果基礎之上,選擇空間聯立方程模型。空間聯立方程模型既可以驗證因變量和自變量交互關系又可以避開變量間的內生性問題。
(一)空間自相關檢驗



基于各省面板數據構建空間鄰接矩陣和空間經濟距離矩陣。其中各省經度和緯度具體值用31個省(市)的首府城市的數據表示;經濟水平的衡量用31省(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GDP表示;在確定空間鄰接矩陣的空間權重時,以兩省之間是否有地區接壤相鄰為判斷標準;在確定空間經濟距離矩陣時將兩省之間的PGDP做差,并對差值取絕對值作為確定權重的標準;進行空間自相關檢驗,得出2010年—2022年數字經濟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的莫蘭指數和Z值,如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