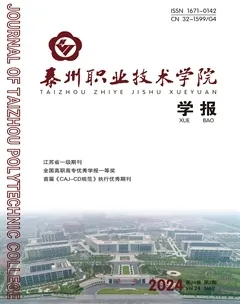科幻小說下的美國現實
摘 要:《漂流在時間里的人》是歐茨創作晚期的一部科幻作品,小說描寫了兩位陷入主體危機的主人公的命運悲劇。歐茨善于從個體悲劇命運出發展現作者本人的社會關切,文章以身份構建為線索,剖析角色悲劇命運的深層原因,探究歐茨的創作觀和其濃厚的現實主義風格。小說與作者成長經歷高度重合的背景設置也體現了歐茨強烈的社會道德責任感和傳統文化意識。
關鍵詞:歐茨;《漂流在時間里的人》;身份危機;現實主義
中圖分類號:I207.41 " " " " " "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671-0142(2024)02-0050-04
歐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是美國當代一位重要且多產的作家。她的各類創作中,以小說方面成就最高,影響最大,廣受好評,屢屢獲獎。暴力是歐茨作品中最顯著的主題,歐茨不斷在美國的社會、家庭與個人生活中尋找愛與暴力相互交錯的故事,并且無情地剖析美國社會的暴力傾向。在2018年發表的科幻小說《漂流在時間里的人》中,歐茨再次展現了她對暴力的興趣。但在這部新作中,歐茨并沒有側重描寫作用于身體的硬暴力,而是將視線放到了作用于心理的“軟暴力”。由于軟暴力的滯后性和不易察覺性,也可以將這種暴力稱為隱性暴力。
歐茨在小說中描繪了暴力語境下個體身份建構失敗的過程,而在暴力之下,是根植于美國文化中心的“自我中心主義”,即“孤獨自我神話”導致了悲劇的產生。《漂流在時間里的人》是一部“以科幻面目出現的現實主義作品”[1],歐茨借助科幻反思美國社會,批判美國文化中心的“孤獨自我神話”。展現了歐茨濃厚的社會責任感、現實主義風格和創作觀。
1 隱性暴力——身份危機的開端
小說中展現的直接暴力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更應該引起關注的是那些潛藏于日常生活中常演不衰且不易察覺的隱性暴力。
小說中展現了沃爾夫曼對埃德利安的冷暴力、語言威脅背后代表的隱性暴力,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暴力性質的“凝視”。現實生活中,因為凝視太司空見慣又容易被人忽視,它的暴力屬性就被忽略了。小說借助反烏托邦的背景設置——“監視”,把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凝視暴力凸顯了出來。“監視”是《漂流在時間里的人》中的重要設定,它不僅是流放地居民的噩夢,也是籠罩在2039年普通民眾頭上的陰云。“你可以把‘有人’或‘他們’想象成陰沉的天空。低沉的天空下有一團團流云,有謠傳說那些都是監控設施,被塑造成了龐大的船形,因空氣污染而呈現出斑斕的色彩,時常呈青紫色,變動不居卻終是揮之不去。”[2]這段描寫體現了2039年,針對民眾的監視已成為常態,而民眾草木皆兵,連云朵都會被想象成監視器,而在這樣的高壓監視下,日常生活的色彩也是晦暗無光的。“監控”是為了讓民眾“忘記”被“刪除”或“蒸發”的親人朋友,群眾因此被弱化連接。揚·阿斯曼指出“個體的記憶和回憶是在與其他成員相互作用和交流過程中對過去進行的一種重構,是建立和確認身份并強化身份認同的過程,每一個成員重新經歷和強加他與所屬的集體之間特有的一一關聯,并有意識地融入他所屬的集體的秩序中去。”[3]“自我”需要與“他者”形成關照才有意義,而人需要與他人連結,在記憶這一處理器中完成對“自我”和“他者”的分辨,身份建構才能成功完成,所以小說中個體的身份建構也會在人與人之間越來越淡化的關系中走向失敗。歐茨在《漂流在時間里的人》中指出“除了記憶的總和,人還能是什么?關照內心,而不是外部世界,靈魂就在內心,我信這個。可是若記憶被剝奪,我會怎樣?靈魂會怎樣?”[2]具有隱性暴力性質的凝視讓大部分普通人出現了身份危機,而具有叛逆精神的埃德利安則在更極端的監視中走向了精神崩潰。
埃德莉安的叛逆讓她最終被判處“流放”,在一個無時無刻都不在被監視的狀態中,她的身份建構走向幻滅。“流放”這一設定的監視機制與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描述的全景敞視建筑(panopticon)契合 ,“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4]。全景敞視監獄中監視者監控著囚犯的一舉一動,但是對于囚犯而言監視者卻是隱形的。被流放的埃德莉安深受這樣極端的凝視暴力侵害,承受了極大的精神壓力,“如果知道自己處于他人的視線中,我就不能正常呼吸。”[2]然而“‘他者’注視我的可能被我感知到時,我才會注視我自己,喚醒我的自我意識。”[5]也即是說,從被流放伊始,在暴力語境之下埃德莉安對于自我價值的尋找和自我意識的建構由于缺乏真實“他者”的存在就具有想象性,就注定失敗。
當今存在的隱性暴力有很多,但是在《漂流在時間里的人》中,歐茨重點展現了作為隱性暴力的凝視危害。這是因為,隨著網絡的發展,凝視暴力的實現越來越簡單。韓炳哲在《暴力拓撲學》中說:“而今,整個社會、整個地球都成了全景監獄。臉書和谷歌之類的社交網絡同時也是安全局的數字全景監獄。”[6]人人都處于一個被凝視的暴力中,忍受暴力,同時也是暴力的施加者。然而可悲的是,人們對暴力的存在都無從知曉,這種慢性暴力卻在慢慢消磨人們與他人與社群之間的連結。在科幻背景之下,歐茨實際上揭露了智能時代,身份危機的源起,但是她并沒有止步于此。她認為,個人悲劇的造成除了在社會上橫行的暴力外,更因為根植于美國人文化中心的“自我中心主義”,即“孤獨自我神話”。
2 “孤獨自我神話”——悲劇的加深
盡管隱性暴力造成了小說主要人物身份危機的開端,但是根植于他們內心的“孤獨自我神話”卻是最終造成他們命運悲劇的原因。不管是埃德莉安還是沃爾夫曼,他們的共同點在于對所處群體的自我放逐。
流放前,埃德莉安是叛逆的,帶有少年特有的虛榮心和冒進,“當我在課堂上舉手回答老師的問題時我沒有問題!我還很篤定。實際上我還暗自得意。可能有點小小的虛榮心吧。”[2]流放后,埃德莉安也因為流放者的身份無法融入群體,這種融入失敗不僅由于流放指令,也因為埃德莉安來自未來,她身上自帶來自穿越者對原住民的優越感。無論流放前還是流放后,埃德莉安都是群體的反叛者,她帶有人文主義者一般的”自我”性,自主與社會脫節。然而社會環境已經變化,與文藝復興時期相比,西方邏各斯主義過分強調的“自我”和“他者”概念和小說中極其左傾的社會環境讓埃德莉安的這種自我異化變得不合時宜,這種對社群的主動脫離只會讓埃德莉安陷入孤獨的牢籠。所以埃德莉安的異化由主動變為被動,“沒有什么狀態比孤獨更可怕了,盡管你未必這么認為,當你必不孤獨時,當你好端端的安居于你的‘生活’中時。”[2]“處于‘社會’中的人沒有任何先定身份可供依賴,對自我的完全處置權意味著身份建構,也需要通過人際交往的選擇才能完成,這種身份即便是建構性的,也是臨時的[5]。所以,當埃德莉安開始與社群脫離聯系時,她就必然陷入異化的牢籠,而她的身份建構從她開始對自我完全處置試圖身份建構時走向了失敗。
埃德莉安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主人公。歐茨認為,文藝復興以來腐朽的理想及其“自我”性,與其他意識均不相容,只能被取代。這一極具男性氣質、好戰的“自我意識”在文明發展的某一階段能讓“自我”區別于其他“我”——同時也區別于自然界——對于把人從對以上帝為中心的宇宙的苦思冥想中解放出來,并采取行動是必要的,但是在現今社會其存在則是多余的,這一意識已然成為一種病態,任何還執著于這一過時理念的人都將滅亡。她認為只要這一孤立與競爭性的“自我”神話存在,我們的社會就依然會迷戀于那些高人一等、征服與毀滅的幼稚的想法。孤獨自我神話只會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7]。
沃爾夫曼一直都是充滿自信的反叛者。流放前,沃爾夫曼是一個頂端黑客,“以我那個年紀來說,我是絕頂聰明的......而且要不是‘朋友’告密,他們永遠也沒法抓到我。”[2]與埃德莉安不同的是,沃爾夫曼自始至終沒有再次與群體和解、融合的傾向。他是冷硬的“孤獨自我神話”信奉者,在韋恩斯科舍州立大學他既不同意傳統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也不愿意附和新興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在與埃德莉安的戀愛關系中,他既不愿和埃德莉安產生深厚聯系又無法與埃德莉安給予他的歸屬感切割,所以他患得患失,精神上極度緊繃。深究他的悲劇成因,是因為他早已深陷自我中心主義打造的牢籠之中。
在歐茨看來,這個“孤獨自我的神話”是西方文化中“最神圣的神話之一”。她指出,“對這一現象的深入探索或許會有助于揭穿我們的其它神話并降低其價值,或者賦予它們新的價值并將其納入新世界的思潮之中。”[8]歐茨借助沃爾夫曼的悲劇企圖喚醒讀者對“孤獨自我神話”的反思,顛覆根植于西方文化中心,被大多數西方人奉為圭臬的“孤獨自我神話”。
3 現實主義科幻小說——超越“孤獨藝術家神話”
“我想要達到一個更富表現力的道德境界,不單是戲劇化地描述一些惡夢般的問題,而是努力表現一些超越它們的可能途徑。”[9]她不再想做一個單純描繪美國噩夢的作家,而是試圖通過自己的作品與社會連接起來,對社會有所幫助。深挖《漂流在時間里的人》背后的設計巧思,可以窺見歐茨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批判。
首先,作品盡管設定在未來,但是實際上影射了六十年代的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民事權利運動、青年反戰運動、嬉皮士反文化運動和9·11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這些精巧的設計都體現了歐茨對美國社會現實的關切。同時“歐茨小說中提到的社會事件在過去和未來是互相關照、互為因果的。”[1]種族歧視、恐怖主義都是小說中的北美合眾國政府諱莫如深的話題。然而原本意在消磨埃德莉安的求知欲的流放刑罰,卻更讓這些歷史清晰地展現在埃德莉安眼前,而與六十年代的美國關照,北美合眾國的荒誕則有了解釋,歐茨或許在小說里表達了她的觀點:模糊歷史是無法掩蓋一個集權擴張的政治巨獸的非正義性的。
第二,小說背景設定在韋恩斯科舍州立大學,小說主人公的經歷與歐茨的成長軌跡高度重合。韋恩斯科舍州立大學隱喻歐茨的母校錫拉丘茲大學。歐茨不僅借小說人物之口批判社會現狀,也表達了對自己的反思和對現代藝術家創作傾向的擔憂。埃德莉安原本是敢于反抗和思考的藝術家,然而,流放后,她沉浸于自己的虛構世界中,龜縮于假身份瑪麗·艾倫中,這其實是埃德莉安作為“藝術家”對自己身份的誤讀,她的結局可以讀出歐茨的隱喻與忠告:藝術家與群體、社會脫離也就不能產出有價值的作品。歐茨呼吁藝術家超越“孤立藝術家神話”,真正與社會連結。只有當藝術家從關注自我轉向關注他人、社會、群體時,藝術家創造的藝術品才會走出虛無,獲得價值。
最后,《漂流在時間里的人》對女性身份危機的出路進行了探索。埃德利安穿越到了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彼時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埃德利安的主體危機日益嚴重,她不僅不敢反抗,反而甘于成為一個依附于男性的家庭主婦,這無疑是對女性主義的深刻諷刺。小說中歐茨諷刺了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脫離女性困境,而過于追求理論構建的問題。在“女性覺醒”逐漸成為主流的現代文壇,歐茨反其道行之,塑造了一個由覺醒到麻木的女性形象。歐茨是想強調刨除女性生活環境和成長背景不談塑造一個進步的女性形象或者一味要求女性覺醒是不切實際的。在經歷了三波女權主義運動的現代社會,越來越多人一味要求某些不符合現代標準的女性盡快“覺醒”,脫離家庭完成獨立,卻忽視了這些女性本來的生存環境。歐茨通過埃德莉安這一角色的塑造呼吁讀者先看到女性遭受的創傷,真正關注女性困境,而不要一味要求女性覺醒或進步。歐茨并不想過分強調對女性傳統的反抗,而是呼吁讀者將視線關注到精神受到傷害的普通女性本身,真正理解其苦難,尊重其選擇——直面女性苦難,愛每一位女性,這即是歐茨對女性困境出路的探索與思考。
4 結語
歐茨向來是一位關切美國現實的作家,讀她的作品不僅可以關照美國現實,也可以書為鑒,關照自身。《漂流在時間里的人》擺脫科幻小說的娛樂性,描述了兩位主角的悲劇故事,用他們的悲劇提醒世人“孤獨自我神話”扎根的社會現實土壤已經不復存在,個體如果仍耽于自我中心主義,飲鴆止渴,則不可避免地會陷入精神崩潰,難尋生存意義。在科技、政治環境日新月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漂流在時間里的人》以精妙的反諷和隱喻反思美國現實,引導讀者居安思危。當年邁的歐茨創作《漂流在時間里的人》面對與自己成長經歷高度重合的埃德莉安時,她謙卑地反省自身,同時又對美國年輕一代藝術家的忠告與展望:希望年輕作家能夠關注美國現實,承擔成為作家的社會道德責任感,避免陷入虛無主義的樊籠。作為歐茨晚期的力作,《漂流在時間里的人》不僅不失水準,而且意義雋永,發人深思。
參考文獻:
[1]韋清琦.科幻背后的美國現實批判——以歐茨的新著《漂流在時間里的人》為例[J].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2(2):39-46.
[2]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漂流在時間里的人[M].韋清琦,譯.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2021.
[3]金壽福.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J].外國語文,2017,33(2):36-40.
[4]米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上海:三聯書店,2019.
[5]吳盛博.《夜半撞車》中的社會身份建構與日常生活批判[J].當代外語研究,2021(5):101-108.
[6]韓炳哲.暴力拓撲學[M].安尼,馬琰,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7]肖旭.從超越“自我中心主義”到建構倫理共同體——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的共同體思想研究[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20,31(6):115-122,156.
[8]林斌.超越“孤立藝術家的神話”——從《奇境》和《婚姻與不忠》淺析歐茨創作過渡期的藝術觀[J].當代外國文學,2003(1):147-155.
[9]Sjoberg L,Oates J. An Interview with Joyce Carol Oates[J].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82(3):267-284.
(責任編輯 劉 紅)
The American Reality under Science Fiction
——On the Identity Crisis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Way out in Hazards of Time Travel
HE Kang-g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China)
Abstract: Hazards of Time Travel is a science fiction in the late period of Oates's creation. The novel describes the tragedy of two protagonists who fall into the identity crisis. Oates criticizes the states qu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tragic fate.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cess of identical deconstruction as a clue to analyze the deep causes of the tragic fate of the characters, and probes into Oates's creative view and her realism style. The highly coincident background of the novel and the author's own growth experience also reflects Oates's strong sense of social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awareness.
Key words: Joyce Carol Oates; Hazards of Time Travel; identity crisis; realism
作者簡介:何康歌(1999-),女,江蘇如皋人,碩士生,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
基金項目: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創新實踐項目(KYCX22_3320,項目主持人:何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