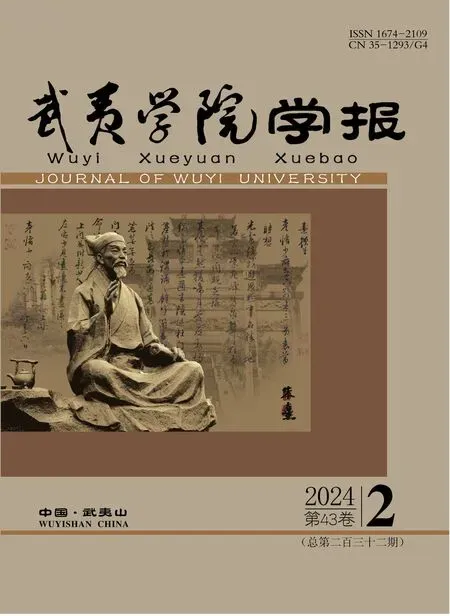朱熹的義利觀
——以朱熹對《孟子》首章的詮釋為中心
賈 超
(上海師范大學 哲學與法政學院,上海 200234)
義利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儒家思想中的一個核心關切,自孔子首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1]義與利便經常綁定在一起,相對而論。隨后,《孟子》首章亦寫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這一關鍵論述可以看作是對孔子以來義利問題重要性的再一次確認,同時,孟子旗幟鮮明地指出了仁義相對于利而言的優先性。在此之后,這一問題便成為歷代學者繞不開的重要話題。無論他們對孟子之言是贊成或是反對,都不得不對這一問題詳加思考。如司馬遷便贊成道:“愚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嗟乎!利誠亂之始也。”[2]王充則詰難道:“夫利有二:有財貨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之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3]即使到了現代,義利之辨同樣作為一個基本而核心的問題引發諸多學者的討論與關注。如陳來認為義利之辨指向的是價值觀建設的問題,“不僅僅是上下級的政治關系要處理的價值觀,它廣泛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普遍相接”[4];朱承指出義利之辨實質是對公共生活中公義與私利何者更具優先性的思考,“體現著儒家在公私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傳統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邏輯展開”[5]。
對此,本文試圖回歸朱熹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作為宋代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觀點無疑極具啟發意義。他曾不止一次說道:“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6]由此足見其對義利問題的重視,同時這一問題又關涉到朱熹對理氣、心性等問題獨有的思考。可以說,厘清朱熹的義利觀不僅對理解儒家思想傳統大有裨益,而且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朱熹深刻的哲學思考。由于義利問題主要是因孟子的提出而得到廣泛的討論,因此,本文關注的焦點便集中在朱熹對《孟子》首章的詮釋,通過分析其對《孟子》首章“造端托始之深意”的解讀及其背后特有的邏輯架構,試圖對這一核心問題作出更加真切的理解。
一、朱熹對《孟子》首章的解讀
眾所周知,《孟子》首章便直入主題,劈頭拋出了一個影響千古的話題——義利之辨。朱熹正是通過對《孟子》首章的詳細解釋展開了仁義與利關系的論述。具體來說,他在《集注》中將《孟子》首章分成了三個部分,并依次加以詮釋,首先是: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
朱熹先對梁惠王所提到的“利”做出解釋,認為“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隨后進一步說道:“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在這里,朱熹雖然僅僅是對利與仁義做了一個簡單的概念分判,指出這兩句總起下文。但這看似簡單的概念分梳實則濃縮了朱熹極大的心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可以說是朱熹關于“仁義”思考的不易之論。可惜的是,朱熹在此處對“利”的言說較為簡略。
隨后,第二部分為: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
對于這一段論述,朱熹認為是在具體地解釋上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同時,這一段話也可分為兩個方面,首先是“王曰何必利吾國”至“不奪不饜”,這一部分是講“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朱熹指出如果一味地提倡先利后義,則臣只有弒君而盡奪其財才會知足,終將導致國破家亡;后“未有”兩句則是在說明“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這一部分表明若人君踐行仁義之道,自然能夠化民成俗,為百姓所親戴。可以看出,朱熹將孟子對義利的觀點分成了“何必曰利”和“亦有仁義而已矣”兩個方面,并且還將這兩方面進一步展開為“求利之害”和“仁義未嘗不利”。總觀朱熹這一段解釋,可以得出他對義利問題的兩點基本看法:一是利未必就是不好,富國強兵是利,而愛親急君同樣是利。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利,而在于是否有求利之心。如果一味地求利,則必然會導致禍患。二是人君應當躬行仁義,行仁義則自然無所不利。
至于第三部分,則是: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朱熹注道:“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他指出孟子將上文兩節的觀點再次重申,也即是再次表明“求利之害”和“仁義未嘗不利”這兩個核心觀點。
在朱熹分析完這三部分后,他總結出了此一章之宗旨:
此章言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這樣一段關于章旨的論述,可以看作是朱熹對孟子義利觀的進一步詮釋,主要的觀點仍舊是上文提到的“求利之害”和“仁義未嘗不利”。同時,還可以發現朱熹對于這一問題的幾點獨特理解:
首先,朱熹并不是直接處理仁義與利的關系問題,而是說“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尤其值得注意,這里所提到的是 “仁義”“利心”,而非“仁義”“利”。也就是說朱熹是在討論“義心”“利心”與“利”的關系。這樣一來,朱熹就將孟子在政治治理層面上對義利的探討歸攝到了心性論層面,這無疑是對《孟子》原文隱含邏輯的揭示與推進。因為孟子本人也曾提到過“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1],所以這種對仁政心性論基礎的解讀可以說十分契合于孟子自身的致思理路。
其次,朱熹進一步將義心與利心的生成機制加以揭示,他指出仁義是人心中固有之存在,利心則是物我相形之后的產物。這樣一種解釋與朱熹特有的理氣同構的生成論密切相關。而且,義利之辨也從人在行為活動中對結果的抉擇問題轉變成了人是否朝向本真性生存的問題,使得儒家哲學傳統中關于義與利的探討獲得了真正本質性的分判與說明。
最后,朱熹將仁義等同于“天理”,利心等同于“人欲”,用“天理”“人欲”這一對理學家慣用的概念賦予了這個古老的命題以全新的意涵。同時,由于“天理”“人欲”這對概念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意涵,所以自然推出了“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從而證明了前文所提出的兩個觀點——“求利之害”和“仁義未嘗不利”。
通過上文的簡單梳理,已可初步了解朱熹對《孟子》首章的解讀,不過有一點還是需要注意,在這里,朱熹只是給予了一種結論式的說法,并未詳細說明其解讀背后的邏輯基礎。這樣一來,自然會產生兩個問題:一是義心和利心具體是如何產生的?二是為什么義心能無不利,而利心則害相隨?下面,將依次解決這兩個問題。
二、義心與利心的生成機制
事實上,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已經指明了義心與利心的詮釋方向,“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說明義心是根源于人心固有的性理;“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則表示利心是物我“相形”之后的產物,而這樣一種“相形”的根源則在于物我的“氣稟”之不同。如果通觀朱熹其它的著作會發現,他在《大禹謨注》中使用過相同的話語,“心者人之知覺,主于身而應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7]。這時,我們會發現,在朱熹的思想中,利心對應的其實就是人心,義心對應的則是道心,利心和義心的問題事實上也就是人心和道心的問題,只是在解釋不同文本時所使用的方便話語。于是,問題便轉向了考察朱熹是如何理解人心和道心。
人心和道心之語出自《古文尚書》,其中提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厥執中。”這句話被朱熹視為“堯舜禹相傳之密旨”,是其道統說的重要文本依據,同時,他也據此詳加闡發自己獨特的心性論與工夫論。對于此句的具體解釋,集中體現在《中庸章句序》中,為了論述的方便,茲錄其相關部分如下: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于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1]
這段話是朱熹對于人心和道心論述得比較清楚的一段,內涵極其豐富。首先是“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這句話是對心的總體概述。在朱熹的思想中“心”的主要含義指的便是知覺,他曾不止一次說道,“有知覺謂之心”[8]和“心者人之知覺”[7]。至于“虛靈”,則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心之知覺的特性,“虛”指的是心在未感物之前的虛靜狀態,他曾說道:“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鑒之空,如衡之平……故其未感之時,至虛之靜,所謂鑒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9]“靈”則是指心之知覺的神妙不測,“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里,神妙如此”[8]。無論是空間上還是時間上都不受限制。盡管“心”有這些特質,但從根本上來說,“心”只有一個。“一而已矣”便突出強調了這些不同的特質都是統攝在“心”這一整體意義之內,“虛靈知覺”只是從不同的角度來描述“心”而已。
心雖然是一個,但卻會有人心和道心之別,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生于形氣之私”,道心“源于性命之正”,從而導致“知覺者不同”。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對人心和道心在生成論意義上的解釋。在朱熹看來,心的主要意涵是知覺,而關于知覺的產生,他則認為是理與氣結合所致。其門人曾問他:“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他回答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8]按照朱熹的觀點,須先有知覺之理,然后氣以成形,理與氣相結合,才能產生知覺之心。因此,雖然知覺之心是一個,但根據來源的不同它可以有兩種結果,“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8]。從個體形骸出發產生的是人心,從普遍義理出發產生的是道心。同時,由于無論是上智還是下愚,都無一例外地稟理為性、稟氣為形,故而,所有人都天生地兼有人心和道心。
人心和道心雖然都是天生所固有的,但并不意味著二者具有相同的地位,朱熹認為,人心“危殆而難安”,道心“微妙而難見”,二者雜于方寸之間,如果不能加以整治,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對于這一點,在與蔡季通的書信中,朱熹詳細地解釋道: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既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后流於人欲也。[10]
人之所生都是性與氣相合之后的產物,根據已合之后的結果分析來看,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因為性主於理而無形,所以公而無不善;因為氣主於形而有質,所以私而或不善。在這里,我們需要關注朱熹論述背后隱含的邏輯。首先,這里所說的“性”指的是“天命之性”,是上天賦予每一個人內在固有的人之性,即天理通貫至人身而凝成的人之性理。換句話說,此處所言人之性理亦即是天理。而天理在朱熹看來,則是公而無不善的。此處的“公”有兩層含義,首先是指生成意義上的普遍性,天理是一切存有的根源與根據;其次它表明了天理的自然非人為性,人之所為并不能改變天理固有的傾向。所以他才會說:“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8]無有不善的天理下貫至人身便成了人心內在固有的本質性理。
但是當天理落到具體事物當中便會有氣的影響,氣則構成了人之形質,不同的人會有各自獨特的形質,因而,氣則具有個體性、私人性的特點,所以朱熹認為氣“私而或不善”。《語類》中便提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里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8]需要注意的是,朱熹在這里用的是“私而或不善”,也就是說氣并非一定是不善的,但如果不用義理加以約束的話,便會流於放縱。進一步分析的話,由于性是公而無不善的,所以性之所發皆是天理之所行;而氣是私而或不善的,所以氣之所發皆是人欲之所作,這樣導致的結果便是會有人心道心之別。可以看到,朱熹在這里將道心人心等同于天理人欲。知覺之心按照天理所發則為道心,如果局限于個人私己的話則為人心。
雖然從產生的結果來看,天理人欲同時并有,但如果從本源上說則只有天理,并無人欲。為此朱熹還專門批評過胡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的說法,他說:“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圣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11]朱熹認為從本體根源處來說只有天理并無人欲,這一點不容有半點差疑,也正因如此圣人才只是教人克己復禮的為學工夫,天理本身固有,只要除卻人欲,天理便自然會實現出來。
對于人欲的來源,朱熹在與何鎬的書信中說道:“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之中本無人欲,惟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或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10]就本原處而言,“體”中只有天理而無人欲,但是在天理流行的過程中,由于氣稟的遮蔽有可能會導致天理流之有差,從而產生人欲。所以只能說“因天理而有人欲”,而不能說“人欲亦是天理”。同時,朱熹還批評了程顥“善惡皆天理”的觀點,認為其所提“惡者本非惡”的說法才更為妥當,人欲只是天理流行過程中的過或不及。
總結來看,朱熹認為心雖然只有一個,但由于心是理與氣相合而產生的,所以會有人心道心之別,“只是這一個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8]。從形氣之私出發產生的是人心,從義理之公出發產生的便是道心。雖然產生的結果有兩種,但從本源處來說則渾然只是一個天理,所以“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再看朱熹在《孟子集注》中的解釋,“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義心是根源于心中的固有性理,屬于“天理之公”;利心則是生于后天的形氣,因而是“人欲之私”。
三、義心、利心與利之間的關系
上一節已經討論了義心與利心的生成機制,接下來則重點關注義心利心與利之間的關系,為什么義心能夠無不利,利心則害相隨?對此,需要先來分析朱熹所言之利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在《孟子集注》中,他曾提道:“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1]也即是說,朱熹認為梁惠王所關注的利主要指的是財貨土地的多少。至于孟子所關注的利,朱熹則說道:“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9]可見,朱熹認為真正的利應該是萬物各得其所。同時,他還引述了《周易》中的話說道:“《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并且詳細闡明道:“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8]無論是君臣還是父子,天地萬物都各得其分,這便是天下之大利。
事實上,如果聯系到朱熹在其它地方的相關表達的話,這里所說的“分”其實指的便是事物各自的“當然之則”。對于這一點,朱熹在《語類》中具體地論述道: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卻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個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8]
在朱熹看來,天在降生萬物的同時賦予了萬物以各自的當然之則,君之則是仁,臣之則是敬,目之則是明,耳之則是聰,四肢百骸,萬物萬事,無一不各有其當然之則。可以看到,朱熹在這里區分了兩類當然之則,即人的當然之則與物的當然之則。其中,人的當然之則是人與他人相處時君仁臣敬這類的道德準則,物的當然之則是人對于物恰當的使用原則。這里尤其需要關注的是朱熹對“耳目之則”的論述,他認為目之則是“視遠”,耳之則是“聽德”,也即是說,朱熹認為耳目的當然之則并非是耳目的生理功能,而是人對于這些功能恰當的實現原則。正因為如此,朱熹才會強調:“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于口之于味,鼻之于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8]相對于耳目的生理功能,朱熹更強調的是人使用耳目的方式,認為這才是物的當然之則。這樣一來,再聯系到上文朱熹所提及的“無一物不得其所者”的論述來看,他所認為的“利”其實指向的便是人與物當然之則的充分實現。
但是,對于人與物當然之則的實現離不開對人與物各自之“性”的了解,在朱熹看來,“至於天下之物,則必有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9]天下萬物都各具其理,理包含所當然之則與所以然之故兩個方面。對于這兩個方面,簡而言之,所當然之則是萬事萬物應當遵循的當然之則,所以然之故是當然之則的根源。朱熹有時也會用性——道這一對概念,“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于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于性,然后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10]“道”是事物的當然之理,“性”則是“所以為道”,也即是當然之理的根據。因此,要想實現事物的當然之理必須了解事物之“性”。
對于人物的“性”與“道”,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性”和“道”是人物本身所固有的,“性”是“道”的根據,“道”是具體事物各自的當然之則,無論具體事物是否按照其當然之則去活動,都不影響當然之則自身的存在,所以朱熹才會說:“‘率性之謂道’,性是一個渾淪底物,道是支脈。恁地物,便有恁地道。率人之性,則為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為牛之道,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后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8]有一物,便有一物之“道”,率人之性,則為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為牛之道。如果說“道”必須依賴于人行而后有,那么在沒有人的行動之前難道就可以說沒有“道”存在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所以在朱熹看來萬物各自的“道”與人的具體實踐無關。
但是,雖然說萬物之“道”的存在與人的活動無關,可是“道”的充分實現則依賴于人。換言之,朱熹認為物性的充分實現并非是處于與人無關的自然狀態,而應該是以人對萬物的恰當使用為前提的。在《語類》中記載了一條關于“繼天立極”的討論,可以提供些許佐證: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卻須圣人為他做也。[8]
朱熹在這里表述得非常清楚,盡管天理遍在于天地萬物之中,然而天理本身不能自己實現,其恰當的實現有賴于圣人的裁成輔相。
至于圣人為何能夠充分實現人物之性,就朱熹哲學的脈絡而言,可以總結出以下兩個原因。首先,朱熹認為人之性與物之性在源頭上是同一的,“萬物皆只同這一個原頭。圣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8]萬物從根源上來看都出于同一個天理,萬物各自的性理只是同一天理的不同表現樣態,正因如此,圣人才能夠做到盡人物之性。其次,圣人能夠對天理有根本的領悟,“圣人純于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9]。圣人之心純是天理,而無一毫的人欲之私,所以他對萬物的裁處都屬于贊天地之化育,是對萬物之性的充分實現。
朱熹這一獨特的觀點可以說與他對人物的特有理解密切相關,“‘性’ 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為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物物各有這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8]。在他看來,人與物同稟得天理以為“性”,不同的是人與物所稟得的氣有所差異,但從根本上來講物物同具此天理,只是被氣稟遮蔽了而已,隨著物性之所通,其內在固有的道理也會自然地實現出來。對于人與物之間的差異,朱熹在《四書或問》中亦有所提及:
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于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于禽獸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9]
從理的層面來說,萬物一原,彼此沒有貴賤之分,但從氣的角度來看,人之氣正且通,物之氣則偏且塞,是以人貴而物賤。更重要的是,由于物的氣稟偏塞導致其不能充分實現本然之天理,只有稟得正通之氣的人才有可能成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對于人“性”的尊貴之處,朱熹認為集中體現在人心之“虛靈洞徹,萬理咸具”。在《語類》中他對人“心”的這一獨有地位做了更清楚的論述:
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所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8]
在這段話中,朱熹同樣強調從本源上來說,人與物都同得天理以為性,同時,亦明確指出人與物的差異在于“心”的不同。人心虛靈洞徹,包得許多道理,物心則不能如此。這也就是說,只有人心才全具眾理,即意味著只有人才能將人與物本具的天理完整地呈現出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這一過程也被朱熹稱為“盡人物之性”,他曾說道:“至誠之人,通身皆是實理,無少欠闕處,故於事事物物無不盡也。”[8]具體而言: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里,有可開通之理,是以圣人有教化去開通它,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個善,圣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里,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8]
人物所稟之性相同,而氣稟則異。人雖稟得的氣濁,但有可開通之理,所以“盡人性”指的便是圣人教化眾人,開通其本然的善性;物稟得的氣偏,無道理可使之開通,因而“盡物性”指的是圣人按照物本然的性分去處置,使之各當其理。
如上所論,天理是一切存有的根源與根據,萬物各自的當然之則是普遍天理的具體體現,同時,人有可能對人與物所共有的普遍本質有根本的理解。因此,人如果不是出于個人私欲而是出于對天理透徹的領悟的話,便能夠使萬物的當然之則得到充分的實現。此時的人之心亦可稱之為“義心”,而事物當然之則的具體實現便是“利”。正因如此,朱熹才會說:“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1]
四、結語
朱熹通過對《孟子》首章的詮釋,表明了自己獨特的義利觀,具體而言可以分為“求利之害”和“仁義未嘗不利”兩個方面。這一義利觀背后蘊含著朱熹自身一套特有的理氣論與心性論。他認為“利”是萬物各得其分,也即是萬物當然之則的實現,這一實現的前提是對事物之性的充分了解,而物之性與人之性一同根源于天理,同時,只有人才能夠完全知覺天理。所以說,只有人充分知覺天理并且按照天理去做才能實現利,這也就是“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