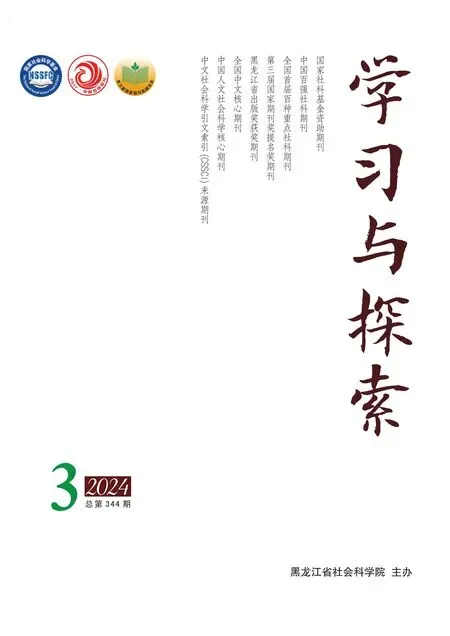宰夫與匠人
——從隱喻看先秦政治思想轉變
匡 釗
如我們所知,不拘古今中西,當論者嘗試表明自身觀點的時候,其言說方式在實踐中均是多種多樣的,在哲學研究領域,以往為我們所熟悉的有舉例、推類的手法,也有調用隱喻或者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營造說理的效果。但在對上述實踐加以研究性反思的時候,源于經典西方哲學的某些前見卻使我們的理論視野迅速收窄,傾向于聚焦對句子做分析性處理,在邏輯性地討論推理時,滌除了大量源于經驗、習慣與日常語言的難以通過傳統方式加以形式化的元素。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現代學術在探索相關話題時,已經開始重新使這些言說思想時的遺落之物回到研究視野當中,比如,隱喻在我們了解世界的過程中所發揮的概念建構作用,就已經得到了相當數量的討論。由此角度探討中國古人的智慧傳遞方式,或許將會有意外的發現,相對于更多受到分析性傳統所轄制的西方哲學而言,中國哲學的理論實踐或為由隱喻探索的進路而趨近人類說理方式之公共性的辨明提供了更易接近的研究平臺[1],而隱喻所能提供的說理力量,不僅局限于哲學概念的言說場景,也可服務于更為復雜的政治論辯環境。事實上,當我們回憶早期文獻中那些經典的政治觀點的展示時,若干反復出現的隱喻將快速俘獲我們的注意力。
當審視先秦經典中出現的政治性言論時,可以發現相關的言說往往是“統治者取向”的,無論真實或假想的言論,其受眾多數情況下總是不同層級的權力掌握者,而話題的焦點則常常在于權力行使的條件、方式、效果或道德評估,而針對統治者身份、品質與行為的討論也很容易成為展開話題的中心線索。早時這種情況無疑來自周初關乎天子與天命互動的政治想象和早期封建貴族政體的運作環境,上述歷史現實在春秋戰國之際發生了重大改變,而我們如何在現代學術范圍內對先秦諸子的相應創見加以合理解釋與安放,則是具有挑戰性的研究事業。對于這個大變局的討論,可能涉及對話語單位的再描述,或對決定其形態的非話語力量的重現,而我們同樣可以從相關言論內部提供的某些信息入手,去檢索那些描述與重現。從這個角度去辨明早期文獻中言說統治者及其行為時出現的擬人化的結構隱喻,將為我們提供某種簡潔的可能性——特定的隱喻性的說理方式何以揭示出政治治理的現實立場轉換。
一、宰夫:統治者的早期隱喻
“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六十章》)老子這一關于國家治理的表述或許是中國哲學史上幾個最著名的隱喻之一,老子運用了“擬人”的手法,向我們展示了他對國家治理活動的理解,把具體的烹調技藝與抽象的統治行為聯系起來(1)“這類隱喻通過人類動機、特點以及活動等讓我們理解各種非人類實體的經歷。”參見喬治·萊考夫、馬克·約翰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何文忠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頁。。其中,對于老子希望傳達的思想,學術界耳熟能詳,而在治國與烹飪的關系背后,自然存在著一對人物形象:統治者與廚師。對于古代國家中擔任類似于今天廚師工作的一類人,本文據《左傳》記載,將其統稱為“宰夫”,如果說在現代人眼中,廚師的任務是較為單純地與烹飪活動本身相聯系,那么,宰夫則可被置于更復雜的古典語境當中。早期文獻在談論扮演宰夫角色的人物時,也將其稱為宰人、庖人、膳夫或雍人。其中“庖人”的說法多見于諸子書,而“宰夫”的說法多見于《左傳》《儀禮》等經典。即使今天廚師的工作也可能是一個要素眾多的系統,我們也可以從《周禮》中找到古人對這個系統更為復雜的理想化描述。《周禮·天官冢宰》提及的宰夫類角色,至少有五種,即“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他們總體上似乎接受小宰的領導,也受到諸如“酒人”“醢人”等掌管,且提供特定飲食材料者的輔助。《周禮》對宰夫類職官角色的解釋也許未能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的真實狀況,比如其在小宰之后亦提到“宰夫”,但將大、小宰與宰夫皆作為輔弼王權的品級不同的司法行政之官,而非專門服務于統治者飲食的人,顯然與《左傳》等用例不合。《左傳·宣公二年》載著名的“晉靈公不君”,便有因“宰夫胹熊蹯不熟”而擅殺其人的罪狀,此處所云宰夫非《周禮》之義——本文所謂“宰夫”取《左傳》義而非《周禮》義。
以上五類宰夫角色,《周禮》對其分工亦有描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修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鄭玄以膳夫為“食官之長”,按現在的標準,他主要負責管理工作,統籌作為更廣泛的禮制的一部分的圍繞國君所展開的飲食活動,工作性質類似于現代酒店之“行政總廚”。其下“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鮮槁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修、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臘。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铏羹;賓客,亦如之。”從這些描述來看,庖人的職責主要在于屠宰,而這個意思實際上也是諸子提及庖人時主要的用法,如孟子所謂“君子遠庖廚”,莊子筆下解牛之“庖丁”。對于內、外饔(《儀禮》《禮記》中所謂“雍人”),內饔職責在于直接服務君王及其“核心家庭”,負責其食材的具體烹飪加工,而外饔則作為一個禮制設計中與內饔對稱的職位,其最大區別在于服務對象的不同,其面對的是王室之外的人,負責君主的公共宴會。從具體工作的角度看,內、外饔履行的才是現代狹義上所稱的廚師的工作,只是他們的工作需要被置于廣義的周禮體制中看待。至于亨人則類似于雍人的助手,專門負責生火燒水之類的下級任務。
從這些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周禮》對宰夫類角色的關注并不在于其烹飪技能的高低,而在于四個方面:其一,將其視為職官,其在權力系統中有確定的地位;其二,他們的工作不僅是世俗化的,同時也涉及薦神的宗教性維度;其三,他們不僅服務于特定的當權者個體或其家庭,亦在更廣泛的內政或外交活動中扮演角色;其四,宰夫們為了稱職,亦應具有辨別名物的能力或豐富的相關知識。《周禮》在談論宰夫時的關注點,明顯與《左傳》和諸子書不同——后者在提及宰夫的時候,主要還是強調其烹飪技能,但這些信息有助于我們理解古人為什么有可能在宰夫和統治者之間建立隱喻關系——統治者無疑占據權位,具有溝通人神的能力和領導公共事物的職責,而且也被認為應該具有關于治理國家的知識或智慧。
回到老子的隱喻,可以看出,他并非是歷史上第一個注意到宰夫與君主之間聯系的人,他的治國隱喻并非出于自己的發明,而是來自對較早說法的直接繼承。
更早時以宰夫與烹飪隱喻統治者與政治治理的例子,出現在春秋晚期齊國名臣晏嬰的言論中。《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晏子與齊景公的一段對話,明確運用了這個隱喻: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此段對話發生的大背景,是齊景公年事已高而齊國內亂象已生,十年前欒、高、陳、鮑四族相攻,齊侯賴晏嬰之助雖得平亂,但陳氏自此而大,為齊國未來埋下重大隱患。之后,齊侯因仍未能妥善處理國內大貴族之間的矛盾,而開始寵信梁丘據之流“小人”。在上述對話發生的當年,齊侯曾因病聽信梁丘據等言語,幾欲殺祝、史以謝諸侯問疾之來使,幸為晏子所阻,并講出一套敬事鬼神莫如外寬其政、內修其德的道理。對話發生的小環境,則為齊侯田獵時不稱心,下級官員不但不從命,還講出一個難以反駁的理由,而此時除了晏子侍側,寵臣梁丘據的到來為齊侯提供了一絲慰藉,但卻引出晏子一番“和”而非“同”的政治勸導來。這段話的重點在于對“和”的政治意義的言說,此點亦因被孔子所看重而知名,即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進而在現代學術語境中成為中國古代思想的標志性概念之一。“和”在這段文字里特指政治過程中君臣關系的維度,其大體意味著相互尊重、妥協與行為調適,而與一味逢迎上意的梁丘據之流的小人行徑涇渭分明。晏子為了向齊侯說明這一點,創造性地運用了宰夫“和羮”的隱喻。可以看到,無論烹飪還是政治活動均非簡單的物理概念,而涉及大量不同的概念內容,如多種食材、烹調手法、滋味效果和君臣角色、權力互動、禮制關系,等等,整合這些內容的“結構隱喻”,“讓我們以一個高度結構化的清晰界定的概念來建構另一個概念”[2]61。在這里,烹飪技術中對于各種食材的調“和”及其效果顯然在經驗中是相對切近、清晰的概念,而晏子正是以此來闡明政治上的“和”。
在春秋晚期,齊景公的困境是普遍的問題,國君權力被世卿貴族蠶食,前者面對后者的威脅與不服從時,往往只能通過任用、寵信“小人”來為自己服務。當這些處于貴族體制末端的人以國君私屬的角色試圖繞開原有體制而發揮作用的時候,在舊的世襲大貴族眼中,他們當然只能是奸佞小人。此時理想的君臣關系仍然籠罩在思古之幽情中,被認為應建基于植根宗法封建的貴族體制,國君應與位居其下的諸級貴族職官以禮相守。齊侯田獵招虞人而后者不奉命,核心則在于齊侯招之非禮,破壞了被認為應得到一致認同的、貴族政治運作所遵循的基本規則。雖然齊侯并不是這種理想化的貴族政治規則的唯一破壞者,但在晏子看來,他或許應肩負維護禮制的表率責任,并從維護宗法封建傳統的角度努力使君臣關系回歸禮制之正軌,而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理解“和”的意義并采用“和”的方式——孔子所謂“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或可為其注解。正如宰夫“和羮”是對現有食材(包括調味品與魚肉之類的主要材料)運用適當的烹調手法(利用水火烹煮)加以良好調和加工,并最終達到滋味適當的食用效果一樣,政治治理也應該調和當時貴族制度內的君臣關系,在雙方不同立場之“可”與“否”的相互妥協與協調配合之間,使國家得到良性運作。
這里晏嬰所希望向齊景公表達的核心意思并不艱深,值得玩味的是,他利用宰夫的隱喻傳達出國君應是一位權力的調和者,而國君作為統治者任務的核心,在于如何使位于其下的種種貴族勢力相互間(且與自己)和諧相處,最終呈現出理想的國家政治狀態。正如一位高明的宰夫所呈獻的一席盛宴,席間君臣各得其所、其樂融融。宰夫這個隱喻,充滿了復古的情調,而當其在戰國時代再次被提及時,卻已經是另一番風味了。
二、匠人:國家治理者的新形象
再回到《老子》的文本,烹飪的隱喻被重新提及時,其所喻指的對象雖然仍是治國,也依然將君王與宰夫潛在地聯系起來,其運用這個隱喻的重點也仍舊在于強調烹飪技巧與治國方略之間的對應性,但其借助這個隱喻為此話題注入的語義則發生了重大變化。《老子·河上公章句》對此解釋說:“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韓非子·解老》亦稱:“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王弼注《老子》此段亦落腳“不擾”“主靜”。上述的理解一脈相承,都強調老子通過這個隱喻為國家治理行為植入了新語義:君主應像宰夫烹小魚時避免隨意撥弄、翻動一樣,在治國過程中也應保持“不擾民”(《說文》:“撓,擾也。”)——這既可從君主的主觀意志(智與故)方面看,也可從制度設計(法令滋生)的客觀實踐方面看。在這個解釋序列中,晏嬰所運用的宰夫隱喻的原始意思“和”消失了,而這同樣可被視為特殊技藝的“不擾”取代其成為隱喻的中心。
這種宰夫技藝的變化,絕非是出現在戰國文本中的孤立事件,事實上為了理解這種變化,必須借助同時期涌現出的關于國家治理的新隱喻。《老子·七十四章》便引入了一個這樣的新隱喻:“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河上公章句》就此而謂:“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斫,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這里出現了一個新的隱喻形象“大匠”,而其在文本中喻指的對象雖然是道,但這個形象很容易被轉移到君主身上。現在難以評估“匠”這個隱喻是否為《老子》首次采用,但其作為對國家治理者的隱喻以各種變體廣泛存在于先秦的諸子書中,如《孟子》《淮南子》中亦有“大匠”,《荀子》中有“工匠”,《墨子》《莊子》《管子》中有“匠人”等,其中“匠人”的用法最為多見。當然,在所有“匠人”的用法中,亦不乏實指,而其中只有部分被作為統治者形象的隱喻,但本文仍依照其作為此類關于國家治理者新隱喻的統稱。匠人的頭銜,也可見《周禮》,《考工記》專論“匠人建國”“匠人營國”與“匠人為溝洫”之法,這里的匠人按現代職責分類,當屬建筑工程師。考慮到中國古建筑主要為木質結構,那么,在歷史上其建造者實際往往由木匠充任,匠人的第一義便是木匠,而其他能力職責皆由此第一義衍生而來。歷史故事中的魯班(或公輸班)便是匠人中的典型,魯班作為機巧的木匠,也是大型機械乃至城郭橋梁的制造者。回到《老子》,其言及“大匠”時所強調的便是匠人的第一義,而在木匠工作中,切削木料是最基本的活動,只不過當《老子》以此為喻時,強調的是對這種行為的否定。就像切削是對木料的強力、破壞性加工,而類似的強制性、介入式的國家治理策略在僅以君主的私人意志為主導時,對政治治理也只能造成負面影響。《老子》中“不斫”的意思顯然與“不擾”相呼應,都是對隨意、多余且強制性的國家治理策略的否定,文本中“宰夫”與“匠人”的隱喻具有一種連續性或對等性:在兩者均可被作為國家治理者形象的同時,利用對兩者特殊技藝的強調,表達某種對于政治行為方式的否定性意見。
可以看到,《老子》中這些隱喻的用法,與較早時《左傳》中晏嬰的用法相比,既有共同點也有差異——“和”的肯定性意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于國家治理的否定性主張。但是關鍵在于,這種否定性的主張是否直接針對晏嬰的觀點呢?為了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從宰夫到匠人的隱喻轉換。在諸子書中,匠人開始被設定為統治者的新隱喻形象,而如果匠人首先被視為木匠的這一判斷是正確的,則此隱喻的引入或許可能始于墨家——墨家與工匠團體的關系早為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所知,雖然從文獻時代順序的角度看,墨家的某些基本文獻極有可能先于任何已知道家類文獻,但前文的討論從《老子》開始,后面我們仍繼續從道家系文獻入手討論問題。除《老子》中的匠人以外,如《管子》《淮南子》(此雖非先秦著作,但其思想可視為先秦道家的延長)中的相關用法,皆為《老子》文義之承續。如《管子·小稱》曰:“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殼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廁,故遫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淮南子·齊俗訓》曰:“圣人裁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斫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這兩種文本在將匠人作為統治者隱喻形象的同時,與《老子》的共同點在于均強調匠人的切削技藝,但同時也引入了新的內容,即不僅對這種技藝持簡單的否定性態度,而且同時也表明了這種技藝的可控制性,如果由“善人”或“圣人”來實施,其效果則完全可能是正面積極的,也就是說,統治者特殊、可控的治理行為如同匠人以正確的方式切斷繩索或制作木器的榫卯結構一樣,也可以“得其宜”而不產生消極作用。對于這種新語義的出現,需將其置于先秦諸子的廣泛背景中去理解,而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齊俗訓》中出現的與“工匠”并舉的“宰庖”。在《淮南子·主術訓》中,也有類似的用法:“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斫也。”從表達的意思來看,這里的說法是對《老子》中的隱喻更為直接的引申:首先,君主不應隨意介入國家治理活動;其次,應把相關問題交給專門負責的臣下處理,專門負責的臣下則如“庖宰”或“大匠”掌握處理牲畜或木料的專門技藝一樣,也具備政治治理的知識與能力。對君臣關系的這種判斷是黃老之學的普遍主張,而聚焦于“宰庖”或“庖宰”,下文將繼續揭示出隱喻在概念建構過程中的工作機制。
上面這個隱喻形象,在道家譜系內或許源于《莊子·養生主》中著名的“庖丁”。“庖丁解牛”的故事眾所周知,但這個庖丁的身份實際上非常令人疑惑。如《周禮》所言,庖人被列入宰夫的行列,但實際上他負責的工作并非制作飲食,而是宰殺牲畜,如前文所言,無論莊子還是孟子,在提到這個身份的時候運用的都是這層意思。也就是說,庖丁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廚師(cook),而是屠夫(butcher)(2)對庖丁職能方面的粗糙化處理存在于海外研究界,如Roel Sterckx著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Cook Ding(Pelican Books,2019)便未能在自己的討論中充分討論廚師(cook)或宰夫與屠夫(butcher)或庖人之間技藝方面差異所產生的理論后果,雖然該書第九章(第417-433頁)也廣泛涉及了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但對早期治理思想的種種變化未做精細分辨。。庖丁這個隱喻在某種程度上非常重要,具有語義黏合器的作用,其將宰夫與匠人兩個形象聯系起來:從身份上看,庖人或庖丁屬于宰夫的一類,但從技藝的角度看,庖丁的技藝則與木匠高度相似,均關乎刀斧的運用——兩者的差異僅在于切削牲畜還是木料,而與晏嬰心目中宰夫調“和”食材的任務相去較遠。《莊子》強調庖丁神乎其技的刀工,其隱喻一方面保持了與早期存在的宰夫隱喻的字面上的連貫性,另一方面建立了與新出現的匠人隱喻的語義上的一致性,如前引《淮南子·主術訓》將兩者對舉,便是由其切削的技藝著眼。而庖丁的形象實際上可以被納入匠人的形象當中,這意味著在諸子書中,匠人隱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完成了對宰夫隱喻的替換,如《呂氏春秋·去私》仍以晏嬰意義上的庖人喻指君主:“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不過,《呂氏春秋》在運用這個隱喻的時候,雖然提及了庖人調和食材的原始任務,但并未將其作為建構“王伯之君”概念的語義要素,而是從庖人并不食用自己烹飪成果的角度,發展了《老子》“為而不恃”“功成弗居”的思想。這個討論角度,雖然與道家“不擾”式的政治策略相承接——君主在政治上的徹底退場是對國家治理活動絕對的不介入,但在表達這層意思時,并未利用有關烹飪技藝的語義要素,也因此與本文討論的概念建構方式殊途。
除以上例子,《淮南子·齊俗訓》中還有一段話進一步拓展了匠人的身份:“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爐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則?游乎眾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這段話告訴我們:其一,各種不同職分的工匠,若從技藝的角度著眼,均可被視為同類,對他們的描繪共同構成了喻指統治者的匠人類隱喻;其二,這里回答了我們所引用的《齊俗訓》的遺留問題——國家治理者的行為為什么是可控的且可以產生積極效果,而對此問題的解答,亦與道家“主逸臣勞”的設定密切相關。在以上兩個意義層面,這種隱喻的用法已經見于更早的諸子書中,如《孟子·梁惠王下》言: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斵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這里的木匠和“玉人”都被作為治理國家的匠人隱喻,且對他們活動的記載,表達了信任專業人員的專業技能這層意思——就像木匠或雕刻玉石的工匠具有專業能力一樣,治理國家也是一項專門的技能,君主也應該信任具備這種技能的專業人員。孟子的這個觀點,與《淮南子·主術訓》“主逸臣勞”的主張在某種程度上相對應,也與整個戰國時代要求選賢任能的思潮一致,其背景均為當時人們認為治理國家需要某種特殊的專門知識。這個主張,在我們討論的文本中,可被認為是由強調匠人特殊切削技能而引申出的另一個新的語義要素,國家治理者正因為像一位優秀的匠人一樣具有相關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其政治行為才像精確處理木料一樣是可控的且具有積極影響的。君主可能具備或不具備這種專門知識(黃老學派并不期待君主具備這樣的知識,但儒家、法家的態度則要復雜一些),但如果能充分信任具備這種專門知識的賢能之士,則同樣可以在不直接介入國家治理活動的同時,獲得最佳的治理效果。這些內容,涉及由《老子》到其后道家文獻中判斷良性政治的一貫立場,即在國家治理中,對可能受困于私智的君主說“不”,要求其避免多余的、負面的政治介入,但對可能具備專門政治治理知識的臣下說“是”,要求他們以適當的方式擔負治理國家的職責。那么,臣下的這種專業性來自何處呢?在道家文本中無疑是“道”,對此,《齊俗訓》已經以“規矩鉤繩”加以暗示。這里的“規矩鉤繩”之類木匠常備的基本工具作為實現他們工作技藝的“巧之具”,被視為具象性的事物,而從上下文可以很容易地推斷,其出場是作為道的物質載體,是《淮南子》文本以可言說者引入不可言說者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表達實際是作為轉喻(Metonymy)在發揮作用以暗示道的出場,與本文主題略不相類,但此處“規矩”的用法在諸子書中極為特殊,事實上對其言說的主流仍然是隱喻性的。
如前文所言,對匠人隱喻的引入或與墨家相關,而“規矩”的隱喻可能是作為與其高度相關的項目被同步采用的——畢竟規矩是木匠用來確定木料分解方式的基本工具。如《墨子·天志下》有言:
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圜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儀法。
上文中的規矩無疑是對“天志”的隱喻,而對其喻指的觀念稍加變化,便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將其作為道或法度的隱喻表達。這個隱喻在諸子書中也多有所見,且常與喻指國家治理者的匠人隱喻同時出現,在《孟子》《荀子》《韓非子》和黃老學文獻中均有一貫的用例,而其最為具象化的表達,大約就是漢代帛畫當中手持規矩的伏羲女媧形象——伏羲女媧作為宇宙秩序的最高立法者,其手中掌握的木匠常用工具無疑可被視為天人之道的典型標志。
回到早期文獻,如《孟子·離婁上》曰:“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規矩,方員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告子上》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盡心下》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以上第一段引文中規矩的用法具有典型性,被作為堯舜或先王之道的隱喻,喻指政治原則,且公輸、師曠作為匠人的代表亦同時被言及;第三段引文中規矩的用法與其類似,只是隱喻的對象轉換為抽象的學術法則。但以上第二段和第四段引文中規矩的用法稍有變化,其中第二段引文中的規矩似被用以喻指抽象倫理原則的設定者,而第四段引文中的規矩似亦被作為轉喻使用,與“巧”的語義構成指代關系,亦與前文所引《淮南子·齊俗訓》中的用法相類。
再如《荀子·王霸》曰:“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禮論》曰:“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以規矩隱喻“禮”。再如《韓非子·有度》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用人》曰:“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以規矩隱喻“法”。亦如《管子·法法》曰:“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圣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形勢解》曰:“以規矩為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同以規矩隱喻“法”。以上種種,均以規矩為各種抽象法則或行為指導原則,如對道、禮、法的隱喻,并多將之置于政治性的言說語境當中。如不考慮其在政治語境中的特殊運用,則規矩的上述意思所獲得的廣泛認可一直延伸到現代漢語里,今天要求某人“懂規矩”與兩千余年前的用法幾無差異。
規矩隱喻的出現,是為了對匠人隱喻加以進一步解釋,即解釋國家治理者在實踐中何以能夠正確行事,正如匠人適當地分解切削木料是依賴對規矩的掌握一樣,治理者能夠開展、運作某種良性的政治活動亦是由于對某些抽象原則的把握與遵循。雖然不同的人可以對政治活動的不同參與者持不同的臧否態度,甚至從整體上對這種活動加以拒斥,但上述隱喻的內容與工作機制在諸子書中卻是一以貫之的。如《莊子·馬蹄》所言:“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莊子》雖然對“治天下”這件事整體上持否定態度,但在言說過程中,匠人與治天下者、規矩與文中未曾明言的治理之道的隱喻關系仍然存在,其運思方式與前文所討論的文獻如出一轍。
三、守官與守道
與《左傳》中的宰夫隱喻相比,諸子書中利用匠人隱喻建立起來的國家治理者的新形象要復雜得多,而這種說理過程中隱喻選擇的替換,則標志著政治思考的深化與復雜化。回顧宰夫的隱喻,其在運用中至少包含三個要點:其一,喻指君主本人;其二,君主政治技藝的核心在于調和;其三,政治活動主要被視為貴族宗法體制內部的問題,相關活動被局限在君臣關系的軸線上。而就匠人的隱喻而言,其同樣作為結構隱喻在上述三個方面所發生的重大語義變化:其一,喻指廣義上的國家治理者,即匠人喻指的對象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作為臣下的賢能者,而在多數用例中似乎更偏重于喻指后者,特別是在黃老學的語境中,君主本人反而應和國家治理活動保持距離。其二,國家治理者的技藝重點在于利用、追隨某種可被視為超級治理工具的道或抽象原則,而此概念進一步通過規矩的隱喻被引入討論的場域中。對此,不同學者可以強調不同的甚至完全對立的方面:如果治理行為遵循道,其后果就是積極的、正面的、良性的;相反,其后果就是消極的、負面的、惡性的。這回答了為什么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可以信任作為人臣的賢能之士——因為作為人臣的賢能之士像優秀的匠人掌握規矩一樣掌握治國之要道。其三,當掌握治理國家知識的賢能之士成為治理活動的主導者,那么這種活動實際上已經溢出了君臣關系的維度,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宗法制度內部的問題,而在廣泛的意義上涉及對于社會與民眾的治理,并將社會與民眾視為國家治理問題的主要對象。如果說在《左傳》描述的時代,政治問題仍然被想象為如何處理君臣之間或貴族體制內部的問題,那么到了諸子的時代,政治問題則顯然變得更加復雜,廣義上的統治者集體如何治理或面對構成國家主體的被統治者群體,則成為緊迫的新問題。當政治活動被限制在周代宗法貴族內部時,對于晏嬰這樣的反思者來說,存在著現成的可以作為參照標準的傳統制度——“周禮”,而以此作為政治行為的參照標準,也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得到廣泛的認可。但當國家治理活動進入如何治理廣大被統治者群體的未知水域,上述制度上的保障就不再有跡可循,在原有的周禮失效的同時,留下了大片的政治理論空白有待人們去填補。如何填補這個空白就是先秦諸子用力最多的思想方向,而在某種程度上講,他們的思考均以不同方式向所謂“道”的國家治理原則聚焦,在此意義上,規矩作為道的隱喻,被引入對于匠人作為國家治理者的隱喻的進一步說明中,則是順理成章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道的存在僅限于普遍的抽象原則,如果將其落實在現實治理活動中,仍需要大量的制度設計工作,反觀先秦諸子,大都曾明確致力于這種類型的工作,而其中或以黃老學與法家最具代表性。于是,道的現實化意味著大量的制度創制工作,而對這種工作的新言說與想象也成為戰國中后期的廣泛話題,無論后世所謂的儒家“托古改制”,還是出現在《周易·系辭下》中大量有關圣人“觀象制器”的描述,實際上都在以不同方式解釋著新興的、必然成為思想焦點的制度創設工作。尤其是《系辭下》中的表述,典型地以隱喻的方式為道的現實化提供注腳:道通過顯現為可被傳說中的圣王直接解讀的天地自然之“象”,引導出器物制度的制作設計,最終達到“以教天下”“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理想效果,而文中提到的每一位古之圣王都以匠人的形象出現,恰與前揭諸子書中出現的匠人隱喻相互呼應(3)王中江教授曾討論過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起源的“圣創論”,參見王中江:《圣創論的圖像和形態:社會起源論的中國版本》,《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這種君主或制度建立者匠人化的想象,正反映了戰國時期的一種思潮。如果我們將其內容視為“神話”,這些神話則不具備回溯性的歷史或人類學價值,從隱喻的角度看,它們是新思潮的產物。。這些內容,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制作的意思,可以說來自與匠人隱喻捆綁在一起的規矩隱喻,而最早強調圣王具有這種制作能力的文本,則是《墨子·辭過》——我們已經知道《墨子》與匠人和規矩隱喻的采用均高度相關。
以隱喻的替換為標志,我們可以很方便地識別出不同時代說理策略的變化和同步出現的新思想,從思想轉變的角度看,上述過程中“規矩”隱喻的出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其在宰夫隱喻中沒有突出的顯現,但卻是匠人隱喻的不可忽視的伴生物,標志著正當行為必須遵循更高位階的抽象原則。嚴格來說,規矩所喻指的道,作為高度抽象的概念雖然是公認的諸子共同追求的理論目標,但在前諸子時代卻未形成多少理論共識。這個語詞在更早的文獻中不乏用例,只是其語義內容與諸子相比較為狹窄,一般都有專門的指向而不被作為普遍化的原則看待。回到前文列舉的齊景公召虞人不至事,《左傳》中附有一條據說是孔子的評價,即“守道不如守官”。這個評價與荀子所謂的“從道不從君”相比,具有巨大的反差,而其中對“道”的理解,也極不同于總將其視為最高的、普遍的奠基性概念的戰國諸子,無論這段評價是否是孔子或儒家的言語,其反映的更是春秋時代理解問題的方式。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曾對此句有專門討論:
麟案:《賈子·道術》云:“道者,所從接物也。”然則散言則三達道也,析言則所從接物者亦曰道。臣之接君,《荀子·大略》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架,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乃臣接君之道也。故司常呼象路,以朝者為道車,有道右、道仆之官。謂君臣相接為道,其車遂由此名。《士冠禮》:“委貌,周道;章甫,殷道;牟追,夏后氏之道。”注:“皆所常服以行道。”實亦由君臣相接為義,故所招不當其官,則可以不守是道[3]678。
章氏在此對道的窄化理解應該說更貼近文本的原意,他并未將其視為容納天地、貫通古今之常道,而將其限制在君臣交往關系的范圍內。這種有限的道,在章氏的解釋中,實則受制于更具有政治行為規范意義的“禮”,而此即章氏引荀子言語的用意所在。虞人不奉命,理由在于“守官”,即值守其職分應有之行為原則,而這些內容,均由周禮所規定,也就是說,“守官”即“守禮”,而齊景公的種種行為之所以招致非議,亦因其不能“守禮”,晏嬰的批評也仍是希望能讓齊侯回歸禮的軌道而以“和”的方式使君臣交往保持正常運作。這種狀況,只有在封建宗法控制下的貴族制度依然保持最低限度的有效運作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在此背景中,禮的地位與內容是毋庸置疑的,并受到傳統與習俗的有力保護,而所謂政治活動,即讓君臣在此禮的框架內遵循固有的要求而行動。無論君臣,值守其職分的標準即在于遵循現有的禮制,而無須進一步轉向對更普遍的、更具包容性和抽象的道的訴求,或者說無須設想某種更高層級的概念來維護禮的現實性——這種更高層級的概念的力量來自傳統與習俗:宗法制中貫徹的血親—姻親盟約原則和周天子封建諸侯時形成的層級化的領主間的效忠關系,甚至貴族社會中對優良品質或德性的一致承認。此處《左傳》所言的“守道”,雖然不能將其與“守官”或“守禮”對立起來,但也只能將其視為由現實存在之禮制推導出的對于君臣交往方式的事后總結,但對于其合理與否,則應視禮制的實際要求而判定,而不能賦予這種道超出禮之上的優先性。這也就意味著,由春秋時代對道的言說與思考,不能推導出現實的禮和與其相應的行為方式;對于政治活動而言,以高度遵循傳統的方式“守官”或“守禮”反而具有無可置疑的優先地位。
如果可以據此總結說,春秋時代禮未全崩、樂未均壞之時,如果也存在著對于種種道的思考,那么其則是一種基于“循禮以見道”的思考模式,這就是為什么《左傳》中斷言“守道不如守官”,也是為什么宰夫的隱喻相對單純,既不涉及對額外的行為標準的討論(如規矩),也不涉及對政治治理效果良性與否的預判的原因所在。在諸子那里,上述問題則變得復雜很多,隨著舊制度被摧毀,出現了大量的有關人事安排、制度設計與治理方法的空白,而所有這些內容都需要新興的知識階層去填補,司馬談對諸子蜂起“此務為治者”的判斷大約便是來自對這種狀況的記憶。這種填補空白的工作在歷史上并非真的有章可循,實為擺在諸子面前的全新任務,而這也使得戰國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創造性的時代。在這一時期,諸子各持己說、取合諸侯,寫下了思想史上最有活力的一頁。在上述過程中,也形成了一個相對自由的思想市場,為了說服那些身為新權貴的潛在思想買主,每一位諸子都需要首先證明自己的觀點具有最高的合理性與普遍意義,于是,全新的至高無上的、最為抽象與普遍化的道的概念就應運而生——所有人都宣稱自己掌握了這種真理或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獲得了這種真理的一部分,而他們所提供的國家治理方案之所以有效,則完全是由于對這種真理或普遍恒常之道的演繹。對于自身思想的創造性,有的學派將對道的發現視為自己的新主張,比如老子和道家在申明自己言道的創新性時無所顧忌,有的學派則仍然更為小心地試圖將其與傳統聯系起來,比如孔子和儒家總希望通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方式來強化自己主張的權威性,但“古史辨”的努力早就告訴我們這種向后的回溯,不過是戰國通行的自重其義的方式而已。諸子關于道的思考,可以推演出種種甚至可能完全相互矛盾的制度設計和政治治理措施來,但他們整體上都基于一種“依道而立制”的思考模式去想象什么才是真正合規矩的、良性的政治行為。在這個背景下,在政治活動中號稱遵循某種抽象的道而非人工的、可改變的制度設計或治理措施,被認為具有更高的合理性,而后者的現實存在與操作上的差異或好壞高低之別,反映了設計者或參與者對道的理解與把握的程度——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如果所有的政治活動參與者都足夠真誠、智慧且具備應有的德性與能力,那么理想的制度將體現為“守道”與“守官”的完全合一,而對于任何人來說,盡到自己在政治系統中被規定的本分,就是對治理之道的充分實現——此即孔子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與上述背景相應,當關注政治活動中建設性要素與普遍規則的考量成為諸子的主流話語時,則標志著思想轉型的匠人隱喻也將成為重要的說理方式,這個隱喻與規矩的隱喻協同運作,可以將多種關乎賢能、良治、抽象規范與制度創造的思考集成在一起。
當諸子的思想廣為流傳并為我們所熟悉后,《左傳》中“守道不如守官”的論調反而變得難以理解,甚至成為需要專門加以討論的問題。匠人隱喻對宰夫隱喻的替換,表明了思想傾向在諸子時代的根本性轉變,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轉變過程無疑意味著大量新思想信息的涌現,但在我們所討論的政治維度上,有關“調和”的舊觀念也并未完全隱退。雖然宰夫的隱喻不再被以原有的方式加以采用,但孔子與儒家卻通過自己對舊時代禮制的溫情將晏嬰曾經表達出的政治上的“和”的思想繼承下來。
結 語
如果我們像晏嬰那樣,把春秋時代的貴族政治想象為某場盛宴的參與者,那么伴隨禮崩樂壞的歷史巨變,這場盛宴到戰國時代僅剩下遍地的杯盤狼藉,須待某種六合一掃的力量方可宇內澄清。戰國諸子,或許都在不同程度上期待這種力量的出現,并設想自己可以成為這種力量的一部分。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那樣,諸子為此而均辯稱自己擁有高度的思想權威,而對這種權威的證成,則往往與對傳統的回溯密不可分。不僅儒家喜歡回憶上古圣王,黃帝也被道家后學拉出來為之背書,而從更廣泛的角度看,類似的思路與做法似乎通行于戰國中后期,此即“古史辨”在神圣故事的復雜化過程中發現的古史的層累化增益。從故事的效果來看,在思想的表層,上述努力傾向于抹平歷史的真實變化,如果現有的一切仍然在歷史上有跡可循,那么來自舊時代的經驗、習俗與慣例總能為新制度的安全運作提供額外的保障——如《易傳》所表述的那樣,一切器物制度的創制均來自遠古圣王的智慧遺存而非時人的異想天開。
無論我們如何在價值層面評價上述思想傾向,研究性的反思均不必被諸子所講述的故事與由此而產生的思想表面上的連續性所阻止,誠如馬克思的偉大發現,歷史的轉變一定會在哲學上留下痕跡,而宗法封建和與之相應的貴族社會的崩潰會對諸子產生無法否認的后果。回到政治治理語境,對于上述痕跡,可以從類似“道”這樣的標志性概念的語義變化中加以探索,亦可以嘗試下沉到體現上述表層變化的底層說理機制當中尋求。從后面(下沉到底層說理機制當中尋求)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似乎更有價值,而對概念變化的討論往往容易陷入由簡單到復雜、由具體到抽象的線性發展模式,有時反而不易讓我們識別出思想上的重要變異。
在這種意義上,對于隱喻的考察具有無可替代的特殊意義,作為未曾被古人加以主動提煉與反思的說理方式,作為曾被現代分析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的思維機制,隱喻的運用關乎特定時代的思想底層運作,而我們可以將其作為測定或度量思想轉變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