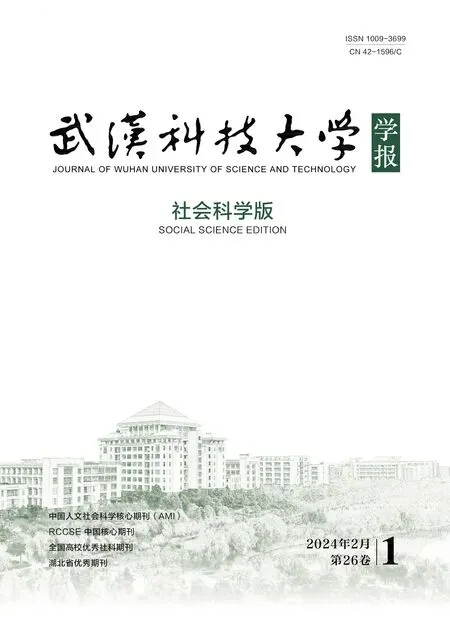歸納使真者與真之定義
陳 曉 平
(華南師范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廣東財經大學 智能社會與人的發展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320)
一、從使真者理論談起
關于真的理論(簡稱“真理論”)可說是最為悠久的哲學理論之一,亞里士多德的符合真理論堪稱經典的真理論,20世紀前半葉異軍突起的塔斯基(Alfred Tarski)的真理論,也宣稱是對亞里士多德的符合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不過,近二三十年以來,使真者理論(truthmaker theory)聲名鵲起,似乎大有取代符合真理論之勢。
何謂“使真者”(truthmaker)?顧名思義,使真者就是真理制造者或使之為真者。使之為真的對象被稱為“持真者”(truthbearer),一般被看作是命題或語句;相應地,使真者理論也就是關于如何使命題或語句為真的理論。當我們深入使真者理論的內部,便發現它實際上不是一個具體的理論,而是一個理論框架或綱領,里面的內容可謂豐富多彩、名目繁多,甚至讓人應接不暇。
其實,這并不奇怪,因為人們真正感興趣的并不是有沒有使真者,而是使真者是什么樣子的。這樣一來,幾乎所有的真理論都屬于使真者理論,因為它們都對使真者的模樣或多或少地給予某種刻畫。例如,傳統的符合真理論就是一種使真者理論,它強調使命題得以為真的是“對事實的符合”,因此,命題對事實的符合或事實本身就是使真者。當然,使真者理論不限于符合真理論,實用真理論、等同真理論和融貫真理論等都可納入其中。要說有什么真理論超出使真者理論的范圍,那就當推塔斯基的基于T模式的真理論,因為塔斯基真理論的特點就是對使真者的淡化甚至取消,以致引起一股“收縮真理論”(deflationary theory of truth)的思潮。
收縮真理論也叫“非實質真理論”(insubstantial theory of truth),其目標就是削除“真”這個概念的實質內容,使之僅僅停留在語言分析的層面,而與事實或其他本體論機制無關。在筆者看來,收縮真理論或非實質真理論是誤入歧途的;與之對照,如果說使真者理論有什么積極意義的話,那就是它看起來是對收縮真理論的反動和向實質真理論的回歸,因為對使真者的強調似乎就是要凸顯真理的某種實質,即使真者理論所志在必得的“真理的本體論基礎”。
關于收縮真理論與使真者理論之間的對立性,M·大衛(Marian David)評論道:收縮論者“拒絕事實或事態的本體論,他們應該也拒絕阿姆斯特朗(D. M. Armstrong)的使真原則本身”[1]147。然而,使真者理論的領軍人物阿姆斯特朗似乎并不這么看,他說:“這里提出的建議是,我們可以接受這兩種理念(符合論和收縮論,后者也叫冗余論——引者注),兩者都告訴我們某些有關真的本質的真東西。”[2]128的確,阿姆斯特朗作為一位還原物理主義者(reductive physicalism),主張命題的真可以還原為它的物質基礎(即事實),正如他在心靈哲學上的主張:心靈可以還原為大腦結構。在這個意義上,命題的真是非本質的和冗余的。對此,大衛又給出這樣的評論:“阿姆斯特朗認為使真理論是符合真理論的一種形式,同時他又試圖接納一些收縮論的元素,以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達到符合論和收縮論之間的某種妥協。”[1]146
關于符合真理論,阿姆斯特朗承認它與使真者理論密切相關,他說:“在較深的本體論層次上,符合論告訴我們,既然真理需要使真者,那么世界中存在某些事物符合那個命題。那個符合者與使真者是相同的東西。”[2]128然而,阿姆斯特朗話鋒一轉,又說:“對于真理和使真者之間的符合關系我們將說些什么?我們將說的首要和基本的東西是否定性的,即:它不是一對一的關系。”[2]128對于這種非一對一的符合關系或使真關系,阿姆斯特朗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析取命題“p或者q”:無論是p真而q假,還是p假而q真,都能使“p或者q”成為真的,可見,“p或者q”至少有兩個使真者,即p的使真者和q的使真者。
對于阿姆斯特朗關于非一對一符合關系的論述,筆者是不以為然的,因為他把演繹邏輯的推理前提也看作使真者。不錯,以p為前提可以推出p或者q,以q為前提也可推出p或者q;但是,演繹推理的作用是“保真”或“持真”,而不是“造真”或“使真”。這里存在對使真者和持真者的混淆,其結果是把符合關系弄得雜亂無章、無所適從,并且引出“無關使真者難題”。
阿姆斯特朗在使真者理論中引入“蘊涵原則”(entailment principle),即:如果p蘊涵q,并且T是p的使真者,那么,T是q的使真者。他特別指出,這里的“蘊涵”不是經典邏輯的蘊涵,因為經典蘊涵關系“將使任何偶然真理成為任何必然真理的使真者”[3]11。這就是一個無關使真者的例子。為了避免無關使真者的出現,阿姆斯特朗必須對經典邏輯的蘊涵規則加以限制,至于如何限制,他承認自己尚未考慮成熟。
在筆者看來,阿姆斯特朗所面臨的“無關使真者難題”可以輕而易舉地得以消除,只需在符合使真關系與演繹持真關系之間做出區分,進而在符合使真者與混合使真者之間做出區分,而無需對任何演繹推理規則加以限制。具體地說,T是p的符合使真者,通過蘊涵規則進行演繹推理,p的真保持性地傳遞給q,因此,T是q的混合使真者。
由于阿姆斯特朗沒有區分符合使真關系和演繹持真關系,也沒有區分符合使真者和混合使真者,這使他在“無關使真者問題”面前顯得手忙腳亂,捉襟見肘。其結果是,他不得不放棄一對一的符合關系,以致連“真”的定義也難以給出,只給出如下使真者原則:
“p(一個命題)是真的,當且僅當,T[世界中的某個實體(entity)]存在,并且:T使p成為必然(necessitation),而且p憑借(in virtue of)T而成為真的。”[3]17
顯然,這個使真者原則不是關于“真”的定義,因為連接詞“當且僅當”的兩邊都包含了“真”;如果作為真之定義,那便是錯誤的“循環定義”。該原則作為一個雙條件句,斷言世界中的某個實體T的存在是命題p為真的充分且必要條件,并且此條件具有必然性。這個表述包含了阿姆斯特朗稱之為“使真者極大主義”(truthmaker maximalism)的思想,即“每一個真理都有使真者”[3]17;也包含了他所謂的“使真者必然主義”(truthmaker necessitarianism),即“一個真理的使真者使它必然為真”[2]115。可以說,阿姆斯特朗的使真者原則就是使真者極大主義和必然主義的合取,雖然不是關于“真”的定義,但卻明確了使真關系的某些特征。
然而,阿姆斯特朗對于使真關系的必然性給出一種特別的解釋,即所謂的“隨附性”(supervenience),從而得出還原主義的結論,即命題的真可以還原為它的本體論基礎(即事實)。他宣稱:“由于隨附者在本體論上沒有比它的基礎多出什么,‘本體論的免費午餐’的信條使我們擺脫了多余的實體。”[2]13這就是說,作為隨附者的真和使真關系可以還原為它的本體論基礎(即事實或事態),而無需另外付出本體論的代價;換言之,真可以免費使用它的使真者,從使真者那里獲得真是一樁無本生意。
由此可見,阿姆斯特朗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繼承了收縮真理論的觀點,即命題的真是非本質的和冗余的,因而可以削除。大衛對阿姆斯特朗的使真者理論的總體評價是:“嚴肅地對待使真者,而不嚴肅地對待真和使真性。”[1]147既然真和使真者之間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東西,那么阿姆斯特朗的使真者理論便只剩一個框架,其中既沒有關于真的定義,也沒有關于真如何從使真者產生出來的機制,這不能不說是使真者理論的一個嚴重缺陷。
總之,就使真者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背離收縮真理論而向實質真理論回歸(探求真理的本體論基礎)的取向而言,筆者對它給予肯定,并將沿此方向加以推進;但就使真者理論在具體內容上的龐雜和空泛,特別是缺少真之定義和使真機制而言,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之加以梳理整飭、正本清源。為此,本文首先對收縮真理論的主要依據——塔斯基的T模式——進行批判性考察。
二、塔斯基的T模式對使真者的缺失
塔斯基從語義學的角度提出著名的關于真之定義的T模式,他堅稱其理論是對亞里士多德的符合論的繼承。然而,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塔斯基的T模式對符合論的發展并未起到實質的促進作用,反倒使其對立面之一即冗余論(redundancy theory of truth)得到長足發展,進而形成關于真理論的新的研究綱領,此綱領被稱為“收縮論”(deflationism)。收縮論的倡導者包括蒯因(W. V. O. Quine)和霍里奇(P. Horwich)等,他們主張:斷言一個語句是真的就是斷言該語句本身,除此之外,真再沒有更多的性質。收縮論的主要根據就是塔斯基的真之T模式,即:
T:“p”是真的,當且僅當,p(1)這里對塔斯基的T模式在表述上略作改變,原表達式是:X是真的,當且僅當,p。原表達式在這里記為Tx,其中的X大致相當于“p”。對于這兩種表述之間的區別,下面將給予討論。參見塔斯基:《語義性真理概念和語義學的基礎》,載馬蒂尼奇編《語言哲學》,牟博、楊音萊、韓林合譯,商務印書館,1998,第85-86頁。
T模式中的p可以代入任何一個命題,例如:“雪是白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塔斯基強調,左邊加引號的“p”是該命題的名稱,屬于元語言,右邊不加引號的p是命題本身,屬于對象語言。請注意,T模式的右邊只有p,以此來定義其左邊:“p”是真的。這無異于說,“真”這個謂詞是無實質內容的,因而可以去掉;如果說“真”有什么作用的話,那就是使T模式左邊“p”的引號連同“真”都在右邊消失,右邊只剩下孤零零的p。正是在“真”可以省略的意義上,真之收縮論得以提出。真之收縮論又被稱為“去引號理論”(disquotational theory)、“極小理論”(minimalist theory)等。
塔斯基宣稱,T模式屬于符合論,因為等值號左右兩邊的p是相符合的。不過,這是元語言與對象語言之間的符合,而不是語言與事實的符合,這正是T模式區別于傳統符合論的地方。傳統符合論是指語言與事實的符合,而不是語言與語言的符合。塔斯基把傳統符合論的真之定義轉述如下:
T*:“p”是真的,當且僅當,p是事實(即p所述是事實)(2)這里的T*是原文中的(T″),在表述上略有改變,即將原來的X改為“p”。參見塔斯基:《語義性真理概念和語義學的基礎》,載馬蒂尼奇編《語言哲學》,牟博、楊音萊、韓林合譯,商務印書館,1998,第103頁。
此定義是朱霍斯(B. von Juhos)為彌補T模式的非本質性而作的修正,朱霍斯指責T模式作為真之定義具有“令人不可接受的簡短性即不完全性”。也就是說,T模式缺失了重要的內容,即p與事實之間的符合關系,故而在T*模式中作了補充。但是,塔斯基并不接受T*模式,他指出:“一般來說,那位作者的整個論證建立在一個明顯的對語句與它們的名稱的混淆上面……這是因為在短語‘p是真的’和‘p是事實’(即‘p所述是事實’)中,如果‘p’由一個語句而不是語句名稱所替換,那么這兩個句子都變成無意義的了。”[4]103
在塔斯基看來,只要在p上增加謂詞,無論是“……是真的”,還是“……是事實”,甚或是“……是存在的”等,都必須用加引號的“p”作為主詞,否則會因為不合語法而成為無意義的表述。正因如此,T模式右邊不加引號的p只能孤立地出現,而不能對它再給予限定。然而,T*模式卻把“……是事實”加于p上而非“p”上,因而是無意義的;但若加到“p”上則成為:“p”是事實,這雖然合乎語法因而有意義,但卻是假的,因為加引號的“p”是語句p的名稱,而任何名稱都不是事實。總之,塔斯基認為,T*模式要么無意義,要么是假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在筆者看來,塔斯基在這里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即混淆了語法與語義,這種混淆使他把關注點放在語句名稱的語法結構上,而未放在語句為“真”的實質意義上,以致他最終給出一個比T模式更為空洞的真之定義,并且用以取代T模式。此模式是:
Tx:X是真的,當且僅當,p[4]93
Tx模式與T模式的唯一區別是用X取代“p”。為什么塔斯基要這樣做呢?那是因為,塔斯基把T模式中的“p”不僅看作語句p的名稱,而且著眼于它的語法結構。從名稱的語法結構上講,p的名稱可以是多種多樣的,而“p”只是其中一種,塔斯基稱之為“加引號名稱”(quotation-mark names)。另一種呈現名稱的方式叫作“結構描述性名稱”(structural-descriptive names),例如,把雪是白的代入T模式可得:
“雪是白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
(1)
式(1)中,“雪是白的”是語句的加引號名稱。如果采用結構性名稱替換加引號名稱,一種可供選擇的呈現方式是:
依次由“雪”“是”“白”“的”這四個字構成的那個語句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
(2)
在塔斯基看來,作為真之定義的例子,式(1)和式(2)是完全等價的,“把語句放在引號中絕不是構造語句名稱的唯一方法”[4]85。既然一個語句的名稱不限于加引號,那么我們應當用X而不是“p”作為語句p的名稱,否則我們就會以偏概全。這就是塔斯基煞費苦心地用Tx模式來取代T模式的原因。
然而,Tx模式作為真之定義的不恰當性是顯而易見的,其左右兩邊分別涉及X和p,簡直就是把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串符號硬是用“當且僅當”連在一起。如果說T模式作為真之定義是空洞的,但其共同元素p至少使左右兩邊還有某種聯系,Tx模式卻把這僅有的一點聯系也去掉了,幾乎讓人不知所云。
Tx模式和T模式作為真之定義都是空洞的,定義的右邊只能孤零零地出現p,這便導致朱霍斯所說的“令人不可接受的簡短性即不完全性”。T模式的不完全性是什么?朱霍斯說是缺失了使p為真的“符合事實”,而“符合事實”就是一種使真者。其實,Tx模式和T模式右邊的孤零零的p不僅缺失了符合論使真者,而且缺失了一切使真者,從而為收縮真理論或非實質真理論大開方便之門。收縮真理論的最大缺陷是沒有給出判別一個命題之真假的實質性標準。
舉例來說,由T模式可得“‘雪是白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也可得“‘雪是綠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綠的”。這兩個語句都是對T模式的正確例示,并無高低優劣之分。人們不禁要問:“雪是白的”和“雪是綠的”這兩句話究竟哪個是真的?對此,T模式保持中立,不做任何回答,其平庸性和空洞性由此可見一斑。
達米特(M. Dummett)曾經精辟地指出:“符合論表達了真理概念的一個重要特征,但這個特征在公式——‘p’是真的,當且僅當,p——中卻沒有表達出來,并且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考慮這個特征。這個特征是:一個陳述是真的,僅當世界上存在某個東西使該陳述為真。”[5]244達米特所說的世界上“使該陳述為真”的那個東西就是該陳述的使真者,符合真理論應該給出真理的使真者,即真語句對事實的符合,但T模式沒有做到這一點。
三、為塔斯基的T模式添加使真者:符合真理論與等同真理論
朱霍斯為T模式補充了“p是事實”,從而提出T*模式。朱霍斯的這一補充是實質性的,它把“p”與p的符合關系從T模式的元語言與對象語言之間的符合,改變為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符合,相當于為塔斯基的T模式添加了使真者。T*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回到傳統符合論,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塔斯基T模式的優點。T模式的優點在于,它關于元語言與對象語言之間的符合關系滿足弗雷格(G. Frege)的一項要求,即:觀念(語言)只能與觀念(語言)相符合,而不能與其他東西相符合。既然使真者要求語言與事實符合,那么這兩種符合關系如何協調?這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需要給予細致的探討。
弗雷格指出:“用一個事物與觀念(idea)做比較時,僅當該事物也是觀念,這一比較才是可能的。于是,如果第一個完全符合(correspond perfectly)第二個,它們將重合(coincide)。但是,當真被定義為一個觀念與某些實在事物相符合的時候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實在(reality)不同于觀念,這一點是絕對實質性的。”[6]202一方面,由于實在不同于觀念,某個觀念符合某個事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傳統符合論正是用觀念與事實的符合來定義“真”的。因此,弗雷格認為,傳統的符合真理論是不成立的。按此標準,雖然T*模式所涉及的“p”與p之間的符合是成立的,但p與事實之間的符合是不成立,故而T*模式作為真之定義在總體上是不成立的。
在筆者看來,弗雷格的符合原則有一半是對的,另一半是錯的,這取決于對 “符合”做何解釋。如果把“符合”解釋為“等同”(即弗雷格所說的“完全符合”),那么只有同質的兩個事物之間才有可能具有這種關系,否則,即使兩個東西完全重合也達不到等同。反之,如果把“符合”解釋為兩個事物之間的某種“同構性”(isomorphism),那么即使那兩個事物不是同質的,它們之間也可能具有符合關系。例如,一個人的照片與那個人的形象具有某種同構性,盡管是不同質的,我們也可說那張照片符合那個人,但卻不能說,那張照片等同于那個人。類似地,雖然觀念和事實是不同質的,但是如果二者之間具有某種同構性,我們仍然可以說,那個觀念符合事實,因而是真的。
問題在于,我們憑什么說一個觀念與某個事實之間具有同構性?按照康德的觀點,事實的最后根基是自在之物,而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因此,我們永遠不能說,一個觀念與自在之物之間具有某種同構性。僅當人們運用先驗范疇對那些源于自在之物的感覺材料加以整理之后,才能對現實情況有所認識,進而才能談論一個觀念與這個被認識的現實情況(即事實)之間的同構性。不過,這個被認識了的現實情況已經不是事實本身,而是人們通過先驗范疇加以整理的現象,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觀念化了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所謂一個觀念與一個事實之間的比較,其實是一個觀念與另一個觀念之間的比較,只是后者比前者具有較強的客觀性,不妨稱之為“事實性觀念”,即康德所說的“經驗現象”。在我們對“事實”作了康德式解讀之后,便可對T*模式給予進一步的辯護。
弗雷格提出“觀念只能與觀念符合”的原則本來是為證明傳統的符合真理論是錯誤的,因為觀念與實在是絕對地不同的。我們則反其道而行之,表明傳統的符合真理論是有其本體論根據的,因為觀念與實在只是相對地不同,而非絕對地不同。接下來的問題是,那種相對客觀的事實性觀念與事實是等同關系嗎?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從康德的立場出發,壓根兒沒有什么獨立于任何觀念的事實,除非它是自在之物,而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因而不可能成為事實。這樣一來,我們便在觀念與事實之間建立了一種等同關系,即事實等同于事實性觀念。
前面談到,等同是“符合”的一種意思,即弗雷格所說的“完全符合”。“符合”的另一種意思是“同構符合”。同構符合的雙方雖然在質上或其他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但在結構上具有某種一一對應的關系,如飛機原型與飛機模型之間具有同構符合關系。如果說,等同符合是弗雷格所意指的,那么同構符合則是弗雷格所忽視的,這使其對傳統符合論的批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弗雷格宣稱:“只有一半為真的東西是不真的。真不能是或多或少的真。”[6]202按此說法,除了等同關系就沒有其他符合可以作為真理的標準;根據同構符合原則所確定的“真理”只是“或多或少的真”,因而是不真的。即便是一個人的照片,對于這個人來說也只是同構符合,因為二者畢竟不是等同的。那么,我們能說這張照片是這個人的真實寫照嗎?對此,常識將給予肯定的回答。傳統的符合真理論也正是在常識的意義上說,如果一個命題(同構地)符合事實,那么它就是真的。
現在,我們將把傳統的同構符合真理論與弗雷格暗含的等同符合真理論結合起來,亦即把常識的直觀性與命題意義的精準性結合起來,從而給出一個比較健全的符合真理論,其基本思想是:命題的意義(meaning)包含兩個層面,即涵義(sense)和指稱(reference),涵義是語詞性觀念,指稱是事實性觀念。作為指稱的事實性觀念與事實是等同符合的,作為語詞性觀念的涵義與事實是同構符合的。如果一個命題滿足這兩種符合關系,那么該命題就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
不難看出,這個符合論真理定義是在弗雷格的意義理論的基礎上給出的。首先,命題的意義被分為兩個層次,即涵義和指稱,這是弗雷格對語義學的重大貢獻。其次,把涵義和指稱分別稱為“語詞性觀念”和“事實性觀念”,雖然弗雷格沒有這樣明說,但這是其理論的暗含之義。由于對任何事實的認識都是在一定的思維結構——康德所說的先驗范疇——之中完成的,因此,只要作為指稱的事實性觀念與事實之間具有等同符合的關系,那么,作為涵義的語言性觀念與事實之間的同構性符合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這是因為一個命題的涵義與指稱之間具有同構關系。例如,“雪是白的”這個命題的涵義與它所指稱的事態之間必然是同構的,否則涵義和指稱之間便成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了。因此,一個命題為真的關鍵還在于其指稱與事實之間的等同符合。如何達到這一點,我們將在下一節進行討論。在此,我們還將對弗雷格的意義理論作進一步的挖掘和清理。
弗雷格的另一個著名觀點是:真思想就是事實。他說:“什么是事實?一個事實是一個真實的思想。而科學家們肯定不會認為那些依賴人們變化著的心態的東西是科學的堅實基礎。”[6]215我們知道,弗雷格把命題(語句)所表達的思想看作命題的涵義,于是他的這一說法相當于:真涵義就是事實。乍看上去,弗雷格似乎是把涵義等同于事實,實則非也,因為他這句話的另一層意思是:假涵義不是事實。既然命題的涵義有真假之分,而事實沒有真假之分,這便表明涵義不是事實。與之不同,作為指稱的思想對象沒有真假之分,只有存在與不存在之分:思想對象如果存在則等同于事實,如果不存在則空有其名,只剩下它的語言表達方式,即涵義。換言之,如果命題的指稱存在,那么它等同于事實;如果命題的指稱不存在,那么它蛻化為涵義(3)這既是對弗雷格指稱概念的引申,也是對其指稱概念的修正。弗雷格把語句(命題)的指稱看作真值,筆者以為這是他的一個嚴重失誤。參見陳曉平:《專名、摹狀詞和命題的涵義與指稱:兼評弗雷格的意義理論》,《哲學分析》2012年第6期;陳曉平:《心靈、語言與實在》,人民出版社,2015,第169-171頁。。
這意味著,命題的指稱是動態的,它游移在兩個靜態的終端之間:一個終端是事實,另一個終端是涵義。命題指稱的這種動態性使它實則是一種意向性,其意向目標指向客觀世界,不妨稱之為“指稱意向”。如果指稱意向在客觀世界能夠落實,即有對應物,那它便進化為它的終點即事實,二者是等同關系,并使其涵義成為真的;反之,如果指稱意向在客觀世界不能落實,即沒有對應物,那便蛻化為它的起點(即涵義),并使涵義是假的。
進而言之,如果命題的指稱對象在客觀世界具有對應物,那么主觀世界的涵義與客觀世界的指稱(即事實)之間具有同構符合的關系,盡管二者在質上是不同的,即一個是主觀的、另一個是客觀的。與此同時,其指稱與事實是等同符合的關系,二者是同一個東西。正是在這雙重意義上,命題的涵義符合事實,因而是真的。反之,如果指稱意向在客觀世界沒有對應物,指稱則蛻化為涵義。在這種情況下,命題只有主觀的涵義而沒有客觀的指稱,因而沒有任何符合關系可言。
需要強調兩點:一、命題的涵義不符合事實的確切意思是:沒有事實可被它符合,而非它有另一個不同的事實;二、命題的涵義符合事實的雙重性是一次性完成的,即命題的指稱與事實等同符合的同時,命題的涵義與事實同構符合。
至此,我們對T*模式給予新的解釋和辯護,并用T*模式替換了塔斯基的T模式。這意味著,我們把符合真理論的使真者補充進來,從而把塔斯基的收縮真理論改造為擴展真理論。接下來的問題是:命題的指稱對象存在或不存在是什么意思?這實際上就是“何謂事實”的問題,這將把我們引向對“存在”問題的思考,這是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可以說,存在者就是最深層次的使真者。
四、歸納-符合使真者:使真者的雙層結構
當前流行的使真者理論有一個明顯的缺點,那就是對它的配對物持真者重視不夠,討論得不夠深入。按照一般的說法,持真者就是命題(或語句),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說法是粗略的,準確的說法應是:持真者是命題(或語句)系統。一個命題系統的真是一組命題的真,并且這組命題通過演繹推理而聯系起來,從而把基本命題的真傳遞到各個命題之上;那些真的基本命題就是演繹推理的前提或演繹系統的公理。演繹推理的這種性質叫作“保真性”,即:如果前提為真,必然地,結論也是真的。演繹推理的基本規則之一是同一律,即在推理過程中每一個概念的含義保持一致,包括“真”概念。這就是說,演繹推理所保持的“真”是單義的,而非多義的。
作為持真者的演繹推理系統只是保持真理,而不制造真理,因而不具備使真者的品質。具體地說,演繹推理所需要的真前提不是由它自己提供的,而是由歸納法提供的,至少是通過歸納法加以驗證的;因此,歸納法具有使真者的品質,它與演繹推理形成使真者與持真者的功能搭配,從而共同完成建立諸如科學理論的真理系統的任務。
關于演繹推理的保真性,需要強調兩點:其一,真具有單義性,否則“保真”所保的就不是同一個東西,因而也就無所謂“保真”;其二,保真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說,從前提的真得出結論的真是必然的,不存在反例。與之相比,歸納法的作用不是保真或持真,而是造真或使真,并且其前提與結論之間的關系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既然演繹推理所保持的“真”是單義的,那么,歸納法為演繹推理所提供的各種前提的“真”也必須是單義的。后面兩節將具體闡釋歸納法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以此表明歸納法作為使真者是合格的,故而稱之為“歸納使真者”。
歸納法有時也被稱為“歸納推理”,但自從休謨對歸納的邏輯性質提出質疑之后,人們發現,更恰當的名稱還是“歸納法”。歸納法至少可分為兩大類,即發現真命題的歸納法和驗證真命題的歸納法。最為基本的歸納法是由事件的相對頻率得出頻率極限的方法,頻率極限就是概率,故而這種方法也就是發現事件之概率的方法。萊欣巴赫(H. Reichenbach)最早系統地研究這種歸納方法,并稱之為“歸納認定法”。
歸納認定法的推導模式是:如果事件A在一定條件下出現的相對頻率是m/n,那么我們就認定(posit)A的頻率極限(即概率)為m/n;隨著觀察次數n 的增大,相對頻率m/n會發生變化,我們對概率的認定也一同變化。萊欣巴赫指出:“重要的一步在于認識到歸納推理并不意味著提出一個真命題,而只是提出一個認定:我們認定這個序列要按已觀察到的方式繼續下去。”[7]402概率是無限序列的頻率極限,不可能由有限的相對頻率而必然地得出,而只是一種具有或然性的不斷修正的人為認定的結果。萊欣巴赫又把這種方法稱之為“漸近認定法”。與之相比,演繹推理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這是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之間的根本區別。
與一般概率認定相比,對于概率1的認定尤為重要,因為概率為1的事件意味著該事件在一定條件下總是出現,即出現的相對頻率是n/n。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概率為1的事件在一定條件下是存在的,這便是關于“存在”的歸納定義。
定義一:一個事態是存在的,當且僅當,該事態在一定條件下總是出現,即概率為1。
此定義之所以被看作“存在”的歸納定義,是因為作為存在之根據的概率1是通過歸納法(即漸近認定法)得到的。由于漸近認定法的關鍵一步是把n/n的相對頻率認定為頻率極限(即概率),所以由“概率為1”定義的“存在”也具有人為認定的性質,因而具有主觀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色彩。這樣的“存在”概念也就為前文的符合真理概念所涉及的“事實性觀念”(或“觀念性事實”)提供了依據。
另需指出,此定義用“事態”(state of affairs)取代前面的“事件”(event),因為事態比事件更具穩定性,而概率為1的事件具有這種穩定性,故把“存在”一詞用于“事態”更加自然。相對而言,事件比事態更為多變,將非1的概率用于其上更加自然。可以說,事態是靜止的事件,事件是活動的事態,二者在原則上可以互換,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在“存在”定義的基礎上,我們很容易給出“事實”和“真”的定義,即
定義二:一個事態是事實,當且僅當,該事態是存在的。
定義三:命題p是真的,當且僅當,p所表達的事態是事實。
根據前一節的討論,我們可以把定義三左邊被賦予真性質的p看作命題的涵義,并加引號即“p”;其右邊被命題所表達的事態看作命題的指稱,并記為p,那么定義三可被重新表達為:
T^:“p”是真的,當且僅當,p是事實
顯然,T^模式正是T*模式,即為T模式增加了使真者,并且成為符合論的真之定義。根據定義二,所謂“事實”不過是“存在著的事態”;又根據定義一,“存在著的事態”不過是“概率為1的事態”。由于“概率為1”是歸納認定的結果,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觀性。這意味著,事實歸根到底不過是事實性觀念,它與命題指稱p之間的關系可以成為等同關系。正如前面對T*模式的分析,T^模式是雙重符合意義的真之定義,即命題涵義與事實之間的同構符合和命題指稱與事實之間的等同符合。
不過,這里仍然遺留一個問題:既然這里所說的“事實”在其本質上是一種觀念性事實,那么在什么意義上認為它具有客觀性?對此,筆者的回答是:對于事態概率為1的歸納認定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語言-實踐共同體的共識,其客觀性在于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這種主體間性的客觀實在性也就是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說的“內在實在”(internal reality),它不同于完全獨立于主觀世界的“外在實在”(external reality)。
在普特南看來,外在實在論預設了“上帝之眼”(God’s eyes),因而可以看到康德所說的自在之物。如果我們擯棄上帝之眼,而從人類之眼看待事實,那么事實就不能完全獨立于人的觀念而存在,而以某種方式依賴于人的觀念。普特南宣稱,他的內在實在論是對康德哲學的繼承——“我們讀康德時最好把他理解成第一次提出我所謂的‘內在論’的或‘內在實在論’的真理觀的人,盡管康德本人從未道破這一點”[8]66。
普特南明確地指出內在實在論的實用主義特征,他說:“在內在論者看來,‘真理’是某種(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并不存在我們能知道或能有效地想象的上帝的眼光;存在著的只是現實的人的各種看法,這些現實的人思考著他們的理論或描述為之服務的各種利益和目的。”[8]55-66普特南把“真理”看作現實的人們為其“各種利益和目的”而達到的“合理的可接受性”,這樣,真理便與實用主義密切地關聯起來。
無獨有偶,萊欣巴赫在為歸納認定法進行辯護的時候,也把它的合理性看作實用的合理性。他指出:“在這種考慮下,漸近認定的方法才找到其合理的根據。如果有什么目的要達到的話,歸納推理是唯一可以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我們知道歸納推理不能夠被當作發現真命題的工具,而是當作發現認定的工具,并且我們還知道,我們并不是由真假的觀點,而是由我們所能走的最有利的步驟的觀點而推出我們的結論來的。”[7]408-409
我們把命題的“真”定義為“符合事實”,“事實”定義為“存在著的事態”,“存在著的事態”定義為“概率為1的事態”,而事態的概率是由歸納認定法得到的,這意味著,使真者具有雙層結構:上層是符合真理論及其真之符合定義,即T^模式(亦即T*模式);下層是實用存在論及其存在之概率定義。由于概率是由歸納認定法得到的,存在之概率定義相當于存在之歸納定義。于是,我們把使真者的這一雙層結構稱為“歸納-符合使真者”,它是由歸納使真者和符合使真者結合而成。
再次強調,這個雙層結構的下層——關于事實或存在的歸納定義——是相對于語言-實踐共同體而言的。也就是說,對事態概率的歸納認定是一個集體行為,而非個人行為。但是,一個事態的概率一旦被共同體認定為1從而成為事實,這個事實便成為該共同體的共識,當再次辨認有關這個事實之命題的真假時,不必重復初始認定事實的歸納過程,即使一個人從來沒有見過那個事實。例如,珠穆朗瑪峰的峰頂被冰雪覆蓋,這個事實已經成為人類共同體的共識,對于那些沒有登上過珠穆朗瑪峰峰頂的人來說,也有理由斷言“珠穆朗瑪峰的峰頂被冰雪覆蓋”這句話符合事實因而是真的。
再如,你看見一朵花便有把握地說“這朵花是紅的”,而不必重復多次地看這朵花。這是因為,你在以前的生活實踐中通過多次觀察顏色并且在與他人的交流中已經確立了一個事實,即你不是色盲。正是在這一事實的支撐下,在一般情況下,你對顏色的辨認幾乎是一目了然而無需重復地進行觀察。這意味著,在許多情況下,共同體的成員可以越過下層歸納認定事實的步驟,直接根據上層符合使真者的定義而斷定命題p是否符合事實,進而斷定p是否為真。這就是為何處于上層的真理符合定義比較引人注目,而處于下層的對事實的歸納定義容易被人忽視的原因。
五、統一多元真理論與真之單義性問題
前一節關于“歸納-符合使真者”的闡述,已經在我們面前展現出統一多元真理論的輪廓,現在將這一輪廓加以具體化。第一,歸納使真者與符合使真者構成一個統一的真之理論的雙層結構。處于底層的歸納使真者的作用是為事態提供存在性,即提供事實;處于高層的符合使真者的作用是對真理賦予符合事實的特征。第二,歸納使真者與符合使真者的結合標志著實用真理論與符合真理論的結合,既然歸納使真者所依賴的漸近認定法在其本質上是實用主義的。第三,符合真理論的“符合”具有雙重涵義,即等同符合與同構符合,這意味著符合真理論是把等同真理論包含在內的。第四,以上三種真理論——實用真理論、等同真理論和符合真理論——的結合是使真者內部的結合,而使真者與持真者的密切關聯就是融貫真理論的體現。因為融貫真理論的本意就是通過演繹推理把諸多命題系統地與基本命題聯系起來,從而把基本命題從使真者那里獲得的真保持性地傳遞給系統內的所有命題(4)這里所說的融貫真理論是廣義的,狹義的融貫真理論只要求諸多命題之間彼此融貫,而不要求該命題系統與事實發生聯系。在筆者看來,狹義的融貫真理論是不可取的。。第五,本節還將表明,一個語言-實踐共同體對于概率為1的事態(即事實)的認定是一種功能實現,相應地,與事實相符的真也是功能實現的產物,這便把功能主義真理論包含在內了(5)筆者于2014年就提出統一多元真理論,但未提出歸納-符合的雙重結構。可以說,本文是對統一多元真理論的重大發展。參見陳曉平:《真之統一多元論》,《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4年第2期;陳曉平:《心靈、語言與實在》,人民出版社,2015,第170頁。。關于功能主義真理論,下面將給予進一步的闡述。
在演繹推理的持真性(或保真性)和歸納-符合的使真性之間作出區分,這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基于這種區分,我們在第一節提出“符合使真者”和“混合使真者”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從而解決了所謂的“無關使真者問題”。現在我們著手解決“演繹推理的真之單義性(univocality)問題”,此解決需要借助歸納-符合使真者的雙層結構。
演繹推理的同一律要求其保真性或持真性所保持的“真”是單義的,因而要求使真者所提供的“真”也是單義的。然而,在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實際進行的演繹推理的不同前提常常來自不同的領域,似乎具有不同的真之涵義。請看如下推理:
如果暴力導致傷痛,那么暴力是錯誤的;暴力的確導致傷痛;所以,暴力是錯誤的。
這個演繹推理顯然是有效的。然而,它的第二個前提是描述世界上的因果關系,屬于事實命題;第一個前提和結論是關于道德評價的,屬于價值命題。這似乎意味著該演繹推理涉及不同涵義的“真”,因而違反了演繹推理的同一律要求。既然以上推理被公認為是有效的,那便意味著該演繹推理所涉及的“真”是單義的。如何解釋這種單義性?這就是“演繹推理的真之單義性問題”。
為解決這一問題,M·林奇(Michael P. Lynch)提出一種主張,即:真概念必須具有跨語境同義性(uniform across context),但真的深層性質可以具有歧義性。他說:“我們可以是真概念的一元論者,同時是真的深層性質的多元論者。關鍵在于把真概念看作具有多重實現性質(multiply realizable property)的概念。”[5]727林奇把自己的真理論稱之為“功能主義真理論”(functionalist theory of truth)。
在筆者看來,林奇的功能主義真理論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其中“真”所表達的不是簡單性質,而是功能。功能是相對于系統而言的,系統具有功能和結構這兩個不同的層次。在林奇看來,真作為功能是高階性質,而使真得以實現的結構具有低階性質,實現真的系統結構就是語境,語境是以語言-實踐共同體為其要素的。語境可以是不同的,但不同語境所實現的真之功能卻是同義的,這就是真作為功能的跨語境同義性,它體現了功能主義的多重實現原理,即同一種功能可以在多種不同的系統結構中得以實現。
應該說,對于解決演繹推理的真之單義性問題,林奇的功能主義真理論給出的方案是富有啟發性的。不過,筆者認為問題解決得還不夠徹底。舉個例子來說,醫生檢查暴力場合的受害者后可能得出結論:暴力導致傷痛;倫理學家從這一事實命題和倫理準則“如果暴力導致傷痛,那么暴力是錯誤的”可能得出道德判斷:暴力是錯誤的。既然這些不同的前提和結論是由不同的實現者——醫生的語境和倫理學家的語境——得出的,憑什么說它們的真之功能或高階性質是相同的或單義的呢?換言之,“暴力導致傷痛”是一個事實命題,而“如果暴力導致傷痛,那么暴力是錯誤的”是一個價值命題,這兩個命題在什么意義上具有單義的真?由于林奇的功能主義方案不是存在-真的雙層結構,而只是關于真之功能的單層結構,即他所謂的“似真網絡模型”(themodelofalethicnetwork)[5]732-733,這使事實命題和價值命題的真之歧義性沒有經過存在功能的過濾而滲透到真的涵義之中,致使林奇對于真之單義性問題的解決難以令人滿意。為此,筆者將從歸納-符合雙重使真者的立場出發,對真之單義性問題給予深入探討(6)筆者曾把林奇的似真網絡模型改為“似存在網絡模型”,用以過濾各種命題的真之歧義性,然后通過符合論定義達到真之同義性,這也體現了雙層使真者的思想。但現在看來,那個網絡過于復雜繁瑣,因此本文提出歸納-符合雙重結構的使真者取而代之。參見陳曉平:《心靈、語言與實在》,人民出版社,2015,第340-341頁。。
筆者接受林奇的功能主義真理論,但有所不同的是,筆者認為作為功能實現者的不同語境所直接實現的不是真之功能,而是存在之功能,更確切地說,是事態之概率為1的功能,其運作機制就是漸近認定的歸納法。如前所述,漸近認定歸納法的合理性是實用主義的,即語言-實踐共同體出于實踐的需要而把事態A的相對頻率1認定為概率1。這一語言-實踐共同體是實現存在之功能的系統結構,認定的結果——事態A的概率為1并且A存在——相當于系統功能。盡管不同的語言-實踐共同體如醫學共同體和倫理學共同體所討論的命題是不同的,但是被確定為真的命題具有相同的涵義,即符合事實并且事實出現的概率為1。
例如,“暴力導致傷痛”是一個事實命題,對于醫學共同體來說,該事實出現的概率是1。“如果暴力導致傷痛,那么暴力是錯誤的”對于倫理學共同體來說,該命題也表達了一個事實,即該共同體接受這一道德規范。如果有一天該共同體不接受這一道德規范,那么這一命題便不符合事實,因而是假的。需要強調的是,一個共同體是否接受一個倫理命題(即把它作為行為規范)是一個事實問題,同樣可以通過考察該事態的概率是否為1來確定,盡管倫理命題的內容是關于“應該”的。具體地說,如果通過考察發現該共同體總是以某個倫理命題為行為規范,即該共同體以某倫理命題為行為規范的概率為1,那么該倫理命題就是真的,否則是假的。
須指出,一個共同體是否把一個倫理命題作為行為規范是著眼于該共同體的整體,而非其中的個人;即使有個別人不遵守這一行為規范也不表明該行為規范不被該共同體所接受。這便涉及二級概率的問題。例如,如果最初的考察結果是該共同體有70%以上的人接受某個倫理命題,現又假定該共同體奉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那么該倫理命題就被該共同體確立為行為規范,即接受這一倫理命題。繼續考察該共同體對這一倫理命題的接受情況,發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相當大的范圍內,接受該倫理命題的相對頻率都超過70%,于是該共同體的成員便認定該倫理命題被接受的概率是1,進而將它確定為事實。這個概率1是二級概率,即概率的概率,而一級概率為0.7及以上。
一般而言,確定一個倫理命題是否被共同體接受都涉及二級以上的概率,而確定事實命題是否為真大都只涉及一級概率。雖然倫理命題的真假和事實命題的真假有以上區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命題的最高級概率被認定為1。這個結論也可以推廣到美學命題或其他命題的真假上,“演繹推理的真之單義性問題”就此得到解決。
至此,我們從歸納-符合使真者的雙重結構的觀點出發,把多種真理論統一起來,并對以往真理論所面對的諸多疑難問題給予解決。需強調的是,在這諸多真理論中,功能主義真理論具有奠基性作用,因為它通過多重實現原理賦予“存在”進而賦予“真”以相同的含義,從而從根本上使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持真者和使真者——之間的協調問題得以解決,也使多種不同真理論的統一得以實現。可以說,我們的統一多元真理論是奠基于系統本體論之上的。接下來,我們將立足于系統本體論和功能主義真理論,對當前流行的使真者理論給予進一步澄清和改進。
六、使真者理論的兩大原則和兩大“事實”
我們在第一節談到,當前流行的使真者理論實際上是一個粗略的理論框架,其內部觀點繁多、論述龐雜。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的討論應當有所選擇,不妨以其領軍人物阿姆斯特朗的理論作為分析評價的對象。
阿姆斯特朗作為一位還原物理主義者,主張命題的真可以還原為它的本體論基礎即事實,類似于他的另一主張——心靈可以還原為大腦結構。在這個方面,他接受或繼承了收縮真理論的觀點,即命題的真是非本質的和冗余的,因而可以在本體論上予以消除。其結果是,阿姆斯特朗的使真者理論大致只剩下對真的“本體論基礎”的強調和重申,而連真的定義都沒給出,更未給出真得以實現的具體機制。
我們在前面還指出,阿姆斯特朗的使真者原則——命題p是真的,當且僅當p有一個使真者(即事實)T,p憑借T而真,并且T使p必然為真——包含了所謂的使真者極大主義和使真者必然主義。然而,如果真在本體論上是多余的或可去除的,那么,把真及其本體論基礎(即事實)聯系起來的那兩大原則也將成為多余的或無價值的。事實上,阿姆斯特朗把使真關系看作“本體論的免費午餐”,相當于把兩大原則看作這一“免費午餐”的無價值的餐券。與之相反,基于系統本體論的歸納-符合使真者理論,把真作為一種系統功能,從而具有本體論的實在性。
我們已經表明,一個命題的真實性在于它與事實的符合。這樣的真命題將成為語言-實踐共同體的成員們的信念,對他們的實踐行為具有指導作用,即產生因果力。與此對照,真假未定的命題不能成為人們的信念,因而對于人們的實踐行為不具有因果力。按照亞歷山大格言——“是實在的就是具有因果力”,那么,命題的真具有本體論上的實在性,而并非本體論上的“免費午餐”;相應地,作為“餐券”的使真者兩大原則也具有本體論的實在性。從系統本體論或功能主義的觀點看,使真者極大主義和使真者必然主義分別對應于物理實現原則和多重實現原則。物理實現原則和多重實現原則是現代功能主義的兩大原則。
物理實現原則說的是:任何功能最終是由物理結構實現的,實現者與功能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必然關系,即實現者使其功能必然實現。系統本體論或功能主義真理論已經把命題之真看作一種功能,使真者就是真之功能的實現者,即它所符合的那個事實;那個事實必然使表達它的那個命題為真。這正是使真者必然主義。
多重實現原則說的是:同一種功能可以由多種不同的實現者來實現。我們區分了“符合使真者”和“混合使真者”,雖然符合使真者與真命題之間具有一對一的關系,但是混合使真者與真命題之間可以是多對一的關系;并且,任何真命題都有使真者(符合使真者或者混合使真者),正如任何功能都有實現者。這正是使真者極大主義。
這樣,使真者必然主義和使真者極大主義便在系統本體論或功能主義真理論的基礎上得以辯護。接下來,我們重新審視阿姆斯特朗十分重視的兩大“事實”,即否定性事實(negative fact)和普遍性事實(general fact),二者分別對應于否定性真理和普遍性真理。
否定性真理是說某物不存在,如“獨角獸不存在”;普遍性真理是一個全稱命題,如“所有人都有死”。這兩種真理的使真者是什么?這是使真者理論所面臨的棘手問題。“獨角獸不存在”所對應的事態是獨角獸的無,而任何無都是無法展示出來的,所以否定性真理所對應的否定性事實是不存在的。類似地,“所有人都有死”所對應的事態是無限多的單個事態——張三有死、李四有死……——所形成的集合,而這個集合我們永遠只能展示其中的一部分,而不能完整地展示出來,所以普遍性真理所對應的普遍性事態也是不存在的。
阿姆斯特朗指出,大多數使真者理論者要么回避這些問題,要么否認這兩種事實的存在,但有一個“光榮的例外”,那就是羅素。羅素同時承認否定性事實和普遍性事實,這在阿姆斯特朗看來,雖然有可借鑒之處,但做得過頭了[3]54。阿姆斯特朗認為,普遍性事實既可作為普遍性真理的使真者,也可作為否定性真理的使真者,因此只需承認普遍性事實即可,而無需承認否定性事實。他說:“我自己的建議(已經提出)是跟隨羅素在其《數學原理》中勾勒出來的路徑,在人們的使真者中增添普遍性事實即全體事態(totality states of affairs),再不增添別的什么。”[3]70這里的“全體事態”就是普遍性事實。
需指出的是,阿姆斯特朗承認普遍性事實是較為勉強的,因為如果不承認普遍性事實,那么普遍性真理便沒有使真者,從而違反使真者極大主義。為了維護使真者極大主義,他不得不接受普遍性事實,但也只是假設性地接受。他含蓄地說:“全體事態的假設(postulation),或者,至少存在一個這種事態的假設,這就是我所采取的方式。界限(如果不是缺失)也是本體論的實在。”[3]82在他看來,界限是“全體事態”這一概念所蘊涵的,未被包含在全體事態的界限以內的任何事態都是不存在的或缺失的,否定性真理由此獲得使真者。“獨角獸不存在”的使真者是全體事態,因為全體事態的界限之內沒有獨角獸,或者說,獨角獸在全體事態之內是缺失的。因此,“個別事實(事態)和普遍性事實(事態)足以成為否定性真理和存在性真理的使真者”[3]80。
然而,我們從以上引文看到,阿姆斯特朗不得不承認全體事態畢竟只是一個假設,而假設沒有資格成為使真者。所以,阿姆斯特朗關于普遍性事實的論證是不成立的,相應地,他基于普遍性事實而對否定性真理的論證也是不成立的。為此,我們將另辟蹊徑,借助歸納使真者的漸近認定性質,表明否定性事實和普遍性事實都是存在的。
歸納-符合使真者底層的歸納認定方法是:如果事件A在一定條件下出現的相對頻率是m/n,那么我們就認定A的頻率極限(即概率)為m/n。當事態A的概率被認定為1時,則意味著事態A總是出現,故而被語言-實踐共同體確定為A是存在的,這使事態A成為一個肯定性事實。反之,當事態A的概率被認定為0時,則意味著事態A總是不出現,故而被語言-實踐共同體確定為A是不存在的,這使事態A成為一個否定性事實。只要頻率樣本的容量n充分大,這一認定就是合情合理的。
正如羅素所說:“更簡單的做法是將否定事實看成事實,在與‘蘇格拉底是人’是一個事實同樣的意義上承認‘蘇格拉底沒有活著’實際上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9]羅素這樣說只是一種“簡單的做法”,而拿不出理由來。與之不同,我們以漸近認定的歸納使真者為根據,接受否定性事實是有充分理由的。
類似地,根據歸納認定法,當在充分大的樣本中,人們有死的比例(相對頻率)趨近于m/n=1時,我們就認定人們有死的概率(即有死者在全體人中的比例)為1,這只是一級概率;接下來我們對這一普遍性事態加以進一步的考察,如果“所有人都有死”所表達的普遍性事態在一系列考察中的相對頻率仍然是1,我們就認定這一普遍性事態的二級概率是1,因而是存在的;這樣,所有人都有死便成為一個普遍性事實,進而成為“所有人都有死”這一普遍命題的使真者。
阿姆斯特朗把普遍性事態叫作“高階事態”(higher-order state of affairs)[3]70,筆者進而指出,高階事態所涉及的概率是“高階概率”。正如萊欣巴赫所說,“科學知識開始于最初認定;但是我們并不停留在最初認定上面,我們進而到二級認定,二級認定給最初認定提供一個權重”[7]406,“這個權重是由某種概率出現的概率(即二級概率)來給出”[7]402。在以上分析中,有死者在全體人中所占的比例是一階概率,一階概率為1的事態(即所有人都有死)出現的頻率極限是二階概率;普遍事態的一階概率與二階概率都是1。與之相比,倫理命題的一階概率往往低于1,只有二階概率為1,這是普遍性事實與倫理學事實或其他事實之間的一個區別。
至此,我們從系統本體論或功能主義真理論的立場出發,提出具有雙層結構的歸納-符合使真者,建立了統一多元真理論,并對使真者極大主義和必然主義給予新的闡釋,使之具有不可去除的本體論意義。與此同時,我們對否定性事實和普遍性事實的存在性給予證明,以此為否定性真理和普遍性真理提供本體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