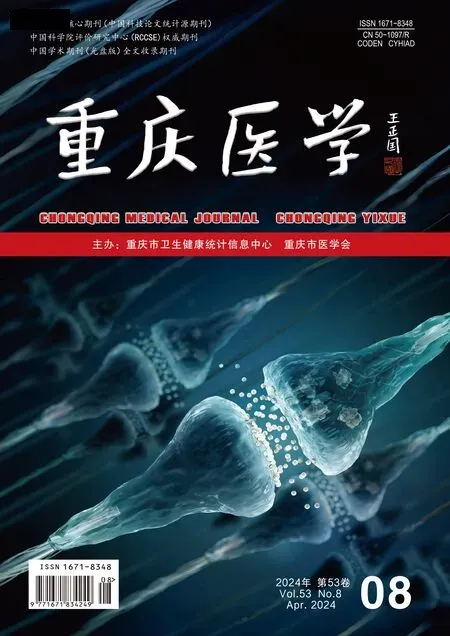基于孟德爾隨機化的DHA水平與ADHD的關系研究*
張 鄭,譚景藍,羅慶華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科,重慶 400016)
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最常見的兒童神經發育障礙之一,其特點是持續注意力不集中、難以控制沖動行為或過度活躍,常發病于7~12歲,男孩的發病率是女孩的3倍,影響著世界5%~7%的兒童[1]。與其他精神疾病相同,遺傳因素發揮了重要的病因作用,但其他外部環境因素,如懷孕期間接觸酒精、煙草或毒素、情緒障礙、早產、低出生體重和產前或產后腦損傷等也被證明是ADHD的致病原因[2]。
Omega-3多不飽和脂肪酸(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n-3PUFAs)在大腦功能和神經細胞膜結構及髓鞘和視網膜的發育中發揮著核心作用[3],特別是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構成了人類大腦中90%的n-3PUFAs和總脂質的10%~20%[4],對母嬰健康有許多積極的影響[5],其主要是通過食用富含脂肪的魚類和其他海鮮攝入。有研究表明,ADHD患兒血清中DHA和n-3PUFAs水平較正常對照組低[6]。還有研究發現,較高的DHA攝入量可以降低精神分裂癥、雙相情感障礙、抑郁、焦慮和行為障礙的風險,而較低的DHA水平似乎是精神疾病的潛在風險因素[7]。此外,DHA對于神經發育的改善,尤其是認知功能的改善仍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證明[8]。
觀察性研究因難以準確考慮所有的混雜因素,很容易受到混雜偏倚的影響。相比之下,孟德爾隨機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分析將遺傳變異作為工具變量,規避了混雜因素或反向因果關系的影響,并可用于研究影響人群健康的風險因素[9]。目前還沒有研究采用MR方法來探究DHA對ADHD發病風險是否存在因果效應,或ADHD和DHA水平的因果關系。基于此,本研究設計并完成了一項雙向MR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表1 MR研究中GWAS數據庫的簡要信息
1.2 方法
1.2.1MR研究3個假設
SNP作為代理表型的遺傳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IVs)被用來進行雙樣本MR研究。所篩選的SNP應滿足MR的3個主要假設:(1)假設一,工具變量應與相應的表型具有強相關;(2)假設二,工具變量不受與結局有關聯的潛在混雜因素的影響;(3)假設三,工具變量和結果之間沒有直接關系[9]。通過MR分析來評估DHA與ADHD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流程見圖1。

實線箭頭線:MR分析流程,且只能通過暴露影響結局;虛線箭頭:違背MR 3個假設的影響路徑。
1.2.2工具變量的選擇
所選用于代理DHA工具變量的SNP均滿足全基因組統計顯著性閾值(P<5×10-8),以滿足假設一,為了獲得獨立的SNP,進行了去連鎖不平衡LD(r2<0.001,kb=10 000)[13]。為了進一步評價工具變量強度(R2),計算了每個SNP的F統計量,其中F<10(視為弱工具變量)的工具變量被剔除[14],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F=[(N-k-1)/k]×[R2/(1-R2)][15]
①
R2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來:
R2=2×(1-MAF)×MAF×(β/SD)2[16-17]
②
公式中的N代表所選取數據集的樣本量,k是選擇用于MR分析的SNP總數,MAF是次要等位基因頻率,β是SNP對DHA的效應估計值,SD是β的標準差。
此外,進行反向MR分析,以驗證ADHD對DHA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同樣從數據集中篩選了全基因組顯著(P<5×10-8)和獨立遺傳(r2<0.001)且無LD的SNP,通過上述標準篩選的SNP用作MR分析的最終工具變量。
1.2.3去除混雜和回文SNP
為了滿足MR假設二,在PhenoScannerV2數據庫(http://www.phenoscanner.medschl.cam.ac.uk/)評估了每個SNP及其相關表型,并在r2>0.80的閾值上剔除了與ADHD相關性狀的SNP[18-19]。通過上述選擇的SNP去除具有中間等位基因頻率的所有回文SNP來協調DHA和ADHD的數據[20],回文SNP定義為具有A/T或G/C等位基因的SNP,且中間等位基因頻率為0.01~0.30[21]。
實驗組學生和教師任務分解。學生任務:(1)小組學習:學生按5~6人組成學習小組,學習內容分為熱點問題和案例學習兩部分。課外每名學生根據發放材料進行文獻收集、閱讀、思考,然后開展小組討論,達成小組共識,重新組織內容,為課堂展示做準備。(2)學生課堂: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學習內容講解,同時回答其他組的提問。其中熱點問題6學時,案例學習6學時,學習成果、學習經驗分享2學時。(3)課外訓練:利用第二課堂,以小組為單位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學生以問卷形式開展社區、養老機構老年健康需求調查,或應用所學知識、技能開展老年慢性病健康教育、護理服務活動。
1.2.4效應統計和敏感性分析
采用逆方差加權法(inverse-varianceweighted,IVW)作為主要的統計分析方法,該方法通過應用Wald比率結合了SNP特異性估計,通過meta分析法綜合了DHA對ADHD的匯總因果效應[22]。并使用了加權中位數法(weighted median,WM)、MR-Egger回歸和MR多效性殘差和離群值(MR-PRESSO)模型作為補充分析方法。MR-Egger截距的P值用于指示定向多效性,MR-PRESSO法用于檢測并去除異常值后再生成估計值,以區分去除異常值前后估計值之間的差異[23]。此外,使用Cochran’sQ值來表示DHA所用的工具變量之間的異質性[24]。此后,在反向MR分析中使用與上述相同的MR方法。用效應指標優勢比(odds ratio,OR)和95%CI報告效應估計值,若OR>1,說明暴露對結局可能是一個危險因素,增加了該結局發生的可能性;若OR>0~<1,則說明暴露對結局存在潛在保護作用。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R4.1.0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比表示,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正向MR分析
經過上述篩選標準(P<5×10-8,r2<0.001,F>10),并排除與結局存在潛在關聯的混雜因素后,共納入37個SNP作為DHA的工具變量。分別與ADHD1、ADHD2數據集進行同方向糾正,并剔除回文SNP后確定了兩組工具變量,包括19個來自PGC2019和15個來自PGC2022的SNP,且篩選出的SNP具有較強的統計強度,F為398.1~441.5,超過了常規閾值10,見表2。

表2 基于IVW模型的DHA對ADHD風險的因果效應
IVW結果顯示,DHA對ADHD存在潛在因果效應,兩組MR分析結果均說明DHA是ADHD的潛在保護因素;此外,WM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結論,但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然而,在PGC2019數據集中MR-Egger方法得到了相反的結論,但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2。

A:ADHD1與DHA水平分析;B:ADHD2與DHA水平分析;水平X軸:DHA遺傳效應;垂直Y軸:ADHD遺傳效應;黑點:MR分析中使用的SNP;由于IVW和WM在分析中估計值相似,圖片視覺上顯示重疊。

表3 基于3種MR方法的DHA與ADHD風險因果關系
2.2 反向MR分析
在滿足上述閾值(P<5×10-8,r2<0.001,F>10)下,來自PGC2019數據集的ADHD1未找到足夠的SNP,因此反向MR共納入了來自PGC2022數據集的27個SNP作為ADHD的工具變量,與DHA數據集進行同方向糾正,并剔除回文SNP后確定20個SNP,結果顯示ADHD對DHA存在潛在因果效應,IVW和WM提示ADHD患者體內DHA水平低于健康人群(P<0.05),見表4。此外,MR-Egger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結論,但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3。

水平X軸:ADHD遺傳效應;垂直Y軸:DHA遺傳效應;黑點:MR分析中使用的SNP;由于IVW和WM在分析中估計值相似,圖片視覺上顯示重疊。

表4 基于3種MR方法的ADHD與DHA風險因果關系
2.3 敏感性與多效性分析
正向MR分析中,MR-Egger未顯示任何多效性(P>0.05);對于反向MR分析,MR-Egger也未顯示存在任何多效性(P>0.05)。使用Cochran’sQ檢驗評估每個數據集內部異質性,檢驗數據集內無明顯的異質性證據(P>0.05)。此外,還進行了MR-PRESSO檢驗,得到一致結果,均未發現存在定向多效性和離群SNP,見表5。

表5 敏感性分析結果的總結
3 討 論
本研究從遺傳角度發現DHA和ADHD存在雙向因果關聯,為ADHD的早期預防提供了依據,有助于為孕產婦飲食攝入提供指導,以降低ADHD的發病風險。
正向MR分析結果顯示,DHA是ADHD發病的潛在保護因素。有研究表明,DHA在妊娠晚期至兒童2歲時被迅速融入視網膜和腦神經組織中[25],由于胎兒DHA的自主合成較低,母體DHA的攝入和胎盤的轉運功能對胎兒獲取DHA至關重要[26]。存在多項流行病學證據表明DHA水平與注意力呈正相關,與ADHD的嚴重程度呈負相關[27],而DHA補充劑有助于改善7~14歲兒童的心理社會功能、注意力集中及情緒問題[28]。此外,產前補充DHA同樣有益于學齡前兒童的注意力和執行能力[29],尤其是早產兒[30],這與本研究結果一致。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因胎兒較低的DHA水平導致腦白質完整性缺陷和額底神經膠質回路的功能連接降低,進而增加兒童患ADHD癥狀的風險[31]。還有研究表明,DHA可能通過抑制核因子-κB活性,促進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PPAR-γ)的活性,進而起到抗炎作用來控制ADHD癥狀[32]。目前來說,DHA影響ADHD的具體機制尚不明確,其可能還與皮層多巴胺神經遞質的改變[25]及腦-腸軸有關[33]。
反向MR分析結果顯示,ADHD患者具有較低的DHA水平,這與既往研究[34]結論一致,ADHD兒童在紅細胞膜上呈現獨特的脂肪酸譜,DHA水平明顯低于健康兒童。
本研究優勢在于使用MR來研究DHA與ADHD之間的雙向因果效應,由于遺傳信息在時間順序上先于出生后環境因素的暴露,故而避免了觀察性研究中混雜因素帶來的偏倚,相比于隨機對照試驗的成本和倫理問題,更高效地探討了二者的因果關系。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對象為歐洲人群,其他種族能否得出相同的結論有待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基于雙向MR,利用遺傳數據進行了DHA與ADHD的雙向因果推斷,結果發現DHA水平對ADHD的發病存在潛在保護作用,同時ADHD患兒具有較低的DHA水平。但二者之間具體的作用機制尚不明確,仍需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