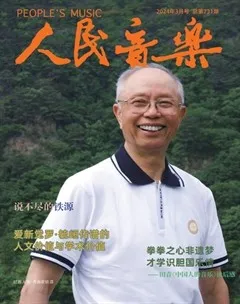對阿炳若干史實的再梳理
顧 穎



在一首經典的傳世名曲面前, 原本只需傾情地演繹或聆聽,任何言語和文字都是多余的。但《二泉映月》似乎是個例外,圍繞這首二胡曲和阿炳本人,至今依舊眾說紛紜,各種謠言、誤傳在一定時間、范圍內還愈演愈烈。
《二泉映月》之所以聞名于世,除曲子自身的藝術高度外,時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1950 年夏,楊蔭瀏、曹安和搶救采錄阿炳二胡、琵琶曲之后,將鋼絲錄音機帶回時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作為相對比較熟悉的家鄉音樂, 楊蔭瀏開始并未特別在意,后來還是學院研究部主任李元慶向時任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的呂驥匯報時,推介了《二泉映月》,才讓這首作品的命運出現了轉機。在呂驥的支持下,李元慶把《二泉映月》的錄音推薦給天津廣播電臺進行宣傳,又安排楊蔭瀏編輯出版《瞎子阿炳曲集》,阿炳和他演奏的《二泉映月》逐漸為人所知,而揚名于國內外。呂驥、李元慶為什么這么重視呢? 因為1950 年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代中,作為新政權在音樂領域的掌門人,首先要考慮的是用民族大眾的音樂取代過去封建士大夫音樂和西方的資產階級音樂,而《二泉映月》適逢其時,也開始成為對舊社會控訴的一種藝術載體。阿炳也被賦予了階級的標簽, 以一個貧苦勞動人民的形象被反復演繹,逐漸概念化、臉譜化,無意中離真實的阿炳越來越遠。
而楊蔭瀏與阿炳是舊交。楊蔭瀏6 歲起便從近鄰的道士穎泉處學習簫、笛、笙和二胡,楊約10 歲時,穎泉回道觀當主持,便介紹道友阿炳繼續教他琵琶和三弦,為時約一年。1947 年夏,天韻社梵音組在赴滬演奏錄音之前,楊蔭瀏還專請阿炳到場旁聽排練。
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與阿炳有著舊交且對其大略了解的楊蔭瀏也只能順著潮流走,而對阿炳的一些負面情況持緘默的態度。另一方面,阿炳是貧困潦倒的道士,處于社會底層。雖有一些關于他的新聞見諸地方報端,但生平情況非常缺乏官方的記載,而僅有的檔案記錄也很難為一般人看到或得到正確解讀,故很多有關他情況,基本都是傳聞,缺乏可靠性,從而使一些本來并不復雜的人和事,長期處于一個各說各話的撲朔迷離狀態。盡管楊蔭瀏和曹安和生前多次在文章和訪談中予以糾謬和辟謠,楊蔭瀏大女兒楊國蘭和幼女楊國葳也針對相關誤傳作過專門調查和撰有回憶文章,但收效甚微。
一、戶籍
目前所知官方的檔案僅存于無錫市公安檔案館所藏四件阿炳戶籍記錄中, 分別是1950 年阿炳戶籍記錄、民國三十八年華阿炳戶籍記錄(檔案號:0020-SW2-4.1-0018)、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華阿炳將孫女球娣遷入其戶的申請書(檔案號:0020-SW2-4.1-0019) 和偽無錫縣填發國民身份證底冊(檔案號:0020-SW2-4.1-0020)。
第一件檔案1950 年阿炳的戶籍記錄中, 阿炳生年為1892 年7 月9 日,籍貫無錫,已婚,文化程度為私塾,職業是道士,殘疾特征為失盲。戶籍于1950 年12 月12 日注銷,原因是死亡。妻董氏,生于1889 年1 月18 日, 家務,1951 年3 月27 日因死亡注銷戶籍。孫女球娣,生于1944 年1 月15 日,1951 年4 月1 日戶籍遷回江陰北漍。戶籍民警冀文樑在戶籍登記表左側備注“華阿炳為全國音樂藝人”。門牌號為當時圖書館路36 號四組二十三戶。此件戶籍記錄中阿炳生年為1892 年, 與楊蔭瀏的回憶差一年,造成一個懸案,但更早的第二件檔案,即民國三十八年華阿炳的戶籍記錄中,阿炳生年為民國前十九年七月九日,民國前十九年,就是1893年。1949 年前的民國政府是用民國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為公元紀年,戶籍在民國紀年轉換到公元紀年時,往往錯算一年,這是當時無錫戶籍檔案中出現的一個常見情況,故有了第二件檔案的記載。阿炳的生年為1893,應該是確定無疑了,這也印證了楊蔭瀏回憶的準確性。而且,從戶籍記錄中也能明確阿炳是正常死亡,如有他殺、自殺等情節,警方一定會有相應的記載和勘查現場的報告。
戶籍中阿炳妻子為董氏,其名是催娣還是彩娣已無法確定,似也沒有必要確定,因原本就可能只有兩字的發音。董氏原籍為江陰,前夫姓鐘,是江陰北漍德興村鐘家堂人, 阿炳繼孫女鐘球娣1949 年戶籍遷入阿炳家中,在阿炳夫婦去世后又遷回江陰原籍,現居上海。
當時崇安寺派出所戶籍民警冀文樑在此戶籍登記表左側用藍色蘸水鋼筆書寫的備注非常重要,華阿炳有了政府賦予的某種標簽———全國音樂藝人, 這說明最遲在1950 年下半年人民政府已經將阿炳納入視線,對他的藝術成就已有認識。然當時百廢待興,新政權要迫切解決的問題繁多,一時還來不及出臺相應的政策或舉措來顧及阿炳這一類人員的生活。但當時社會上已有為改善阿炳貧困生活的呼吁,如《曉報》在1950 年10 月7 日,就刊載了署名阿方的報道(見圖1)。而實際上,當時阿炳已常有親友接濟,生活狀況有了不少改善。
第四件檔案是偽無錫縣填發國民身份證底冊,底冊中有華阿炳及其妻華董氏照片,傳世的阿炳照片就來源于此,但需要說明的是,這是抗戰后民國政府頒發“國民身份證”的底冊,而非許多文章所說的阿炳照片是“良民證”上的,“良民證”是日軍侵華期間的證件,兩者不是一回事。此份戶籍登記的地址是阿炳所住的雷尊殿披屋前部, 因發現有一張1950 年11 月阿炳“地價稅繳款書”,曾出現過阿炳有不少房產的傳聞(見圖2)。其實雷尊殿是屬于道產,舊時由本縣道會司管轄,當家道士僅有使用權和從中獲取香火收入的權利,并無所有權。地價稅繳款書中阿炳應是作為使用權人依法納稅,納稅金額是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元,也有人依此認為阿炳十分富有,其實這是第一套人民幣的幣值,1 萬元相當于1955 年3 月1 日之后的人民幣一元。這張“地價稅繳款書”的發現也否定了阿炳被議出道門喪失道籍的傳聞,與戶籍登記中阿炳職業明確仍為道士的記錄相符。關于這點,楊蔭瀏在與黎松壽的通信(見圖7)和錢鐵民《縹緲孤鴻影》一書中譹訛均有詳細的辨析,不再贅述。此外,阿炳付得起相當于后來近12 元的稅,這也說明他當時的經濟狀況并沒有低到許多人想當然的山窮水盡的地步。
二、家譜
2011 年,由華仲興等續修的華氏通八支宗譜,阿炳已入譜, 屬于通八山心派南宅小四房分支,這表明阿炳無論是華清和(本名挹秀,號雪梅)的私生子還是養子,目前算已歸宗華氏。但從譜中可知,華清和之父華德勝(阿炳祖父)是華興章(阿炳曾祖)的螟蛉之子,出自外姓,所以從血緣上講,阿炳又不是華氏血脈。
三、照片
楊蔭瀏、曹安和1950 年回錫為阿炳錄音的過程最為眾說紛紜,策劃者是誰,參與者有誰,錄音地點在哪兒,《二泉映月》的命名者是誰,許多問題至今還莫衷一是。但歷史總會留扇小窗,讓真相之光透出。時任《曉報》攝影記者的費適居然到過錄音現場采訪,并拍攝了一組照片。歷史又總是跟人們開玩笑,費適在20 世紀50 年代中期曾入職一家在寧的省級新聞單位, 但在1958 年前后人生遭遇一大挫折,被調回無錫,在印鐵制罐廠擔任印稿設計。退休后,他曾想用這組照片作為讓有關部門恢復其先前待遇的籌碼未果, 致使這批照片未能公諸于世,故日前只能請這位無錫攝影家的高足、親歷者之一的秦紹楹于2023 年10 月回憶了有關情況。
《曉報》專長報道蘇南地區文藝動態,對豐富人民業余生活不無裨益。費逵(費適之兄)妻子張氏是《曉報》社址無錫市中市橋巷33 號房東的外甥女,據說與秋瑾是親戚。費適一家租住在新生路341 號謝家第一進三開間,而費適則住在側廂內。南鄰X光醫師李嘉令家,北近公園路、盛巷口。
1950 年夏,楊蔭瀏為華彥鈞錄音是《曉報》當然要報道的重點事件,身任攝影記者的費適接受了采訪拍攝任務。當時已是新社會新氣象,加之“鎮壓反革命運動”已然開展,費適心里嘀咕“在舊社會,這種大少爺白相叫花子絕對是小報喜歡的,現在不時興了”, 況且阿炳在敵偽時期與日本人的關系說不清道不明,因而對這次拍攝任務不怎么樂意。報社說楊蔭瀏是大教授,華彥鈞(阿炳)雖然人不怎么樣,但胡琴、琵琶蠻來事,再說曹(安和)家還要給你介紹女朋友,你還是要去完成采訪拍攝任務。費適就到三民照相館拿了兩只膠卷去離他家不遠(不超過150 米)的曹安和家。曹家接待了年輕英俊的攝影記者鄰居費適, 告知錄音將在樓上房間進行,時間選擇在夜深人靜辰光。費適就往樓上走,正好有人在布置房間,見費來就叫他一起幫忙把棉被掛起來蓋住所有沿街檻窗,說是為了隔音。掛好被子后,費自覺不能在錄音場所拍攝(快門聲、閃光泡),決定在錄音前后拍幾張交差。
2005 年夏的一天,費適來單位找我,要我下班后到他風和里家里去。當晚他給我看了兩張老的拷貝底片。一張是120 正方形,應該是祿萊雙鏡頭反光照相機拍攝,三個人分前后站立,另有一個人坐在方凳上,靠在茶桌上。另一張是一把二胡。費適介紹說當時用120 和135 共拍了十三張照片, 原底片大多不在了,現在只找到這兩張拷貝片了。我問怎么沒拍阿炳的正面照片? 費適說阿炳是盲人,正面照片會突出身體缺陷, 要被人吃生活(筆者注:挨揍)的。當時阿炳的墨鏡也沒有了,更不能拍正面照片了。至于那張二胡是當時他特意拍的,二胡是阿炳自己的,原來琴筒已壞掉了,他找了個美國罐頭盒蒙上蛇皮就當琴筒用了。后來,費適想以這兩張珍貴的照片改變他的境遇,可惜沒有結果。
以上文字可知,錄音現場采取隔音措施,從而可以明確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參與“見證”。阿炳原來的二胡已是簡易的罐頭蒙皮所制,故有從中興樂器店幫其借二胡一節。當時阿炳已不戴墨鏡,又是一種形象。
四、現場
1950 年夏末,楊蔭瀏、曹安和按原定計劃暑假回錫做錄音工作, 其中包括錄阿炳的演奏, 這并不是黎松壽在《我親歷了〈二泉映月〉的最初錄音》(載于黑陶著《二泉映月》,新星出版社2010 年版)一文所稱是由于他的建議而臨時決定的, 這是既定的。總之,楊蔭瀏后來講得非常清楚:一是他沒有把發現阿炳精于二胡一事歸之于己,二是沒有把自己原定的錄音計劃說成是人家的建議。
從多方的回憶看,給阿炳錄音,預先做了一些必要的準備工作,時間大約在1950 年8 月30 日,楊、曹與阿炳見面,了解其情況。當發現阿炳沒有完好的樂器時,就從中興樂器店借來了二胡,琵琶是曹安和提供的,這次見面可能就在阿炳家后面的三圣閣,其間也有黎松壽所說的“一共八人在內的多人在場”。三圣閣, 主體建筑為二層樓房, 當時是一個公共場所,可以在內公開演奏,但不適合錄音,何況有多人在場,更不可能。原三圣閣早已拆除,近年在馬山祥符寺又原樣復建了一個三圣閣,從中可以一窺原貌。
根據楊蔭瀏長女《關于錄〈二泉映月〉情況的回憶》, 阿炳借來樂器練了三天后的9 月2 日, 楊蔭瀏、曹安和和她到阿炳家正式錄音,董氏也在場。9月3 日,在曹安和家樓上繼續正式錄音。
我是楊蔭瀏的長女,名叫楊國蘭,在太原理工大學任教授,已退休。錄音那年,我是無錫輔仁中學高中的學生,18 歲。1950 年暑假期間, 父親返錫度假,帶回一臺又大又重的鋼絲錄音機,說準備收集民間音樂等。給我的任務是負責錄音機的運送、保管與操作,為此,父親還對我進行了培訓。一天,父親和我提上錄音機去阿炳(華彥鈞)家(記得阿炳家在無錫圖書館東側圖書館路的一間平房中)。那天錄音時,房內有阿炳夫婦、曹安和、父親和我共五人。在錄完一首二胡曲子后,因錄音順利,大家都很高興,我也覺得好聽,只是阿炳自己并不太滿意。這時,父親問阿炳:“這首二胡曲叫什么名字? ”當時,沒聽到阿炳說什么,只聽到阿炳、曹安和、父親三人在討論該曲的曲名,后來,好像是阿炳說出《二泉映月》這一名字來,很快他們就一致同意了。這次共錄了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等三首二胡曲(第二次錄音我因發高燒未能前往。父親錄完音后回家對我說,這次錄音是在盛巷曹安和家樓上,錄音時阿炳、曹安和、父親三人在場,錄了三首琵琶曲)譺訛。
五、信件
近期,無錫收藏家江其源向筆者展示了所藏的一批信件, 其中有十余封是楊蔭瀏寫給黎松壽的,年代涵蓋20 世紀50 年代中期以及70 年代末。信件中大量涉及有關阿炳的討論,也有對黎“說了一些沒有根據的話”作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
黎松壽(1921—2010),原籍廣東中山,生于無錫,父親黎才生是無錫火車站第一任站長,母親陸氏是無錫人。黎松壽1948 年在南京第一次見到楊蔭瀏,經楊蔭瀏推薦向儲師竹學習音樂,從此走上音樂教育之路,后任南京師范大學音樂教授。其兄黎松祥(1916—1977),是無錫市第二人民醫院胸科醫生,業余愛好音樂,曾隨楊蔭瀏學習古琴。黎家1951 年前住在圖書館路2 號,與阿炳是距離不太近的鄰居。
1978 年10 月11 日和1979 年1 月3 日的兩封信件中, 楊蔭瀏提及的無錫市文化局長趙源(元),曾在1963 年全面主持調查阿炳的工作,并最終形成一份調查報告。對此次調查,楊蔭瀏認為有值得肯定的部分,也有不準確、毫無價值的地方。筆者在無錫市檔案史志館查到了該份報告。
調查主持人趙源(元),應作趙沅,生于1924年,原名叢昌源,江蘇如東人,1945 年就讀于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期間,曾參加地下黨。20 世紀50年代初起,歷任無錫市文聯主席、無錫市文化局長、江蘇省京劇院院長等職,于2020 年去世。筆者近期與其子叢笑猿取得了聯系,也獲得了一些不為人知的材料。
綜上, 筆者對新發現的材料做一點新的解讀,希望能夠進一步厘清關于阿炳的幾點關鍵史實,還原真相,進而讓大眾能更多地關注阿炳傳世音樂本身,也更加清晰地了解楊蔭瀏對中國音樂作出的不平凡貢獻。
顧穎 無錫市公安局梁溪分局一級警長,無錫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古琴藝術代表性傳承人
(責任編輯 李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