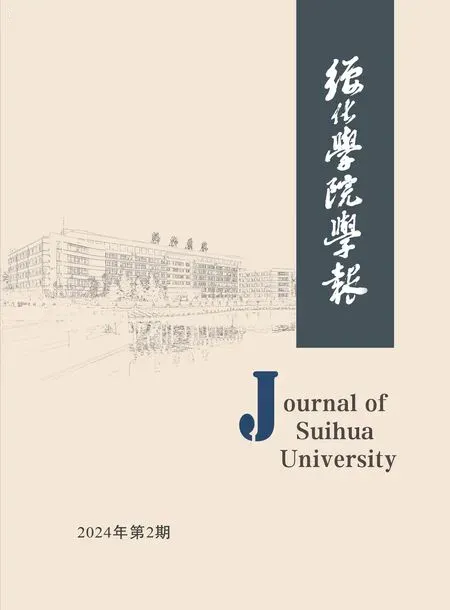追溯·整合·融通
——英詩漢譯中的翻譯“達合”方法論初探
高 玥 王宇弘
(沈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遼寧沈陽 110034)
縱觀古今,橫看中外,中西方譯論構建經歷了從見譯是譯的直觀期到見譯似譯的轉向期兩次重要歷史階段。未來譯論構建是否還要繼續停留在“盲人摸象”的微觀層面,論尾、評足、摸頭、撫耳,卻終究無法窺得象之全貌;亦或是退一步或升一格,觀其全貌,察其整體,述其本質?筆者更傾向于后者。相較于政府報告、法律文書和散文隨筆,詩歌翻譯可謂是翻譯實踐中的“華山之路”——唯勇者敢攀登。
一、追溯:中西方譯論“達合”發展
不論是以青銅饕餮為起源的華夏文化,還是以愛琴希臘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翻譯理論的起步都晚于翻譯實踐。中國宋代禪宗大師青原行思提出的參禪三境界同樣適用于一切認知發展,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故而人類對翻譯的認知也可劃分為見譯是譯、見譯非譯以及見譯唯譯三大歷史進程。中國早期翻譯實踐起源于佛經翻譯,周作人、馬祖毅、裘柱常等學者在對翻譯史進行分期時,都明確將唐代以前的佛經翻譯劃分為第一次翻譯高潮[1](P11)。與此同時,西方早期翻譯活動則起源于《圣經》翻譯。隨著翻譯實踐日趨擴大化與普及化,翻譯理論也被提上日程。中西方譯論發展整體成雙線、同向、并進的“達合”之態。
(一)譯論發展直觀期——見譯是譯。中西方譯論發展初期均以直觀感受為主,通過觀察、發現、加以總結,形成了對翻譯的肯定性描述。西方《圣經》翻譯時期先后形成了主張活譯的西塞羅、賀拉斯;主張直譯的奧古斯丁、斐洛;以及主張折中的哲羅姆[2](P121-122)。中國早期佛經翻譯也經歷了與西方譯論發展極為類似的文質之爭。從主張直譯的道安,到傾向意譯的羅什,再到“厥中”論提倡者慧遠。雖然地處兩個半球,卻向同一方向蓄力發展,但始終逃不過與翻譯行為相關的具體問題描述。此外,中國近現代譯論發展仍可歸屬東方譯論發展直觀期。與佛經翻譯不同,該階段雖仍在探討“怎么譯”的問題,但雜糅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其他因素,如傅雷借用繪畫知識,提出了“神似”說;錢鐘書援引美學理念,闡釋了“化境”論。整體而言,譯論發展直觀期內翻譯理論多未經系統邏輯推理,探討內容也多圍繞譯論本身展開。
(二)譯論發展分化期——見譯似譯。事物的發展總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再肯定)”的辯證邏輯中循環往復。譯論發展在經過直觀期的肯定性描述后,步入了分化期的自我否定階段。西方譯論發生了兩次重大“轉向”,即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因而也由此衍生出了眾多學派,如闡釋學派、功能學派、蘇東學派等等。西方譯論轉向轉得“暈頭轉向”,譯界已然分不清到底何為翻譯,各派學者在霧里看花的迷途中,在“花非花,譯非譯”的茫然中束手無策。與此同時,國內譯論發展也呈現多元趨勢,涌現了諸多方興未艾的譯論,如黃忠廉的變異理論、胡庚申的生態翻譯、周領順的譯者批評等等。諸多譯論呈放射狀分化,且多借引其他學科知識,交叉融通后加以闡述;但上述譯論過于碎片化,像極了盲人摸象中每個人對大象的片面描述。此類只見木不見林的譯論是否真能對翻譯學科全局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呢?答案可想而知。但不可否認,每一譯論的誕生都有其自身的歷史獨特性,眾多譯論共同推動翻譯學科的“達合”發展,正如諸多譯作最終匯聚成本雅明所堅持的純語言一樣。
(三)譯論發展“達合”期——見譯唯譯。中西方譯論經過螺旋式的發展期,必然會向上躍進。任何學科均屬于哲學范疇,而哲學作為原始學科,即所有學科的母學科,為具體學科發展起到了指引作用。哲學講究的是方法論而非具體方法,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論一樣[3](P17-19),譯界是否也需要在具體方法和一般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方法論層面的建設性指導呢?
目前國內譯論呈百家爭鳴之態,致使出現眾多“借一譯論,評一譯作”的學術論文,作者以青年學者和研究生為主。李長栓教授在重慶翻譯學會第二十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上曾指出,上述“套用型”論文是否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價值還需進一步探討。說到底,現階段譯論發展需要“形而上”層面的方法論體系,前期“形而下”的分說則是方法論的載體,也就是“道”與“器”、“上”與“下”、“恒長”與“變化”的相互關系。近些年,已有少數學者在方法論層面不斷嘗試,如陳東城(2016)提出了大易翻譯學[4](P2),紀東津(2015)提出了融合翻譯理論等等[5](P84-93)。雖然上述理論仍處于發軔期,但正如儒釋道定會合流、度量衡誠被統一一樣,百家譯論終會合一,形成去偽存真的“達合”方法論體系。
二、整合:翻譯“達合”方法論
何謂“達合”?“達合”一詞為偏正短語,偏向“合”之側;傳遞了中國文化體系中由“治道”引發的長治久安、和合而治的思想。“達合”二字皆可顧名思義:“達”取其本意,即“到達”;“合”亦取其本意,即“會合”。將“達”與“合”二字整合,意為融合通達、貫通融會。固而“達合”方法論旨在融合前人譯論之精華,系統闡述翻譯之本、譯論之源以及策略之脈,最終形成以“無”勝有的境界。翻譯本身就是因時、因地、因人的隨機性行為。從某種程度上說,譯者若能將源語語義準確無誤地傳遞給譯入語,就完成了翻譯任務,就可以稱得上是一名合格譯者。況且不可譯因素貫穿翻譯始終,不同譯者會出于不同原因,創造出不同的譯文形式。而正是這些各具特色的譯文,造就了大衛·達姆羅達(David Damrosch)所認定的世界文學[6]。
當然,翻譯“達合”方法論體系絕非空中樓閣。就目前翻譯場域內紛雜譯論而言,方法論構建大致可以從如下三個維度入手:1.翻譯“達合”方法論譜系研究:即“正本清源,逐級搭建”;2.翻譯“達合”方法論支譜研究:即“分衍側支,層層深入”;3.翻譯“達合”方法論語篇研究:即“以本為例,融通達合”。通過構建翻譯“達合”方法論體系,融通翻譯學科各級分支,在體系中闡述,在語篇中詮釋,在譯論中體現。翻譯實踐活動與方法論體系構建整體呈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
另外需要提及一點,盡管國內譯界竭力推進純理論研究,試圖摒棄以往的應用性理論;但就目前形勢而言,各家分說的最終落腳點終究逃不過對“怎么譯”、“如何譯”的探討。如生態翻譯涉及的“十化”譯法、譯者行為批評論述的“求真—務實”連續統以及知識翻譯學構建伊始就提出的“知識剪刀差”等一系列實操性較強的衍生概念等。
信息化時代塑造了更加紛繁復雜的翻譯形式和譯本呈現,從眾包翻譯到多模態語料,翻譯領域勢必會有更加寬廣的空間和無限可能的未來。與此同時,翻譯也成功于2022年榮升為一級學科。面對如此龐雜的源語形式,譯論不應再向以往一樣,一味針對不同類型的翻譯提出不同類型的譯論,而應提升一個臺階,提出方法論的構建,以不變應萬變,并逐漸深入對方法論的分析和探究。現階段的翻譯“達合”方法論旨在統一分化期的百家理論,取其精華,去之糟粕,融通升華。本文僅拋磚引玉,翻譯“達合”方法論還需很長一段時間的接續發展。
三、融通:英詩漢譯中的翻譯“達合”方法論
(一)韻律——詩之外形。弗羅斯特曾說:“何謂詩?詩即譯之失也。”詩的不可譯性在其表層韻律方面已然體現的酣暢淋漓。《愛與問題》一詩共四段,每段八行,皆以長短句結合的方式展現;且每段均壓了“abcbdefe”的韻,讀起來朗朗上口,抑揚頓挫,節奏感強。正所謂“洪荒造塔語言殊”,英詩特有的尾韻在其他任何語言那里都無法完全重現,只能進行替代或轉換。江楓秉持了英師譯者的傳統慣習,巧用漢語韻母的結構成分,重塑英語尾韻,大部分情況下做到了韻母完全押韻,如“郎”和“杖”;但也有少數情況只壓了韻頭或韻身的部分韻律,如“宿”和“口”。以至于英詩只在二、四、六、八句押了尾韻,但譯文韻母幾乎押了所有詩行,構成了“ababcdcd”的韻。江楓并沒有再去追求“陰陽上去”的協調,聲調部分較為自由,沒有花費太大精力。但是,這同樣符合“美化之藝術,創優似競賽”的準則;也同樣貼合變異之理論、生態之譯論、體認之內涵。通過轉換的具體譯法,在“求真—務實”連續上自由轉換。
(二)詞句——詩之結構。若把詩歌比美人,詩之韻律就好比其外在華美秀麗的衣衫,而詩之結構則好比其內在冰壑玉壺的風骨。原詩段落和行數均為偶數,且每段中奇數行長,偶數行短。江楓把這種外顯型特征表達得恰到好處。同一詩行中,原詩幾乎沒有斷句,且有時兩句后才出現一個標點。但中文相較于英文簡短干練,四字格和流水句比比皆是。為了吸引讀者亦或是受譯者自身慣習影響,譯文中出現了四字格連用的形式,即“勞頓不堪,憂心忡忡”,且斷句數量多于原詩。江楓通過歸化策略使原文生命得以在譯入語世界延續,讓碎片化語言不斷向純語言靠攏,就像女性與男性間相互扶持,彼此成就一樣。
江楓在遣詞造句上緊密貼合原文,除加入部分并列句外,幾乎未做改動。選擇并列、對偶、排比之類的對稱句式也是為了使譯文更好地在漢語世界流通。全詩只有一處進行了意譯處理,即將“the woodbine berries were blue”譯為了“忍冬的漿果已經熟了”。這里,譯者在初讀英詩時也頗感不解:為什么果實變藍了?是憂傷之果嗎?中國讀者的潛意識認為,“金黃燦燦”才是“碩果累累”的標配;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藍色果實”恐怕也只有藍莓這一例了。江楓讀罷應該也感到些許疑惑與不解,大抵是查閱資料后才諳熟了其中內涵,怕造成閱讀障礙,因而如是翻譯的。這不也是譯者主體性的切實體現嗎?
(三)思想——詩之內核。《愛與問題》一詩和弗羅斯特另一首耳熟能詳的詩歌The Road Not Taken(《未選擇的路》)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表面上描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卻折射出引人深思的哲理。《愛與問題》刻畫了一位新郎需在短時間內做出選擇:新婚之夜,陌生旅人請求借宿,同意與否?其實新郎自己也知道,不論怎樣選擇,都會心有愧疚——讓進對不住新娘,讓走不放心老人。弗羅斯特就是描繪了這樣一個簡單又復雜的開門瞬間,但卻沒有寫出關門后陌生人究竟在門外還是門內,給足了讀者思考空間。江楓把原詩這種余音繞梁刻畫得酣暢淋漓,譯者將全詩最后一行的“The bridegroom wished he knew”劃分為兩小句,譯為“他希望,他能知道”,突出強調了新郎希望的內容,言外之意是他壓根不知道應該怎么辦,卻又不得不面對。從某種程度上說,譯文放大了原文的空白,讓讀者更加意猶未盡。
但上述只是表面留白,該詩還包括對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即選擇。正如《未選擇的路》中兩條林中小路,使讀者看到了人生之路;《愛與問題》中一個留不留的問題,同樣引發了讀者對人生其他抉擇的思考。誠然,所有選擇都是帶有遺憾的,世間本無所謂正確取舍,每個人都如同江楓筆下遠渡重洋的西方新郎,偶爾面臨選擇,難免踟躕不前;但生而為人必須做出決定,并勇敢面對未來,而這一潛在命題也由江譯本娓娓道來,簡單緩慢卻后勁十足。
研究發現,同一首英詩漢譯可選用諸多譯論從不同方面予以解釋分析;同理,同一篇譯作也可以選用各種譯論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但不論“套用”何種公式,其分析的對象無外乎原文、譯作、譯者、環境等固有因素,且目前國內譯論出現譯論新趨勢,即用跨學科概念附加“翻譯學”合成某一新概念,諸如地理翻譯學、知識翻譯學、體認翻譯學等等。倘若按此趨勢,是否會出現類似拓撲翻譯學、泛函翻譯學、張量翻譯學(均引自數學領域概念)等“為了譯論而譯論”的翻譯理論?方法論構建具有歷史必然性,學者必須跳出譯論發展死循環,高瞻遠矚,見譯唯譯。
結語
從早期見譯是譯的肯定階段,到如今見譯似譯的否定階段,至未來見譯唯譯的否定之否定階段(尚未完全成型),譯路發展一路磕磕絆絆卻螺旋上升。翻譯固然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但也同樣符合一般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形而下”的具體方法闡釋只是“器”層面的分析,“形而上”的方法論探究才是“道”水平的建樹。正如無招勝有招的登峰造極,恰似無劍勝有劍的爐火純青,通過追溯歷史、整合譯論、融通譯例,提出方法論層面的構建——翻譯“達合”方法論。目前翻譯“達合”方法論略呈雜糅之態,且哲學理論根基相對薄弱,還需很長一段時間完善發展。“達合”二字雖需商榷,方法論層面的構建卻勢在必行。未來可以從三個維度就方法論構建深入探究,也可以進一步深化對翻譯“達合”方法論本質的認識,進而促成譯論的跨越式發展。
注釋:
本文第二部分受啟發于黃忠廉教授在重慶翻譯學會第二十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上做出的《觀翻譯與翻譯觀》主旨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