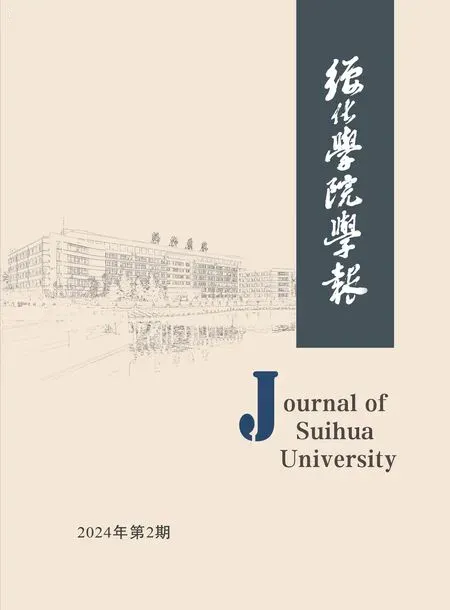邊緣突破與思想實驗
——中國新科幻小說的亞文化研究
王佳偉 夏 雨
(伊犁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新疆伊寧 835000)
作為一種“與主文化相對立的局部文化現象”,科幻文學始終處于“非普適、非大眾”的文學史邊緣地位。盡管科幻文學在各時期都存在著試圖突圍主流話語、反思科學價值和局限的嘗試,進而“將科學與富國強兵分離開來,將科學發明者與道德完善者分離開來,科學頭上的神圣的光環消失了”[1],但這種“越軌”傾向,卻始終無法實現對歷史與政治話語的祛蔽。這種定性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重塑性嘗試,到20世紀90年代逐漸形成了新科幻作家群體對亞文化特質的自我身份認同。他們不再滿足依附于意識形態的搖旗吶喊和“烏托邦”憧憬,而追求作家與科學之獨立主體性的雙重回歸。他們主動展現了在時代“共名”的語境下,對主導文化霸權的邊緣突破和當代文學話語的理論實驗。
一、自由與逃離的“脫逸”意識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生代科幻作家群體較之于前輩,一是獲得了更加寬松的文學環境與政策支持,二是或身為科學領域的從業人員、或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與文化視野,使科幻文學擁有了高屋建瓴、殫見洽聞的底蘊。這也催生了他們針對“舊”科幻文學和當代主流話語的低沉與無力,試圖建構以“科學”為根本、“未來”為理想,重塑后工業社會下“啟蒙新學”的嘗試。重新自我反思、定位后的科幻文學,正在逐漸實現文學邊緣地位的突破,進一步承擔起為文學發展提供新的價值思考、反映時代精神向度的重任。
以科幻文學為文本中介,新生代科幻作家展現了自身的青年亞文化審美趨向,即自我與“他者”的文學審美差異和創作思想的不拘一格。就前者而言,針對文學在后工業現代化時代所面臨的諸多困難,科幻作家擁有了較之主流更為堅實、寬廣的視野和想象。他們有的以科幻想象和異化“空間”建構了既偏離現實的“惡托邦”場域,又與現實呼應的社會文化圖景。如韓松的《地鐵》,以一位遠離時代發展中心、“被暗夜牢牢擒住的老人,什么都會被當做夢囈”[3](P27)的“落伍者”邊緣形象,去觀察體驗具有“幽暗”性、不斷前行的地鐵空間。“列車從地窖中鉆出了浮胖的、蛇頸龍似的頭,緊接著是腫脹得不成比例的身軀,大搖大擺、慢慢吞吞停下……站臺上的‘墓碑’們飄飄舞舞,像被吸塵器吸了進去”[3](P16)。小說隱喻著社會邊緣的“時代遺民”在飛速發展的后工業時代被排斥拋棄的絕望。老人與“白晝的同盟軍”存在著代際關系、價值觀念、社會地位等諸方面的明顯隔閡。他只是一個在空間與時間高速發展的洪流下被置換、被遺棄的“垃圾”,“正被搬運向一個秘密的焚化場所”[3](P78)。這種身份的不斷解構和建構,是如亨利·列斐伏爾所言的“空間”的權利和政治性體現,使人在某一限定空間內被動地完成了身份的劃分和價值的定義。有的作者則對個體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境遇表達出自己的思考,如何夕的《傷心者》、劉慈欣的《地火》。主人公都懷揣著在自己從事的領域做出新突破的夢想,可社會對功利價值的追求和研究基礎的不足,導致知識分子價值的遮蔽和話語的旁落,最終使這類人的努力化為失意的人生。《三體》《流浪地球》等作品則借人類文明的末日想象,通過宇宙宏觀視野的超脫性,去反思后工業現代化社會將要面臨的科技、倫理、生態等一系列危機。最終以“留白”式話語將希望寄托于遙遠而微末的未來,體現出“科幻”主題對未來的期待與不安。總的來說,不同于主流文學通過身體敘事、欲望發泄等后現代寫作去戳破美好的“烏托邦”,以刺痛讀者的感官體驗和情感機制,這一批新科幻作家以全新的科幻審美視角、更加宏大的總體性敘述視野,強化了讀者的閱讀體驗和審美接受能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還未對這些社會異化問題給出自己的答案,對主流話語的突破實驗雖逐漸走向成熟,卻仍缺少最后的方案。質言之,啟蒙承續的方式得以更新,卻仍在繼續。
就后者而言,他們認為科幻文學是“一種消遣,是一種個人化的自我超越。科幻小說是為自己寫的,是為科幻文學本身寫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種看法,都可能是創造力的桎梏”[3]。他們追求的是文學創作主體性的自由。繼而可以發現,新科幻小說作為一種新啟的文學類型,其作家群體雖均圍繞在“科幻”母題之下,卻擁有不同的文體風格和價值意識。他們不滿足僅僅要求打破主流話語的規訓,還希冀自我的張揚和野蠻的生長。90年代以來的科幻文學創作曾被學者宋明煒以“新浪潮”命名,但顯然科幻作家創作的異質性并不適宜以某種指代性概念進行統攝,劉慈欣和《三體》也無法成為全體作家作品的審美路標。劉慈欣的文學思想是復雜的,是“對于文類成規的重構與創新”。他一方面曾多次聲稱自己是一個“技術至上”者,飽含“技術樂觀主義”的價值傾向;主張科幻對未來的超脫想象,避免現實干預的成規。但另一方面,其作品亦顯示了對古典人文主義傳統的回歸,繼承了傳統文學的宏大敘事和人性考量,呼吁“科幻文學是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最后一個棲身之地,就讓它們在這里多呆一會兒吧”[4]。相較之下,韓松的文學思想更具有英美“新浪潮”的反叛性與先鋒性。在他的作品中,“科幻正在侵入現實”,不斷呈現的是對科技發展導致人與社會剝離、隔閡的反思。科技異化帶來身份意義的缺失、社會發展造成生存的焦慮,這些都反映了作者對科技與人性關系的“絕望”思考。王晉康則側重于對科技與人的倫理關系和“人”的價值存在進行探索,情感較為溫和而富于哲學意義。在《亞當回歸》《生命之歌》《豹》等作品中,“賽博格”能否與“自然人”共存的想象性表述,二者在身份秩序、倫理道德、精神意識等維度所面臨的沖突危機,是王晉康展望“后人類”想象的核心主題。此外,諸如何夕作品里物理、愛情、現實、宗教等題材的雜糅,郝景芳對社會矛盾的反思,陳楸帆對技術發展和社會退化這一悖論的批判等,都可以看出新生代科幻作家寫作的主體自由和風格異質的特點。
“脫逸”的亞文化特質還體現在科幻文化圈的形成,典型代表如國內首個科幻博士姜振宇組織的的“靠譜科幻研究”群。這種文化現象被學者認為“對于大眾讀者、主流文學評論家等圈外人的進入造成了一定的阻礙,使科幻小說創作難以突破‘小眾化’狀態”[5]。困境固然存在,但從另一角度看未嘗不是科幻愛好者們的被迫選擇。劉慈欣曾無奈而諷刺地表示,“我們并沒有創造出屬于自己的表現手法,新浪潮運動不過是把主流文學的表現工具拿過來為已所用,后來又發現不合適,整個運動被科幻理論研究者稱為‘將科幻的價值和地位讓位于主流文學的努力’”[4]。“反觀國內科幻的評論者們,卻正在虔誠地拾起人家扔掉的破爛枷鎖,莊嚴地套到自己身上,把上面的螺栓擰到最緊,然后對那些稍越雷池一步的科幻小說大加討伐,儼然成了文學尊嚴的維護者”[4]。主流批判語境的持續惡化、價值觀的干預和始終存在著的偏頗與矛盾,迫使他們形成完整的“創作—出版—研究”的內部消化體系,從而拒絕強勢的話語霸權對科幻創作并不“靠譜”的管束和指點。
二、獨立的文學面孔與現代性品格
科幻文學在20 世紀90 年代形成了對科學技術的再審視,它打破了以往盲目樂觀的“科學萬能主義”和“在地上爬行”的科學觀,并以科學為基底,建構了不同于當代主流文學的審美視角。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對“科學”的現代性理解曾呈現出一種“萬能主義”的價值盲從。社會、經濟、人文等諸層面的發展被冠以“科學觀”的口號予以指導,“為蕓蕓眾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學乎,其唯科學科乎!”[6]“科學”內在的求索與辯證精神被絕對化為一種形而上的“宗教式”信仰,從而“形成了一種類似漣漪效應的思想氣氛,會對那個時代多數個人的價值觀念和言說方式造成一種或明或暗的影響”。盡管在當時已產生了對這種價值崇拜的反對聲音,卻“以潛流或者說‘執拗的低音’的方式呈現”[7]。這最終導致“科學”的革命熱潮消退后,人們發現這種“魔法”成為了空洞虛假的“戲法”。受鼓舞的人民“發現想象中的和平、民主、自由、繁榮等等并沒有自然而然地到來,失望之余連幻想也不要了,于是科幻小說迅速沒落了”[8]。另一方面,由于科學被賦予介入現實發展和思想引導的功能,導致了追求線性發展的歷史觀、基于反映社會現實的唯物論、營造“真善美”的人性和社會“烏托邦”等話語霸權的生成。這使得科幻文學所特有的“未來式”幻想被消解,而落入“在地性”的窠臼之中,失去了科幻所追求的超脫性和空靈性。正如劉慈欣所言:“想看對現實的描寫干嘛要看科幻……科幻是一種能飛進來的文學,我們偏偏喜歡讓它在地上爬行”[4]。隨著社會發展和科學思想的逐漸成熟,新生代科幻作家秉持著一種新的探究姿態去介入科學的內在機理,將其知識理念、社會認同乃至焦慮想象都包容進了科幻文學的表述范疇之內。在此之下,科幻文學獨立的文學面孔和現代品格才得以確立。
(一)新科幻小說確認了以“科學”為中心的闡釋話語,“科學家”成為文本青睞的主人公形象。這種與主流文學存在巨大差異的變化,主要源自作家主體面臨知識分子話語旁落的困境,進而呼吁身份認同的沖動。與傳統作家相比,部分新生代科幻作家作為現實的科學事業工作者,他們更善于憑借踏實的科學素養和獨特的科學視野,去剖析當代工業社會的癥結所在。他們將自己的現實身份內化進文本中,承擔起人物與主題的敘述中心,從而建構“合法”的文學話語。此類文本在科幻小說中屢見不鮮,如《鄉村教師》的李老師,《地火》的劉欣,《臨界》的文少博等。這種文學話語不同于底層人物身體、情感的發泄和命運的共情,因為后者的文學意識在經過時間的沉淀和考量后,其“先鋒性”已然被收編、祛魅。對個體生命的表達在將其苦難、欲望書寫到極致后,已然是無根之萍。“遠離講故事形態的‘嚴肅’小說運動所留下的空白已經被帶著超越了敘事刺激的虛榮感的‘大眾化’的形式所填補。這些形式十分空虛,它們對文學的處理形成了另一個缺口——只滿足讀者的敘事需要而不滿足讀者的智力需要”[9]。因此,反思造成“啟蒙終結”這一人文危機的時代因素、知識分子的社會認同和命運關照等成為了科幻文學的價值追求之一。它“能夠滿足我們的認知要求,還能滿足我們的精神需要”。晚清至五四的人文危機,背景是民族危亡的戰爭國難;新中國以后批判話語的旁落,源于價值觀的要求和“烏托邦”的過度強調;到了當代,科幻文學考量人文危機和社會發展的根源落實到了科學。這種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剖析,是科幻文學建構現代性品格的一個體現。
(二)作家的現實觀察和生活體驗引發了對科學的焦慮想象,確立了文學邊緣群體反“烏托邦”的價值追求。新科幻小說對“科學”的把握并非是一元的,以“科學”為基底并不是將其奉為新神。相反,新科幻小說更多呈現出的是對科技發展帶來的異化問題和文明沖突危機的反思。這就與以往主流話語規訓下的科幻文學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傳統科幻文學亦是以“科學”為價值基底,但其暢想的是基于破碎現實之上的未來世界,它急于尋求“烏托邦”來肯定現實的努力和希望。因此,“科學”是立足當下,憧憬未來。它成為了一種社會理想和價值追求,更多起到的是鼓舞和慰藉作用。而到20世紀90年代,目睹了現實異象的新生代科幻作家秉持著知識分子的憂慮本能和批判眼光,形成了對科學理想與現實的考量。技術發展帶來的種種社會矛盾和倫理問題,使科學率先主動打破了被遮蔽的面紗,宣布了“烏托邦”的破滅。其后,一系列由此呈現的形而上思考和未來描寫,如虛擬與真實的不可把握、“人”的靈與肉的異化、末日危機和宇宙戰爭等等,都是作家學者們基于現實存在而產生的質詢和想象。它不是空虛的幻想,也并非局限于傳統現實場域的囹圄。相反,這種“跳脫”的背后是立足未來,觀照當下。如郝景芳的《北京折疊》,三層空間共享48小時的生活世界,但作者并沒有投入筆墨去交代如“魔方”般折疊的高樓、翻轉的地表等場面生成的科幻原理。換言之,作為一部科幻作品,其“科學”幻想并不是小說的闡釋中心。它只作為文本先在的未來背景,以推動情節的敘述。這也是學界對其“科幻性”表示質疑的主要原因。但小說的重點不單是以科幻想象表達對階層、分配的批判,更是以復雜的思考呈現出對上流精英和底層平民關系的探索。這也是作者在經歷了相似的現實工作后,面對這一現狀產生的思考與質詢。在科技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社會,上層決策者并沒有采取機器流水線等形式去治理垃圾問題,而是為了底層人能有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采取了更費力、效果更差的人力模式。基于此,底層人的反抗也就無從談起。因為所謂的剝削敵人并不存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賦予他們生存機會的有恩之人,最可悲的是他們對社會的價值也是決策者所賦予的。相比于主流文學所鐘意的二元對立,《北京折疊》則更多表現為底層人物社會價值虛無的殘酷。在這里,郝景芳強調了對社會矛盾的反思,以及科技發展與底層平民關系的解構式質詢。科技發展是否能造福整個社會、階層差異帶來的是否只有對立與仇恨、底層人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如何實現,這些都是作者在科幻背景下做出的深刻剖析。質言之,新科幻小說是通過想象未來的姿態來確證自身特點,通過對現實的反思和重構來實現其終極追求。
(三)文學觀念的更新,體現為對支配性話語的反駁。90年代以來的科幻文學打破了早期“科普性”和“工具性”的陳舊枷鎖。拒絕承載政治任務和宣傳功能的公共話語,使得科幻文學不再從屬于主流文學的統籌之下,避免了淪為思想教育和價值傳輸的工具。因此,寫作者的“導師”身份被直接解構,知識分子指引群眾的“啟蒙—被啟蒙”關系得以消弭,轉而以一種平等的姿態去分享、交流。文學高高在上的指導和灌輸作用不復存在,轉而形成的是期待讀者通過文本實現自覺無意識的自我啟蒙。這種“外部權威”的自我解構是科幻文學所做的反抗努力,為科幻文學現代品格的建構打破了牢籠。
三、“對話性”和“延伸預測”的思想實驗
作為一種“具有生動的藝術感染力的審美形式”,文學形象在新科幻小說中已具有了獨特的審美內涵。其塑造的族群形象、自然形象、科學形象,超越了主流文學所強調的自我與他者的“獨白”形式,表現為一種對話溝通的“復調”性。在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中,一方面是自我和他者存在主客體之間的對立關系。雙方通過“凝視”,把對方當成意識對象,甚至把別人虛化為一個存在物,即薩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獄”。每個人都會為了實現自我主體的獨立性,而試圖去收編他者,從而把他者變成客體,自己成為支配者。支配性話語所追求的,就是如巴赫金所言“致命的理論化”的獨白思維,一種強調統攝性的普遍意識和普遍價值。另一方面即新科幻小說所追求的“對話性”。人物形象的臉譜化是科幻文學常被主流話語批判的原因之一,但若從文學形象這一維度出發,可以看出這是作家有意采取的顛覆性手法。具言之,簡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我”的個體主體性被淡化,這是服膺于凸顯族群視域的需要。基于此,文學視野得以完成超越,個人的情感機制、社會地位、文化心理等因素被置換成人類視域下的文明未來、生存危機和種族沖突等宏觀想象。正是這種“宇宙詩學”下的族群視域,才使得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與自然、科學展開對話成為了可能。在陳楸帆的《荒潮》中,科技發展推動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展開了全球性的資源掠奪和生態殖民,由此導致的電子垃圾傾瀉使自然生態面臨如馬克思所言的“新陳代謝的斷裂”。社會勞動分工以及“鈴木變種”計劃使得人類社會處于階級分裂和自我價值異化的危機當中,個體主體性的喪失和“身份”的模糊使人類文明退化到“叢林法則”的原始競爭當中。在《命運》《人與吞噬者》等作品中,作為地球主人的人類成為了被任意宰割的“小蟲蟲”。《微紀元》《超行星紀元》中,人類在太陽聚變和恒星爆發面前所做的一切自救都顯得如此力不從心,只能無奈地接受被自然支配的命運。《贍養人類》里造成“終產者”把控地球全部生態資源、智能科技和社會秩序的原因,是“社會機器”的執法保護和科技發展帶來的人力資源的被剝奪。諸如此類的文本表述將“科技”、“自然”的形象視為“自我”,人類反而成為了一種被支配、收編的“他者”形象,體現了“去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傾向。作家通過權力話語的轉換闡釋了人類與“他者”發展的悖論關系,意在表達人類與自然、科學應處于一種平等和對話的位置。若人類始終秉持著收編“他者”的心態,自然與科學將反過來統攝人類的命運,并催生人類內部的權力霸權,形成反噬效果。只有在這種對話中,任何一方的“自我”與“他者”形象才能不再是支配與從屬的關系,神圣話語也將在這種溝通交流中被祛魅、消解。
主流支配性話語多善于建構一種終極目的,這種目的是當下社會所缺失而又具有可預知性的,被賦予了實現發展進步的超越性價值,遵循著歷史唯物觀的發展趨向。而科幻文學則與此相反,它所追求的是一種“認知解離”,“是一種想象的框架或一個在作者的現實經驗環境之外同時并存的擬換性可能世界”[10]。它將當下社會未被確證的某種概念或現象,投放到虛構的未來世界里,進行演繹與類推的思想實驗,使之成為某種業已形成的文學圖景。由此,歷史到未來的既定發展秩序被割裂,歷史進程的向度被外延類推,從而形成了“延伸預測”的科幻史觀。新科幻小說中時常出現的宇宙飛行、時空穿越、腦域鏈接,以及“真空衰變”“微連續理論”“宇宙坍縮”等理論,種種現階段無法解釋的問題并沒有在文本中得到詳細的解答,科幻作家的作用也不在于闡釋此等現象的原理。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在自己營造的虛擬世界中,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向度,隱喻現實社會的危機。《三體》中,故事從經歷“文革”苦難的葉文潔向太空發射廣播展開。自此,歷史發展的向度從現實走向了未來式的“科幻”想象。《人人都愛查爾斯》向我們展現了人類駕駛以核聚變為推動力的航天飛船競賽,一種與現實相似卻又割裂的未來世界。《六道眾生》更是打破了歷史唯物觀的時空概念,創造出了并存于一個地球的六層空間異域。新科幻小說的這種想象,使循序漸進的歷史進程被終止,科技發展的“終極目的”只作為科幻文本中的闡釋背景和工具性而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文本的思想實驗,作家借科技發展作為推動文本敘述的動力,將人類文明的歷程向外延伸,去類推社會的未來前景,從而呈現出文明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可能性想象。由此,新科幻小說或出現時間的跨越,或出現空間的跳轉,或呈現人類文明消亡后的“新生命”世界。這種史觀的“延伸預測”,最終為新科幻小說建構起了開放、多遠的想象空間和文學話語。進而使其跳出傳統文學場域反映現實的單一維度,而展現出新的文學批判視域和審美維度。
綜上所述,中國新科幻小說從“脫逸意識”“現代品格”“思想實驗”三個維度,展現出了與傳統主流文學相悖的亞文化特征,顯示出對支配性話語的突圍和重構。這種具有亞文化特質的邊緣突破,使得科幻文學在當代確立了作家與科學主體性的雙重回歸,建構起了獨立的文學批判話語和闡釋空間,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科幻文學實現與世界科幻文學的主題契合和思想呼應,強化了科幻文學想象未來,觀照現實的生命力。